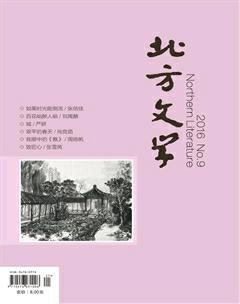淺析嚴歌苓作品的敘事模式
李潔
摘要:作為新一代的女性作家,嚴歌苓近些年來越來越受到讀者和學界人士的關注。她的小說以獨特的語言風格、細致的心理描寫而著稱。在敘事方面,“逃離-隱藏”模式是她創作中的常用的一種,尤其在《第九個寡婦》和《小姨多鶴》這兩部中篇小說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本文通過對這兩部小說的細讀和對此種敘事模式的分析,試圖揭示出“逃離-隱藏”敘事模式背后的深層意蘊,即表達了作者對非理性“集體”的不信任感,對人與人之間親情、對女性優秀品質和生命力的贊美。
關鍵詞:敘事模式;深層意蘊
旅居海外的作家嚴歌苓近年來連續創作了很多優秀小說,深受讀者和研究者的好評。同時,她的作品也吸引了很多導演的再創作,不斷地被改編成影視劇,她本人也參與編劇,比較著名的有《歸來》、《天浴》、《少女小漁》、《扶桑》、《金陵十三釵》、《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鐵梨花》、《梅蘭芳》、《幸福來敲門》等等。但是,一部分作品的改編效果并不理想,與原著相去甚遠,原因就是:她的小說不以情節取勝,而以對內心細致的描寫、獨特的語言風格彰顯其因獨特性。因此,想要繞過文學語言的魅力而用畫面來代替,于她的小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通過文本細讀,我發現,在她的小說中總貫穿這樣一個模式,即“逃離-隱藏”。其中《第九個寡婦》和《小姨多鶴》兩部長篇小說中尤其明顯,可以說是這種模式的貫徹。作者在整體的故事敘述中將模式貫穿在敘事策略的構成、敘事事件的設置以及敘事時間的安排上。
一
《第九個寡婦》講述的是一個名叫王葡萄的女人將自己的公公藏匿近三十年的故事。公公孫懷清被定為“地主惡霸”而遭到鎮壓,王葡萄則將幸免一死的公公藏到紅薯窖里,一藏就是二十多年,這期間不管外面風云變化,她始終和公公相濡以沫,渡過很多難關。王葡萄的天真率直、潑辣仁愛和孫懷清的睿智仁慈的形象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躍然紙上,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小姨多鶴》的開篇則較為血腥。日本戰敗后,不愿集體自殺的日本女孩多鶴被賣到了一戶普通的中國人——張站長家里。從那兒開始,她成為張二孩的“地下”妻子,承擔起了為之傳宗接代的任務。
兩部小說雖然情節大不相同,但都是圍繞著“逃離-隱藏”來組織時間和展開故事情節的。《第九個寡婦》中被定為地主惡霸的孫懷清藏身在紅薯窖二十多年卻以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睿智的頭腦幫助、指導王葡萄度過了一個個難關。王葡萄應付著外面生活的風風雨雨,以自己的潑辣、率直和敢愛敢恨的性格抵擋著各種各樣的打擊和厄難,生活過得反而比那些“政治性強覺悟高”的人好。《小姨多鶴》中的日本少女多鶴在給“二孩”張儉生了三個孩子后,就以孩子“小姨”的身份被安置在家里。為了不讓外人懷疑這種畸形的家庭構成,她也放棄了作為親生母親可以光明正大地享有的一切。所以說,多鶴也是在隱藏身份的陰影里生活著。嚴歌苓在兩部小說中用同一種敘事模式,顯示了她對這種模式的熱衷和偏愛。除去這種模式本身帶給讀者強烈的閱讀期待之外,作者通過模式傳達出來的深一層的意蘊更值得我們探討。
二
首先,作者通過“逃離-隱藏”敘事模式表達了對一個非理性“集體”的不信任,更表達了對人與人之間親情的禮贊。《第九個寡婦》中,當解放軍土改工作組批判孫懷清時,他們沒有認真分析孫懷清的實際情況,只是憑借著占有財富的多寡來劃分成分。這種標準無疑是粗放的,其后果就是導致了一些無產流氓者趁機混入人民隊伍中來,并且制造一些與事實不符的輿論,誤導決策者的決策。從這層意義上說,這樣的集體本身是不成熟的,缺乏理性的。組成這樣的“集體”的無非是一些庸眾,他們聚在一起,卻對于群集的目的不甚了了,只是在某種號召之下應和的傳聲筒而已。所以在批判孫懷清時,由于他們缺乏具體的罪名和證據,一時間會場鴉雀無聲,就連平日里對孫懷清多有不滿的史修陽也借故離開,批判會一時陷入僵局。這時——
喇叭筒里的口號像是生了很大的氣,喊著“消滅封建剝削!打倒地主富農!”
喊著喊著,下頭跟著喊的人也生起氣來。他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只是一股怒氣在心里越拱越高。他們被周圍人的理直氣壯給震了,也都越來越理直氣壯。剝削、壓迫、封建不再是外地來的新字眼,它們開始有意義。幾十聲口號喊過,他們已經怒發沖冠,正氣凜然。原來這就是血海深仇。原來他們是有仇可報,有冤可伸。他們祖祖輩輩太悲苦了,都得從一聲比一聲高亢,一聲比一聲嘶啞的口號喊出去。喊著喊著,他們的冤仇有了具體落實,就是對立在他們面前的孫懷清。[1]
在這里,口號具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通過同義反復的形式使內容得到了強化,并且可以讓人放棄自己的立場,屈服于口號所指的內容,“也許呼口號的人本來也不相信口號中的一切,但是經過反復地呼喊,一百遍、一千遍地呼喊,口號漸漸地深入到他的內心,他感到這呼喊是發自他的內心的,而不是來自外界的,口號的觀點就是他自己的觀點……口號用它強大的聲音形式將聽眾俘獲。”[2]
所以,這樣非理性的“集體”利用口號及輿論羅織罪名就非常方便了。就連孫懷清的親兒子孫少勇面對葡萄的詰問也啞口無言:為什么他是反革命,因為大伙兒都說!這種非理性“集體”以進步為名把“孫少勇們”規訓成工具,人被異化,喪失了應有的人性和美德(比如,孫少勇就是為了顯示更加革命而主動表態槍決自己的父親)。所以,對于想保持個體人性和人情的王葡萄來說,逃離這樣的集體是她必然的選擇。其實,多鶴的逃難也是這層意義上的逃離。代浪村的人們不愿接受村長替他們做的集體自殺的決定,而走上了逃難之路。不愿反抗而使全村人被屠戮凈盡的崎戶村人卻付出了殘酷的代價,那血腥的場面成了多鶴永久的夢魘。
其次,嚴歌苓“逃離-隱藏”的敘事模式顯示了她對于人間真情和女性優秀品質的珍視和贊美。王葡萄冒著生命危險把公公藏了二十多年,只是因為她覺得公公不是壞人,對她很好,把她當成親閨女看待。她對于孫懷清的感情就是這樣簡單的人間親情,沒有任何的雜質。為了保護公公,她甘愿拒絕孫少勇,甘愿把兒子送人。在嚴歌苓筆下,王葡萄是一個任情而為、率性倔強的人,她認定孫懷清不是壞人,就為她甘冒生命危險。在那樣狂熱的年代里,她的這種看似自私的“親情觀念”恰好顯示了那個時代的一些非理性和非人道的事實,相比之下彰顯了人情的可貴。
在《小姨多鶴》中,嚴歌苓又以日本少女多鶴的“逃離-隱藏”再次申明了自己的立場。在多鶴的旁邊,有個心直口快、湊合遷就的“姐姐”朱小環——張儉的原配妻子。朱小環的爽直潑辣,對保護多鶴身份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不拘小節,大大咧咧,對人熱情大度,對事湊合遷就,只要能把日子過下去,就絕不會放棄。這種性格的彈性和對生活態度影響和感染了來自崇尚自殺民族的多鶴。
在遇到困難時,多鶴多次想以自殺的方式了結痛苦,第一次是被張儉丟棄到野外,費盡千辛萬苦回到家里,想到了自殺;第二次是和張儉熱戀之后受到阻礙而被冷落,又一次想到自殺。在這兩次的預謀自殺的過程中,出現在多鶴腦中的總是幼時看到的那個崎戶村人自殺后留下的巨大血球,血球在她腦海中滾動,推動著她下一步行動。嚴歌苓在這里運用了重復預敘的手法,“在‘重復預敘中,當第一次表現某一個即將在以后的時間內反復發生的事件時,便對此后該事件的重復加以預告,讀者被告知,這幕景象在未來將會重復出現,重復預敘的描寫越詳盡,它的可信程度就越低”[3]而事實正是如此,多鶴的每一次預謀自殺,都被朱小環那種對生活的熱情消解,變成一種對“活著”的執著,湊合活著吧!
可以說,在“逃離-隱藏”過程中,多鶴不僅得到了身體的拯救,而且得到了靈魂的拯救,這種雙層拯救使其從易于棄世轉變成熱愛生活并且生命力頑強,而這正如王葡萄所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一樣,是作者所珍視和贊美的。
參考文獻:
[1]嚴歌苓.第九個寡婦[M].作家出版社,2010.
[2]葛紅兵.人為與人言[M].上海三聯書店,2003,8:11-13.
[3]羅鋼.敘事學導論[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