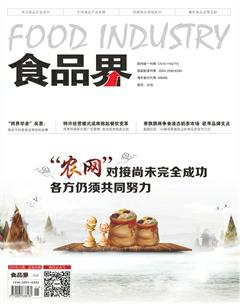“跨界學者”吳思:我在乎的是食品背后的故事
思是當代著名作家、歷史學者。2008年,他著的《潛規則》入選“30年30本書”。2010年,他的《血酬定律》入選新世紀10年10本書。從“潛規則”到“元規則”,從“血酬定律”到“官家主義”,他創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新詞匯,并用此描述那些未曾被正式命名的歷史景觀、政治弈局,開創了嶄新的中國歷史的通讀方式。吳思曾任《農民日報》社總編室副主任、群工部主任、機動組記者;《橋》雜志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炎黃春秋》雜志社總編輯,常務社長。現為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與文字打交道,我與父親在這點上是一致的
“我也說不清,自己究竟算哪里人,我是1957年5月生于北京。”吳思說,太爺出生在山東,父親出生在黑龍江,但和父親有一點是一致的,我們都是與文字打交道。
吳思的父親是一家部隊雜志的編輯,母親是大學老師。吳思說:“我小學上了好幾個,一年級時,去了離母親教書的地方最近的左家莊第二小學。“文革”開始了,母親被批斗,只得轉到父親所在的部隊大院附近的九間房小學就讀。很快,父母都去了“五七干校”,不得不跟著去“五七干校”所在的河北省文安縣小務村小學讀書,沒多久,又轉到五七干校小學。因為快上初中了,就回到了九間房小學。小學畢業后,去了北京石油附中,在那里念到高中畢業。然后下鄉插隊。
在國家恢復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的高考中,吳思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1982年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了《中國農民報》社。
吳思說,《中國農民報》在1985年改成了《農民日報》。我在《農民日報》工作了十年,于1992年離開去的《橋》雜志,在那里任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在《橋》雜志工作期間,感覺就是沒錢,印刷刊物都沒錢。這時,香港《明報》進入大陸,走的是市場化道路,于是《橋》雜志與其合作,但做了三期就停刊了。明報集團那邊就叫我們編書,把香港的書編成大陸版,干了一年多,我就失業了,這是1994年。
失業后,吳思就在家看書、寫作、炒股。1996年底,吳思正在寫《潛規則》一書,他的一個老領導、原在《農民日報》經濟部當主任,后來在《中國食品報》社當社長。他退休后,和他的老領導一起合辦了《炎黃春秋》雜志,讓吳思過去。吳思最初并沒有答應,只說過去看看,結果到了門口,幾個老領導站在門口握手歡迎他。從1997年初,一直干到2014年底,吳思才從《炎黃春秋》雜志社辭職。辭職以后,他一邊寫東西,一邊在中山大學當訪問學者。在今年年初,任職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吳思說,在大學,自己絕對不是考試天才,因為我身邊有一學期不上課三兩天突擊拿下高分的“高人”,而自己往往復習一個星期考個中等偏上成績。“很多人說我聰明,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傻,要不然也不會一天到晚認準了一個事情就較勁這么多年。”
炒股賺錢,直接引發對經濟學的興趣
吳思學的是中文,但在他的興趣中,經濟學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問及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對經濟學產生興趣時,吳思表示,因為首次炒股賺了錢。
吳思說,當年考大學,自己算是文學青年,而文學青年幾乎都會選擇中文系,這是時代潮流。而我對于經濟學的喜歡,是有一個過程的。那是在我上大二和大三時,經濟學開始熱起來了,那時的口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時我就明確意識到,未來最火的那個集團應該是學經濟學的,但我不想干那個,像賬房先生一樣解決的是賺錢多少的問題,那不是我關心的問題。后來,我當《農民日報》的記者,經常涉及到經濟方面的問題,被迫關心一點,但也興趣不大。后來,在1992年,我寫《陳永貴沉浮中南海》,要大量涉及農業經濟方面的知識,對經濟學才略微有了點興趣,因為要理解當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非得算很多經濟賬不可。但我直接對經濟學產生興趣是在1996年。那一年,我讓一個親戚誘惑著買了點股票,很快就掙了一筆錢,那時我就想,這股票是怎么選的,怎么就賺錢了?由于好奇,看了很多金融、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方面的書,覺得這事挺有意思,不知不覺就看了摞起來有兩尺高的經濟學書籍。
正好從那時起,我準備從潛規則的角度研究歷史。帶著經濟學的眼光進入歷史,覺得很多事越來越明白了。微觀經濟學就是讓人們計算成本收益,把賬算得很細。同樣用這個方式看歷史,也會算得很細。這就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對經濟學越來越感興趣,但我的經濟學水平不高,始終停留在邊際成本、邊際收益,外加一些曲線的入門水平。我覺得夠用了,也沒必要再深入鉆研。
我的世界觀核心也是政治
細心的讀者,在閱讀吳思的著作時,會發現一個特點:他寫《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游戲》、《我想重新解釋歷史》等,看似寫的是歷史,但都有濃濃的政治傾向。對于這個問題,吳思解釋道,中國是一個政治主導的社會。他說,如果說市場受誰的主導,那肯定是政治。如果關心的是社會是怎么運行的,關心的是這個社會往哪里去,這個社會最核心的利益是怎么分配的,這些事都涉及到政治問題。如果寫托爾斯泰那樣的小說,也會涉及政治。迄今為止,中國最核心的主導就是政治。市場的地位,近些年來有所提高,但仍然要服從于政治,我的世界觀核心自然也是政治。
吳思說,讀中學時,我的理論興趣挺濃,并有著嚴重的教條主義。初三啃讀政治經濟學,高中啃哲學,假期悶在家里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那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和書中的保爾·柯察金成了我的榜樣。
“看托爾斯泰的作品,他對列文、安德烈的描述,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理解他們的同時,也更深地理解了自己。”吳思說,在托爾斯泰的傳記中有一句話“與人們生活彼此分不開”讓他觸動很深。
但是,吳思對各種理論一直感到不滿。他想找到一種新的世界觀,其中經濟學是一部分,還有政治學,也包括心理學、社會學。最后發現,這些學科并不能解釋他的經歷,解釋他所了解的社會。然后,就需要有個新的創造。
他說,我的兩個創造一個是《潛規則》,一個是《血酬定律》。我覺得《血酬定律》是更重要的創造。在西方經濟學里面,會談各種生產要素:資本這個要素投入了,帶來的回報是利息;勞動要素投入了,回報就是工資;土地或其他自然資源要素投入了,回報就是地租。每一個要素投入,都會帶來相應的那份回報。然后,這個經濟運行會形成均衡,這就是經濟學觀點。在運用到政治方面時,就會說政府提供的服務是公共服務,民眾支付的價格就是稅收,于是就可以把市場這個要素擴展到政府領域。如果把暴力要素引入社會均衡的計算,引進政治經濟計算,這就是血酬定律。把這個核心要素引入西方各種政治經濟學,就會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
在《潛規則》中,吳思以記者的敏銳和寫作技巧,把這部以二十多個有著共同點的不同朝代的歷史故事,通過亦雅亦俗、亦莊亦諧的方式,解讀了隱藏在正式規則下、但卻支配著社會運行的不成文的規矩的歷史現象。
安全問題是大眾普遍關注的問題
與吳思交談的過程中,我們也談到了食品安全的問題。作為新聞界翹楚,媒體人應該如何關注食品安全問題呢?吳思表示,食品安全問題是大眾普遍關注的問題,而且抓住這個問題就能出新聞,因為這個領域很神秘,大家都關心,但又不知道。因此,新聞就一定會層出不窮。你走多深,都會有故事。而且我覺得,你一定會遇到政治。遇到一個掌握權力的政治集團,他們的態度、他們的決策,對食品安全有著重大影響。而他們的決策、他們的想法,又包含著眾多的計算。
比如,食品作假,它的成本收益發生變化就是政治。在市場領域,一個有毒的食品,或者造假的食品,本來是市場行為。我掏錢買了東西,對方賣的是假貨,是有毒的東西,對方出現了欺詐,這個不是標準的一買一賣。進入這個領域,維護這個市場秩序的就是政治。以此類推,一個好的規則是什么?這個規則怎樣實施?維護這個規則相應的費用是多少?如果有這筆費用,為什么沒有撥到這里來?分配這費用是誰來決定的?等等。這個分配的程序或者價值是怎么排序的,這就是政治問題。
順著這個思路,不僅可以看到精彩的食品故事、經濟故事、企業故事,還能看到精彩的政治故事。吳思說,要是我做這方面的報道的話,我在乎的是食品背后的政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