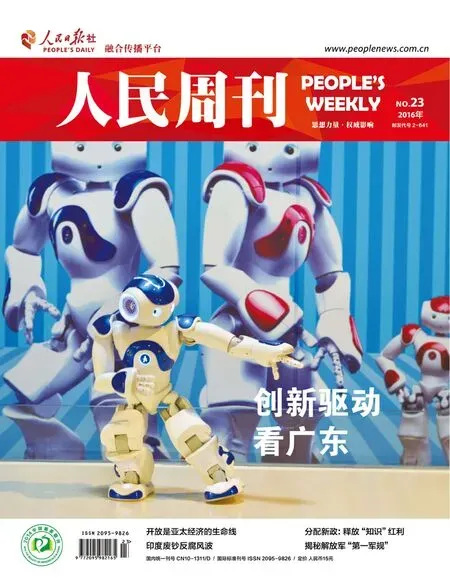《環球人物》2016年第28期刊文諜戰片成了個筐
韓松落
《環球人物》2016年第28期刊文諜戰片成了個筐
韓松落
武俠、奇情、冒險、偶像劇,原來類型劇里所擁有的元素,在新的類型劇里一點都不缺,一旦發現了這點,觀眾就和電視劇制作者達成了默契。不過在筆者看來,莫不如武俠的歸武俠,諜戰的歸諜戰。

在近10年的電視屏幕上,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諜戰片。
這種來勢洶洶,曾讓影視業人士擔心它的熱度會被透支,但《胭脂》《麻雀》的出現,卻又打消了這種疑慮,緊隨其后的,還有電影版的《新冰山上的來客》和《新保密局的槍聲》。在這種熱度影響下,一些原本和諜戰關系并不密切的題材,也在向著諜戰靠攏。
不過所有這些諜戰片,卻并不讓人感到陌生。持續了10年的諜戰片浪潮,到底是橫空出世前無古人,還是在復古基礎上的創新?
1949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了《無形的戰線》,講述東北解放后,公安機關與國民黨特務的斗爭,這是新中國的第一部反特電影。此后,它的故事模式一再被沿用,片尾打出毛主席語錄:“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這成為此后反特片的指導思想。
整個上世紀50年代,直至60年代初,各大電影廠爭相拍攝反特片(有時被稱作驚險片),形成反特片的第一次浪潮。“文革”過后,反特電影浪潮再度出現。反特片其實就是諜戰片的前身,兩次反特片浪潮,則為諜戰片在內容、模式、審美心理上做好了準備。
大的變革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反特片開始向諜戰片演變,最顯著的變化,是故事的時代背景被放在了1949年前,從《狼行拂曉》里的侵華初期中日遠東情報戰,一直到《北平合談》里解放前夕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到了新世紀,即使是《無悔追蹤》《誓言無聲》《數風流人物》這種把年代放在1949年之后的諜戰劇里,情節和人物性格也更加立體。在進一步豐富我方特工和情報人員性格的同時,開始為潛伏的特務賦予人性內容。雙方的正邪身份,被職業身份所替換。
2005年的《暗算》之后,諜戰片更是大量出現,但卻漸漸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去:特工們總是過分富有人性,反面人物愈加立體鮮明。直到《潛伏》和《懸崖》,甚至淡化了諜戰色彩,到了被當作職場教育片的地步,屢屢被拿來舉例解讀職場厚黑學。這種變化是發生在更為大眾的電視屏幕上,顯得更耐人尋味。
其實,諜戰片和抗日劇一樣,是用諜戰和抗日的框架,裝進去更豐富的內容。在政治正確之余,它們完全可以是經過改裝的宮斗、武俠、奇幻、職場,乃至青春偶像劇:奸妃換作特務頭子,武林邪惡勢力改成皇軍,武林秘籍變成志士名單,英雄成長歷程滿滿的都是青春熱血。
同理,如今風行的盜墓題材也是這個路數。盜墓小說要改編成電視劇,恐怕很難通過,但如果把盜墓改成尋寶,盜墓人改成為籌措抗日經費而臥底的尋寶小分隊,“粽子”改成日本鬼子,故事完全講得通,觀眾也一樣看得津津有味。
武俠、奇情、冒險、偶像劇,原來類型劇里所擁有的元素,在新的類型劇里一點都不缺,一旦發現了這點,觀眾就和電視劇制作者達成了默契。不過在筆者看來,莫不如武俠的歸武俠,諜戰的歸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