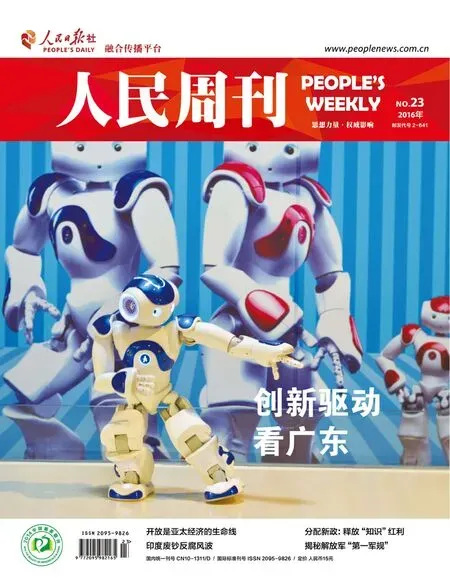你有手機依賴癥嗎
本刊記者 李海燕
你有手機依賴癥嗎
本刊記者李海燕
除了朋友,有趣的生活也可以幫助我們擺脫或預防對手機的過度依賴。

手機已然成為現(xiàn)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日本經濟新聞》網站的報道稱,中國人吃飯時單手玩手機,開會時藏在桌下玩手機,甚至過人行橫道和開車時也不放下手機,就連在辦公樓擠滿人的電梯里,也有人爭分奪秒地看手機。手機依賴癥已然成為了一個引起廣泛熱議的名詞。
手機依賴癥是病嗎
“舉頭望明月,低頭玩手機。” 一整天不讓你用手機會怎樣?在一項調查中,絕大多數(shù)人表示會不習慣,只是程度不同,有人表示“忍忍就過了”,而有人用“寧可一日無肉,不可一日無手機”來形容自己對手機的依賴。手機依賴癥,成為一個被大肆渲染的熱點話題。
那么手機依賴癥究竟是否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心理疾病呢?中山大學心理學系研究生導師穆巖稱,每一種心理疾病都要有專業(yè)機構來認定,比如美國心理學會每年都會出版疾病診斷手冊,需要嚴格按照臨床標準確定其是否有獨立的病癥及背后導致疾病的機制等,方能通過一種心理疾病的確認。手機依賴比較像通俗來講的網癮,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手機依賴癥就是一種心理疾病。“我們小時候有游戲機依賴,再后來電腦依賴,現(xiàn)在則更為方便,變成了手機依賴。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xiàn)象,這些隨著社會信息化發(fā)展趨勢而產生的現(xiàn)象不能簡單用好或者壞來貼標簽。”穆巖這樣表示。
“不過我們會把手機依賴稱之為一個不良的行為習慣,因為它客觀上確實會破壞我們正常生活的平衡。拿著手機的時候,時間會過得飛快,過分依賴手機會侵占我們本來可以進行深度思考閱讀的時間。”穆巖依然指出了手機依賴者所面臨的問題,如果經常拿著手機,那么本來就少的碎塊化時間就被手機操作更多地占用了。
手機何以成“癮”
手機為何能如此輕易地吸引使用者,甚至使之“上癮”呢?穆巖解釋道,我們會依賴手機,是因為手機承載了大量的社交功能,無論是正常工作需要還是私人生活需求,手機可以說是我們現(xiàn)代社交生活所有的入口,而正常人都有社交需求。手機社交的特征是即時化,一個有即時反饋的功能設置會對大腦產生更強烈的刺激,就像微信朋友圈,不僅有點贊功能,還能讓你看到能有多少個贊、誰在回復,這些交互設計是吸引人們的一個重要原因。
手機給我們提供的社交反饋是游戲化的、可視化的交互方式,所有的手機應用都是由研發(fā)工程師依據(jù)大量的用戶體驗精心設計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相比之下,實景的體驗則沒有經過專業(yè)設計,需要自己去掌握調整,實景環(huán)境中的運動、出行等活動反饋不一定都是積極的,有時甚至得不到反饋。而在手機上想要設計出很好的刺激性反饋效果,不僅易行,成本還很低。
也有人認為,國人對手機的熱愛,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業(yè)余生活比較貧乏。運動健身、旅行觀光、藝術體驗、讀書學習,這些“線下”活動的普及程度,跟許多國家和地區(qū)比,差距還很大。“成本差別太大,畢竟出門看電影、話劇,和在電腦上看視頻的成本是沒法比的。”穆巖贊同這種說法,“現(xiàn)在大部分的成年人,在成長過程中接受到的文化、運動方面的教育和熏陶比較有限。整個基礎教育中的關注點雖說不是只有考分和課業(yè),但是焦點依然是學業(yè)本身。相應的,對于藝術類、運動類只是作為副科,不作重點培養(yǎng),于是就導致現(xiàn)在有健身意識和懂正確方法的年輕人在比例上還很少。在學校里,缺乏有針對性的、科學系統(tǒng)的鍛煉指導,長大之后,就算知道健身是重要的,也不知道如何下手,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一種借口,只能算了吧。”
手機依賴傷身又傷“心”
說起手機過度依賴的危害,可謂傷身又傷“心”。專家介紹說,長時間玩手機,會造成眼疲勞,頸部、手臂肌肉疲勞,手指、手腕關節(jié)疼痛無力等,夜晚玩手機時間長,容易打亂人體生物鐘,影響新陳代謝、情緒、免疫力。不僅如此,手機依賴癥對心理的傷害也很大:患者忽略情感交流的重要性,使得親情、友情、愛情出現(xiàn)裂痕。比如有的父母在家只顧玩手機,忽略了陪伴孩子的意義,給孩子的成長留下陰影;社交能力變差,語言表達能力衰退;手機會讓人陷入一種持續(xù)的“多任務”狀態(tài),長此以往可能會讓人們患上類似“注意力障礙”的心理問題,削減思考的能力,讓思考難以深入;過度關注手機還會讓人隨時處于應激狀態(tài),身體、精神上無法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息。
手機依賴對于人們心理的影響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深遠。虛擬情景的設計理想化很多,很輕松就可以完成任務升級、賺金幣等獎勵,得到很多成就感,這種人為的、虛擬的刺激,比現(xiàn)實帶來的快感強烈得多。“但它始終是一個虛擬的環(huán)境,我們人類并沒有生活在虛擬的電子化社會中,人最根本的需求是跟他人、跟社會發(fā)生關聯(lián)。一個人要擁有健康的心態(tài)要得到自我價值的認可,然而沒有一個人的價值是宅在家里就可以被評估的。人的價值取決于你能夠為別人創(chuàng)造什么樣的價值、能夠幫到多少人,最終還是需要回到現(xiàn)實當中。”穆巖認為,手機依賴最大的問題是,本來信息化時代的很多工作和社交,已經在電子化的虛擬情景中進行了,如果再加上虛擬快樂的誘惑,就會使我們更加忽視從自然和社會中得到真正的快樂。
如何擺脫手機依賴
被問及應該如何擺脫對手機的過度依賴時,穆巖回答,“朋友很重要,哪怕是微信上的朋友”。手機提供的虛擬的快樂分為兩種,一種是純人工的,即游戲類的,這種是最為虛幻的。同時,手機又能帶來真實的社交,即遠程溝通,這種快樂是真實的。所謂重度依賴,首先要區(qū)分一個人是被虛假的快樂所誘惑,還是只是利用手機作為一個社交工具。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取決于是否能夠平衡不同類型的需求,如果生活中的社交非常少,完全依賴于網絡,不是說這種行為不好,而是有風險。
“所有的心理干預都講究循序漸進的原則,讓手機重度依賴者一下子放下手機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可以把手機上進行的活動從純游戲類轉換成社交層面活動,幫助回歸自然狀態(tài)下的心理需求。在這個基礎上,如果是在手機上跟朋友溝通,那么看能不能進一步深化拓展,演變成現(xiàn)實中的聚會或其他活動。”
穆巖告訴記者,對于手機依賴,成年人要依靠自己去調整,而兒童自控能力本身沒有發(fā)展完善,家長和老師尤其要注意,想要引導孩子放下手中的手機和游戲,最根本的方法只有設計出更好的實際體驗,比如帶他們去踢球、逛博物館、學畫畫,去體驗不一樣的、有趣的實景體驗,才能讓他們脫離手機的依賴。現(xiàn)在的家庭和學校教育普遍有一個誤區(qū),家長和老師只是跟孩子說長時間玩手機有這樣那樣的壞處,以為下一個行政命令,孩子就會改變,這是不可能的。現(xiàn)在接受信息的渠道非常多,我們必須采用一種競爭的方式,用更有趣的實景體驗幫助孩子實現(xiàn)實景情景和虛擬情景時間的平衡分配。
“除了朋友,有趣的生活也可以幫助我們擺脫或預防對手機的過度依賴。現(xiàn)在很多大學里都在推行通識教育,例如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無論你學歷史也好、物理也好,都能廣泛地涉獵不同學科。通識教育的理念不是說要專精或廣博,而是使人能夠理解人類積累下來的大體知識體系,也能夠從中汲取到精神上的滿足。如果能夠廣泛地了解多樣的文化,從事更有趣的思考性活動,欣賞探索這個世界,才是能夠保持快樂最根本的方法。”穆巖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