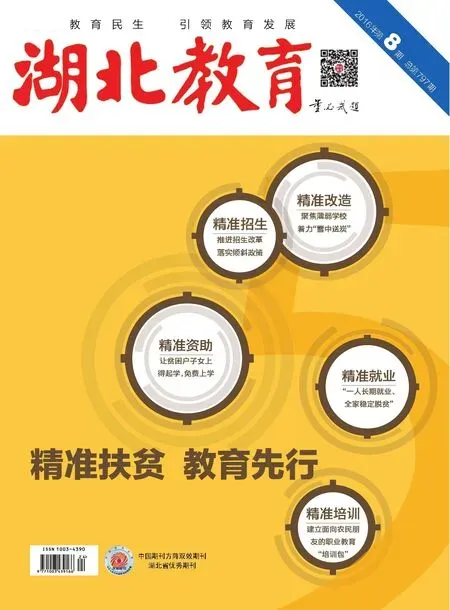重建“樂文化”
蔡興蓉
重建“樂文化”
蔡興蓉

原鐘祥市實驗中學教師,現自由教育人。湖南衛視曾謂之“癲師”。多家教育雜志專欄作者。出版暢銷書《走在孩子的后面》《下輩子還教書》等。現致力于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若有人要問中國文化之核心,我認為可以用一個字概括:樂。東漢時期,佛教慢慢傳入中國,據說,當時寺廟里的佛像,是帶苦相的,中國人不喜歡,于是中國的佛像逐漸演變成微笑乃至大笑。當然,這笑不是來自外在,而是發乎本心,是生命自身的喜樂與完滿。
1600年,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瑪竇來到北京,他在傳播教義上不可謂不盡心竭力,甚至為了“本土化”,特意將“真主”改為“上帝”——“上帝”一詞,本是中國“特產”,殷商時稱死去的天子為“上帝”,而稱活著的天子為“下帝”,結果又怎樣呢?除了士大夫階層多有響應外,其教義實際上并未在全國范圍(江南一帶除外)燎原開來。至于原因,還是因為真主像帶有“苦相”。
說中國的文化是樂文化,實在是切中肯綮的。孔子周游列國,倍受辛苦,好幾次命懸一線,別人看他棲棲遑遑,“累累若喪家之犬”,其實,他老人家活得好著呢!匡國解圍后,首席弟子顏回許久才從后面趕來,孔子說,我還以為你死了呢!顏回說,老師不死,弟子怎么敢先死呢?你可以想象孔子的朗然大笑。陳蔡被圍時,孔子天天以野菜度日,他還跟弟子們開玩笑說,我們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牛,怎么住在野外了呢?
《呂氏春秋》里記載的“子路打虎”的故事,更有意趣:當時孔子口渴了,子路就去找水,誰知一只老虎也來找水,一人一虎就打了起來。子路一刀砍斷了老虎的一小截尾巴,老虎負痛,跑了。子路就用袖子藏了小尾巴,然后回來問孔子:“上士殺虎當如何?”孔子說:“取其頭。”“中士殺虎當如何?”孔子說:“取其耳。”“下士殺虎當如何?”孔子說:“取其尾。”子路受了奚落,就舉起一塊石頭,接著問:“上士殺人當如何?”孔子說:“用筆。”“中士殺人當如何?”孔子說:“用舌。”“下士殺人當如何?”孔子說:“用石頭。”說完師生哈哈大笑。
真正的文明,大概就是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吧?真正的文明,大概就是元氣豐沛,神清氣爽吧?后來的諸多“讀書種子”,亦是平常,親切,直指當下,沒有一絲暮氣,如陶淵明的平淡和暢,李白的逸興遄飛,蘇東坡的興致盎然。說到蘇東坡,這里不妨錄一趣事:他當年被流放到海南島時,有漁民看他們父子孤單,就送一些生蠔給他,蘇東坡立即將生蠔或燒烤,或酒煮,味道都特別好。他還壓低嗓門對兒子說:“千萬不能讓他們(朝廷官員)知道!他們要是知道了,哭著鬧著都要到海南來,我們可就再也吃不到這么好的東西了!”
倘若有朋友問,中國樂文化的根基安在?筆者不怕淺薄,謹呈一孔之見:中國文化朝斯夕斯,念茲在茲的,大約正是打通了三種關系:與自然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與自己的關系。與自然的關系: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馮延巳的“梅落繁枝千萬片,猶自多情,學雪隨風轉”等。與他人的關系:蘇東坡先生在《前赤壁賦》中說:“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又如趙嘏在《長安秋望》有二句:“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等。與自己的關系:辛棄疾《賀新郎·甚矣吾衰矣》:“白發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等。如此境界,可以光照世界——若見一個阡陌路人,也會頓生親情好意。
今天的中國人,面目模糊,不知文化身世;言行之間,多有濁氣暮氣。喚回天地初造般清朗的樂文化,實為文化重建之要旨也。
(責任編輯 曾憲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