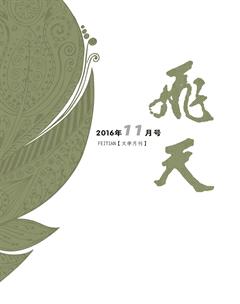詩人筆下的金崖鎮
秋風送爽,院子里的棗子紅熟時,我便不由地懷念起詩人、編輯家楊文林先生來。
先生與我相交整整六十個年頭。
遠在1956年12月,甘肅省第一次創作會議上,我這個滿身土氣的鄉下青年,也因《甘肅文藝》(《飛天》前身)栽培了我的一篇小說而得以與會。會上我見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人,其中有兩位身著戎裝的軍人,我請他倆簽名留念。那位憨實的青年軍人簽名是——崔八娃;那位英武軍官所簽的名字是——楊文林。他們是部隊上來的。
楊文林三字是熟練的草書體;崔八娃三字是剛脫盲后初學寫字的生硬模樣,盡管這樣,但當時的崔八娃卻是和高玉寶齊名,是名滿天下的。
會后我仍回到鄉下握起我的鋤頭。
迨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鄉下大饑,我又偏患大疾,正在無糧缺藥之際,編輯部的清波老師下鄉來我家,幫我修改了一篇小說。這篇名叫《修渠記》的小說發表以后,省上的另一位老師趙燕翼對我說:你不知道,現在的刊物由楊文林管事,我會向他建議,對你,稿費從優。在各位好心人的關懷下,一篇《修渠記》收到稿費80元。當時我覺得我發了橫財,光是我急需的鏈霉素就買了一大堆。我常常對人說:《修渠記》是我的救命篇。
及至1972年春,為紀念毛主席《講話》發表三十周年的盛大活動中,主事的楊文林先生從全省抽調作者時,竟然也抽調了四個鄉下作者——劉志清、任國一、張國宏和我。當時農村貧困,我輩四人在友誼飯店門口一出現,光是衣著就太扎眼,我們有的戴“火車頭”棉帽,我的褲子膝蓋上打一塊大補丁,所以我們四人屢遭門衛查看出入證件。在討論稿件時,劉志清不坐椅子,而是坐在地毯上,掏出羊腿骨煙斗吸起旱煙來。坐在領導位置上的楊文林先生,面對這種場面樂呵呵地看著。
當時的目標是編輯、出版五本文學書:一本小說集,一本詩歌集,一本散文集,一本報告文學集,一本兒童文學集。在抽調來的作者中,搞兒童文學的只有曾萬謙和我兩個人,楊文林先生便給寫小說散文的人硬攤派了一篇兒童文學的任務,這樣才湊夠了五本書的數字。
編輯作者同住一層樓上,時不時開會碰頭,對每篇稿子逐一討論,先由作者本人修改,最后由負總責的楊文林先生把關。
先生特能熬夜,桌上是煙灰缸和一杯釅茶,他蹲在圈椅里,手拿紅筆,對所有的稿件逐字逐句批點刪改,直到定稿。
抽調來的作者們,誰的稿子完成誰就回原單位。而我的一篇小說一篇兒童文學完成之后,楊文林先生知我家太窮、農村里太苦,就把我特意留下,讓我謄清定稿的稿件,使我在豪華的友誼飯店滯留了四個多月。當時用來招待蘇聯專家的友誼飯店,其生活水平和鄉下比,那可是天上地下,所以我在那里住了一百多天之后回到鄉下時,鄉親們有點認不出我了。
我本來是寫小說的,因受楊文林先生重視兒童文學的影響以及我對童話奇幻魅力的癡愛,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試寫了幾篇童話,當我把這些娃娃故事送交先生時,先生又驚喜又不敢在他主編的刊物上發表,因為在全國范圍內,以成人讀者為對象的文藝刊物,就沒有一家刊登此類體裁作品的。后來,還是先生和各方溝通、游說,終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把我的一篇有點不大對口的童話在他主編的文藝刊物上發表出來。這就是我的第一篇童話《革命指頭歷險記》出土的經過。可以說《飛天》是我童話的發芽生根之地,是故土苗圃。更有甚者,多年后,在先生退休離職后,接班的編輯、園丁繼承先生的傳統,繼續發表我的童話至今,使我的童話在這里搖曳了幾十年。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殊令人感動。
時光流逝,有一段時間,我去蘭州新聞界打工,在《蘭州晚報》農村版做合同編輯。這時,我離楊文林先生很近,離曾栽培過我幫扶過我的清波、趙燕翼、汪玉良、許維等諸位老師也都很近,但我走動不勤,無事不找他們,因為我有個信條,覺得對在位的領導、在崗的編輯,跑得太勤會有“套近乎”之嫌。及至楊先生和諸位老師退休離職,我似乎獲得了自由,才頻頻去看望拜訪他們。清波老師中風住院,我去省人民醫院看他,老人家居然感動了,直說他和幾十個作者打過交道,現在來看他的只有我一個。至于楊文林先生,我更是多次敲門找他。先生有的是時間,我也談興更濃,我順便帶去了家鄉的蠶豆角和嫩苞谷棒子。暢談中他詳細詢問我的童話在全國各地發表的情況,此后先生竟著文論述了當年從鄉下來的我們四個泥腿子作者。當這篇文章見報時,我吃驚不少,因為當年倡導的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時興培養工農作者,可現在時過境遷,這時候已不是那時候,一個錢字了得!誰還說那陳舊話題?再者,嚴格意義上說,我們這些草根作者只是文學界的票友罷了。后來這篇文章竟在《飛天》的顯要位置上出現時,我呆立了好久。今日的《飛天》不嫌我們四人土氣嗎?難得!
這使我又想起當年在友誼飯店,楊文林先生笑盈盈地看著劉志清用羊腿骨煙斗吸旱煙的情景,現在足以證明先生當時是真情地欣賞,而不是表面的客氣。
在和先生的暢談中,先生多次問起我家小院里的棗子幾時成熟,他想親手打打棗。因為在此前先生曾在一個雨天,和李老鄉、馬青山、趙劍云去過我家。多次相約后,終于在2012年深秋、枝頭棗紅似瑪瑙的一天,先生和詩人何來、李云鵬一起來到鄉下,來到絲綢古道上的金崖鎮,來到我家院落里的紅棗樹下。我縣本土詩作者尤效清、孫清祖、黃治文、古風(楊秀珍)等早早趕來。
金崖鎮副鎮長唐霞也聞訊趕來,她熱烈歡迎詩人們踏上本鎮地面,并向三位詩人贈送了本鎮志書《金崖史話》,并展示了反映本鎮風物的剪紙長卷《榆中境內絲路圖》。此長卷是一位農婦的創作。
楊文林先生當即說:我要為這畫作寫一首詩。
唐霞接茬兒說:詩人們,你們不僅要為剪紙長卷賦詩,而且請把我鎮的種種風物也要入詩吟嘆呢!我這不是雁過拔毛,而是雁過留聲、人過留名。詩人們來金崖一趟,總要留些紀念詩篇,為我鎮增光添色呀!
應女副鎮長請求,詩人李云鵬即興吟就《金崖農家》:
苑水農家秋色濃,綠芹紅棗饗賓朋。
壁頭嵌畫饒詩意,志卷修文鑒古今。
驛鎮滄海驚巨變,田園童話自青蔥。
塵湮古道駝鈴遠,雄起隔墻鋼鐵城。
詩人何來聽到我鎮動用推土機群在一處山坪上人工造田一萬畝,對此很有興趣,但他當時沒有動筆,而是事后冒雨登上高沿坪,親眼展望了這片萬畝人造田及新修的房屋,還有那尚無人入住的空屋村落,之后補寫了一首《雨中登高沿坪感賦》:
細雨驅車高沿坪,輕煙繚繞如畫屏。
林間新瓦承天露,陌上初霜染丹青。
堪憶群機推秦壑,當夸長嶺演雄兵。
登臨何艱重陽日,一瞥苑川總是情。
詩的末尾用小字注云:壬辰仲秋應邀至金崖農家與眾文友歡會,又蒙金崖鎮政府贈《金崖史話》而言。
現場上本土詩人尤效清應和酬唱道:
玄奘西游 念的是什么經
今人念一本致富經
風霜抹不掉 春風吹又生
千百年開花的
是文成公主的腳印
白馬爺上城
老天爺下個不晴
七月官神 帶來了風調雨順……
本土詩人孫清祖有感于金崖菜農黎明摸黑下菜田剁菜收菜時男女菜農頭上一律戴礦燈照亮子,吟出《蔬菜地里的礦燈》一詩:
那是一盞照徹黑暗之燈
那又是一盞引領光明之燈
我平生第一次看見
菜農頭頂的礦燈
他們凌晨四點砍菜
那盞燈是他們的第三只眼
他們一手扶菜 一手拿砍刀
那盞燈便是他們的第三只眼
青年女詩人古風(楊秀珍),是種田、放羊回來再用電腦寫作的鄉下女詩人。她一到金崖鎮,便深情地吟唱道:
躺在繁華的金城的邊沿
仰望一個時代的繁華
唐朝的萬卷經書
公主文成遠去的車隊
清朝總督的三千里左公柳
絲路上匆忙的腳印
即使千年萬年
依然是小鎮飄不盡的詩情畫意
……
當我站在車水馬龍的小鎮中央
閱讀小鎮
我不再用一個詩人的想象與敏感
而是用仰望星空的眼神
仰望小鎮
仰望小鎮古往今來的輝煌
最后輪到楊文林先生了,他閉口不言神情凝重,只示意叫人們在樹陰下的桌面上鋪上畫氈,并叫拿過紙墨筆硯。之后,先生專注地用毛筆蘸墨揮毫在宣紙上書寫了起來。
我早知道先生退休后練書法,今天我要看看先生的書法練得怎么樣了。殊料當我把頭從圍觀者中間伸過去一看,著實把我嚇了一大跳。先生的筆底下竟出現了我的名字,先生用書法寫的這首詩,竟拿我當主角。可憐我輩草根作者,業余愛好,半路出家,我能掂出我是誰。從嚴格意義上講,我不是什么作家,充其量只是文學界的一名票友而已。先生拿我入詩,真叫人惴惴不安。
等先生躬著腰、顫抖著毛筆緩慢地寫完時,見全幅內容是:
隴上金吉泰,文壇田舍翁;
幼學知稼穡,耕讀立門庭。
鋤下歲月稠,筆底苦樂深;
文章寫大塊,天地一草根。
勞作報春暉,拳拳雕龍心;
固窮守初志,蕩蕩君子風。
并落款:“吉泰老弟作家雜家也著述頗豐以小說醉瓜王登上文壇童話作品榮登全國寶典年將八秩猶犁耕不歇筆耕不輟余詩書以贊作五十五年友情之留念 楊文林 壬辰秋月”。
當先生把這幅詩作書法贈我時,圍觀的文友一齊鼓起掌來。我則有愧地接受了這幅書法,珍藏起來,從不示人。
舞文弄墨后,大家放松閑聊,為了助興,我請了本鎮會唱歌的兩位女村民獻唱。詩人李云鵬先唱了一段《花兒》,女村民孫子梅唱了一曲《青藏高原》,陸尕玲清唱了一段秦腔。
沒想到的是楊文林先生也酷愛秦腔,他接過話筒竟唱起秦腔劇《花亭相會》中的選段,陸尕玲應和先生對唱。
農家小院里氣氛是歡樂融洽的,我們約定后會有期,相約就在來年的棗子變紅時。
整整一天,唐霞始終在場,她見詩人們把苑川河的歷史、菜農頭戴礦燈的場景及推土機群開辟萬畝耕地的壯舉寫入詩作,這在本鎮還是第一次,所以她很高興。之后,她把這些詩作全交鎮政府資料室保存。
事后,我將先生贈我的詩作書法深深珍藏,同時找了一盤秦腔《花亭相會》的光碟,每天播放先生唱過的五句清唱。這是為何?因為先生那天清唱時,雖激情飽滿,但畢竟年事已高,有些上氣不接下氣,我要把這幾句學會,以便來年棗紅、先生再度走訪我家時,我就可以為他幫腔,唱一家伙。
殊料這五句清唱我還沒學會,在一個陰霾的日子里噩耗傳來,我所尊敬的看似身體還康健的先生卻駕鶴西去了!哀哉!
這樣,先生的那五句清唱成了絕唱,贈我的詩作書法也成了絕筆文物!
我將此幅書法打開看,細品細讀,不錯,詩里是有過譽的地方,但其中“鋤下歲月稠,筆底苦樂深”句,卻也道出了農民作者的個中甘苦。再看事件本身,一位退休的老領導老編輯,深入鄉下,在樹陰里伏案,為他所培育的底層的八十歲草根作者書寫贈詩,這是何等情懷!若非胸懷寬厚、真情實意、看重群眾,胡能如此?這猶如當年在友誼飯店,先生含笑欣賞劉志清用羊腿骨煙斗吸旱煙一樣。毋庸諱言,就在毛爺爺在世時,盡管強調工農兵多重要多重要,但個別文化部門的個別人,忽悠小看鄉下人的鮮活例子不少呢!兩相對照,先生的這種精神難能可貴了!
先生走了,先生培育的我這個草根作者也年過八十,垂垂老矣。每當回首往事,清晰地記得自1955年清波老師幫我在文學園地里出土以后,緊接著在《飛天》園圃里培育我們的園丁就是楊文林先生以及何來、李云鵬、李禾、冉丹、張平、馬青山、閻強國、趙劍云、王文思等幾代園丁了。他們為作者做嫁衣,付出了心血!
屈指算來,我扎根《飛天》園地至今已整整六十個年頭,可謂年輪很多的老老草根了,屢屢懷舊,一個鄉下泥腿小伙,懷揣一篇稿子,出入木塔巷30號、中蘇友好館小樓、省政府禮堂前院大樓,去《飛天》園地的種種場景,人物言談及接到新雜志的各種鏡頭,歷歷在目,令人眷戀懷念,感到溫馨幸福。
辛苦了,寬厚的楊文林先生!
辛苦了,做嫁衣的《飛天》歷屆園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