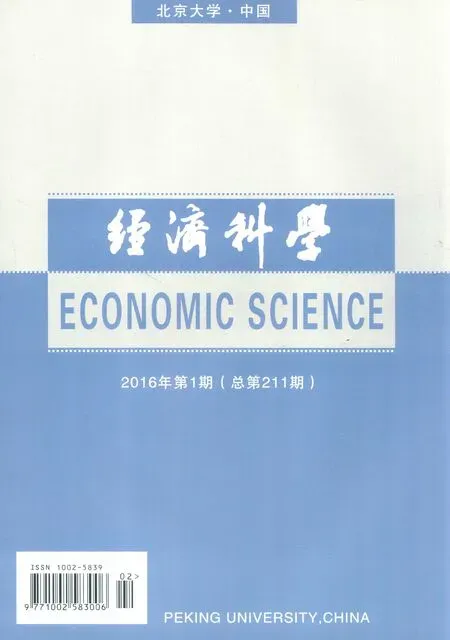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出口行為——基于微觀企業數據的經驗研究*
王 杰 劉 斌孫學敏
?
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出口行為——基于微觀企業數據的經驗研究*
王 杰1劉 斌2孫學敏3
(1.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河南鄭州 450002)(2.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 北京100029)(3.鄭州大學商學院 河南鄭州 450001)
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是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主導全球生產網絡及價值鏈也已成為重要趨勢。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國微觀企業數據分別從企業出口貿易結構以及貿易持續時間系統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結果表明:第一,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產品價格、出口數量以及出口地理范圍的廣化。第二,通過引入生存分析模型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延長企業出口持續時間,增強了出口企業與特定出口目的國的貿易穩定性。因此,實施“走出去”戰略對于改善我國企業出口表現具有重要的意義。
對外直接投資 出口行為 傾向評分匹配 生存模型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近年來,隨著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國際分工模式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中國制造”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然而,“繁榮”的背后卻存在著巨大的“隱憂”,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以及出口貿易的不穩定性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之路上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也深刻說明我國出口企業依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與此密切相關的一個事實是,在出口貿易日益增長的同時,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也蓬勃興起,而且隨著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走國際化經營的道路也已經成為大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重要途徑,中國企業正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全方位融入國際市場參與全球競爭。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擴大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允許發揮自身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合作”,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和國家戰略中的地位愈來愈凸顯。商務部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了1231.2億美元的歷史新高,連續3年位列全球三大對外投資國。在這一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一直是該領域的熱點話題,也形成了三種比較重要的理論觀點:替代關系、促進關系以及不確定關系。比如,Buckley 和Casson(1981)研究發現:為了減少貿易壁壘、降低貿易運輸成本,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利用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市場。Grubert和Mutti(1991)利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存在替代效應。但Lipsey和Wesis(1981)同樣利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卻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促進了貿易的發展。Blonigen(2001)、Head 和Ries(2001)則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明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要根據產品性質來判斷,如果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生產最終產品,則會減少母國對東道國的出口,但如果生產這種產品需要從母國進口大量中間產品,則會促進母國出口。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保持快速發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限于數據的可獲性,有關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的研究相對較少。項本武(2009)利用2000-2006年中國對50個國家的直接投資和貿易數據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顯著促進出口;謝杰和劉任余(2011)發現外向FDI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張春萍(2012)采用1996-2010年中國對18個國家的直接投資和貿易數據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關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微觀層面的研究文獻更是匱乏,蔣冠宏和蔣殿春(2014)首次運用2005-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微觀企業數據,通過計量檢驗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上促進了企業出口,而且增加了出口金額。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結論的形成都是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對行業、地區或企業出口規模影響的分析,并沒有對企業出口貿易結構(包括出口產品質量、價格等)和貿易穩定性(出口持續時間)的進一步分析。基于此,本文從微觀企業層面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企業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并進一步驗證對外直接投資是否有利于延長企業出口持續時間。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改進之處在于:第一,運用傾向評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從出口產品質量、價格、數量以及出口目的地等多個維度計量檢驗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第二,引入生存模型深入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到特定目的國持續時間的影響。從企業出口貿易結構到貿易穩定性逐步深入考察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出口表現的典型事實
隨著中國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以及國家“走出去”政策的刺激,中國大量企業開始通過設立海外分支機構走國際化經營道路。在進行經驗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特征及企業出口表現的典型事實做簡要的描述性分析。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特征
商務部《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止2014年底,中國1.85萬家境內投資者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近3萬家,分布在全球186個國家(地區),投資存量規模達到6.4億美元,首次步入全球前10行列。表1報告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與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基本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在樣本期內,除2009年外,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目逐年增加,從2004年的69家上升至2008年的1279家。雖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重也逐年上升,2004年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占企業總數的0.13%,2008年達到0.33%,但比重仍然較低。2009年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目下降,可能的原因是世界經濟危機導致世界經濟低迷,導致我國企業減少對外直接投資。另外,我們按照境外投資企業數量,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劃分為多分支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和單分支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結果發現大部分境外投資企業為單分支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009年單分支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達到85.8%,多分支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僅為14.2%。

表1 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與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基本統計
(二)中國企業出口表現的典型事實
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與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相比,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出口表現方面究竟存在哪些差異。接下來,本文就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和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出口表現上的差異進行均值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從中可以看出,與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相比,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數量、出口產品質量以及產品價格相對較高。其中,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數量均值為11.765,而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數量均值僅為11.074,這一差異值在1%檢驗水平上顯著;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和出口產品價格均值分別比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高出0.022和4.266,而且差異值均通過了1%顯著性檢驗。以上初步分析表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比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具有更好的出口表現。那么,據此得出“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企業出口表現”的結論是否可靠?問題的關鍵是,單純的統計數據比較往往會掩蓋事件背后的真相,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下文將采用更嚴謹的計量分析來檢驗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表現的影響效應。

表2 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與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出口表現差異的均值檢驗結果
另外,本文對企業在特定出口國市場上的連續出口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從表3可知,在特定出口國市場上,企業連續出口超過3年的樣本僅占10.21%,55.25%的企業持續時間僅為1年,僅有6.08%的企業存在多個持續時間段(如表3所示,持續時間段的定義在后文中作詳細說明)。從以上分析可以明顯看出,在出口國市場上,中國企業出口持續時間往往較短,企業的貿易關系不具有持久性。

表3 貿易持續時間的統計性描述
三、計量模型、變量度量與數據說明
本文研究目的是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表現的影響,然而在經驗分析中,往往會存在選擇性偏差造成估計結果的偏差。接下來,本文就為克服這一問題建立適當的估計模型,并對主要變量和采用的數據進行測算和說明。
(一)估計模型
本文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視為處理組,將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集合視為對照組,構造一個二元虛擬變量對外直接投資,設=1表示企業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0則表示企業為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同時,我們將企業初始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記為0,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后的第年。我們用表示企業出口表現,包括出口產品價格、數量、質量以及出口目的地數目(具體測度方法將在下文詳細闡明)。那么,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和非對外直接投資兩種情況下的出口表現差異就可以記為:
其中,W和W分別表示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和非對外直接投資兩種狀態下的出口表現。=1表示企業首次對外直接投資。但由于在企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后,其非對外直接投資時的狀態已經不可觀測,因此是不可觀測的,導致公式(1)無法估計。本文參照現有文獻(Girma et al., 2004)的做法,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選取合適的對照組來研究兩種狀態下的企業出口表現差異。在尋找到能夠盡可能代表處理組企業的對照組企業后,本文進一步檢驗對外直接投資后處理組和對照組企業之間的出口表現差異。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二)主要變量的測算
1、產品質量的測度。本文利用事后反推的方法測度產品質量(Manova and Zhang, 2012)。假設消費者效用函數為:,其中,和分別表示產品種類的質量和數量,表示產品種類間替代彈性。對應的價格指數為:,對應的消費數量為:,其中,E為消費者支出。企業在年對國出口產品的出口數量可表示為:
取對數并整理得到如下計量回歸方程式:
對式(6)測算的產品質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從而得出企業在年對國出口產品的標準化質量指標,如式(7):
式(8)中Q代表企業第年出口產品的質量,v為企業在年對國出口產品的價值量(),為企業在年對國出口所有出口產品價值量之和。
2、其他被解釋變量的界定和度量。(1)出口價格為企業在第年出口所有產品價格平均值。(2)出口數量為企業在第年出口所有產品的數量之和。(3)出口目的地數目指企業在第年出口目的地數目之和。
3、企業生產率的計算。本文采用LP方法(Levinsohn and Petrin, 2003)分兩步估計勞動、資本和中間投入的系數:第一步,使用資本和中間投入高階多項式的近似式,運用OLS方法估計勞動的系數;第二步,利用第一步估計出的勞動系數估計資本和中間投入的系數,最后得出生產率的有效估計。其中,用企業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衡量勞動力投入;用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衡量資本投入。
4、行業進口關稅率的計算。本文對行業進口關稅率的衡量采用如下公式:。其中,代表行業最終產品進口關稅率,表示協調編碼產品,表示該行業產品的集合,N表示HS6位數產品的稅目數,Tariff表示在第年進口產品從價關稅率(AV Duty Rate)。
5、其他控制變量的設定。(1)企業規模用企業年均從業人數表示。新貿易理論強調了規模經濟對出口比較優勢的作用,同時,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也認為規模因素對企業出口表現具有重要影響。(2)企業成立時間指企業成立以來的時間,計算公式為:企業成立時間=當年年份-企業開業年份+1。隨著企業成立時間的增加,生產經營方式也日趨成熟,經驗越豐富的企業通常擁有更好的出口表現。(3)國有企業虛擬變量。由于體制性原因,國有企業缺乏技術創新和學習的動力,在有限的技術活動中效率低下。在識別企業所有制類型時,以國有的實收資本比例是否超過50%作為識別國有企業的方法(路江涌, 2008)。
(三)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有《中國海關進出口數據庫》、《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以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本文首先按照企業名稱與年份將對外直接投資數據與工業企業數據進行合并,然后參照田巍和余淼杰(2013)的方法,分兩步進行匹配:首先,采用企業名稱和年份進行匹配,然后用企業所在地郵政編碼以及企業電話號碼的后七位將用企業名稱沒有識別的企業再次合并。另外,本文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進行了如下篩選:(1)刪除企業工業總產值、企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缺失的觀測值。(2)刪除不符合會計原則的樣本。(3)刪除不滿足“規模以上”標準的樣本(謝千里等, 2008)。貿易伙伴國GDP數據來源于IMF數據庫;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距離、貿易伙伴國是否為內陸國數據來源于CEPII數據庫;貿易伙伴國的風險等級數據來源于OECD數據庫。
四、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出口表現的估計結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最小鄰近匹配方法以及馬氏距離配對法為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選擇對照組企業,并進一步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表現的影響效應。
(一)最小鄰近匹配及估計結果

表4 匹配前、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和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指標的比較
由表4配對后的處理組與對照組的各類配對指標均值差異的概率值可見,與未配對前的原始樣本相比,配對后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和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選取的匹配指標變量上均不存在顯著的差異,這一結果說明配對效果較好。

表5 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表現的初始檢驗結果
注:①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②*、**和***分別代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③由于企業出口不同產品的數量、價格以及質量不能簡單進行加總,本文第(1)-(3)列按照“年份-企業-產品”層面進行回歸,第(5)列按照年份-企業進行回歸,所以觀測值存在差別。
表5報告了式(2)的估計結果,因變量分別為出口產品質量、價格、數量以及出口目的地數目。首先,觀察一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產品質量和價格的影響,表5第(1)列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產品質量有密切關系。企業“走出去”必定會接觸到國外的先進技術,產生的逆向技術轉移可能使得母公司進一步改善企業生產工藝和流程來提升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產品質量。隨著消費者對高質量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企業出口產品質量越高,意味著產品的預期價值得到提升,出口價格也就越高(施炳展, 2013)。表5第(2)列對外直接投資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產品價格的正向促進作用。
其次,觀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數量的影響。表5第(3)列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數量的影響不明顯。一方面,如果企業基于東道國優勢資源而設立分支機構進行生產和銷售,就不需要從母國進口配件、原材料和中間品,那么無疑是對母國企業出口的替代,而且東道國企業也可能通過技術模仿掌握產品生產技術,隨后開始生產和銷售該產品,這會進一步替代母國企業對該國同類產品的出口(毛其淋和許家云, 2014);另一方面,如果企業通過提供出口服務來擴大和開辟海外市場,并且不在投資東道國建立工廠,那么就會減少企業的前期固定資本投資,大大降低了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出口;如果企業為滿足海外子公司生產產品的需求,從母國進口配件、原材料和中間品等,顯然也促進母國企業出口。而技術研發類投資主要傾向于利用東道國的先進技術進行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競爭力的同時必定帶來出口的增加。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數量的影響要視“促進效應”和“替代效應”的大小決定。
最后,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目的地數目的影響。表5第(4)列估計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增加了企業出口目的地選擇范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是擴大和開辟海外市場,企業在某國建立海外分支機構后,然后以該東道國為中心將出口目的地進一步擴大到投資東道國的鄰國;另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提高效應以及對生產技術的創新效應都會增加出口產品的暢銷度,進而使產品出口到更多的國家。
(二)基于馬氏距離匹配的再估計
為了消除由于匹配方法的不同對估計結果造成的影響,本文進一步運用馬氏距離匹配法進行研究匹配。馬氏距離配對的原理如下:對于與,與間距離D為:。其中,U和U分別為和的匹配變量值,為對照組各匹配變量值的協方差矩陣。表6運用馬氏距離匹配后的估計結果顯示,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產品質量、價格以及出口目的地數目估計系數均為正,對出口數量估計系數為負,且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與運用最小鄰近匹配法的估計結果一致,進一步證明了本文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表6 基于馬氏距離匹配的估計結果
續表6

產品質量產品價格出口數量出口目的地數目(1)(2)(3)(4)是否國有企業0.0410***(3.4607)-0.4266***(-2.9908)0.2358(1.3257)-0.2755(-1.6373)成立時間0.0529***(14.0780)0.2719***(6.0935)-0.2412***(-4.3339)-0.0228(-0.4608)企業規模-0.0052(-1.6113)0.0716*(1.9053)0.0774*(1.6525)0.4274***(10.5612)行業關稅率-0.0405(-1.4223)0.2566(0.7637)-0.0624(-0.1489)-0.1788(-0.5565)常數項-1.8744***(-16.2003)-3.1099*(-1.8310)15.6657***(7.3953)2.2585(1.4564)年份效應是是是是行業效應是是是是地區效應是是是是R20.47440.32290.21090.3861觀測值10,19610,17210,1721,141
五、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生存分析
從上文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中國企業出口的貿易結構問題,那么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這種在兩國搭建的“有形橋梁”是否更有利于貿易關系的持續?下面我們將進一步采用生存分析方法來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在某一特定出口國市場持續時間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通過Cloglog離散時間模型進行計量檢驗。
在生存分析中,通常用生存函數來刻畫生存時間的分布特征。由于企業在某一特定出口國市場上的生存時間更能衡量企業出口貿易的穩定性。因此,本文利用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三維數據,包括“企業—年份—出口目的國”,更細致地考察對外直接投資是否能夠降低企業在特定出口目的國的退出風險。
我們定義企業在某一特定出口國家的出口持續時間為企業從進入該出口國市場到退出該市場所經歷的時間。企業退出某一國外市場稱為“風險事件”,風險事件是由于企業出口交貨值為零或者企業倒閉引起的。令T表示企業出口市場上的生存時間長度,取值為t=1,2,3…,其中,表示貿易關系中的特定時間段,如果一個企業出口持續時間段是完整的,記為c=1,如果出口持續時間段是右側刪失,則記為c=0。我們把企業保持出口持續狀態的生存函數定義為:
另外,我們采用Kaplan-Meier乘積項對生存函數進行非參數估計:
式(11)中,n表示在期處于風險狀態中的出口持續時間段的個數,d表示在同一時期觀測到的“失敗”對象個數。風險函數表示企業在第期出口,而在第期停止出口的概率,即:
風險函數的非參數估計表示為:
首先采用Kaplan-Meier方法初步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持續時間的影響。為了避免樣本數據刪失問題,本文利用2000年沒有出口而在2001-2006年期間有出口的企業作為新的分析樣本。從圖1可以看出,首先,生存曲線呈下降趨勢,而且隨著持續時間的延長,生存率趨于穩定。其次,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特定出口國市場上的生存曲線一直位于未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生存曲線的上方,說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延長企業對特定國家出口的持續時間。
圖1 企業出口特定目的國的生存曲線
接下來我們使用計量模型來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的影響。由于本文樣本數據都是年度觀測值,因此選用離散時間模型進行估計,離散時間的Cloglog生存模型如下:

表7 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特定出口目的地持續時間影響的估計結果
表7第(1)列不考慮風險函數的時間依存性特征的結果顯示,是否對外直接投資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并且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對外直接投資降低了企業退出某一特定出口國市場的風險率,貿易關系的持續時間更長,這與理論預期以及K-M生存曲線的初步判斷一致。企業在某一特定出口國市場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無論其目的是擴大市場、技術學習或者資源尋求,都是最便利的途徑。降低出口成本、逆向技術溢出以及獲取當地資源,都會提高企業的出口競爭力,有助于延長企業在該國的出口持續時間。第(2)列加入時間段特定虛擬變量的估計結果顯示,是否對外直接投資系數仍然顯著為負,進一步驗證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在各控制變量中,企業成立時間越長、規模越大越有助于提高企業在出口市場上的生存率。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面臨較高的風險,如果出口企業是國有企業,則其出口持續時間會較短,這與G?rg et al.(2008)的結論是一致的。生產率高反而不利于出口時間的持續,說明存在“生產率悖論”。行業關稅率越高,其退出出口市場的可能性越低,說明我國加入WTO后,產出關稅的降低所引致的競爭效應對企業生存能力會產生一定負向效應。另外,我們發現國家層面的因素對企業出口持續時間有著重要的影響。貿易伙伴國風險等級越高,越不利于貿易關系的持續,但出口到GDP規模較大的國家或地區會降低失敗的概率。如果企業出口到內陸國家或地區,出口持續時間會較短,與貿易伙伴國距離越近越有利于貿易關系的時間。
以上分析為多重持續時間段樣本,①為了考察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我們也分別對唯一持續時間段樣本和首個持續時間段②樣本進行估計。表7第(3)和(4)列結果顯示,是否對外直接投資的估計系數均為負,且均通過1%顯著性水平檢驗,再次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延長企業出口到特定目的國的持續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表7第(2)-(4)列時間段特定虛擬變量(Duration2-Duration5)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且隨著時間段的增加呈上升的趨勢,說明隨著企業在某一特定出口市場上出口持續時間段的推移,企業退出該國市場的風險較大,反映了中國企業出口的不穩定性,企業在特定出口國市場上的合作關系不長久,容易出現所謂的“一錘子買賣”現象,存在出口市場不穩定的問題。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中國微觀企業數據,實證考察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表現的影響,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提高出口企業產品質量和價格,對外直接投資引致的“競爭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使得出口企業更多地參與到國際市場競爭中去,擴大了出口目的國選擇范圍。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出口既存在替代效應也存在促進效應,因此對企業出口數量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同時,本文發現對外直接投資降低了企業退出某一特定出口國市場的風險率,有助于延長企業出口持續時間。
本文研究結論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結構調整均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第一,鼓勵有實力的出口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直接投資。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可以增加與投資國家聯系的便利性,有助于企業以更加靈活的策略促進出口;對發達國家或地區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有利于企業改良生產工藝和提升創新能力,有助于提高出口產品質量,為出口提供更有利的保障;第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延長企業出口持續時間。中國企業出口持續時間較短或者不持續,這種不平穩性不僅不利于出口的穩定增長,而且使得企業面對外部沖擊時毫無招架之力。企業通過海外子公司一方面更容易打開當前營銷市場,采取因地制宜的營銷策略來減少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而且依據當地消費者的偏好生產產品,以此增加產品的市場接受度,提高產品在當地的持續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充分了解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加快技術創新步伐,提高產品競爭力,增強企業持續出口動力。
1. 蔣冠宏、蔣殿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效應”》[J],《經濟研究》2014年第5期。
2. 路江涌:《外商直接投資對內資企業效率的影響和渠道》[J],《經濟研究》2008年第6期。
3. 毛其淋、許家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抑或抑制了企業出口?》[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年第9期。
4. 施炳展:《中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異質性:測度與事實》[J],《經濟學(季刊)》2013年第13卷第1期。
5. 田巍、余淼杰:《企業出口強度與進口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來自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
6. 項本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基于面板數據的協整分析》[J],《財貿經濟》2009年第4期。
7. 謝千里、羅斯基、張軼凡:《中國工業生產率的增長與收斂》[J],《經濟學(季刊)》2008第7卷第3期。
8. 張春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年第6期。
9. Bernard, A. and B. Jensen, 1999, “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Cause, Effect or Both?”[J],, Vol.47(1), pp1-25.
10. Blonigen, B.A., 2001, “In Search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Foreign Product and Export”[J],, Vol.53(1), pp81-104.
11. Girma, S., D. Greenway and R. Kneller, 2004, “Does Exporting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 Microeconomic Analysis of Matched Firms”[J],, Vol.12(5), pp855-866.
12. G?rg, H., K. Richard and M. Nalázs, 2008,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Export?” [R],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6614.
13. Grubert, H., and J. Mutti, 1991, “Taxes, Tariffs and Transfer Pricing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J],Vol.73(2), pp285-293.
14. Head, K. and J. Ries, 2001,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irm Export”[J],Vol.9(1), pp300-316.
15. Helpman, E., M. Melitz and S. R. Yeaple, 2004, “Export vs. FDI” [J],, Vol.94(1), pp300-316.
16. Levinsohn, J. and A. Petrin, 2003,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R], NBER Working Paper, No.7819,.
17. Lipsey, R. E. and M. Y. Weiss, 1981, “Foreign Product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Vol.63(4), pp488-493.
18. Manova, K. and Z. Zhang, 2012, “Export Prices Across Firms and Destinations”[J],, Vol.127(1), pp379-436.
(RD)
①國家風險等級變量按照OECD國家風險分類法,0為最小風險,7為最大風險,由于國家風險等級一年之內會有多次調整,本文使用樣本期內各國國家風險等級的年度平均值。
①多重時間段指企業連續出口一段時間,然后轉為內銷或者完全退出市場,或者接著再次進入出口市場。
②例如某個企業在2001-2003年為出口企業,2004年退出出口市場并持續到2006年,但在2007年又進入出口市場,那么2001-2003年就是首個持續時間段,顯然,唯一持續時間段一定是首個持續時間段,但首個持續時間段并不一定是唯一持續時間段。
* 本文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71503046),以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4JDGC027)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