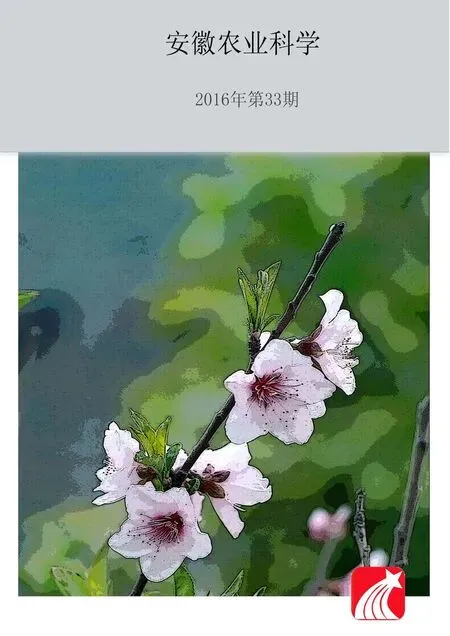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協調性研究
李劍波,李純鍇
(1.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重慶 400700;2.重慶市旅游學校,重慶 400084)
(12)
(13)
式中,rj為第j項指標所屬的子系統權重;wj為第j項指標的綜合權重;
為第i年份j項指標的標準化值。
?
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鎮化發展協調性研究
李劍波1,李純鍇2
(1.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重慶 400700;2.重慶市旅游學校,重慶 400084)
新型城鎮化是人口、土地、經濟、生態、社會5大城鎮化子系統的協調推進,運用協調度模型、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和障礙度模型,判別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發展的協調性。結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綜合水平整體不高,其均值和標準差隨時間增大,各區域間差異顯著;子系統的發展在空間上呈現非均衡性特征,人口城鎮化分異程度始終最高但空間分異不斷縮小,社會和經濟城鎮化的空間分異逐漸增大,土地和生態城鎮化的空間分異不斷縮小。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度總體呈現遞增態勢,空間分異特征較明顯但不斷縮小;城鎮化協調度相似地區在空間上呈現強集聚狀態,成都市、德陽市、眉山市、南川區、綦江區始終為熱點區域,渝東及渝東南始終為冷點區域,熱點區和冷點區比重逐漸增加。
協調度;新型城鎮化;ESDA;障礙度;成渝城市群
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及經濟全球化等促進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帶動了我國城鎮化快速發展[1]。但是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脫離了循序漸進的原則,出現了冒進態勢[2],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各地資源環境保障能力建設與城鎮化發展矛盾愈演愈烈,城鎮化協調發展作為癥結破解的根本,成為普遍關注的熱點之一。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平臺、長江經濟帶的戰略支撐、國家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示范區,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的協調發展能夠充分提高西部地區城市群協調發展能力。
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學科和視角對城鎮化協調發展展開研究,經過梳理總結發現:國外學者主要聚焦于城鎮化與經濟發展的正向關系而非其協調性水平[3-4]。國內學者在研究內容上主要關注城鎮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5-6],土地城鎮化[7-8]和人口城鎮化[9-10]的單個評估,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的協調關系研究[11],人口、土地、經濟、社會城鎮化之間[12-14]的相互協調研究,較少體現生態城鎮化;在城鎮化水平測度方法上,主要分為單一指標測度法[9-11]和復合指標測度法[14-18],靜態測度城鎮化各子系統發展的互動特征,忽視動態演變規律;在研究對象上從全國[15]、跨省域[16]、省域[17-18]、縣域[19-20]等尺度開展討論,對于跨行政區的城市群較少涉及。關于成渝城市群的研究主要有城市群的等級規模結構[21]、新型城鎮化水平測度與發展[22]、生長發育與空間演化[23]、綜合交通發展構架[24]等,對城市群新型城鎮化協調度的研究頗少。
基于此,筆者以2005、2014年為時間斷面,利用協調度模型、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和障礙度模型,探討成渝城市群36個研究單元新型城鎮化發展協調度的時空格局特征,描述其演變規律和總體走向,診斷影響城鎮化協調的障礙性因素,旨在為各級政府制定區域戰略政策提供理論支撐。
1 指標構建、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成渝城市群是引領西部開發開放的國家級城市群,是貫徹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升內陸開放水平、促進區域發展平衡的重要支撐。根據《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成渝城市群具體范圍包括重慶市的渝中、萬州、黔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壩、九龍坡、南岸、北碚、綦江、大足、渝北、巴南、長壽、江津、合川、永川、南川、潼南、銅梁、榮昌、璧山、梁平、豐都、墊江、忠縣等27個區(縣)以及開州區、云陽縣的部分地區,四川省的成都、自貢、瀘州、德陽、綿陽(除北川縣、平武縣)、遂寧、內江、樂山、南充、眉山、宜賓、廣安、達州(除萬源市)、雅安(除天全縣、寶興縣)、資陽等15個市(圖1),總面積18.5萬km2,2014年常住人口9 094萬,地區生產總值376億元,分別占全國的1.92%、6.65%和5.49%[25]。

圖1 成渝城市群Fig.1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1.2 指標體系構建 人口城鎮化是城鎮化的核心,其實質是人口經濟活動的轉移過程;經濟城鎮化是動力,主要指經濟總量的提高和經濟結構的非農化;土地城鎮化是城鎮化的載體,主要表現為城鎮建成區面積的增加;社會城鎮化是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向鄉村擴散的變化過程[14];生態城鎮化是將生態建設納入城鎮化全過程,使區域發展按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原則在時間(過程)和空間(狀態)2個維度上同時同地實現生態化、城鎮化[26]。從以上新型城鎮化內涵的5大方面出發,遵循指標選取的科學性、完整性、系統性、可操作性原則,構建城鎮化水平綜合測度指標體系(表1)。
表1 城鎮化發展協調度指標評價指標體系與指標權重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urbanization and weight

目標層Targetlayer準則層Criterionlayer指標層Indexlayer2005年權重Weightin20052014年權重Weightin2014城鎮化水平綜合測度體系Compre?hensiveeval?uationindexsystemonurbanization人口城鎮化城鎮人口比重(%)0.01910.0317非農人口規模(萬人)0.11990.1381萬人大學生人數(人)0.16850.1360非農產業就業人口比例(%)0.07550.0512社會城鎮化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輛)0.03230.0585萬人床位數(床)0.03590.0335萬人移動電話數(部)0.06720.0442人均教育經費(元)0.03940.0681土地城鎮化建成區面積(km2)0.14920.1476人均建成區面積(m2)0.03770.0452人均城市道路面積(m2)0.04660.0376經濟城鎮化人均GDP(元)0.03430.0391GDP增長速度(%)0.00700.0276非農產業產值比重(%)0.01240.0352職工平均工資(元)0.04570.0187生態城鎮化單位GDP能耗(噸標準煤/萬元)0.04360.0186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0.02220.0127生活垃圾處理率(%)0.01070.0112人均綠地面積(m2)0.03280.0452
1.3 數據來源 選取2005和2014年成渝城市群城市相關數據,主要來自2006和2015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四川統計年鑒》《重慶統計年鑒》,重慶市部分數據選自相關區縣國民經濟統計公報(重慶市作為省域架構的直轄市,不能以整體與四川省的地級市進行比較,因此將重慶市拆分成主城區和其他區縣共計21個研究單元,其在行政級別上與四川省地級市同級。重慶市的開州區、云陽縣部分行政區進入城市群,因其統計數據難以獲取而將上述2個區縣整體納入城市群。四川省的北川縣、平武縣、萬源市、天全縣、寶興縣因未納入城市群,其相關統計數據已從所屬地級市中去除)。個別缺失的數據采用相鄰年份插值法獲取。
1.4 研究方法
1.4.1 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分法。熵值法是利用指標自身的信息來判斷其有效性和價值,是一種客觀的賦權方法,可以對系統做出客觀、公正的綜合評價。在信息論中,熵是系統無序程度的度量,若某項指標的指標值變異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該指標提供的信息量越大,其權重也越大。反之,該指標的權重也越小[20]。熵值法的具體步驟如下:
(1)利用極差變換法標準化數據。


(2)指標權重的確定。
(1)
(2)
(3)
(4)

1.4.2 協調度模型。利用協調系數函數計算評價單元人口、土地、經濟、社會和生態城鎮化發展的協調系數,然后再利用協調發展度函數計算評價單元城鎮化發展協調度[16]。
(5)
(6)

1.4.3 空間關聯分析。
(1)Moran’sI指數。引入全局Moran’sI指數[27]對觀測值空間模式的整體定量描述,用于探測整個研究區的空間關聯結構模式。
(7)

采用Z檢驗對Moran’sI結果進行統計檢驗:
(8)
式中,E(I)為數學期望;Var(I)為變異系數。
在給定顯著水平下,如果Moran’sI數值為正,表示空間鄰接單位擁有相似性,空間集聚性強,越接近 1 說明空間分布正相關性越強;反之,接近0說明空間單元無相關性,屬隨機分布。
(2)Getis-WOrdGi*。Getis-WOrdGi*用于識別不同空間位置上的高值簇與低值簇[28],即熱點區(hot spots)與冷點區(cold spots)的空間分布。計算公式為:
(9)
為了便于比較,需要對Gi*(d)進行標準化處理,其中:
(10)
式中,Wij為空間權重矩陣,空間相鄰為1,不相鄰為0;E(Gi*)和Var(Gi*)分別為Gi*的數學期望和變異系數。如果Z(Gi*)為正且顯著,表明位置i周圍的值相對較高(高于均值),屬高值空間集聚(熱點區);反之,如果Z(Gi*)為負且顯著,則表明位置i周圍的值相對較低(低于均值),屬低值空間集聚(冷點區)。
1.4.4 障礙度模型 。測算出各年度協調度水平后,要對各指標進行更深層次的系統分析,提煉出影響成渝城市群城鎮化水平及協調度主要因素,為制定差異化、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論借鑒與支持。通常采用因子貢獻度Fij(單項指標對總目標的影響程度)、指標偏離度Iij(單項指標評估值與 100% 之差)和障礙度(Yij,yij)(分別表示第i年各子系統指標和單項指標對協調度的影響程度)3個指標對障礙因素進行分析診斷[29],具體計算公式為:
Fij=rj×wj
(11)
(12)
(13)

為第i年份j項指標的標準化值。
2 結果與分析
2.1 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分析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分布見圖2。由圖2可知,2005年城鎮化綜合水平得分排前4位的分別是重慶(主城區)、成都市、永川區、綿陽市,其數值分別為0.818 6、0.774 1、0.402 4、0.323 8。城鎮化綜合水平得分在0.3以上的還有德陽市和樂山市,其余城市得分都在0.3以下。2014年得分前4位仍然是重慶(主城區)、成都市、永川區、綿陽市,城鎮化綜合水平在0.3以上的還有涪陵區、璧山區、德陽市、萬州區、黔江區,其余城市得分都在0.3以下。城鎮化綜合水平的均值由2005年的0.248 6增加到2014年的0.273 3,標準差由0.150 4增加到0.152 0,這表明2005—2014年成渝城市群區域城鎮化綜合水平的增長和城鎮化綜合水平分布差異的加劇。總體來看,區域綜合水平基本格局保持穩定,區域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重慶(主城區)、成都兩大中心城市及周邊的永川區和綿陽市,而城鎮化綜合水平較低的區域主要分布在云陽、豐都、潼南等地區。
從城鎮化子系統的發展來看,36個研究單元的人口城鎮化分異程度始終最高,但空間分異不斷縮小,2005和2014年人口城鎮化的標準差分別為0.073、0.066,人口城鎮化水平最大得分地域均為重慶(主城區),最小得分地域均為潼南縣;社會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的空間分異逐漸增大,標準差分別由2005年的0.031、0.020增至2014年的0.039、0.022,其中四川省的成都市、樂山市、雅安市、綿陽市,重慶市的主城區、永川區、萬州區、涪陵區、黔江區、璧山區的社會城鎮化水平始終高于城市群社會城鎮化平均水平,四川省的成都市,重慶市的主城區、永川區、長壽區、涪陵區、黔江區、璧山區的經濟城鎮化水平始終高于城市群經濟城鎮化平均水平;土地城鎮化和生態城鎮化的空間分異不斷縮小,標準差分別由2005年的0.041、0.015降至2014年的0.039、0.011,其中四川省的成都市、綿陽市,重慶市的主城區、萬州區、涪陵區、長壽區、江津區、永川區、合川區的土地城鎮化水平始終高于城市群土地城鎮化平均水平,僅有四川省的成都市、綿陽市,重慶市的長壽區、涪陵區、璧山區、南川區、墊江縣的生態城鎮化水平始終高于城市群生態城鎮化平均水平,占全部研究單元數量的19.4%。
2.2 城鎮化發展協調度分析 利用公式(6)計算2005和2014年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發展協調度(圖3)。由圖3可知,2005和2014年成渝城市群36個研究單元城鎮化發展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678、0.726,總體呈現遞增態勢,2個年份的協調度標準差分別為0.178、0.171,空間分異較明顯但在不斷縮小。2005年16個研究單元城鎮化發展協調度高于平均水平,集中分布在分別以成都、重慶(主城區)為核心的東北—西南向城市帶上,以重慶(主城區)最高(1.256),渝東北的豐都、云陽等地區的城鎮化協調度較低;2014年13個研究單元城鎮化發展協調度高于平均水平,最高得分區域成都市和最低得分區域豐都縣的協調度相差0.75,低于2005年的協調度極值差(0.83)。
運用Jenks自然斷裂法將城鎮化協調度進行分級。其中,處于基本協調區的區域數量由2005年的11個降至2014年的9個;處于輕度失調區的數量由2005年的8個增至2014年的10個;處于優質協調區、良好協調區、中度失調區的研究單元10年間沒有數量的變化,分別為2、6、9個。2005年基本協調區研究單元所占比重最高,為30.56%,2014年城市群中處于輕度失調區的研究單元所占比重最高,為27.78%。

圖2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綜合水平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圖3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發展協調度Fig.3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2.3 城鎮化發展協調度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2.3.1 總體格局。利用ArcGIS.3軟件計算Moran’sI與GeneralG,分析整體空間自相關程度。表2顯示,2005年Moran’sI值為正,并且達到了0.27,說明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度相關性較高,高值和低值集聚程度高,呈現強集聚分布;2014年Moran’sI仍然為正,但比2005年下降了0.11,表明城鎮化協調度仍然處于較強的集聚分布狀態,但集聚程度在下降。
2005和2004年全局G統計指標的觀測值都為0.03,檢驗顯著,說明檢測區高值和低值的集聚現象較為顯著。G值沒有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2005年以來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度的總體格局熱點區在空間上沒有明顯的演化和遷移現象,城市群城鎮化協調度的區域差距依然存在。
表2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的Moran’sI和GeneralG
Table 2 Estimation of Moran’sIand GeneralGfor the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年份YearMoran’sIE(I)Z(I)G(d)Z(d)20050.27-0.02862.840.032.3720140.16-0.02861.800.031.81
2.3.2 熱點區域演化。Moran’s I值能夠判斷出現象在空間上的整體分布情況,但難以探測出聚集的位置所在及區域相關的程度[30]。因此,為了進一步研究城鎮化協調度演化狀況,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其內部集聚熱點區域的變化情況,運用Getis-WOrdGi*公式,計算2005和2014年的Gi*,利用Jenks自然斷裂點法將其由高到低分成4 類(圖4),分析城鎮化發展協調度的熱點區演化特征。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度熱點區存在明顯的空間分異,成都市及其南北地區,重慶(主城區)及其以南地區成為最具有活力的熱點集聚區,渝東及渝東南始終為冷點的低值簇;不同類型區的數量發生一定的變化,熱點區的比重由2005年的16.67%增加到2014年的38.89%,其中綿陽市、瀘州市、江津區、永川區、大足區、銅梁區、合川區、璧山區成為新增熱點區域,冷點區比重由2005年的11.11%增加到2014年的13.89%,其中涪陵區成為新增冷點區域,內江市、自貢市、潼南區、榮昌縣提升為次熱點區;未發生變化的熱點區包括成都市、重慶(主城區)、德陽市、眉山市,未發生變化的冷點區包括墊江縣、忠縣、豐都縣、黔江區,冷點區城鎮化協調發展水平相對滯后。

圖4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發展協調度的熱點演化Fig.4 Evolvement of hotspot for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2.4 城鎮化協調的障礙度測算 利用公式(12)、(13),計算城鎮化各子系統指數的標準化值與權重,測算單項指標和子系統障礙度。
單項指標障礙度出現小幅提升,變化的平均值為1.57%。2005年阻礙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水平提升的前5項指標是萬人大學生數(28.89%)、非農人口規模(20.72%)、建成區面積(15.40%)、非農產業從業人員比重(7.01)、萬人移動電話(4.90%),除土地、社會城鎮化各占一項外,其余均為人口城鎮化指標。2014年前5項障礙指標是非農人口規模(23.10%)、萬人大學生(21.75%)、建成區面積(16.16%)、人均教育經費(5.54%)、萬人公共汽車(5.11%),人口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成為主要障礙因子。2005—2014年,萬人大學生、非農產業就業人員比重、萬人移動電話數、人均城市道路面積、單位GDP能耗、職工平均工資、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處理率這8個指標對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的障礙作用有所減弱,其余11個指標的障礙作用增強。
2005年子系統障礙度排序依次為人口城鎮化、生態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社會城鎮化,2014年的排序依次為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生態城鎮化。其中,人口城鎮化和生態城鎮化障礙度分別由2005年的59.13%、38.64%降至2014年53.14%和22.57%,土地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分別由2005年的22.41%、11.43%、31.62%增至2014年22.99%、16.92%、46.95%。從空間分異上看,人口城鎮化障礙度的空間分異最為明顯,2005和2014年標準差分別為0.044、0.038,2個年份的障礙度最高區域依次為成都市(68.83%)、璧山區(61.09%),最低區域始終為永川區,障礙度依次為49.23%、46.42%;土地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生態城鎮化障礙度的空間分異次之,2個年份的障礙度標準差均值分別為0.026、0.024、0.019;經濟城鎮化對城鎮化協調發展的障礙作用空間相對均衡,2005和2014年障礙度標準差分別為0.008、0.013,障礙度最高區域分別為南充市和成都市,最低區域分別為重慶(主城區)和涪陵區。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綜合水平整體不高,增長和分布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綜合水平的均值和標準差隨時間增大,各區域間城鎮化綜合水平差異顯著,其取值為0.096~0.832,2005年以來區域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重慶(主城區)、成都兩大中心城市及周邊的永川區和綿陽市,而城鎮化綜合水平較低的區域主要分布在云陽、豐都、潼南等地區;城鎮化子系統的發展在空間上呈現非均衡性特征,人口城鎮化分異程度始終最高但空間分異不斷縮小,社會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的空間分異逐漸增大,標準差由0.031、0.020增至0.039、0.022,土地城鎮化和生態城鎮化的空間分異不斷縮小,標準差分別由2005年的0.041、0.015降至2014年的0.039、0.011。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度總體呈現遞增態勢,空間分異特征較明顯但不斷縮小。高協調度地區集中在成都、重慶(主城區)2大核心區及其周邊,重慶(主城區)和成都市分別為2個年份的最高協調區域,重慶東部的豐都縣、云陽縣城鎮化協調度較低;2005年基本協調區域所占比重最高(30.56%),2014年處于輕度失調區的研究單元所占比重最高(27.78%)。
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度相似地區在空間上呈現強集聚狀態,成都市及其南北地區,重慶(主城區)及其以南地區是城鎮化協調的熱點,渝東及渝東南始終為冷點區域,熱點區比重不斷增加,冷點區比重逐漸增加,成都市、重慶(主城區)、德陽市和眉山市成為沒有發生變化的熱點區,墊江縣、忠縣、豐都縣和黔江區是沒有發生變化的冷點區。
單項指標對成渝城市群城鎮化協調發展的障礙度有小幅提升,2005 年前5項障礙指標依次是萬人大學生數、非農人口規模、建成區面積、非農產業從業人員比重、萬人移動電話,2014 年前5 項障礙指標依次是非農人口規模、萬人大學生、建成區面積、人均教育經費、萬人公共汽車;2005年子系統對城鎮化協調發展的障礙度由大到小依次為人口城鎮化、生態城鎮化、經濟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社會城鎮化,2014年排序為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生態城鎮化,2年中人口城鎮化障礙度的空間分異最為明顯。
3.2 討論 成渝城市群應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有序引導人口向城鎮集中,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轉換和就業結構的較快轉變,提高區域創造財富的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引進高技術和人才改造升級傳統工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與核心競爭力,加快軟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從而提升經濟和社會城鎮化水平,遏制二者空間分異的進一步擴大;繼續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保護基本農田,抑制土地城鎮化的過快發展,將生態建設納入城鎮化全過程,全方位提升城鎮化發展水平。
城鎮化發展高協調度地區,產業基礎較好,交通便利,現有產業主要以高新技術和第三產業服務經濟為主,都市核心產業競爭力得到了極大提升,制約該區城鎮化協調發展水平的因素是土地城鎮化水平,因此應充分挖掘存量建設用地的潛力,提高城鎮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協調水平較低地區,經濟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城鎮用地的擴張支撐,城鎮用地的節約集約利用水平偏低,土地利用水平較低導致城鎮化協調狀況持續低迷。這些地區應重點關注土地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在控制城鎮無序擴張的同時注重提高城鎮土地利用效率,實現城鎮用地節約集約利用,深入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城鎮化發展協調度的研究是復雜的、系統的和持續發展的,該研究從人口、經濟、土地、社會和生態5個方面建立城鎮化綜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基于熵值法、協調度模型、探索性空間數據、障礙度模型對研究區2005和2014年城鎮化發展協調度空間格局進行實證研究,揭示了城鎮化進程中系統內部的協調關系,為城市群城鎮化協調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對改善城鎮化發展狀況及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 陳明星.城市化領域的研究進展和科學問題[J].地理研究,2015,34(4):614-630.
[2] 陸大道.我國的城鎮化進程與空間擴張[J].城市規劃學刊,2007(4):14-17.
[3] XIAO B H,NICHOLAS C S S.Does economic growth affect urbanization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gres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5(36):62-71.
[4] HENDERSON V.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so-what ques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8(1):47-71.
[5] 王艷飛,劉彥隨,李裕瑞.環渤海地區城鎮化與農村協調發展的時空特征[J].地理研究,2015,34(1):122-130.
[6] 李國平.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關系分析與評估[J].地域研究與開發,2008,27(5):6-11.
[7] 李昕,文婧,林堅.土地城鎮化及相關問題研究綜述[J].地理科學進展,2012,31(8):1042-1049.
[8] 魯德銀.土地城鎮化過程的中國路徑選擇及優化研究[J].農業經濟,2010(5):41-42.
[9] 周一星,史育龍.解決我國城鄉劃分和城鎮人口統計的新思路[J].統計研究,1993,10(2):55-61.
[10] 秦佳,李建民.中國人口城鎮化的空間差異與影響因素[J].人口研究,2013,37(2):25-40.
[11] 陳鳳桂,張虹鷗,吳旗韜,等.我國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研究[J].人文地理,2010,115(5):53-58.
[12] 曹文莉,張小林,潘義勇,等.發達地區人口、土地與經濟城鎮化協調發展度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2,22(2):141-146.
[13] 孫平軍,丁四保,修春亮,等.東北地區“人口-經濟-空間”城市化協調性研究[J].地理科學,2012,32(4):450-457.
[14] 陳春.健康城鎮化發展研究[J].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2008(4):7-9.
[15] 陳明星,陸大道,張華.中國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度及其動力因子分析[J].地理學報,2009,64(4):387-398.
[16] 楊剩富,胡守庚,葉菁,等.中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協調度時空變化及形成機制[J].經濟地理,2014,34(11):23-29.
[17] 李鑫,李興校,歐名豪.江蘇省城鎮化發展協調度評價與地區差異分析[J].人文地理,2012(3):50-54.
[18] 雒海潮,李國梁.河南省城鎮化協調發展評價與空間差異分析[J].地理科學,2015,35(6):749-755.
[19] 汪志,焦華富,郇恒飛.皖江城市帶縣域經濟發展差異演變特征分析[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11,27(1):53-58.
[20] 李雪梅,張小雷,杜宏茹.新疆塔河流域城鎮化空間格局演變及驅動因素[J].地理研究,2011,30(2):348-358.
[21] 鐘海燕.成渝城市群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
[22] 張濤,武超茹,孫媛媛,等.成渝城市群新型城鎮化水平測度與發展研究[J].決策咨詢,2016(1):1-7,23.
[23] 程前昌.成渝城市群的生長發育與空間演化[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5.
[24] 單連龍.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成渝城市群綜合交通發展構架[J].綜合運輸,2016(6):40-43,48.
[25] 國務院.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 [EB/OL].(2016-03-30)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605/t20160504_800779.html.2016.
[26] 崔照忠.區域生態城鎮化發展研究:以山東省青州市為例[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4.
[27] ANSE L.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LISA[J].Geographical ana1ysis,1995,27(2):93-115.
[28] GETIS A,ORD J K.The analysis of spatia1 association by use of distance statistics[J].Geographica1 Analysis,1992,24(3):189-206.
[29] 周曉飛,雷國平,徐珊.城市土地利用績效評價及障礙度診斷:以哈爾濱市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2,19(2):126-130.
[30] 李春華,張小雷,王薇.新疆城市化過程特征與評價[J].干旱區地理,2003,26(4):396-401.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LI Jian-bo1, LI Chun-kai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00; 2.Chongqing Tourist School,Chongqing 400084)
New-type urbanization is the coordinate of population, land,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subsystem of urbanization. Using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the disorder degree model, discriminant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coordin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mong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not too high,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creases with time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ubsystem was non-equilibrium.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demographic urbanizationis was always highest but shrinking,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economic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urbanization increase gradually,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land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urbani-zation keeps reducing.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ization in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keeps increasing, spatial variation was obvious but shrinking. The similar region of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shows a strong aggregation state. The hotspots of urbanization co-ordination were centralized in the regions of Chengdu, Deyang, Meishan, Nanchuan and Qijiang, and the coldspots were centralized in the regions of eastern Chongqing and southeast Chongqing. The hotspot and coldspot regions had been increased graduall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New-type urbanization; ESDA; Obstacle degree;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6XSH001)。
李劍波(1985- ),男,四川瀘定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市與區域規劃。
2016-09-26
S-9
A
0517-6611(2016)33-02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