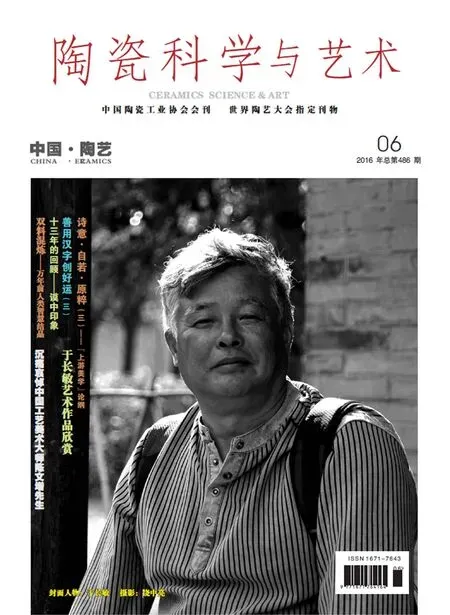略論唐代長沙窯彩繪蓮花紋飾的藝術特征和歷史文化因素
劉泓藝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
略論唐代長沙窯彩繪蓮花紋飾的藝術特征和歷史文化因素
劉泓藝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
長沙窯彩繪蓮花紋飾以自由的創作心態和對自然生活的體悟,在深受以線造型繪畫傳統的影響和花鳥畫至唐代獨立分科的背景下,吸收佛教因素,創造性地將寫意風格蓮花紋飾融入瓷器裝飾,發展出迥異于唐代工筆花鳥畫法的新畫風,開創了寫意畫融入瓷器之先河。
蓮花紋飾;陶瓷寫意繪畫;以線造型;花鳥畫獨立分科;佛教因素
1.引言
長沙窯創燒于初唐,興盛于中晚唐。作為唐代彩瓷的集大成者,是彩瓷發展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長沙窯彩瓷采用褐綠彩在瓷坯體上描繪圖案,然后罩釉,形成釉下彩。釉下彩中有一批是寫字、繪圖和印紋的產品。其中又以繪圖的器物數量最多,約占總數的16.6%,這種[1]直接在瓷胎上的繪畫,繼承和發揚了中國繪畫以線造型的傳統,追求風格的個性和自由化,創造性地開辟了寫意繪畫裝飾瓷器之先河,其簡括抽象的造型,恣意流暢的筆法,靈動和諧的構圖,幻化成具有濃厚時代氣息和世俗審美趣味的大唐藝術新篇章。
2.唐代長沙窯蓮花紋飾的藝術特征
長沙窯彩繪裝飾主要分為文字裝飾、圖案裝飾。彩繪蓮花紋飾則歸于圖案裝飾的花鳥圖裝飾中。
蓮花紋飾可以根據花與葉、構圖、畫法、蓮花數量四方面劃分。以花與葉組合情況為依據,可分為蓮花與蓮葉組合型、純蓮葉型;以構圖為依據,可分為中心對稱型、軸對稱型、獨立單枝蓮花型;以畫法為依據,可分為點彩型、線描型;以蓮花數量為依據,可分為單枝蓮、多枝蓮。在一幅蓮花紋飾中,也時常出現以上兩種或三種類型并置的情況。不同類型的表現因素相輔相成,豐富了圖像的藝術表現語匯的構成,增強了圖案裝飾效果。主要表現在:
2.1 構圖多變靈動

圖1 《長沙窯褐紅黑彩蓮花紋碟》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蓮花紋碟》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蓮花紋壺》
長沙窯蓮花紋飾的構圖多采用中心對稱形式(圖1左)、軸對稱形式(圖1中)和獨立蓮花式(圖1右)。三種構圖形式,均表現了動態平衡。不似后世瓷業一些按照粉本繪制的裝飾,長沙窯蓮花紋飾屬于一定程度的創作繪制,蓮花的花瓣尺寸沒有完全相同的,位置各有差異,卻不影響整體布局的呈現。
《長沙窯撇口褐紅黑彩繪荷花紋執壺》(圖2左)為一枝五瓣荷花,左右兩側呈軸對稱分布著兩枝荷葉,枝干富于自然韌性。同時包含了蓮花蓮葉并置、軸對稱和線描的要素。荷花荷葉的枝干長短粗細及彎曲程度不同,呈現出自由生長的情態。《長沙窯青釉褐黑彩蓮葉紋壺》(圖2右)則體現出不拘一格的構圖創意。放逸的寥寥數筆,蓮花蓮葉在陽光照射下稍顯倦怠。較周敦頤筆下的蓮花“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這枝蓮花并不羞怯于露出平易近人的一面,清新而親和。
長沙窯蓮花紋飾善用多種構圖形式,表現出手工繪制的隨性感和微妙動勢,調和出圓融生動的視覺效果。

圖2 長沙窯撇口褐紅黑彩繪荷花紋執壺 長沙窯青釉褐黑彩蓮葉紋壺
2.2 線條俊逸寫意
線條是中國繪畫藝術中極具表現力的語匯。工致謹嚴、圓勁暢快,富于微彈婉轉的韻律的線條,于長沙窯蓮花圖中亦有直觀生動的體現。
《長沙窯撇口褐紅黑彩繪荷花紋執壺》(圖2左)中荷花花瓣以較粗的綠彩線條描繪,花瓣尖端處有意識地拓寬了線條,加深了用色。兩側荷葉邊緣和枝干又以色彩稍淡于花瓣和略細的線條表現,卻又比荷葉紋路的用線厚重。線條的粗細,荷葉次于荷花,荷葉紋路再次之。用色濃淡荷葉次于荷花,枝干次于荷葉,荷葉紋路再次之。這些粗細濃淡變化,巧妙地與各物象在蓮花紋飾中的視覺地位相呼應。白描意味的線條,看似簡括抽象,實則不僅是傳統的造型語言,更是運力變化、情感起伏的藝術外化表現。《青釉褐綠彩連珠紋大罐》(圖3),具有濃烈現代抽象裝飾意味和視覺張力。構成圖案的依次首尾相連的色點為點彩連珠紋,是從金銀器工藝中借鑒而來。點彩連珠紋呈現以線為主的視覺效果,在以線造型的中國繪畫傳統中,又賦予線條新的構成形式。其罐肩部置雙耳,口沿部飾有釉下褐綠點彩兩圈,下部繪有蓮花型連珠紋四組。有意無意地弱化了單個色點的邊緣,產生暈染效果。將點彩畫法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彩繪以線條為主的造型表現手段。

圖3 《青釉褐綠彩連珠紋大罐》
3.唐代長沙窯彩繪蓮花圖的歷史文化因素
3.1 繼承以線造型的傳統
以線條為主要造型手段是中國傳統繪畫的傳統。自原始社會至夏商周,以線條造型的繪畫語言漸趨成熟。長沙出土的戰國楚國《人物御龍帛畫》和《龍鳳仕女圖》正式確立了中國傳統繪畫以線造型的主體地位。至隋唐、五代時期,畫家對線條作為獨立繪畫語匯進行了更進一步的規律性自覺性探索,閻立本用筆富于概括性,線條簡括而不簡單。吳道子在線條上創新,其筆法帶有寫意因素,實際上開啟了寫意人物畫之先河。敦煌壁畫《維摩經變相》局部《維摩詰圖》中線描筆法明顯吸收了吳道子畫法的特點,足以表明吳道子藝術的巨大影響力。
長沙窯陶瓷畫工身處閻立本、吳道子畫風廣泛影響的唐代,潛移默化的影響不言而喻。長沙窯各類彩繪圖就繼承且發揚了這樣傳統,“把楚藝術的造型意識和審美追求,把古代楚人的生活理想從又一個側面生動地展現出來。”[2]畫工們重視線條的造型功能,更注重線條對情感個性的表達作用,將其轉化為“有意味的形式”,用線流轉和概括,構成主體裝飾。長沙窯開創了海上陶瓷之路,產品主要銷往中東及亞洲其他地區,大批量產品等待繪制,畫師們更多地選擇以線為主要造型手段,從而提高繪制速度和數量的行為,無疑是對傳統以線造型、探求線條自身趣味和審美的具體體現。
3.2 花鳥畫的獨立分科
中華民族素來對草木情有獨鐘,自稱為華夏,“華”者“花”也。[3]追溯至原始社會時期,花鳥草木的題材較為普遍。在原始陶器青銅器上,均可見花鳥等動植物的題材。秦漢至初唐,繪畫中也時見植物花枝蔓葉為紋樣的圖案,但多是其他主題(如人物、山水)的附屬。
至唐代,社會的物質財富的積累達到中國歷史新高度,思想文化開放發展,兼收并蓄。張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和其他藝術創作理論的提出,為花鳥畫獨立分科和繼續發展營造了有利的文化氛圍。“師造化”于藝術創作有其重要性,“得心源”同樣不可或缺,兩者相輔相成,揭示了繪畫須調和客觀物象的真實性和主觀情感的能動性的創作規律。這些,恰與唐代花鳥畫的創作旨趣是一脈相通的。
中國花鳥畫到了唐代,已在傳統基礎上獲得更大的發展,同時對水墨畫視覺藝術形式創新性借鑒吸收,逐漸厘分、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畫科,這為長沙窯花彩繪蓮花紋飾的產生,提供了歷史的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因此,長沙窯彩繪中蓮花圖以獨立自覺的面貌成為裝飾彩繪的主體,是水到渠成的。

圖4 《青釉褐綠彩繪花草紋碗1》 《青釉褐綠彩繪花草紋碗2》
3.3 寫意畫融入瓷器裝飾
無論《道德經》“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以及“道之惟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還是《莊子·外物》中“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中的“意”,都是通過“象”體悟天地之道的過程和結果。以入世為本的儒家,也有“素以為絢兮”及追求“圣而不可知之為什”的境界的要求。到魏晉時期,王弼從意象言三者的辯證角度,糅合儒道而為新觀念。從更為根本更為堅實的哲學角度,奠定了中國古代繪畫重神輕形的美學基礎。[4]

圖5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蓮花紋執壺1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蓮花紋執壺2
真正意義上的寫意畫最早出現于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論畫六法》中寫道“以氣韻求其畫,則形式在其間矣。……夫物象必在于形式,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在具體的藝術創作中,表現為抒發胸中意趣,重神輕形的創作行為。長沙窯瓷上彩繪的蓮花紋飾中許多都是畫師“中得心源”,依照自己的心意構圖描繪,并非強調逼真的工筆細描,卻充分表達了一片心境。因為寫意,故注重動勢的表現。線條首濃尾淡的過渡,以放射狀線條表現蓮蓬的疏密變化,可從中體會筆尖運動的緩急頓挫,以及思緒的起伏。對比《青釉褐綠彩繪花草紋碗1》(圖4左)和《青釉褐綠彩繪花草紋碗2》(圖4右),兩者在花瓣造型、線條層次等方面基本一致,但花瓣數量前者為五瓣,而后者為四瓣。且在花蕊上又輔以一褐彩圓圈點綴,這些都是為畫師的審美意識和畫面整體而服務的。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蓮花紋執壺1》(圖5左)基本遵循了軸對稱的形式,兩花蕾和四蓮葉呈對稱分布,同時因下方地勢的從左至右的減緩,表現出生長高度的變化,還原了蓮花蓮葉自然生長環境和其他生物。蓮瓣欲展未展的恬適,枝干將彎未彎的韌性。數只飛蟲點綴空隙,下方以流暢的線條表現水面波紋,一派適意自由的詩意氛圍。《長沙窯青釉綠彩蓮花紋壺》(圖5右)的構圖則更為隨性自由。一朵蓮花在蓮葉掩映中綻放,蓮花蓮葉的枝干在整體向右的伸展趨勢中,又稍往右延伸,畫面饒有意趣。較《青釉褐綠彩蓮花紋執壺1》(圖5左)不同的是,沒有繪制地面和水波。對比之下,前者更注重呈現自然環境中蓮花的生長,后者更注重蓮花蓮葉作為裝飾主體的構建。
《長沙窯蓮花紋瓷枕片》(圖6)描繪自由伸展狀態的兩花蕾一蓮葉,并未采用蓮花紋飾(圖像)中常見的蓮花蓮葉對稱分布構圖,而是兩花蕾稍聚攏分布于右側,一片蓮葉分布于左側。長沙窯陶瓷畫工用寥寥數筆,以類似流云紋的漩渦表現水流湍急,如倪瓚所言“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動靜結合,生命力畢現。
由此可見,在很大程度上長沙窯裝飾紋飾不是機械化的簡單復制式繪制,而是一定程度上的創作型繪畫。寫意風格蓮花紋飾出現于長沙窯瓷器的主要原因,一是陶瓷畫工們在繪制中擁有一定的自由發揮空間,二是畫工們已經具備一定的自覺審美意識。“以及其隨性率意的表現,有別于宮廷院體精工嚴謹的‘富貴’氣而另有‘野逸’氣息的彌漫。”[5]“在目前唐代繪畫缺少‘逸品’繪畫實物作品的情況下,長沙窯彩繪蓮花紋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表明狀態的意義。”[6]“古長沙窯人將瓷器作為一個觀照生命的平臺,進行個性的極度釋放與抒發。”[7]
3.4 佛教因素的影響
蓮花被寓為釋迦牟尼的誕生是神圣與高潔的。佛教藝術中的蓮花形象隨著佛教傳入,極大地充實了中國繪畫的題材,經由中國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又被中國式的改造創新。在被賦予佛教象征意義的同時,又在發展中減弱了宗教色彩。無論是佛教造像或是佛教壁畫,甚至是佛教藝術中的蓮花形象,發展至唐代均表現出愈加明顯的世俗化傾向。

圖6 長沙窯蓮花紋瓷枕片
佛教在唐代社會作為社會整合力量是跨越階層的[8],其思想信仰在民間和其他階層的深入,與社會習俗和市民文化融合,為蓮花紋飾大量躍然于長沙窯瓷坯作了前期準備。且蓮花在中華傳統民俗文化中本身就被賦予許多吉祥寓意。蓮花作為佛教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于陶瓷、絲織等裝飾工藝中。在唐代,蓮花紋樣表現世俗思想的形式多樣,主要為兩類:一類是反映富貴生活的寶相蓮花,通稱蓮花形“寶相花”,另一類則是反映夫妻恩愛的蓮花鴛鴦。[9]長沙窯具有野逸抽象風格的彩繪蓮花紋飾是迥異于以上類別的一種風格。
長沙窯陶瓷畫工們置身佛教文化的浸潤,這種影響具體體現在長沙窯的器物上,是將前代蓮花形象加以抽象提煉,增添了世俗和野逸興味,形成了近似白描的蓮花簡括風格。
3.5 承上啟下的長沙窯彩繪蓮花紋飾
自唐回溯,長沙窯蓮花紋飾的造型因素可從春秋中期所制的青銅盛水或盛酒器《蓮鶴方壺》中找到源頭,《蓮鶴方壺》也有相似的蓮花瓣意象和雙層花瓣構造,卻呈現出迥異的面貌和審美趣味。前者有禮教之莊重神秘氣氛,后者則具有寫意抽象的清新世俗氣息。長沙窯蓮花紋飾的造型因素汲取了前代青銅器等器物中蓮花的造型因素,表現為對蓮花瓣近似水滴形造型,重視蓮花瓣作為裝飾主體的作用,以及注重蓮花裝飾整體輪廓線的塑造。
唐代長沙窯蓮花圖對產生于唐代,成熟于元代的青花瓷以及元青花蓮花紋裝飾和民間工藝裝飾束蓮紋等的造型因素也有影響。《青花鴛鴦荷花(“滿池嬌”)紋花口盤》內外壁均繪纏枝蓮紋,莖上均結有六朵盛開的蓮花。蓮瓣的造型和長沙窯彩繪中蓮瓣的造型頗似,為近似水滴形。每片蓮瓣大小和卷曲程度不盡相似,展現了自然伸展的狀態,與長沙窯彩繪中的蓮瓣是相貫通的。每片蓮瓣又在敷色基礎上,以不多的較濃筆觸表現肌理感,無疑是對前朝抽象寫意蓮花的創新印證。
唐代藝術中的世俗化表現是一個整體性的較為明顯的趨勢。唐代長沙窯的蓮花紋飾亦展現出世俗野逸化的面貌,在選取花草類等生活化題材并對其反復描繪,減弱了蓮花紋的宗教色彩。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長沙窯蓮花紋飾與宮廷院體工筆花鳥畫形成兩種互補的藝術形態。昭示了
[1] 覃小惕,《長沙窯鑒藏面面觀》,《收藏》[J],2010-02,第206期,49
[2] 皮道堅,《楚美術史》[M],2012-07,湖北,湖北美術出版社,6
[3] 陳祥綬,《隋唐繪畫史》[M],2001-8,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86
[4] 林木,《寫意畫溯源》,《美術向導》[J],2005,第1期,14
[5] 孔六慶,《論唐代長沙窯的歷史地位與藝術意義》[J],《陶瓷藝術》,南京藝術學院,58
[6] 孔六慶,《論唐代長沙窯的歷史地位與藝術意義》[J],《陶瓷藝術》,南京藝術學院,62
[7] 王奮英,《大唐意象--古長沙窯瓷上意筆畫藝術》[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07,99
[8] 王奮英,《大唐意象--古長沙窯瓷上意筆畫藝術》[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07,97
[9] 王莉,《唐宋陶瓷蓮花紋的比較研究》[D],景德鎮陶瓷學院,201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