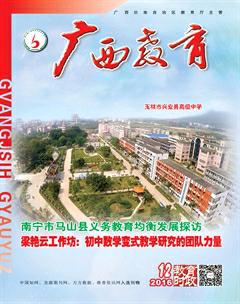“藍瘦香菇”為哪般
文鋒
幾乎一夜之間,“藍瘦香菇”紅了。打開網(wǎng)絡(luò)、微博、微信朋友圈,幾乎人人都在說“藍瘦香菇”。“今天上班遲到了,藍瘦,香菇”“看到自己的工資條后,藍瘦,香菇”“天氣轉(zhuǎn)涼感冒了,藍瘦,香菇”……類似的表達,一時讓人摸不著頭腦。
究竟什么是“藍瘦香菇”?如何看待“藍瘦香菇”這類網(wǎng)絡(luò)熱詞呢?請看本期文化視野。
為何會“藍瘦香菇”
“藍瘦,香菇,本來今顛高高興興,泥為什莫要說射種話?藍瘦,香菇在這里。第一翅為一個女孩屎射么香菇,藍瘦。泥為什莫要說射種話,丟我一個人在射里,香菇,藍瘦在這里,香菇。”
這段話,是南寧市一個叫韋勇的青年男子在自己錄的一段視頻中說的。據(jù)悉,他是因為和女朋友吵架,女朋友負氣離去,他才錄了一小段視頻表達自己的感受,并上傳到QQ空間,沒想到就這樣火了起來。
以上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翻譯成普通話其實就是:“難受,想哭,本來今天高高興興,你為什么要說這種話?難受,想哭在這里。第一次為一個女孩子這么想哭,難受。你為什么要說這種話,丟我一個人在這里,想哭,難受在這里,想哭。”
翻譯出來后,多數(shù)人都明白了,“藍瘦香菇”就是“難受想哭”的意思。這是因為南寧市的這個男青年說普通話不標準,夾帶了壯語的發(fā)音,從而導(dǎo)致表達不夠清晰。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夾壯”。這種現(xiàn)象多見于南寧、河池、百色等說壯語的地方。
為什么會出現(xiàn)說普通話“夾壯”的現(xiàn)象?這是因為壯語里的發(fā)音沒有翹舌音和送氣音,常說壯語的人,舌頭往往是僵直的,如果長時間不進行糾正,就很難發(fā)準翹舌音和送氣音。例如:把“z,zh,s,sh,ch,c”全部讀成“sh”;把“g”和“k”全部讀成“g”;把“q”全部讀成“j”;把“d”和“t”全部讀成“d”;甚至“hu”和“wu”不分,讀成“wu”。常見的例子有:把“梔子花”讀成“獅屎洼”,把“這里”讀成“射里”,把“風口”讀成“瘋狗”,把“江湖”讀成“江無”,把“有錢”讀成“有閑”,把“難受想哭”讀成“藍瘦香菇”。
其實,類似這種在普通話中夾帶方言發(fā)音(注意:是方言發(fā)音,而不是方言,本文只討論前者)的現(xiàn)象,在全國各地并不鮮見。例如:福建一帶講閩南話的人, “f”與“h”不分,把“福建”念成“糊建”;溫州人“ei”與“ui”不分,把“飛機”念成“灰機”;廣東人“u”與“i”不分、“zh”與“j”不分,把“不是這樣”念成“不素借樣”;北京一帶的人說普通話應(yīng)該是比較準確的,但容易發(fā)連音,比如把“中央電視臺”讀成“莊墊兒臺”。
綜上可見,“藍瘦香菇”的出現(xiàn),與說普通話時夾帶了“鄉(xiāng)音”有關(guān)。從語言發(fā)音的角度來說,該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過它能走紅,還是因為別的因素在起作用。
偏偏“藍瘦香菇”紅了
作為網(wǎng)絡(luò)熱詞,“藍瘦香菇”的走紅,首先與信息時代的傳播方式有很大關(guān)系。梳理媒體報道,可以看出其走紅的大致過程:先是南寧一位男青年在QQ空間發(fā)布視頻,接著在百度貼吧引起討論,但傳播范圍有限。轉(zhuǎn)折點出現(xiàn)在網(wǎng)友“當時我就震驚了”對該段視頻的轉(zhuǎn)發(fā),該網(wǎng)友擁有兩千多萬“粉絲”,微博轉(zhuǎn)發(fā)后獲得一千多萬次點贊和跟帖評論。不久演員林更新和穎兒轉(zhuǎn)發(fā),將該詞的熱度推向新高。隨后,多個主流媒體報道陸續(xù)推出該詞,微信朋友圈也出現(xiàn)刷屏,“藍瘦香菇”成為網(wǎng)絡(luò)熱詞。
“藍瘦香菇”的走紅,信息時代的極速傳播是其“技術(shù)原因”,沒有信息技術(shù)作支撐,任何網(wǎng)絡(luò)熱詞都熱不起來。除此之外,像“藍瘦香菇”這樣的網(wǎng)絡(luò)詞匯能夠走紅,更多還是多種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一是“藍瘦香菇”本身吸引眼球。失戀(或者說是與女友吵架)是一件讓人不愉快甚至痛苦的事情,但一個男青年用“夾壯”的普通話發(fā)視頻求安慰,讓人聽了云里霧里,需要配上翻譯才能明白其意思。一件原本略顯痛苦而嚴肅的事情,就這樣被置于特定的傳播情境中,逐漸異化為一件好玩、搞笑的事情,從而引發(fā)了人們的關(guān)注。
二是大眾心理因素的作用。在信息時代,人們特有的獵奇心理和從眾心理,驅(qū)使更多人去跟風關(guān)注一些新鮮事物——看到別人轉(zhuǎn)發(fā)某個熱詞自己也想轉(zhuǎn)發(fā),用上了某些新鮮詞匯表明自己時尚、與時俱進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網(wǎng)絡(luò)熱詞。
三是契合了時下的一種娛樂至上的消費文化心理。當前社會正處于復(fù)雜的轉(zhuǎn)型時期,傳統(tǒng)正在崩潰,新的規(guī)則又未建立起來,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精神生活處于一種轉(zhuǎn)型的壓力之下,于是追求好玩、搞笑都能成為時尚,導(dǎo)致嚴肅變?yōu)榛顾状笮衅涞溃瑦焊愦笫軞g迎,于是才出現(xiàn)了諸多不夠規(guī)范、不夠健康的網(wǎng)絡(luò)流行語、“網(wǎng)紅”等。
網(wǎng)絡(luò)熱詞是當今社會與文化的一個縮影、一面鏡子。與其說網(wǎng)絡(luò)熱詞是人心浮躁的體現(xiàn),不如說它是時代精神文化空白的填充。許多網(wǎng)絡(luò)流行語、網(wǎng)絡(luò)俚語,已經(jīng)成為精神緊張的現(xiàn)代生活中人們宣泄情緒、自我解壓的一種方式。“詞媒體”代表的不僅是人們價值觀的取向,還代表著一種精神文化的整體走向,體現(xiàn)了人們情感歸屬的需要。當社會面臨精神危機、信仰缺失時,個人的某種情緒就會成為社會的共同心理。很多詞能夠快速地引發(fā)集體性、社會性的共鳴,就在于它契合了這種群體性的心理,這就是“藍瘦香菇”能夠走紅的深層原因。
如何看待“藍瘦香菇”
必須指出,“藍瘦香菇”帶有一定的歧視色彩,普通話說不標準畢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因此不建議過分使用該詞,尤其是在特定人群(說話“夾壯”者)面前,更應(yīng)謹慎使用,不應(yīng)嘲笑他人的發(fā)音缺陷。從這個角度來說,政府、學校應(yīng)進一步加大普通話的推廣、教學力度,讓人們都能說準確的普通話,減少交流障礙。
事實上,人們過分關(guān)注“藍瘦香菇”之類的網(wǎng)絡(luò)熱詞,反映了一種不健康的低級趣味。“藍瘦香菇”本身是在別人不愉快、痛苦,加上普通話發(fā)音不標準的情況下產(chǎn)生的,但大家不去關(guān)心、照顧別人的心理感受,反而抓住其中的缺陷進行放大、惡搞、擴散,這其實是在消費別人的痛苦和缺陷,是不值得提倡的。
“藍瘦香菇”的走紅,說明當前的社會文化生態(tài)不容樂觀,把低俗當有趣,把淺薄當文化,無知無畏,娛樂至上。針對這類現(xiàn)象,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梁衡曾撰文分析:“人除了物質(zhì)需求之外,其精神文化需求有六個檔次,由低到高分別為刺激、休閑、信息、知識、思想、審美。搞笑屬于刺激這一檔,是最低檔。刺激是一個巨大的精神需求黑洞,它甚至超過了其他五個檔次……如果不加限制,刺激性的精神產(chǎn)品就有無邊的可怕的市場。”這絕非危言聳聽,任由“這一市場”無限擴大,最終破壞乃至消解的可能就是整個社會的正常文化生態(tài)。
“藍瘦香菇”走紅后,很快就“滲透”到了學校中。不少學生在說話、寫作文時,都盲目跟風用上了這一詞匯。對此,老師應(yīng)該進行必要的教育引導(dǎo),告訴學生要使用規(guī)范的語言,自覺抵制粗俗、不規(guī)范的網(wǎng)絡(luò)用語。
誠然,所謂“存在即合理”,對于網(wǎng)絡(luò)熱詞,不能一棍子都打死。網(wǎng)絡(luò)語言也承載著一定的思想,它們以新穎、簡潔,甚至帶點淘氣、戲謔與無奈的口吻一掃常規(guī)詞匯單調(diào)、呆板、嚴肅的詞風,代之以親昵、幽默,既可避免尷尬,又可協(xié)調(diào)氣氛。像“藍瘦香菇”這類具有輕松幽默特質(zhì)的網(wǎng)絡(luò)熱詞,在網(wǎng)絡(luò)交流、私下場合交流時,如果用得合適、得體,能起到促進交流的作用。
只是,網(wǎng)絡(luò)熱詞只能作為當前語言表達的一種補充。過度使用網(wǎng)絡(luò)流行語,容易使我們患上“語言貧乏癥”。有人曾對古人的表達和我們的網(wǎng)絡(luò)流行語做過一番對比:古人形容人漂亮可以用“玉樹臨風”“顧盼神飛”,我們只會說“高富帥”“白富美”;古人形容人難看可以用“東施效顰”“獐頭鼠目”,我們只會說“矮窮矬”“顏值低”;古人表達悲傷用“肝腸寸斷”,我們只會用“藍瘦香菇”……也許這種對比過于片面,但如果有一天我們張口閉口只會習慣性地說“高富帥”“矮窮矬”,會不會被自己表達的匱乏所驚到?
語言無論如何發(fā)展,都不應(yīng)以犧牲原有的優(yōu)秀成分為代價,如果不加選擇、不加引導(dǎo)地隨意使用網(wǎng)絡(luò)熱詞,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讓語言走向平庸和匱乏,結(jié)果將是得不償失。
(責編 周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