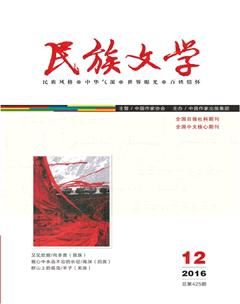彩云之南書華章
黃玲
一、文學成果與現狀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在本文的分析判斷僅以中國作協編選的《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品卷為基礎,不涉及長篇作品的創作。雖然不夠全面,但是從各卷中收入的三種文體來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和比較,還是能從一個側面說明問題。因為在各民族卷的編選過程中,編選者一定是盡可能地把本民族文學中最優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納入其中。
從科學的態度出發,我們應該看到并且充分肯定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①在書面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從“一無所有”到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里迅速成長,并建立起自己的作家隊伍,創作出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這是一項值得贊美的事業。小說、詩歌、散文三種基本文體,除了詩歌之外,其余兩種文體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所以學習的過程充滿艱辛,但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還培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學作者隊伍。
下面我將對8個民族取得的文學成績分別進行簡要述評,以期勾劃出一個基本的輪廓。
“阿昌族卷”收入6位作者的16個中短篇小說,大多發表于《民族文學》《邊疆文學》等省級以上刊物,題材以阿昌族地區的民族生活為主,時間從“文革”極“左”年代到當下的現實生活都有涉及。可喜的是還有一位女作者朗妹喊參與其中,收入了她的兩篇小說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經過三十多年的認真學習和努力實踐,阿昌族作家在小說藝術方面已經比較成熟,能熟練運用這一文體去表現現實生活,刻劃本民族的人物形象。詩歌和散文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優秀作品,羅漢、孫寶廷、曹先強等人在小說和散文方面都有突出表現。詩歌隊伍中有曹明強、孫家林、趙家福等人為阿昌族詩歌撐起一片天空。
值得一提的是阿昌族作家隊伍的梯隊已經基本形成,一批60后、70后的寫作者是這支隊伍的中堅力量,已經先后有五人的作品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他們可以視為阿昌族作家文學的領軍人物。此外,一些80后、90后的新生代寫作者也在迅速成長,他們為這個民族的書面文學注入了生機與活力。比如孫豪、趙興榮、梁昌吉、囊兆東、王文豪、李偉,他們在小說、詩歌、散文方面都有突出表現。他們的作品傳達了振興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情和自信。
“布朗族卷”小說部分收入4位作家的7篇作品,詩歌部分收入5位詩人的21首作品,散文則收入10位作家的作品41篇。客觀地分析,在這三種文體中,布朗族作家的散文優勢大于小說和詩歌。7篇小說中有兩篇取材民間文學,其余幾篇是對布朗族現實生活的表現。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巖香南的《南麗趕街》,比較及時地表現了布朗族人在商品經濟時代的思想和心理轉變。陶玉明的兩篇小說也對布朗族的民俗風情和一些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進行了思考與表現。
散文部分內容比較豐富,對布朗族的歷史文化、現實生活有比較全面生動的表現。文體意識也比較成熟,寫作者能比較好地把握散文的特點,把布朗族的生活從不同側面呈現給讀者。詩歌基本處于寫實的階段,還需要提升。另外,三種文體的作者基本都是由同一批人來承擔,沒有專門的寫作者出現,這也是布朗族書面文學面臨的一個困境。
作為人口最少的獨龍族,其作家隊伍的建立尤其不容易。雖然目前只有十余位寫作者出現,但是從人口比例上看,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進步。“獨龍族卷”中一共收入獨龍族作家創作的小說5篇,散文42篇,詩歌31首。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在獨龍族歷史上堪稱是一次文學的盛會,是對30多年文學成果的集中檢閱。編委會在“后記”中也以非常感慨的語氣說:“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對中國獨龍族文學創作水平的整體呈現,是建國以來獨龍族文學發展中的重大事件,是載入民族文學史冊的工程。”
小說方面,羅榮芬的貢獻是突出的。小說集子中收入的5篇小說中,她的作品就占了3篇,而且無論從題材內容還是從小說藝術的角度看,已經比較成熟。對獨龍族的現實生存和婦女生活都有獨特細致的表現。
散文部分相對要豐富一些,收入了16名作家的42篇作品,既有書寫獨龍族歷史文化和現實生活的一些篇章,也有涉及其他民族生活的作品,還有像陳雪芹的《只要一個人的午后》這種以書寫個體心靈世界為主的作品出現,體現了作家們對散文文體的熟練把握。詩歌隊伍相對要弱一些,但也出現了像巴偉東的《獨龍招魂曲》和曾學光的《雄鷹之夢》這樣比較大氣的作品。
迄今為止,獨龍族的作家隊伍雖然還比較薄弱,但是在文學門類上的收獲還是明顯的。他們已經培養起一批能創作小說、詩歌、散文的作家隊伍,努力實現著零的突破。也出現了本民族的代表性作家,比如羅榮芬,她在小說、散文方面都創作了優秀的作品,代表著獨龍族書面文學目前達到的最好水平。如果從整體上看,獨龍族文學中的小說和詩歌文體還顯得比較薄弱。雖然獨龍族的作品集從篇幅上看是8個民族中最少的一部,但無論從民族人口的比例還是作品的質量上看,卻有自己獨到的特色與收獲。
德昂族的文學也在努力發展中,并取得了一定成績。“德昂族卷”一共收入4名作家的6篇小說,8名作家的27篇散文,11位詩人的58首詩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德昂族作家文學成果的一次集中檢閱,其主要成果明顯集中于中年作家的身上。
德昂族的文學開拓者們當初是從民間文學起步,李臘翁、勐丹青年組合、董小月、王老二、何阿三、楊忠德等人在8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開啟了本民族書面文學的第一頁,可以視為德昂族作家文學的拓荒者。德昂族的第一篇小說是趙家書的《大盈江畔》,雖然內容和德昂族生活沒有關系,但是作者的民族身份決定了這篇作品的意義。楊忠德從民間文學起步,在散文寫作方面也是奠基者,曾經在全國和省內多次獲獎。董曉梅等中年作者緊跟其后,在散文創作方面有比較大的收獲。目前艾傈木諾可以視為德昂族作家文學的代表性人物,她在詩歌、小說、散文三種文體中都有突出表現,尤其是詩歌創作,她的作品提升了德昂族詩歌的水平和品質,其詩歌集曾經榮獲“駿馬獎”,在全國范圍內有一定影響。
基諾族的書面文學隊伍比較強,“基諾族卷”中出現的寫作者有24位,收入各類文學作品123篇(首)。其中小說3篇,散文92篇,詩歌28首。如果單從數量上看確實已經形成一個可觀的寫作群體,但認真分析會發現,在文體的寫作上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現象。散文是基諾族的強項,參與者眾多,而且有成績突出的代表,比如張志華的散文在其中就比較有代表性。他入選的28篇散文題材比較廣泛,對民族生活、軍旅生活都有細致表現。詩歌部分一共收入8位詩人的28首詩,民族生活特色鮮明突出,但是詩歌藝術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基諾族文學中最弱的文體應該是小說,“基諾族卷”中只收入兩位作家的3篇作品,其中兩篇還是在報紙發表的小小說。所以張璨的《我的基諾爸爸和愛伲媽媽》這篇一萬多字的小說,可以視為基諾族小說的代表作。小說藝術雖然尚顯稚嫩,但其基諾族生活特色鮮明突出。
基諾族作家隊伍的發展壯大,和基諾族學會及會刊《太陽鼓》的創辦有密切關系,后者為文學初學者的起步提供了很好的發表平臺,培養了一批作家隊伍。從長遠的目標來看,基諾族文學的發展還需要各方面的關心和扶持,尤其是小說文體方面,更是需要努力才能更上一層樓。
“怒族卷”一共收入小說9篇,詩歌34首,散文61篇。相比之下,小說、詩歌還是處于比較弱勢的地位,需要得到更多寫作者的重視和努力。
“怒族卷”中收入的作家作品,體現了怒族文學三代同堂寫作的局面。其中有老一輩文學開創者羅沙益、彭兆清、葉世富、李衛才、和富才、李紹恩等人的作品,有一批中青年作家羅善榮、羅金剛、李金榮、和建華等緊隨其后,從年齡結構上看比較均勻。目前彭兆清、李金榮已經加入中國作協。怒族老一輩作家在小說方面奠定了比較好的基礎,彭兆清曾經以短篇小說作品獲過“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羅沙益、葉世富也有小說作品發表。達伯、劉文青的作品使怒族文學中的小說文體得到延續和發展。但是相比之下,參與者數量最多的還是散文創作。
從集子中收入的散文作品來看,題材范圍比較廣,其中既有大量傳承怒族歷史文化的篇章,有對怒族現實生活的變遷進行深入表現的作品,也有一些超出民族生活范圍的內容出現。比如和光益的散文《與冰心相識在北京》,王靖生的散文《與進京馬幫同行的168個日子》,起到了擴展怒族散文審美空間的作用,從另一個側面印證著一個民族的發展進步。
“普米族卷”收入小說8篇,詩歌119首,散文60篇。在小說、散文、詩歌領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體現了這個民族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創造力和開拓進取精神。小說方面出現了和順明、和善全、尹善龍、尹秀龍、湯格·薩甲博等一批寫作者,他們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奠定了一個民族小說史的基礎。但是在三種文體中,小說還是相對弱勢的存在。沒有年輕一代寫作者的參與,使普米族的小說寫作面臨危機。相比小說,散文有更自由開放的表現形式,更適合對現實生活和民族文化進行深入細致的表現。從普米族作家的作品中,可以體會到他們對現實生活的日常性和人類精神的普遍性等問題都有獨到的理解和表現。
詩歌方面,魯若迪基的看法比較有權威性,他認為:“普米族書面文學,就目前而言,取得較高成就的當屬詩歌。普米族作家隊伍里,十有八九是寫詩的,創作了數量可觀的作品,而且有相當的質量。”②確實,詩歌文體對表現一個民族在文學上的審美高度更有優勢。像普米族這樣有著古老的歌謠史和豐富心靈追求的民族,詩歌猶如他們的酒杯和火把,能燃燒出熊熊的火焰,照亮文學的書頁。而且還出現了魯若迪基這樣在全國詩壇有一定影響的代表性作家和領軍人物,這對一個民族的詩歌發展來說也是一種高度。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獲得“駿馬獎”的普米族作家幾乎都是以詩歌作品而獲獎。這正好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普米族在詩歌上取得的成就。
“景頗族卷”收入9位作家的小說16篇,8位作家的散文9篇,16位詩人的詩歌56首。由此可見景頗族的小說在8個人口較少民族文學中占據的領先地位。如“景頗族卷·序”所言:“30多年來景頗族文學史上已有三位作家五次榮獲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這是文學發展的最好見證”。“景頗族卷”收入的只是漢語創作的作品,還有一些用母語創作的無法進入。但這部分漢語作品已經是景頗族作家文學創作實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小說成果方面,經過木然、石銳、臘董、岳丁、穆智、瑪波等人多年的努力,已經取得了比較理想的成績,文體開始成熟,作家隊伍相對整齊。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上出現了一些優秀的作品,榮登《人民文學》《民族文學》等國家級大刊。詩歌和散文的水平也比較整齊,從題材到寫作技巧方面,都體現了一個“作家群”穩定成熟的特色。
二、困境與問題
應該客觀冷靜地看到,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奮斗,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每個民族都有作家出版文學作品集,或者獲過全國性文學獎項,或者加入中國作協,在中國文學的舞臺上成功地登臺亮相,為中華多民族文學譜系的建立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但是畢竟起步的歷程短暫,基礎薄弱,各民族文學創作中存在的問題和現象也不容忽視,應該看到邊疆文學和文壇主流文學之間在思想性和藝術性等方面存在的明顯差距。所以為了今后更好地發展,取得更大的成績,有必要對存在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找到問題的癥結,才能制定出切實有用的對策。其實在《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文學卷中可以看到,一些編選者已經有一定的自省和自覺意識,開始對本民族文學的發展進行整體思考。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看到了本民族文學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正在尋找著突圍的方法。從眾多民族作家的創作實際出發,下面簡要分析一下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創作面臨的困境與問題,以期對今后的創作有一定幫助。
一是身份的業余性導致寫作的分散。
各個民族的寫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文學創作純屬個人愛好。大多數人利用業余時間進行創作。有的人出于對文學的熱愛,有的人寫作是民族使命感和責任感驅動下的行為。而且一些基層作者沒有機會接受完整系統的高等教育,閱讀面比較窄,對文學的理解和接受有一定限度,在生活中又承擔著繁重的工作和生活擔子,文學創作只能利用有限的業余時間來進行。加上同一民族的作家,也是分散居住于不同的地區,所以作者隊伍的情況比較復雜,文學修養的層次高低不一,無法形成統一的寫作陣營。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
二是生活環境導致寫作水平滯后。
各民族寫作者生活的地域比較分散,而且大多是貧窮落后的民族地區。對深入民族生活來說是優勢,但對從事文學創作來說卻有許多不便。雖然如今已經進入網絡化時代,但在一些偏遠的民族地區,上網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導致作家之間的交流互動,與刊物編輯的交流溝通不便,寫作會遇到一定障礙。
三是文學的視野和高度,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質量和水平。
這個問題和前兩個問題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8個民族都面臨文學史短暫,經驗積累有限的問題。同時因為民族作家身處的環境條件大多是邊疆基層,在文學創作方面又是利用業余時間,閱讀和寫作都必須依靠寫作者自身的意志和對文學的熱愛來維持和推進。在文學的方法技巧和藝術表現力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所以閱讀一部分民族作家的作品,能感覺到他們的生活底子非常深厚,對民族生活非常熟悉,但是卻缺少進一步的開掘和提升,僅僅停留在生活表象的描寫上。題材方面同質化現象也比較嚴重,比如一些寫故鄉、童年的散文,雖然民族不同作者不同,但是給人的閱讀感受卻大致相同。8個民族的作品集中起來看,寫民族生活的小說不少,但精品力作不多。散文的數量也不少,但佳作不多,多數作品還停留在學習和模仿階段,甚至有學生寫“作文”的感覺。主題和藝術技巧方面也不盡如人意。詩歌方面雖然涌現了一些新生代詩人,給民族詩壇帶來一些新的沖擊力度,但是這樣的詩人數量還比較少,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最后是8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隊伍的建設問題。
從作品集的研究中發現一個現象,8個民族的作家隊伍建設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性。這和每個民族的具體發展情況不同有關,與相關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具體措施的落實也存在密切關系。
有的民族作家隊伍年齡結構比較合理,對年輕作家的培養已經進入比較有序的狀態。比如基諾族的作家隊伍中,就已經有一些80后、90后,甚至00后的身影出現。雖然他們的作品還比較稚拙,但是在前輩作家的精心引導和扶持下,已經開始培養起對文學的興趣,用文字表達了自己對民族的情感,對世界的熱愛。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從“基諾族卷”中收入的三位00后作者頗哲、孫貝、車都的作品中,已經感受到了文學希望和理想對他們生活的滲透和影響。
獨龍族雖然在8個民族中人口最少,但是在作家隊伍的結構上卻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出現了從60后到90后的作家隊伍。小說部分主要由60后、70后的作家領先,散文部分各個年齡段的參與者更多一些。詩歌部分收入了從30后到90后詩人的詩作,體現了獨龍族詩歌的發展進程。對一個人口只有幾千人的民族來說,這支文學隊伍的意義是獨特的。
怒族的作家隊伍年齡層次也比較豐富,“怒族卷”中收入了9篇小說,作家的年齡結構分別由40后、50后、70后、80后所組成,年輕的寫作者已經加入到小說寫作的隊伍中來,這是一個可喜的訊號。散文部分涵蓋了從40后到80后的幾代作家,出現幾代人同堂寫作的局面。詩歌寫作主要由70后、80后的寫作者承擔。從整體上看,怒族作者隊伍的年齡結構是比較科學的。
阿昌族的作者隊伍中實力最強的是一批60后作家,他們承擔著繁榮阿昌族書面文學的重任,也是承上啟下的一代寫作者。此外在“阿昌族卷”中還有30后、50后、70后、80后的身影。同時也感覺到如果不重視培養,讓70后、80后作家盡快跟上來,作家隊伍“斷代”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但是對8個民族作家隊伍的總體進行考察發現,不是每一個民族都能在文學作家隊伍的建設上有如此的自覺意識,一些現象已經到了應該引起重視的時候。
一個方面是年齡結構上的不平衡性,作家年齡普遍偏大。
正常的作家隊伍應該有不同年齡段的寫作者加入,形成多層次狀態下幾代作家共同寫作的局面。但是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隊伍中如今挑大梁的依然是一批50后、60后作家。比如景頗族文學作家隊伍的老齡化現象就已經比較突出,應該引起注意。從集子里面收入的作品來看,小說部分完全沒有70后、80后作家的身影,作家的“斷代”現象非常明顯。散文部分只收入一個70后作家的作品,詩歌部分有兩個70后,一個80后,一個90后出現。從整部作品卷的情況來分析,景頗族文學中占寫作主導地位的仍然是50后、60后作家。不可否認,他們的思想和藝術技巧都已經成熟,發表了很多有影響的作品,確實能代表一個民族在文壇亮相。但是從文學發展的長遠目標來看,后來者的加入也非常重要。一個民族的作家隊伍,需要各個年齡層次的作家共同參與,才能構成一個合理的發展結構。“后繼乏人”的現象應該受到關注。
普米族作家隊伍的年齡結構也有青黃不接的現象。小說隊伍全部是40后、50后的身影,連一個60后的作家都沒有出現,更談不到70后、80后的參與。散文隊伍出現了60后、70后的作家,但沒有80后作家的參與。詩歌隊伍的年齡結構比較豐富一些,從40后到80后都有參與。但明顯看得出在詩歌隊伍中挑大梁的仍然是一批60后、70后的寫作者。從整體上看,普米族作家隊伍的建設已經有了明顯的“斷代”現象,體現在小說和散文文體方面更明顯一些。
布朗族作家隊伍的情況也不容易樂觀,“布朗族卷”中出現的作家只有十余人。年齡結構上有偏向老齡化的傾向。其中出生于50年代的老一輩作家巖香南、金學常、俸春華、鮑啟銘仍然是這支隊伍的主力。其后有出生于60年代的陶玉明、穆文春,和出生于70年代的李俊玲、楊芳,在創作上體現了自己的實力。更年輕的只有80年代末出生的周雅婷,90年代出生的郭應國。本卷編委會在后記中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認為在布朗族知識分子中,“研究民族歷史文化的專家多,從事文學創作的少”。而且作品的質量“參差不齊”,選稿工作比較困難。
德昂族的作家隊伍力量也比較薄弱,青年作家后繼乏人的現象應該引起重視,“德昂族卷”中出現的作家名字不到二十個人,其中還有一些早已經停止寫作。除了70后的艾傈木諾、董曉梅堅持寫作外,80后的作家只有楊文華、劉青峰,90后的只有艾葉安布,一共三個人。從整體上看,德昂族的作家隊伍需要引起重視,要及時進行力量的整合,吸引更多文學愛好者加入其中。艾傈木諾在“德昂族卷·序”中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她在文中發出呼吁:“沒有創作就沒有文學,著力培養德昂族作家是當務之急。每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德昂人都應當樹立文化傳承觀,挖掘和發現文學之星,盡自己的能力去引導和幫助德昂族文學接班人。”
另一個問題是文學人才培養方面面臨的困境。
文學創作是一項復雜的精神勞動,它的人才培養機制也比較特殊。它需要一個人有對文學的興趣和熱情,主動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還需要他對文學有執著的態度,在寫作的過程中守得住孤獨寂寞,有堅守的精神。畢竟我們身處一個商品經濟時代,個體面對的誘惑會很多。能以執著的精神來從事文學創作,并且把它當作事業來進行,是非常不容易的。為了生存很多民族地區的青年會選擇進城打工,人員的流動性非常大。凡此種種都給民族作家隊伍的培養帶來新的問題和難題。
三、對策與建議
對民族作家來說,文學又不僅僅是個體的事,它一定還和作家所屬的民族有密切關系。作為一個民族尤其是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化成員,他的寫作代表著這個民族的文化走向和可能達到的高度。所以,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創作者們,都會面臨這樣的處境,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民族而獲得榮譽,發表的作品會被冠以“本民族第一篇作品”“本民族第一部集子”,獲得一種崇高的精神體驗。另一方面,肩上的責任和義務也會隨著榮譽而逐步加強。你是否能創作出代表自己民族的優秀作品,為本民族文學史增光添彩,也會成為一個沉甸甸的壓力。
下面這段話比較客觀、科學地指出了民族文學創作中應該注意的問題:“既然大家都有優秀的方面,自然也應該有不如別人的地方,這就決定了民族性的鮮明和穩定是與民族的狹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題。民族文化的自信與書寫、開掘與張揚,源于那些積極有價值的珍貴特質。這就要求每個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寬闊的胸懷和開放的姿態,積極學習其他兄弟民族的優長之處,并敢于面對世界,積極進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長補短,反思追問,以民族的優秀傳統為依托,創作出具有時代高度和國家情懷,能體現人類共同追求的作品。”③基于共同的目標和理想,經過前面對8個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分析研究,現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對策和建議,以期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對文學的發展有一點借鑒意義。
一、民族文學需要代表性作家和領軍人物
無論是一個時代,還是一個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領軍人物。他的文學成就不僅代表個人,也要能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學高度和水平,能體現出審美的獨特性。這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的文學開始走向成熟的標志。
可喜的是從對8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大多數民族的文學隊伍中已經開始出現這樣的人物。代表性作家和文學的領軍人物,有時候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他的創作水平能代表一個民族,為這個民族爭光,自然就能在本民族文學中起到領軍的作用。但也有一點區別,前者更強調作品本身的意義,有的是一個民族書面文學的開啟者,有的是一個民族的第一個獲獎者。后者除了作品有代表性外,作家自身還需要體現出一定的組織能力和社會影響力,能對民族文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一個民族文學中出現的領軍人物,不是由哪個機構封贈的,他有自身的條件和相應的要求。比如其作品數量、質量,思想內涵發表的層次,作品的獲獎,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他為本民族文學帶來的榮譽,是否能起到引導后來者的作用等等。
所謂“領軍人物”,其實也代表著某一民族的文學目前所達到的高度,對本民族寫作者的導引作用。他應該也可以成為一個民族文學的一面旗幟,就像老舍之于滿族文學,李喬之于彝族文學。
檢閱目前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文學會發現,大部分民族已經出現能稱得上領軍人物的作家和作品,他的創作對這一民族的影響是深遠的。很多讀者就是通過他的作品而了解他身后的民族,甚至喜歡上這個民族。
比如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德昂族詩人艾傈木諾,獨龍族作家羅榮芬,阿昌族作家羅漢、孫寶廷,怒族作家彭兆清、李金榮,景頗族作家岳丁、瑪波,布朗族作家巖香南、陶玉明,基諾族作家張志華等,他們在文學上取得的成績,能代表一個民族書面文學目前所達到的高度,可以擔起為本民族文學“領軍”的重任。至于如何“領軍”,則需要每個作家激發出高度的責任感和理想主義精神,在創作實踐中努力思考和探索。
二、加強人口較少民族作家隊伍的建設
從前面的剖析中可以看出,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隊伍雖然基本建立,取得了不錯的創作成績。但是存在的問題也比較明顯,需要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并出臺一些切實有效的措施。
1.省作協或地州作協一類機構,應該對8個民族的創作人才進行專項調研,摸清情況,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文學人才的資料信息庫。對一些有創作潛力的青年作者要進行重點關注,及時把握他們的創作動態。
2.文學批評的滯后也是阻礙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發展的因素之一。應該看到很少有評論家愿意花時間來關注一些處于弱勢狀態的文學,為他們的發展給予指導。所以相關機構要定期組織專門針對8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的筆會、改稿會,組織評論對他們的作品進行研究和評說,給予及時的批評與指導。
3.省級或地州級刊物,每年可以用出專號的形式,重點推出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的作品,并組織評論同時發表進行指導,以形成有效的推動作用。但專號一定要推選優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及針對青年作家的欄目,使各民族作家能匯聚一堂,在互相學習中進步。
4.民族文學的繁榮需要多種力量和渠道的共同努力,其中搭建一個展示創作實力的平臺也很重要。可以考慮在省級相關文藝獎勵基金中設立一個專門針對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獎項,以起到引導、鼓勵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健康發展,不斷推出優秀文學人才的作用。
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隊伍建設,是一項長期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上建議和對策不過是一家之言,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三、要精心打造經典作品
所謂經典作品,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或者說有著多重理解的概念。它的客觀性在于,它的出現不是依靠行政命令或者按民族來劃分。最起碼需要接受時間和讀者的雙重檢驗來確定其是否真的是一個民族文學中的經典性作品。
它應該具有比較高的美學價值,既能代表一個民族,又能超越一個民族,為不同民族的讀者所接受。它還要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和審美,在文本意義上體現出新的特質和貢獻。通俗地說,就是禁得住時間檢驗的優秀之作。對民族文學來,它還應該能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學水平和高度,就像阿來的《塵埃落定》,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既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還能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成為一個時代的優秀代表作。
這樣的作品在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文學中還正處于孕育形成的過程中。一些優秀的作家應該已經具備了創作經典的條件,但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經典作品的出現除了作家自身的努力,還需要社會的合力推進。比如文學機構提供重點培訓、扶持的機會,文學評論及時評說與跟進,媒體的宣傳報道等等。
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文學剛剛起步,《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是一個時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點。對前一時期取得的成果進行分析研究,是為了總結經驗教訓,揚長避短,在今后的創作實踐中能更好地發展進步,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文學作品。
三十多年,在歷史長河里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但是對8個人口較少民族來說,卻勝過千年。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發展都已經實現了跨越式的進步,正朝著美好的未來努力前進。閱讀8部作品集,可以進入他們豐富的歷史文化之頁,也可以切入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生動形象地感知到他們內心的希望與喜悅,還可以領略到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具體表現。真正是彩云之南書華章,奇花異草共芬芳,他們的作品理應得到社會更廣泛的理解與關注。
期待這8個民族有更多的優秀作家作品出現,為他們自己的民族,也為中華民族文學增添新的篇章。
注釋:
①指全國總人口在30萬人以下的云南8個少數民族。他們分別是阿昌族、獨龍族、德昂族、基諾族、怒族、普米族、布朗族和景頗族。
②見《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普米族卷·后記》。
③見《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總序》。
責任編輯 安殿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