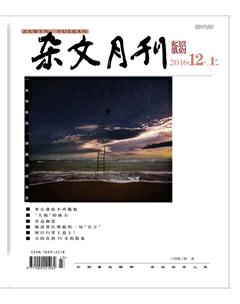晚清重臣剛毅的一句“名言”
理釗
“寧贈友邦,勿與家奴”,是晚清深受慈禧寵信的軍機大臣剛毅,針對改良派的一句名言。剛毅的原文是:“改革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設吾有為,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他塔拉·剛毅是滿族鑲藍旗人,他發跡源于中日甲午戰爭,因他積極主戰,受到慈禧太后的賞識,進入軍機處,任軍機大臣兼禮部侍郞。1898年光緒皇帝主持維新時,他堅決站在慈禧這一邊,反對戊戌變法,甚至主張廢黜光緒皇帝,從而進一步得到了慈禧的龐信,變法被鎮壓后,被提升為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他的這句話,也就是在他堅定地站在反對變革的前沿時說出來的。這句名言之所以“名”,我覺得是因為他在不經意間道出了大清王朝的“真”,說出了隱含在大清王朝,甚至是皇權專制制度里面的基因密碼,解開它,或可以明白為何每一個王朝,開始時轟轟烈烈,弄到最后就在一夜之間,又轟然一聲倒下。
“寧贈友邦”,能夠贈出去的是什么呢?當然是滿清統治集團的手中掌握著什么,才可以贈出去什么。概括起來,這個專制集團手中所掌握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權力、權力壟斷之下的財富及土地,當然也包括他們呼來喝去的“家奴”,也就是除了滿族人以外的其他的中國人。明白了這一點,就會發現,在整個近代史中,這個統治集團“贈”與“友邦”的,其實并不少。
對此,也許有人會說,近代中國向西方列強割地賠款,都是列強用了武力強搶硬奪走的,清廷也是不得已而為之。這一條理由,表面上看顯得“政治正確”,可如果把眼光稍稍地放得遠一點,就會發現這一個理由經不起細想了。在歷史上,中國一向是看不起日本的,文字上稱之為“倭寇”,心理上覺得那是中國的徒兒。當中國被西方國家強行打開國門的時候,日本也正遭受同樣的經歷。被逼之下,日本差不多與清朝的“同治中興”一起,開始進行變革。只是清朝只學習造槍炮,買戰船,而日本則是進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向歐洲靠攏,大力發展近代教育等。三十年下來,那個曾是徒兒的“倭寇”,竟然變成了“列強”之一,甲午一戰,不僅勝了自己覺得已經強大起來了的中國——當時,清朝的海軍號稱世界第六,而且自此之后,竟也三天兩頭到大清王朝來要地要錢,“拳匪”事變時,還派了八千士兵,與英、法、美、意等,一起打進了北京。幾乎是同時“搞變革”,幾乎同樣是“學西方”,結果為何簡直是云泥之別?原因就在這個“寧贈友邦,勿與家奴”所隱含的密碼之中。
由這一句名言可以看出,以愛新覺羅家族為核心的清朝統治集團,自始至終都沒有把中國看作是自己的中國,只是把統治中國的權力看作是自家的權力。如果他們真地把他們治下的國家當作自己的國家,把這個國家的國民看作是自己的國民,他們想到、做到的應該是讓這個自己的國民的生活得到不斷的改善,應該真心實意地發展本國的經濟,并讓國民從中得到福利。因為國民的富有與適意,才是國家真正的強大。
相反,當清廷集團只把統治這個國家的權力當作是自己的權力時,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會圍繞著鞏固和強化這個權力而行。事實也正是如此。“同治中興”,看上去確是在“中興”,可興起來只是造槍造炮的事業,這些東西名義上是為了與西方抗衡,但更是為了鎮壓各地國民因實在活不去而生的“叛亂”;所辦的洋務中,雖然也有開礦山、修鐵路等一些實業,可開辦的方式卻是讓國民中的富商出資,由官方來管理經營,即謂“民辦官助”,結果是朝廷派來管企業的官員,把個實業當作了官場,非但未能賺錢,有些很快賠得底朝天;說大清王朝只愛權力而不愛國民,還有一個理由,就是不但不去開民智,相反還要變著法子不讓國民自己學知識、長智慧。1900年前后,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天津和直隸等地鬧起了義和拳,義和拳相信自己只要練上一年半載,神靈就會附身,刀槍不入,踏步如云,所以他們打起仗來,拒絕使用槍炮,只用大刀長矛。在他們的鼓動下,國民相信修鐵路斷了“龍脈”,開礦山放走了“寶氣”,宣揚要殺盡三種人:大毛子(外國人)、二毛子(信教的中國人)和三毛子(使用洋貨的中國人)。而這個時候,“洋務運動”已經開展了三十年,經歷了整整一代人,而鬧義和拳的地方,又不是中國偏遠地區,國民仍然愚昧至此,可見所謂的“中興”興的是什么,也就此可以看出清廷對于國民的近代教育持一種什么樣的心思。
義和拳不但未能殺退洋人,反而引來了八國聯軍。縱容和利用義和拳的慈禧,看到八國聯軍自天津上岸,在鐵路已被義和拳扒掉的情況下,仍然十天就打進了北京,知道自己闖下了大禍,自己一面化裝逃到了西安,一面裝模做樣地發布“罪己詔”,一面又咬牙切齒地發誓要變革。《辛丑條約》簽訂之后,慈禧發布詔令進行改革,看上去從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做了一些還權于民的變革,可私下里,她又暗示她厭惡西洋,軍機處因此給地方上的改革派打招呼,不要輕言學習西法。熱情的改革者張之洞在給一位軍機大臣的電報中說:“嗣聞人言,內意不愿多言西法,尊電亦言‘勿襲西法皮毛,免遺口實等語,不覺廢然長嘆;若果如此,‘變法二字尚未對題,仍是無用,中國終歸澌滅矣!”可見慈禧等對于權力的愛有多深。
再說“勿與家奴”。在清廷統治者的眼里,其治下的國民,除了滿人以外,均是其“家奴”。“家奴”這個詞,在皇權法律中雖然沒有明確的界定,不像美國內戰前南方蓄奴州那樣,有著明確無誤的法律規定,“黑奴”是其主人的財產,不僅可以買賣,甚至可以生殺予奪。而實質上,中國的國民在秦以后的統治者眼里,一直就是皇權的奴隸。一是中國一直沒有明確的私產概念,更沒有“私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律令。在專制皇權之下,名義上的私產,只是皇權的默許而已,一旦皇權需要個人的財產,一個查封追繳的詔令,不管你是達官顯貴,還是鄉紳大戶,不管非法合法得來的財產,就可以連人帶物一并弄得干干凈凈;二是中國國民的生命,也是依附在皇權之下的,所謂“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死前還要“謝主隆恩”。至于普通百姓的生命,在皇權面前,真的就是螻蟻;三是國民對于皇權的精神依賴,從來就沒有過獨立的人格。1858年,美國與清廷簽訂《天津條約》時,美國代表杜邦曾向直隸總督譚廷襄提出,請清廷派官員駐節美國,以便照顧在美華人。杜邦說:“貴國人民居留太平洋彼岸者,人數甚多,不少于數十萬。”譚回答說:“敝國皇帝撫御萬民,何暇顧及此區區漂流海外之浪民?”杜又說:“惟此等華人已在敝國開采金礦之故,富有者甚眾,似有加以照顧之價值。”譚答:“敝國皇帝富有四海,何暇與此海外游民錙銖計較。”這一番對話雖只涉及“海外浪民”,可國民在官員眼中究竟是何地位,可謂一目了然。所以,剛毅的這句話,只是因為他是外族統治者,有一種不自覺的潛意識,一不小心道出了中國皇權的底子罷了。
【小黑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