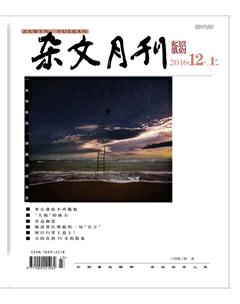我們現在怎樣做父母
柳士同
題目是借用魯迅先生的,只改動了一個字,將“我們怎樣做父親”,改成了“我們怎樣做父母”。故事則是引用外國的:一個年僅6歲,名叫瑞安(Ryan)的加拿大小男孩,聽老師說非洲的小朋友喝的水都很臟,在那兒“最干凈的水是眼淚”。而要讓非洲的小朋友都喝上干凈的水,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打井。于是,小瑞安就決心攢錢資助非洲打井,讓非洲的小朋友都喝上干凈的水。
這是一個充滿了愛的故事,其價值層面可能涉及甚廣,但我最感興趣的是小瑞安父母的態度。近些年來,不是有很多人熱衷于談“家教”嗎?那我們就不妨看看小瑞安的父母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當小瑞安找媽媽要零花錢,并且說明了他攢錢的目的時,家人并沒有滿足他的這一要求,而是對他說,要想幫助別人,必須靠自己的努力。于是,從那一天開始,家里到處都是小瑞安忙碌的身影——踩著板凳洗碗,拿不動拖把就蹲著打濕毛巾擦地板,替爸爸去剪院子里的雜草,而每干完一次家務,他的餅干筒里就會多幾美元。當然,這還遠遠不夠,為了攢足打一口井的2000美元,他又去左鄰右舍攬活兒干……我不由立馬就聯想到本土,我們現在的孩子六七歲的時候都在干什么呢?趴在桌子上做成摞成摞的作業,上各種各樣的輔導班強化班,學各種能讓考試加分的特長,諸如器樂、舞蹈、書畫、棋藝等等。即使孩子聽說非洲孩子沒水喝,想幫助非洲小朋友打井,家長也頂多拿出些錢來讓孩子捐款(權當做慈善吧),而絕不會讓孩子整天以做家務,以幫鄰居干零活來掙錢。“心疼”孩子不說,更重要的是不能耽誤孩子寶貴的時間,從小就“輸在起跑線上”。父母可能帶著孩子去美國呀歐洲呀旅游,即使想去非洲那也是去埃及看看金字塔,絕不可能帶著孩子去烏干達!
可小瑞安的父母不僅讓他在每天的課余時間,以力所能及的勞動來賺足打井的錢,還于2000年7月帶著他來到烏干達,讓他看看因他的努力而打出的第一口井,讓他和非洲的與他同齡的黑孩子交朋友,讓他了解并親身體會非洲窮孩子的生活。于是,回國之后小瑞安便把幫助非洲小朋友打井,把讓非洲的孩子都喝上干凈的水,當作了自己的“夢”,并為實現這一夢想而孜孜不倦地努力。2014年,24歲的他隨同父母再一次來到烏干達,經過18年的努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已經打了1000多口井。像瑞安這樣的年輕人怕是很難出現在中國,至少對于本文的題目所問“我們現在怎樣做父母”?小瑞安的故事大約不會是現在中國父母們的答案。因為我們現在做父母的,對子女的期望就是一個——成功——長大了能夠成為一名成功人士,一名被當今社會所認可的“精英”。而一旦成為成功人士成為精英(哪怕還達不到),那子女首先不能忘記的是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這也大約是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孝道”所一貫張揚的。
然而,瑞安的父母似乎并沒有這樣希望過自己的孩子,也沒有這樣要求過自己的孩子,更沒陪著孩子去上這樣那樣的輔導班、特長班,而任由孩子把幾乎全部的課余時間用在瑣碎繁忙的勞動之中。其實,回想一下,魯迅先生九十七年前也正是這樣認識的。先生絲毫不認為父母有恩于子女,他“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在先生看來,父母對于子女“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導”,“第三,便是‘解放”。對照一下,我真有些吃驚了,瑞安的父母莫非讀過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是遵照先生的說法去做的?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那唯一的解釋,就是瑞安的父母和八九十年前的魯迅,心是相通的,或者用當下頗時髦的話說,他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愛,或者說博愛。瑞安的父母正是以對孩子的“理解”,加以正確的“指導”,讓其心靈獲得“解放”。既尊重孩子的選擇,又給了他充分的自由,從而最大限度地釋放了孩子的潛能和他心中的愛,在扎扎實實的勞動中體現自身的價值。
沒有比喋喋不休的空洞說教更令人厭煩的了。任何動聽的語言,只有身體力行才能呈現出它的美麗。小瑞安的父母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去做的。相比之下,我們的做法,是不是與百年前魯迅的觀念、與眼下小瑞安的作為,相去得太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