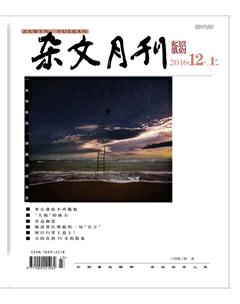官場“稱呼學”里的真問題
化定興
如果你對中國官場稍有了解,就知道里面有諸多學問,如何稱呼便是其中一種。稱呼得體了皆大歡喜,稱呼不當了有可能讓對方反感。在官場,比較穩妥的稱呼是一個人的姓加上其職務,比如一個人姓張,又是局長,那么叫張局長或者張局就不會出現什么問題。現在被不少人嗤之以鼻的就是“叫大不叫小”。比如一個人姓李,是副主任,那么別人不會叫李副主任,而是李主任;一個人如果只是省里來的科長,有時也會喊處長;如果不知道對方的準確職務,也弄不清具體行政級別,那么初次見面還是喊高一點比較好……
因此有人說:“給稱呼‘戴高帽中最常見的是將副職叫成正職。有的同志為了‘討好上級,故意在稱呼中省略‘副字,以此來表示自己對上級的尊重。但這其中也不免有‘奉承心理,從某種程度講,也是一種‘語言賄賂。”
按說稱呼這事就是個禮儀問題,最多反映一個人是否人情練達,根本不用上綱上線,況且官場產生的很多問題并不是因為稱呼產生的。如果對“稱呼學”大加斥責恐怕板子沒有拍對地方。賄賂,一般來講是給予諸如金錢、不動產、女色等實際利益來收買官員,以謀取自己的不正當利益。因此,將副職叫成正職,有奉承心理不假,但如果說是語言賄賂,則有點嚴重了。再說,光靠嘴上這點好處就想賄賂別人恐怕太過廉價。
其實,官場有這樣戴高帽的“稱呼學”不難理解。一方面,起碼在禮儀上可以宣示對對方的尊重,對方總不至于當頭棒喝,說你喊錯了;另一方面,這樣做可以給對方留下好的印象,方便日后自己在官場行走,如同接待里的學問——來的都是客,都要照顧好。這里面充滿了為人處世的精明,與賄賂的干系不大。
再進一步你會發現,“稱呼學”不是官場獨有現象,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生活里,一個人如果碰到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禮貌地稱呼,大家就會覺得這個人懂事有禮貌,或者說嘴比較甜,這樣的人往往比較受歡迎,至于有些人口蜜腹劍那是另外一回事。就算是不沾親帶故的,也不好直呼其名,總要想個貼切的稱呼,比如長一輩的叫個“叔、姨”,同輩的叫個“哥、姐”,實在不知叫什么好,也會稱呼“老師、師傅”。家長教育小孩時,也常從稱呼別人開始,可謂人生必修課。
職場上,姓加職務的叫法也很普遍,這和官場并無什么本質不同。若說戴高帽式的稱呼,社會上也不是沒有,最常見的就是逢人喊總,什么王總、趙總。有些人為了便于辦事,甚至自稱大職務,這看看名片上到處印著“總經理”“主任”就再清楚不過了。
實際上,中國人的稱呼是宗法、習俗、地位、威望等的反映,從稱呼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基本的禮儀規范,而且可以看到國人對長幼尊卑等禮法習俗的重視。比如你喊一個人“老趙”還是“趙老”,體現了不同的含義。
有學者分析道,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尊卑長幼之分和親族間輩分的高下之別確是很嚴格的,這種分別不是經濟意義上的“階級”,而是“倫級”。這一倫級的觀念,擴散到官制之中,就幾乎與官階有了相當的關系。自古以來,大官就是大老爺,小官就是小老爺,底下的就是孝子賢孫。慈禧太后叫作“佛爺”,皇帝退休了叫作“太上皇”。所以在等級森嚴的古代,稱呼之事異常重要,如果弄錯了,有可能賠上身家性命。
由此看來,稱呼之事其實只是表,背后的禮制文化才是里。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硬性規定該如何稱呼效果就不顯著。“同志”一詞曾在黨內流行,隱含著志同道合之意,也意味著大家彼此平等。黨中央多次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但隨著時代發展,這種叫法開始式微,甚至一叫同志,對方還有些不高興。2003年,全國各地黨委都曾專門制定下發《關于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黨內互稱同志優良傳統的通知》,要求“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稱同志,不稱職務”。然而,“同志”除了是正式場合的莊重稱呼外,并未在其他場合流行起來。
所以,如果只是主張大家該怎么稱呼,并不斷鞭笞稱呼庸俗化的現象,而不消除產生這種現象的文化土壤,那么,這樣的主張和批評只能是嘴上說說。結果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你說你的,我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