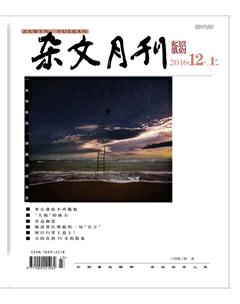漫談碑債
勞燕
在羅布泊深處,矗立著一塊大理石“羊碑”,碑面刻著一只栩栩如生的母羊。她的故事催人淚下。
1992年,烏魯木齊一家旅行社為開辟一條新的旅游路線,委派部門主任王威帶領幾名員工進入羅布泊“探線”,計劃7天完成任務。氣溫高,新鮮肉食易腐,在越野車上除備足水和馕餅,還裝上公母兩只羊。進入羅布泊第四天,殺公羊吃了。第7天任務順利完成,正要殺羊慶祝,忽然刮起黑風暴,衛星電話失靈斷了與外界聯系,只得盡量節約水和食物,也就沒殺羊。第11天食物和水告罄,第12天只得殺羊保命,羊卻不見了!在斷水斷食情況下是走不出羅布泊的,死亡在逼近。第13天風暴平息,中午,一名隊員突然發現那只羊就站在不遠處。隊長王威駕車狂奔,決意撞死它,在沙漠,車速上不去,總也撞不到它。終于,它在一個沙包上站住并向王威張望,像是在等他。王威加大油門撞去……奇跡出現了,他們發現沙包另一側有幾座小房子,那是開發鉀鹽礦的礦工們的駐地。礦工說,這只羊曾來這里找水喝。真相大白,母羊是故意引導王威他們來這里。考察隊得到礦工慷慨幫助,把母羊尸體埋葬后,順利走出沙漠。
王威他們再來時,帶來了這塊感恩的碑。
家畜對人類功莫大焉。新石器時代,馬牛羊狗豬等家畜就已開始為人類服務。它們都值得立碑紀念,可我們一直欠著。實際上,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主張家畜死了要葬之以禮,比如,馬死了埋葬時要用布裹尸,狗死了埋葬時要用車蓋罩頭。養豬本為吃肉,但“君子遠庖廚”,不忍,亦含敬畏之意。
由此想到我們對于同類欠下的碑債也是多不勝數。
一將成名萬骨枯,戰爭動輒幾萬十幾萬地死,秦將白起一次就坑殺了趙軍俘虜40萬。歷史最多只為他們記錄了個大概數字,有的連數字也沒留下。這一筆筆的欠賬想還也沒法還了。
現實中,欠有四種碑債。
一是對于在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唐山建有地震紀念墻,刻有24萬死難者名字。但不是所有自然災害后都建了刻有死難者名字的紀念墻。有必要補上。
二是對于在安全事故中死亡的人,比如礦難罹難者。每當華燈初上,我都會想起“血煤”這個詞,仿佛看到電光里有著礦難者的血光在閃。如果還沒有在礦難井口旁為死難者立碑,那就補上一小塊刻上他們名字的紀念碑吧。他們默默無聞地做著熱與光的貢獻,不能讓他們死得了無蹤影。
三是對于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也請在事故現場旁為他們立一小塊刻上他們名字的碑吧,為紀念,也為警示來者注意安全。
四是對于“非正常死亡者”。將心比心,誰都恐懼于“不正常”,那就出于悲憫也為他們立塊碑吧。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墓碑文化也有了新發展。報載,南方有些豪華墓葬堪比王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死不起現象時有發生。這是社會性虧欠。
墓碑,不限于金石鐫刻。比如將逝者的資料編輯成“志書”,如《中華烈士志》《自然災害死亡年鑒》《安全事故死亡年鑒》《交通事故死亡年鑒》《非正常死亡年鑒》等。
隨著科技的發展,使得祭祀文化顛覆性變革成為可能。日本推出的一種新型“掃墓”,是將親人生前音容笑貌和彌留之際的情形實現數字化保存。每當祭日,可請亡人現身屏幕,面對面“實景”祭拜,甚至可隨時打開手機,“當面”對逝去的親人訴說思念之情。千萬年后的后人,也有機會與他們的“始祖”面對面“交流”。
對于生命無分貧富貴賤也無分族類的敬重程度,對應的是同級別的文明程度。
生命終歸只有二事:生與死,墓碑文明乃生之記憶死之祭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應該成為生也平等死也平等的國家戰略。
【郭德鑫/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