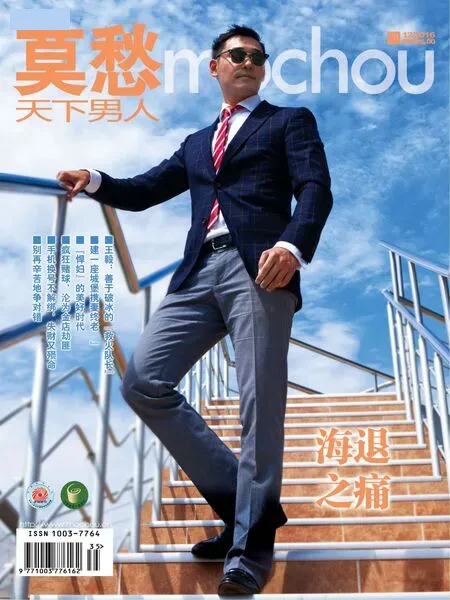劉震云家規一句頂一萬句
□ 二向箔
劉震云家規一句頂一萬句
□ 二向箔
2014年,一個27歲的中國女孩執導的短片《門神》獲得了奧斯卡(學生單元)最佳敘事片獎。消息傳到國內,人們對劉雨霖的名字還稍感陌生,但隨后,面紗揭開了——劉雨霖是著名作家劉震云的女兒。
2016年11月11日,這對父女聯手創作的電影《一句頂一萬句》上映,劉雨霖執導,父親劉震云擔任編劇。劉雨霖說,與父親的合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拿到父親的劇本,也是她一路努力的結果。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劉震云從來不給她夾菜、蓋被、噓寒問暖,但是在她人生的重要時刻,父親永遠陪伴在她身邊,雖然交流不多,甚至不成文的家規,也只是簡短的幾句,但對劉雨霖來說,卻是一句頂一萬句。
好兒女志在四方
劉雨霖最初的夢想是當一名訪談類主持人,像央視里的那些主持人一樣,談笑風生,揮灑自如,于是,她報考了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可是到大二時,看過很多電影之后,劉雨霖心中的電影夢卻如脫韁的野馬,怎么也拽不回來,劉雨霖向父母表達了自己想當導演,到國外藝術學院進修的想法。
從小到大,劉震云對女兒一直采取放養的方式,對她的人生規劃毫不干涉,他的建議是:“你做飯不錯,可以當廚師,你喜歡當導演,這當然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選。你要走多遠,我們就支持你走多遠。”
劉雨霖堅持自己的選擇,2011年,她順利考取了紐約大學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研究生,這所學校以培養了李安、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倫等多位大導演而聲名遠揚。
但剛到美國,沒有專業基礎,語言也不過關,劉雨霖的課業一下子被同學甩出很遠。初到國外接觸完全陌生的知識,劉雨霖一下子蒙了。為了跟上課程,她永遠是在圖書館里坐到最晚的那一個。
劉雨霖內心產生了挫敗感,情緒失控的時候,她不想洗臉,不愿意見人,一想到要上課就特別痛苦。國內過春節,她強顏歡笑跟家人聊視頻,一掛斷臉馬上就垮了,剩下的只是無窮無盡的寂寞和第二天要回學校的壓力,以及無止境地自我懷疑:為什么要來美國?做電影真的開心嗎?為什么放著安逸生活不過卻跑來折磨自己?
劉震云很少給女兒打電話,這一次,也是女兒主動打過來的。拿起話筒,他幾句話就把劉雨霖罵醒了。他問:“到美國這條路是不是你自己選的?”劉雨霖說“是”。劉震云告訴她:“你接下來就兩條路,要不然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把學上完;要不然回來。你永遠不要奢望我和你媽去美國陪你,這個難關必須你自己闖。而且我告訴你,好兒女志在四方。”
劉雨霖一下子想起來自己來美國的初衷:學會拍電影的方式,關注普通人的情感。而她失落、自卑的這樣一段經歷,對今后寫故事、拍電影,不能不說是件好事。
她記住了父親的那句話“好兒女志在四方”,接下來的一切順理成章。這時,劉雨霖得知馮小剛導演要拍電影《一九四二》,決定休學一年去《一九四二》劇組實習。這次,劉震云很支持她,馮小剛則很痛快地給她安排了場記的工作,所謂的場記就是要每天守在導演身邊,守在演員身邊,天天捧著劇本讀。日復一日與導演、演員待在一起,經常面對的是十一架35mm膠片機同時開拍、上千名群眾演員的大場面。電影殺青,再回到三十多人圍著一臺16mm膠片機的課堂,她一下子找回了自信。劉雨霖發現以前的難題完全變成了小事情,內功大漲的她自信了很多,幾年之后回過頭看這一段,她仍然情緒激動,但那種脆弱感已經蕩然無存。對女兒做導演這件事,劉震云的態度是,一個事情你要是做著累,牢騷滿腹,那就別做。讓他欣慰的是女兒做導演真的是享受其中,在拍攝時她根本不覺得苦,甚至都不愿意睡覺、吃飯。
不著急把會的事情一次性做好
劉雨霖從小在北京長大,但經常跟著劉震云回河南老家。5歲到8歲那幾年間,每次回老家,劉雨霖總能在麥收時節,看到鄰居家同歲的小姑娘站在村口等媽媽。小姑娘的爸爸和奶奶也不忍說出媽媽棄家不顧的真相,總說麥收的時候媽媽就回來。于是小姑娘一年年等著,也一年年失落著。小姑娘等媽媽回來的畫面一直盤桓在劉雨霖腦袋里,她決定在大學期間將其拍成電影,這就是后來獲奧斯卡獎的《門神》。
“這個中國鄉村小姑娘的悲傷被大家忽略了,她親人的悲傷也被大家忽略了。像這樣被忽略的情感,在故鄉有很多。我想把這些被忽略的情感告訴大家。”2013年1月,劉雨霖來到河南省延津縣王樓鄉老莊村進行拍攝。陪她一起來的是在電影《一九四二》擔任場記時認識的一群小伙伴,其中包括馮小剛的女兒。到達老家后,劉雨霖很快就進入了電影的故事中,找到農村孩子心中隱忍的情緒并用電影的鏡頭語言娓娓道來。劉雨霖帶著這部電影參加了39個電影節,其中包括戛納電影節、東京電影節、意大利圣蘭托電影節等,并在各大電影節榮獲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最佳女演員等多項大獎。
劉雨霖希望通過電影把自己對于生活的感悟記錄下來,那里面是或悲或喜帶著溫度的人間氣息,所以畢業后,她把電影處女作的目光盯上劉震云的代表作《一句頂一萬句》,就一點也不奇怪了。但拿到這個劇本并不容易,首先劉震云不好說話,外人都以為劉震云是一個特別溫和幽默的人,實際上他在生活中沉默寡言,如果對方該做好的事情沒做好,他一定會發火。他對自己作品的被改編有著嚴苛的標準,首要一點是,導演必須得懂他作品背后的東西。
為此,劉雨霖做了充分的準備,她非常熟悉父親筆下的人物,其中最喜歡的就是《一句頂一萬句》,籌備這部電影時,這本書就是她的枕邊書,讀了有十幾遍。她給父親打電話:“其實這本書的精髓是渴望,這些尋找者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被我們忽略,但他們內心波濤洶涌。我要用干凈、溫暖的鏡頭語言,把這些人內心的洪流拍出來。”
對人物理解到位,足夠與眾不同,這讓劉震云決定將作品交出去。之后,劇本籌備耗時兩年,勘景三四次,籌備工作細致入微。冬天才開機,夏天已經確定好具體某場戲的某個機位怎么擺,全部演員提前兩個月體驗生活。劉震云偶爾去現場探個班,隨意找個地方圍著火爐跟人喝酒聊天,也不多管。他交給劉雨霖的話還是一句簡單的家規:“把會的事情一次性做好。”
劉雨霖是一個在大都市長大的名人二代,怎么會對農村中小人物的故事感興趣?面對別人眼中的不可思議,劉雨霖卻是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小時候父母雖然給了我足夠空間,可是我沒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那時候兩個禮拜能吃頓麥當勞或肯德基,吃頓稻香村的炸魚腸,就覺得生活很幸福了。所謂名人,是社會對他們的認可,而不是對我的認可。”
劉雨霖喜歡李安和許鞍華,伊朗電影《小鞋子》《一次別離》也是她反復看的電影,他們都有自己的節奏,不緩不急。許鞍華的《桃姐》中有個場景,是桃姐和大少爺在一起,大少爺開她玩笑:“聽說最近有人追你。”桃姐趕忙擺手,身子往后一縮。這樣的細節劉雨霖記得很深。
劉家有家訓:不著急。娛樂圈身處浮躁中心,若沒有強大定力,很難不受影響,不過劉雨霖卻是充滿自信:“著急是看你想要什么,著急是得不來的,不能受外界影響,我覺得我踏實,我定力強,是因為我心中有很多好故事,它們足夠把我鎮定在這,不受外界影響。”
劉雨霖顏值高,又拿過奧斯卡獎,這次拍攝《一句頂一萬句》,更是聲名鵲起,在圈子里轉型當演員是很容易的事,但她選擇一輩子只干一件事——做好導演就行,這是家訓。
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編輯 鐘健 12497681@qq.com

劉震云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