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思想的傳承
——音樂教育家蕭友梅的育兒經
王源
音樂思想的傳承
——音樂教育家蕭友梅的育兒經
王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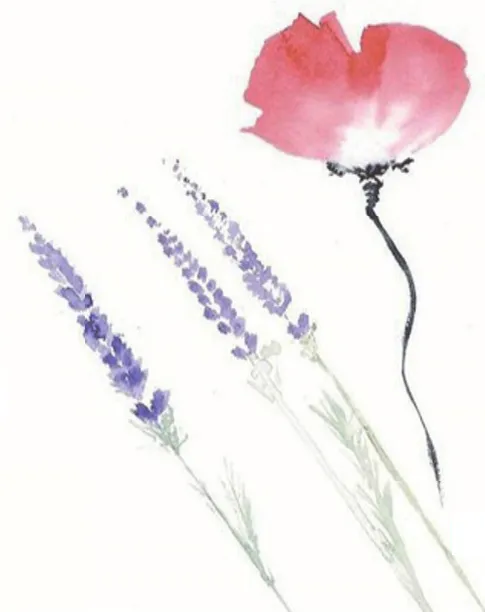
蕭友梅:近代中國音樂教育之父、專業音樂教育的開拓者與奠基者、音樂理論家、作曲家。他先后創辦了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北京國立藝專和上海國立音專(上海音樂學院前身),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早期現代音樂人才,如冼星海、賀綠汀、江定仙、李煥之等。除此之外,他還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早掌握西方作曲手法,并進行創作的作曲家之一,一生創作了100多首歌曲。
蕭淑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杰出的作曲家,創作了以中國傳統元素為主的九樂章構成的管弦樂曲《懷念祖國》等作品。她是蕭友梅的侄女,并且是蕭友梅引領她走上音樂事業的人生道路。
蕭勤:中國臺灣畫家。1956年他在臺北創辦“東方畫會”,是全中文地區第一個抽象藝術團體,還曾在米蘭創辦國際“點”藝術運動、國際太陽藝術運動及在哥本哈根創辦國際SHAKTI藝術運動,這3項運動均獲許多歐洲藝術家們參加與推崇。
蕭友梅的育兒經,確切地說,應該是他的音樂價值觀,他對中國音樂教育事業的奉獻之心。他為音樂執著,立志創辦屬于中國自己的音樂學校,所以他多方奔波、傾囊支持;他愛國,他希望用民族音樂激發人民的愛國熱情與意識,所以他即使身患肺結核,體力不支時,仍堅持主持校務,并為學生講課;他知道音樂人才的可貴之處,所以他教出了一批批杰出的愛國作曲家,冼星海就是其中一名。這樣一位以傳承音樂為己任的音樂教育者、近代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座豐碑,在家庭教育中,用身體力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與教育著孩子們。大概沒有什么比榜樣的力量,對人的影響來得更強烈吧。
隨叔進京,初學鋼琴
假如說,人的一生有諸多緣分,那么蕭淑嫻與音樂的不解之緣,就要歸功于蕭友梅。1920年,蕭友梅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當時年僅15歲的蕭淑嫻就跟隨他來到北京求學。從沒接觸過音樂的她,是在蕭友梅的引導下,開始了音樂之旅。當時她不僅就讀于蕭友梅任職的高等師范女子附屬中學,主攻鋼琴與琵琶,而且她的鋼琴的啟蒙老師也是蕭友梅。
雖然實為叔侄關系,但剛正不阿、不徇私情的蕭友梅,對她同其他學生一樣。由于家里只有一臺鋼琴,所以在蕭友梅的安排下,蕭淑嫻與其他同學要輪流按照他規定的時間進行訓練。為了讓他們更好地學習音樂,蕭友梅還特意編寫教材與練習曲目,與其他音樂人合作,在短短時間里寫下了近百首歌曲。在天高氣爽的日子里,即使只能空出一點點休息時間的蕭友梅,都會帶著蕭淑嫻這幫學生去北海劃船唱歌,讓她們感受自然中的音樂氣息。就是這樣無私的奉獻精神,也讓蕭淑嫻一生為之受益與學習,為之感激。正如前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于潤洋評價蕭淑嫻時說的那樣:“蕭先生一生在奉獻,奉獻作品,除必要的一點開銷外,從不要求報酬。”
為了培養蕭淑嫻這代女學生的新女性的思想與學識,蕭友梅抽空就給她們講解海外風俗、古代文學等知識,還特地讓武術師傅教她們學武術。因為在他看來,男女平等,女子練習武術,同樣可以增強體魄、鍛煉堅強的意志。當然,蕭友梅最為看重的是音樂素養的培養。所以,他曾規定音樂專修科的學生們每個學期都必須舉行幾次音樂會,所演出的曲目與體裁盡量多樣且豐富。這樣的規定,蕭淑嫻作為他的學生之一,肯定不例外。因此,她曾與同學們排過音樂劇,還在中國兒童劇院的舞臺上飾演過蕭友梅親自編排的英語說唱的小歌劇《五月花后》的主角,當時還掀起了北京兒童劇發展的熱潮。

既有血緣間的親情羈絆,又是啟蒙老師之恩情,這雙重關系下的蕭友梅對蕭淑嫻的影響不可不為之深刻。比如蕭友梅主張的是“古今中外的音樂都要學”的音樂理論,蕭淑嫻行走在音樂之路上,就堅定不移地貫徹。她1930年去比利時皇家音樂學院主修創作作曲,雖然之后學習的是西方音樂理論,但她依然深入鉆研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并將蕭友梅等音樂家提倡的古漢語聲韻學的理論與西方音樂中傳統的體裁相結合,去探索、貫通古今與中西的音樂之路。其實,蕭友梅對蕭淑嫻影響最大的是他的愛國之情。蕭友梅終生致力于建立中國的國立音樂學院,培養音樂人才,這深刻地影響著蕭淑嫻。在海外時,蕭淑嫻就積極地傳播中國音樂藝術。比如她會去洛桑、蘇黎世、伯爾尼以及日內瓦音樂學院等地做介紹中國文化藝術的演講,內容豐富,涵蓋了中國音樂、中國民歌及中國文字結構等方面。當時這些演講雖然規模不大,觀眾少則五六十人,多也不過三四百人,但影響不小,據說后來日內瓦大學因此還設立了中文班。在外生活越久,她越向往回到祖國的懷抱。在1950年,她毅然放棄了海外舒適的生活,帶著孩子,回到了中央音樂學院任作曲教授,還為了盡快地將自己在西方所學的知識傳播到中國,更不辭辛苦地在北京大學兼課,甚至還教干部進修班和留學生班等課程。蕭友梅的音樂傳承,就這樣地刻在蕭淑嫻的職業生涯中。
蕭淑嫻在回憶蕭友梅時,提及最多的是北平府右街蕭友梅家中的那間琴室。那里只放著一臺三角鋼琴,墻面正中懸掛著貝多芬的大幅畫像,下面中間是肖邦像,右面是孫中山先生所贈的照片,左面是他祖父蕭炎翹的像,鋼琴兩側懸掛著一副小篆對聯,上聯為“豈能盡如人意”,下聯是“但求無愧我心”。這幅小篆就是蕭友梅的人生寫照,他也是這樣影響著孩子們。正如蕭淑嫻的女兒蕭曼說的那樣,她的母親是以蕭友梅為楷模而走完了她默默奉獻甘為人梯的一生。
緣雖淺,情卻深
蕭友梅48歲才結婚,51歲才有了蕭勤。然而幾年后,蕭友梅由于勞累過度,肺結核等舊疾的困擾,去世了。這時的蕭勤還是一個需要父親呵護與照顧的孩子。但這樣短暫的父子緣分,對蕭勤一生影響卻很深。其實,每當你以為孩子不懂事、不記事時,父母的愛就像影子一樣,刻在記憶的深處,然后潛移默化地伴隨著他們的成長。蕭勤亦是如此。
蕭友梅是老來得子,固然很疼愛蕭勤的。在他出生后,蕭友梅就專門準備了一個筆記本,那里面記錄著蕭勤成長的點點滴滴,平時甚至會比“唱白臉”的母親更細心、更耐心。也許不茍言笑的父親的愛就是如此,有些話說不出口,有些事不知怎么表達,那么就記在心上,寫下來。除此之外,蕭友梅還特別注意音樂對孩子的影響力。幼年頑皮的蕭勤,無意地翻開一個歌劇唱片,準備聽時,蕭友梅看到后,給他換了另一張。問及原因,他告訴蕭勤,那張唱片的唱段過于壓抑與悲傷,他希望孩子接觸更加快樂、詼諧的音樂,培養出樂觀、開朗的性格。
對蕭勤成長來說,記憶最為深刻的是他父親一生為音樂事業的付出與犧牲。為了上海國立音專運作下去,蕭友梅基本把所得收入都貢獻給了學校,還要資助那些貧困的學生,他基本不留什么積蓄給家里。后來,戰爭的緣故,上海淪陷了。他們因為生活所迫,把家里最心愛的樂器與書籍都變賣了,甚至為了支持學校建設,把唯一的那架鋼琴也半賣半送地給了上海國立音專。即使在生病的日子里,蕭友梅依然關心學校建設與學生生活。為了省錢,他拖著病軀,也不愿打黃包車,就這樣步行去學校。正是這樣一位父親,讓從事繪畫藝術的蕭勤有了一種文化上的堅持和理想。因為父親的理想光輝、偉大而且遍地開花,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鼓勵。所以,蕭勤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成為繪畫藝術上的推動者與抽象化的倡導者。大概,這是一個孩子對逝世的父親最大的回報與告慰吧。
正如蕭勤在接受采訪時所說:“我的父親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嚴格,且具有遠大理想并能為之奮斗終生的人,所以我想在理想上與他共鳴。”蕭淑嫻也一直懷揣著對蕭友梅的感激之情,不論是在音樂上的教導,還是新女性思想的啟迪,都給予她們的人生,不一樣的色彩,才讓她們成長得如此的出類拔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