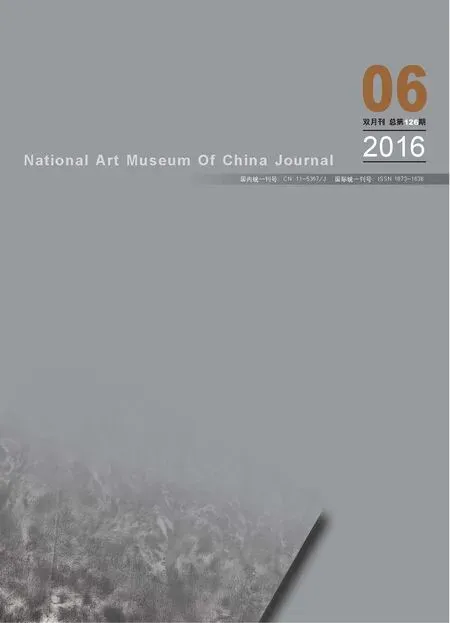主題重構(gòu)空間
——倫敦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藏品陳列展對于20世紀藝術(shù)史的敘述
□ 尚一墨(倫敦中央圣馬丁藝術(shù)與設計學院)
主題重構(gòu)空間
——倫敦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藏品陳列展對于20世紀藝術(shù)史的敘述
□ 尚一墨(倫敦中央圣馬丁藝術(shù)與設計學院)
美術(shù)館對于藝術(shù)史的敘述方式是多種多樣的,而如何通過空間與場域展陳作品所闡釋的藝術(shù)史,也許會帶來不同的觀看歷史的角度與方法。按照編年史的方式將作品展陳出來,雖然給人帶來了閱讀藝術(shù)史的時間演進性,卻也容易造成展陳觀看上的零亂;而按照主題來展陳雖然冒著打亂時序的風險,卻能給人形成主題鮮明、邏輯清晰的整體感受。當然,也可以將這兩者展陳方式相互結(jié)合,以期在整體藝術(shù)史的敘述中呈現(xiàn)條塊式的分割,達到歷時性與空間性的統(tǒng)一。在當代藝術(shù)史的陳列中,主題展陳或許更能體現(xiàn)策展人對于藝術(shù)史的思考,而主題展對于空間的重構(gòu)也更能顯示場域?qū)τ谧髌穬?nèi)涵的詮釋。位于倫敦的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Tate Modern)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自2000年開館以來,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為了不要強加給觀者一個藝術(shù)發(fā)展的單一框架,就一直通過主題展來全面呈現(xiàn)其國際化的20世紀藝術(shù)收藏,希望能夠打開觀眾對于藝術(shù)發(fā)展不同的解讀和思考。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還會定期地將它的收藏品重新組合或是更新,以此來啟發(fā)觀眾以不同的方式去看藝術(shù)發(fā)展的脈絡。(圖1)
在2000年首次揭面的泰特收藏,就打破了從時序的前后來縱觀歷史的觀念,而是以四種經(jīng)典的主題將20世紀的藝術(shù)藏品劃分在四個分別的展館里。這四個主題分別是裸體、風景、靜物和歷史性繪畫,泰特探索著這四個主題在20世紀的延續(xù)和蛻變,就有了我們所見的身體(the body)、環(huán)境(the environment)、真實生活(real life)和社會(society)四個展出主題。[1]單個藝術(shù)家、小型組合甚至是一些更復雜的小主題性的陳列被混合在了一起,其中經(jīng)常還會將不同時期和不同藝術(shù)家的作品進行并置,經(jīng)典名作可以在新的背景下去閱讀,而簇新的作品也可以和一些我們較熟悉的作品進行對話,這樣就避免了以一種按時間順序去展陳作品的傳統(tǒng)方式,讓我們總是以一種嶄新的視角去閱讀那些可能已被我們熟稔了的藝術(shù)歷史。
六年之后,新的布局中每個翼都有一個中心陳列,它們分別鎖定一個20世紀關鍵的藝術(shù)階段,而不是以作品內(nèi)容或者說是作品所表現(xiàn)的對象來排列的。這四個階段分別是:立體主義、未來主義和漩渦主義畫派;超現(xiàn)實主義;抽象表現(xiàn)主義;極簡主義。[2]而每個翼都通過分散式回應的方式來廣泛地、具有包容性地探索現(xiàn)代性。圍繞著中心陳列展開的其他小展廳也都探索著各自藝術(shù)階段的由來,同階段不同的嘗試或是其藝術(shù)階段的后續(xù)發(fā)展。這種新的陳列方式被分為四個大主題部分,分布在三層的兩個展廳和五層的兩個展廳:“States of Flux”、“Poetry and Dream”“Material Gestures”和“Idea and Object”。從2009年起,三組新的陳列被引進了。“Energy and Process”將貧窮藝術(shù)(arte povera)和20世紀70年代的反形式藝術(shù)(anti-form art)匯聚在一起,代替原先的“Idea and Object”。2012年新安置的“Structure and Clarity”代替“States of Flux”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烏托邦抽象主義為線索。“Transformed Visions”演繹的是對20世紀四五十年代藝術(shù)新的思考,它重新放置了部分“Material Gestures”的作品,但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強調(diào),就是作品在釋放抽象的同時也保有了所謂的具象、造型。[3]而如今在二層你會看到“Poetry and Dream”和“Making traces”,在四層則是“Energy and Process”和“Structure and Clarity”。
如上所示,在過去的14年中盡管陳列的布局發(fā)生了變化,但是可以說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的策展小組都選擇了以主題的方式去展示收藏,而放棄了以時間順序為主線的傳統(tǒng)陳列方式。主題的名字甚至陳列的結(jié)構(gòu)都在一直發(fā)生著變化,而這種變化實質(zhì)上正體現(xiàn)了不同策展人對于藝術(shù)史的不同解讀和概括。
較有吸引力的一組陳列顯然是“能量與過程”翼(“Energy and Process”)。圍繞著這個主題共展開了十個部分,其中包含了許多各式各樣的藝術(shù)形式,有繪畫、攝影、影像裝置、裝置藝術(shù)和雕塑。這組陳列是由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的Shooting Picture(圖2)和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Trip Hammer(圖3)的并置與對話作為陳列展開端的。兩件作品都對“能量和過程”提供了一個宏觀的解釋。這兩件作品都包含了一種材料的存在意識。塞拉的兩個不固定卻又達到平衡狀態(tài)的重鋼板,能夠讓我們意識到自然界中不可忽視的雄強壯健的力量——重力。在妮基·桑法勒作品完成的狀態(tài)中,你依舊能感受到顏料從聚乙烯纖維袋中被釋放噴出的那個過程。接下來你便會好奇為什么策展人將這兩件作品作為一對呈現(xiàn)?第二個小展廳很快就做出了回應。

圖1 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

圖2 妮基·桑法勒 Shooting Picture (石膏、顏料、線、聚乙烯、金屬絲和木頭) 143cm×78cm×8.1cm 1961年 Tate
第二個展廳突出的是現(xiàn)代主義和當代藝術(shù)的聯(lián)系。現(xiàn)代主義走出了古典傳統(tǒng)繪畫通過單點透視來創(chuàng)造幻覺的束縛。自1916年起,藝術(shù)家們像是伊萬·普尼(Iwan Puni)開始嘗試在繪畫中加入現(xiàn)成品。繪畫自身由此變成了一個物體,再也不是一個僅僅具有再現(xiàn)功能的媒介。與此同時,藝術(shù)家們開始致力于創(chuàng)造多點視角。甚至到了20世紀60年代,藝術(shù)家們將繪畫這種形式作為一種藝術(shù)手段或?qū)嵺`來探索和創(chuàng)造,從而打開了更多的可能性。豐塔納(Fontana)開始了刺穿畫布表面的行為,三維就此出現(xiàn)。策展人借此想表達當代的裝置藝術(shù)其實是通過繪畫——二維性演變而來的。
這組主題陳列的中心展區(qū)主要致力于那些強調(diào)創(chuàng)作過程,探索來源于自然和日常生活材料與形式的藝術(shù)作品,以及那些包含能量意識的藝術(shù)家們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于不同年代,來自不同國家的藝術(shù)家們的創(chuàng)作被放置在了一起,你可以宏觀性地感受到藝術(shù)家們不同的實踐。例如,意大利的藝術(shù)家們集中于使用破舊的材料,因而他們的作品在展出期間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細微變化。美國的藝術(shù)家們則對探索介于繪畫和雕塑之間的一種形式倍感興趣。作品的含義以及對于材料的選擇,則是基于每位藝術(shù)家的個人背景與個性意趣。你會發(fā)現(xiàn)策展人欲借此傳遞出一種文化和自然的關系。
除此之外,這組陳列也展示了藝術(shù)家們藝術(shù)表達所選的不同方式和媒介。意大利的藝術(shù)家將攝影變成了雕塑;中國的藝術(shù)家運用傳統(tǒng)繪畫再現(xiàn)了一個空的桶,隱含著一個有關存在哲學意識的表達。而近來藝術(shù)家們主要關注于如何使他們的雕塑作品和美術(shù)館空間進行相互作用。在這組展陳中,人們可以體會到空間的延伸——二維是如何演變成三維藝術(shù)的,藝術(shù)家是如何通過材料的使用使觀者意識到展館之外的空間和環(huán)境。
據(jù)對此展廳中心區(qū)域作品數(shù)量的統(tǒng)計(圖4),策展人是以一個客觀的角度來呈現(xiàn)當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的。他們開始關注除了歐洲和美國之外其他國家的藝術(shù)。而對于20世紀英國視覺藝術(shù)的相對忽視,則意味著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并沒有像巴黎和紐約的美術(shù)館那樣擁有大量知名的經(jīng)典大師的作品,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其實一直是致力于創(chuàng)造新的審美偏愛。
如今,策展人作為展品和觀眾之間至關重要的中介,不僅需要有博學的知識儲備,更需要能夠深入理解展品所面對觀眾的廣泛性。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的策展人根據(jù)作品內(nèi)容和想法的共同性,將產(chǎn)生于不同時代和背景的作品組合在一起,其實也冒著相當大的風險。就像Inés Gutiérrez所提出的:“藝術(shù)有時的確可以跨越地理和時間的界限,但是它同樣也是特殊環(huán)境下的產(chǎn)物。考慮到加強觀眾對于藝術(shù)的理解這些特殊情況需要被任何的公共機構(gòu)所清晰地概述和呈現(xiàn)而出。”特別是對于那些高度觀念性的作品,例如在“能量與過程”展廳中展示的貧窮藝術(shù)(arte povera),如果缺乏關于它的背景資料,那么將會導致展覽本身也許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4]盡管貧窮藝術(shù)主要的確是致力于對于不同現(xiàn)成物件和材料的探索,但是它也和它所處同時代的文化、政治和社會背景息息相關。而且強調(diào)意大利曾經(jīng)擁有的藝術(shù)氛圍造就了這種藝術(shù)風格也是十分必要的。而這些在展廳中都沒有被體現(xiàn)出來。皮諾·帕斯卡利的《陷阱》(trap)則在一群視覺上根本就不和諧與背景上無法相連的作品中,顯得十分孤獨。
在20世紀藝術(shù)演進的進程中,博物館和美術(shù)館如同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所做的那樣,將他們的永久性收藏以一種系列性的臨時展覽的模式呈現(xiàn)給觀眾,每個展廳都給觀眾提供了一種對于一個特定主題的封閉式的敘述。因而,你在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將會獲得四個關于20世紀藝術(shù)的不同體驗。除此之外,主題性的陳列方式強調(diào)的是一系列特殊的時間點,而并不是藝術(shù)發(fā)展宏觀輪廓的勾畫。因此,參觀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的陳列并不是一段輕松的旅程,主題性展陳要求你不斷地觀看也不停地思考。這里沒有一條單一的藝術(shù)發(fā)展史,有的是多個故事、多種情境和數(shù)不清的小細節(jié),等待你去探索。

圖3 理查德·塞拉 Trip Hammer(鋼鐵)274.3cm×331.5cm×134.6cm 1988年 Tate
通過參觀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的“能量和過程”這一主題展示,不難發(fā)現(xiàn)伴隨藝術(shù)作品展示的文獻資料對于20世紀70年代的觀念作品起著顯著的作用。這其中觀念裝置藝術(shù)將文獻資料納入其最終作品或者說最終呈現(xiàn)形式的一部分。對于這些高度觀念性的當代藝術(shù)作品來說, 那些為所屬作品提供的說明、釋義和背景文獻的標簽以及信息板對于幫助觀者更好地理解陳列作品,顯然是十分關鍵的。正如麥凱所指出的那樣,“展覽品成功地訴說出它的故事的,卻是通過其標簽信息和歷史材料的有效組織來實現(xiàn)的”[5]。因而對于策展人來說,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去呈現(xiàn)一系列明確而周密的文字材料。
古典藝術(shù)和現(xiàn)代藝術(shù)主要依賴于展墻去呈現(xiàn),但是對于當代裝置藝術(shù),它所處的周邊環(huán)境也是它作品自身的一部分。“能量與過程”其中的一個展廳正體現(xiàn)了策展人如今將注意力放在了對于空間的利用上。在展廳三中,十件作品被合理地安排在了同一個空間內(nèi)。而且策展人在此為觀者留有了足夠的觀賞空間,觀者可以圍繞每件裝置作品來回走動。就像哈拉爾德·史澤曼表明的,策展人應當將他對藝術(shù)作品的理解體現(xiàn)在他對該作品的空間設計與安排上。[6]菅木志雄的裝置作品(圖5)被安排在空間的中心區(qū)域,而并不是墻角,這就暗示了策展人的意圖是想讓我們注意到作品其中那個輕微的開口處。這種設計與安排充分體現(xiàn)了策展人對于藝術(shù)家想要表達內(nèi)容的深刻理解。[7]另外,美術(shù)館角落的空間也被策展人所充分利用。從墻角到地面,這種安排充分展示了藝術(shù)家班格拉斯對于形式、流動和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能量的探索。(圖6)

圖4 各個國家作品占“能量與過程”中心展區(qū)所有作品比重統(tǒng)計

圖5 菅木志雄 Ren-Shiki-Tai(石頭、磚塊、水泥和金屬絲) 65cm×337cm×344cm 1973年 Tate
通過游覽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的展陳,還不難發(fā)現(xiàn)策展人現(xiàn)今已將重點放在對于時間的設計上。在“能量與過程”的第一個展廳中,是兩幅誕生于不同時期的作品被擺放在一起來說明當代藝術(shù)的進程問題。接著,通過轉(zhuǎn)向?qū)τ诖饲艾F(xiàn)代主義末的作品回顧來呈現(xiàn)當代藝術(shù)的元素其實早已埋藏在現(xiàn)代主義之中。而周圍的小展廳,則展示了藝術(shù)家們對于這同一主題的各種發(fā)散式的回應。這種時間的處置方式,在本文一直強調(diào)的打破、挑戰(zhàn)傳統(tǒng)單一時間線的方式上去展示藝術(shù)史的同時,也給觀眾帶來了些許驚喜。除此之外,人們在白盒子空間里還能看到“黑盒子”,其空間主要承載著那些影像裝置作品。影像裝置藝術(shù)強調(diào)作品移動、互動和觀者有意識的參與的過程,這種藝術(shù)是動態(tài)的,是即時的,也具有偶發(fā)性特征。例如,其中祖米佛斯基(Zmijewski)的影像Blindly,只持續(xù)了18分41秒。“黑盒子”的引入不僅能增強了觀眾對于當代藝術(shù)強調(diào)過程性、并不看重最終結(jié)果的認識,而且也豐富了觀眾的視覺審美體驗。
作為收藏20世紀以來的藝術(shù)作品的美術(shù)館,泰特現(xiàn)代美術(shù)館對于藝術(shù)實踐的變化、公眾審美取向的變化以及收藏策略的變化等,做出了及時的回應,它的收藏是在不斷發(fā)展著的。不但它的藏品持續(xù)得到關注,它的展陳方式更是人們議論關注的焦點。無論它的這種探索能夠得到人們怎樣的贊賞還是批評,至少它已經(jīng)激發(fā)了廣泛的社會關注與討論,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免費開放的場所一直在鼓勵著我們?nèi)ニ伎妓囆g(shù)、思考我們生存其間的社會。
(作者按:此文寫于2015年年中,部分作品已被新的收藏代替,陳列的方式和主題一直都在發(fā)生著變化。)

圖6 琳達·班格拉斯 Quartered Meteor(鉛和鋼鐵于鋼制品基座) 150cm×168cm×158cm 1969年 cast 1975年 Tate
注釋:
[1]IwonaBlazwick and Simon Wilson eds.Tate Modern: The Handbook ( London : Tate Gallery, 2000).
[2]Balmond, S 2006,‘Designert to create Tate Modern’s new layout concept’, Design Week, 21, 11, p. 4,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EBSCOhost, viewed 25 May 2015.
[3]Matthew Gale,‘Fixed and Changing:New Displays
at Tate Modern’, in:Frances Morris, Chris Dercon and Nicholas Serotaeds.Tate Modern The Handbook (Tate; Reprint edition March 1, 2012),pp.31-32.
[4]Inés Gutiérrez,“Theme versus Time: Tate Modern’s Display of its Permanent Collection”, Vastari.com ? All rights reserved.
[5]McKay, T. (1982).“A Hierarchy of Labels”. Exchange, a newsletter published by the Wisconsin Historical Society 24, no. 4 (July/August).
[6]HaraldSzeemann, IndividuelleMythologien(Berlin:M erve,1985),p.234.
[7]這個缺口可以看出藝術(shù)家本人對于“內(nèi)”和“外”范疇以及內(nèi)外兩者的邊界和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