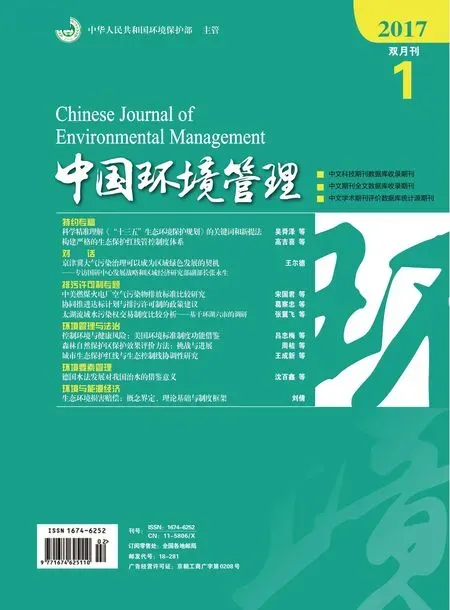控制環境與健康風險:美國環境標準制度功能借鑒
呂忠梅*,楊詩鳴
(1.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湖北武漢 430071;2. 美國南加州大學,加州洛杉磯 90007)
控制環境與健康風險:美國環境標準制度功能借鑒
呂忠梅1*,楊詩鳴2
(1.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湖北武漢 430071;2. 美國南加州大學,加州洛杉磯 90007)
傳統觀念下,環境與健康分屬兩個不同領域,美國作為最早遭遇環境與健康問題的國家,經過多年努力,形成了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體系和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框架,實現了對環境與健康風險的有效控制。美國對環境污染物的界定主要取決于其對公共健康的影響,將污染物分為普遍及對公共健康危害較大的污染物、一些污染范圍較小或對公共健康危害較小的污染物兩類,且采取不同的標準制定方法。在標準制定方面,主要是將有關科學共識轉化為可執行的環境標準。為了避免環境標準的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利影響,建立了包括科學論證、公開透明、周期性審查等較為嚴格的環境標準制定程序。美國賦予環境標準制度以控制環境與健康風險的功能,并通過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體系,實現對環境與健康風險有效控制的執法路徑,對解決中國目前存在的環境標準價值缺失、體系割裂、內容缺失等問題,實現環境標準的功能再造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環境標準;公共健康風險;環境與健康
引言
傳統觀念下,環境與健康分屬兩個不同領域,如何破解研究與管理難題,各國都進行了有益探索。美國作為最早遭遇環境與健康問題的國家,經過多年努力,形成了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制度和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框架,實現了對環境與健康風險的有效控制。當今中國,環境污染已成為影響人群健康的重要因素。控制環境污染帶來的健康風險,是建設“美麗中國”“健康中國”的重大課題。環境標準作為“數字化的法律”,是上升為法律的技術規范,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如何通過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制度,實現對環境與健康風險的協同管控、協調管理,美國的經驗值得在結合中國國情的基礎上予以借鑒。
1 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制度
美國的環境標準制度由相關法律和行政規則共同構成,聯邦環保局作為法律授權的標準制定與執行機構,依照法律履行職權。在標準制定方面,主要是將有關科學共識轉化為可執行的環境標準。經過多年的發展變化,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制度[1,2]。
自19世紀末以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美國的城市環境污染問題顯現。面對日益嚴重的下水道污染、固體懸浮物(黑煙)和其他工業廢氣污染,人們的認識并不相同:有人認為黑煙損壞市容、威脅公眾健康;有人卻認為黑煙可以殺菌;更多人認為空氣污染是經濟繁榮的體現,靠關閉工廠治理污染無異于因噎廢食[3]。
20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些工業城市發生了對污染的小范圍抗議,政府開始對污染進行調查,制定控制污染的標準和政策,試圖運用技術手段應對污染。但由于缺少可靠的測量數據,也沒有根本性的政策,城市的空氣隨著科技進步、煤炭質量和天氣等因素時好時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污染控制未見突破。法律上,大氣污染物的排放者眾多,難以證明某一污染者的責任。科學上,缺少觀測數據,少有研究能證明空氣污染對健康的損害。政府對工業煙塵危害的認識主要局限在美觀損害上,也不可能投入足夠資金、精力解決污染問題。此時雖有一些標準,但并未將健康因素納入。
引起政府對污染問題高度重視的是幾個空氣污染危害人群健康的事件。1943年洛杉磯因其“灼眼的煙霧”(eye-burning smog)引起媒體注意。1948年的多諾拉污染事件在5日內導致40人死亡,1.4萬人患上呼吸道或心血管疾病,更讓全國認識到空氣污染的危害[4]。這些促使聯邦政府采取措施,應對環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害問題,尤其是建立以保障人群健康為核心的標準與政策。1949年,杜魯門總統下令內政部設立一個委員會召開第一屆美國空氣污染技術會議,為各州治污政策提供技術支持和協調。1954年,馬歇爾總統下令健康、教育與福利部設立跨部門空氣污染委員會,以幫助各州和教育機構進行空氣污染的健康問題研究。此時,研究和治理空氣污染主要是地方政府而非聯邦政府的責任。加州于1955年在洛杉磯污染控制區(LAPCD)建立了基于污染監測的光化學煙霧三級報警系統。1959年州議會通過法案授權公共健康部門根據現有數據制定主要污染物的空氣濃度標準,并以此制定各排放源的排放標準。
聯邦政府對空氣污染立法始于1963年的《清潔空氣法》,該法第一次確立了控制空氣污染以保護公眾健康的法律制度。與此同時,全國范圍內的空氣污染監測信息系統基本建成。經過激烈的爭論,1967年制定的《空氣質量法案》采用“空氣資源控制”治理系統(air resource management,ARM)。特點是以空氣質量標準為首要標準來制定排放標準。而空氣質量標準的制定更多地取決于污染物對健康的影響,而非治理技術和經濟可行性a比較之下,Best Available Means (BAM) Approach則以排放標準為首要標準,也就更注重技術可行性。在一些歐洲國家,比如瑞典,當工業生產不高度集中(或規模較小),且主要排放源遠離城市時,采取BAM有可能比ARM更有效。(資料來源:Goran Persson, 1970. “Emission Standards for Stationary Sources in Swede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lean Air Congress.)。但是否運用這種方法,聯邦與各州存在較大分歧。如果采取ARM方式,工業發達地區的排放標準將比工業不發達地區更為嚴格。在各地排放標準不統一的情況下,勢必引起污染企業向環境標準更低的州轉移。因此,工業發達地區出于經濟考慮不愿意選擇ARM方式。
1970年修訂的《清潔空氣法》確立了聯邦政府在污染治理中的主導作用。授權新設立的聯邦環保局(USEPA)制定并執行主要污染物的環境標準,實現了污染治理權力由州向聯邦的轉移。《清潔空氣法》規定了6種主要工業空氣污染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光化學污染物、固體懸浮顆粒、鉛)為指標排放污染物(criteria air pollutants)。因其普遍性和對公共健康的顯著危害,采用ARM治理方式b相比于指標排放物,有害排放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s)則適用需考慮技術和經濟可行性的方法。。起初,由衛生、教育和福利部c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HEW),教育部門后被分出組成教育部,此部門改名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或衛生與公共服務部。負責制定針對各指標污染物的空氣質量指標文件(Criteria Air Quality Document),后來,這一任務改由新成立的聯邦環保局擔任。指標文件的作用是收集整理現有的環境與公共健康研究成果,根據這些科學研究制定出保護公共健康的指標污染物濃度標準(NAAQS)d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NAAQS)。,并要求州政府制定相應的排放標準和達標計劃(state implementation plan, SIP)。至此,以保障公眾健康為核心依據的環境標準制度正式確立。隨著《清潔水法》等更多環境保護法律的制定,這一標準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適用于水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等直接危害公共健康的領域。
2 公共健康在環境標準制定中的作用
美國對環境污染物的界定主要取決于其對公共健康的影響,或者說公共健康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污染治理標準的制定。如上所述,美國將污染物分為兩類:普遍及對公共健康危害較大的污染物(如指標空氣污染物)的標準制定直接取決于公共健康影響;一些污染范圍較小或對公共健康危害較小的污染物(如飲用水污染物和有害空氣污染物)的標準制定則在考慮公共健康影響外,同時考慮技術和經濟可行性。由于大部分類型的污染治理都始于國會相關立法(《清潔空氣法》、《清潔水法》、《安全飲用水法》等),其適用的標準制定方式(ARM或BAM)不可避免也受政治環境和非科學因素的影響。下面我們以指標空氣污染物(NAAQS)為主,其他污染物為輔,分析公共健康在環境標準制定過程中的作用。
2.1 數據收集或基準確定
確認某排放物為“污染物”需經過漫長的數據收集和測試,而確認污染源并從定性和定量上確定單一污染物對公眾健康的危害,更需要大量的毒理學(toxicology)研究和流行病學(epidemiology)研究。1970年最初的指標污染物標準所依據的科學數據相當有限,因此多有借鑒歐洲城市空氣污染的研究結果。
為了獲得更加可靠的數據,美國建立了專門的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機構,開展數據收集和科學研究a美國的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機構設立于19世紀80年代,由美國聯邦環保局(EPA)從事環境與健康監管方面的職能部門——研究與發展司(ORD)管理,主要職責是進行健康風險評價,為將環境與健康風險管理納入各項環保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務。ORD是根據美國環境與健康風險評價和風險管理的框架的要求,由EPA領導的多學科、多領域合作、協同工作機構。(資料來源:U. S.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Understanding Risk: Informing Decision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6;Regan M J, Desvousges W H.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Risks: A Guide to Practical Evaluations. Washington, D.C.: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1990.),目的是從定量上確定污染物對不同受眾的影響。相關科學研究分為毒理學研究和流行病學研究兩種。毒理學研究主要研究污染物在生物圈中的影響途徑和劑量效應。流行病學研究則試圖建立污染物與人的致病關聯。這些研究囊括了不同的人群、影響途徑和時間跨度。
由于總體人口受污染影響嚴重,早期流行病學研究多為觀察性研究(或稱自然實驗)。因為人體實驗不符合科學倫理,早期標準制定多基于(某一時期)污染物濃度和住院率/死亡率/特定發病率的關聯性。為了對公眾健康提供足夠保障,NAAQS標準一般低于可觀察到有影響的污染濃度最低值。這些最低值通常來自于低污染地區研究或以弱勢人群(兒童、老人、病人)為主體的研究,同時也會參考動物實驗的結果。
經過治理,隨著污染濃度整體降低,研究者得以通過觀察和實驗了解低濃度污染物對不同人群的影響。歷年數據的積累也使觀察污染物對人的長期影響成為可能。以指標空氣污染物為例,有些污染物在早期的指標文件中并未標明其長期危害,而近年更新的指標文件中收錄了相關研究,并承認其有長期危害。
將小范圍的公共健康研究結果轉化為宏觀的環境標準需要許多假設。比如,有害重金屬在土壤中含量標準不僅取決于其在食物鏈中的積累系數,也取決于人類對各種相關動植物的攝入。再比如,空氣污染物對人的長期影響不僅取決于污染物濃度,也取決于人的平均體重和壽命。美國聯邦環保局對這些基線做了明確的規定。
以上數據收集和研究成果共同組成了污染治理的指標文件,這是標準制定的基礎。文件包括對現有科學研究的選擇、匯總和整理,對污染物危害原理進行的定性定量分析,判斷其對公共健康(主要標準)及公共財產健康(次要標準)的損害,以此推出不影響公共健康和財產健康的空氣質量標準。
2.2 標準制定
根據法律授權,聯邦環保局負責將指標文件中的科研共識轉化為可執行的環境質量標準。
環境質量標準制定有其技術和政策復雜性。例如,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的標準制定是不同的,因其直接影響排放源的運行,所以空氣質量標準通常會包括平均值標準和峰值標準,測量單位也不盡相同。政策復雜性隨污染物而異,有些法案要求某些污染物治理不考慮執行成本(或技術和經濟可行性),另一些則不然。根據12866號和13563號行政令,大多數環境治理政策需要進行治理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RIA)來比較不同政策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對于需要考慮執行成本的污染物,RIA的結果直接影響治理政策的選擇。RIA主要涉及效益成本分析(benefit cost analysis)和成本效率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公共健康在RIA的效益成本分析中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對于污染治理政策而言,最主要的效益就是公共健康效益。因此公共健康效益的大小直接影響污染治理政策的可行性。計算公共健康效益分兩個步驟;首先是計算治理政策對公眾健康的直接影響,然后是把這種影響轉化為金錢并納入效益成本的計算。
以空氣污染為例,不同政策對公共健康的直接影響可分為五類:器官功能的減弱、呼吸疾病癥狀、曠工/缺課/求醫、住院及急診室接診,死亡。這五類影響由弱到強,而受影響人群依次減少。治污政策導致的環境質量提高可能在五類中的一類或幾類產生相應的健康效益,其公式為:
(某一類)健康效益=基線影響×f(空氣質量改變,某類影響的系數)×受影響人群
一項政策對公共健康的直接影響就為五類健康效益的總和。
確定了每類健康效益的受益人口后,有兩種方法可以把這種健康效益金錢化:
第一種是采用受益者負擔原則計算公共健康效益。這是一種基于問卷調查的計算方法。隨機受訪者在問卷中回答愿意為各種健康效益付出的金錢(willingness to pay),將不同健康效益的金錢價值加起來得到總的健康效益。
第二種方法是通過污染產生的治療費用(cost of illness)、曠工/缺課等導致的經濟損失來估算健康效益。這種方法首先估計每一類健康影響的價格(死亡最高,醫療次之,較低的影響種類可能不產生費用),乘以每一類受影響人群得出總健康影響(在數值上等于健康效益)。
目前公共健康效益的計算尚不精確,因污染物種類、污染程度、人群特點、地理差異而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復雜的空氣污染物,如固體懸浮顆粒,因其排放源頭和對健康影響的多樣化,其政策預期的空氣質量提高和相應健康效益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2.3 周期審查和標準修改
所有的環境質量標準都會經歷周期審查。《清潔空氣法》規定環保局應以五年為周期,結合新的研究成果更新指標文件及NAAQS。但在實踐中,每十年左右才進行一次周期審查,且各污染物不同。審查程序類似于新標準制定。從宣布周期審查之日,環保局開始收集整理自上次審查結束以來新發表的相關科研成果。文件收集通過自由投稿(經過同行審查的學術研究)和公眾聽證會等渠道。根據指標文件,環保局會撰寫(staff paper)工作人員報告,討論現有治理方案是否足夠以及如何改變。基于工作人員報告,環保局會提出對現有標準的修改意見,最終發布新標準(或不改變原標準)。從指標文件到新標準的發布,每一個文件都會根據公眾意見aNotice and Comment Period。及環保局科學顧問委員會bClean Air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CASAC。的反饋進行反復修改。
經過對20個世紀90年代以來積累的數據分析,表明空氣污染對人的健康沒有最低閾值,且空氣污染對人類生命和財產的影響日益復雜,因此環保局對標準周期審查進行了改革。這項改革在不改變環境標準宗旨和公眾參與方式的前提下,把原來的空氣質量評估和工作人員報告根據內容拆分為四個部分,明確了各文件的時間順序。首先,綜合審查計劃(integrated review plan)概述自上一次審查以來出現的新的科學和政策進展,根據這個計劃列出時間表,第二步的綜合科學評估(integrated science assessment)整理自上次審查以來新的關于環境質量和健康關系的科學證據。第三步的風險和暴露評估(risk and exposure assessment)則從公眾實際暴露的角度評估其風險。結合科學評估和風險暴露評估的結果,制定最終的政策文件(policy assessment),提出對環境標準的修改[5]。新的程序加強了政策評估、成本效益評估、風險評估等主要評估工具在標準制定中的運用。
新老周期審查程序簡單對比如下:
(老)空氣質量指標文件→工作人員報告→(環境標準)草案→最終標準
(新)綜合審查計劃→綜合科學評估→風險暴露評估→政策評估→(環境標準)草案→最終標準
除了對現有環境指標的周期審查和修改,聯邦環保局也可以根據排放物對公共健康的損害程度,依法添加或廢除污染物的環境標準。環保局可以在已確定的污染物大類(如指標空氣污染物、有害空氣污染物、可降解/不可降解水污染物)中加入新的物質。1978年,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就通過訴訟的方式使聯邦環保局把鉛加入指標空氣污染物中加以治理[6]。創建新的污染物類別則需要國會以立法的形式授權。比如,1990年《清潔空氣法》修正案建立了“有害空氣污染物”(HAP)新類別,詳細規定了環保局的治理程序和標準。
相應地,立法部門、公眾和環保組織、企業均可對環境指標或污染物本身提出質疑。如果企業或環境組織不滿意最終出臺的標準,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則會判決環保局制定的標準是否與其授權法案一致,即環保局在制定標準上是否有越權(over regulate)或瀆職(under regulate)的行為。
如果國會對環境質量標準有疑問,可以采取國會調查方式要求環保局提供更多信息。如果非政府團體(環境組織或污染企業等)對環境質量標準有疑問,可以通過訴訟讓環保局修改。由于指標空氣污染物僅以環境健康為依據,訴訟中尚未出現環保局因“標準太嚴”而敗訴的情形,但法院曾判決“環保局的標準制定沒有依據清晰的原則”而駁回環保局制定的標準或要求其增加解釋。對需要考慮技術經濟可行性的污染治理,法院理論上有可能判決環保局標準過嚴,相應地,在制定這些污染物的排放標準時環保局也會更多地參考工業界的意見。
從標準制定程序可以看出,無論是否考慮技術和經濟可行性,公共健康因素對于標準制定都具有重要影響。對于不考慮執行成本的污染物,依據環境與健康風險的評估結果確定環境標準;對于需要考慮執行成本的污染物,公共健康效益是成本效益評價的重要指標。
3 環境標準數值的科學不確定性及其克服
把公共健康作為環境質量標準制定的唯一依據在法律上面臨一些挑戰,其中之一就是設定“可接受的” 污染程度。以指標污染物為例,20世紀90年代新的研究表明,許多污染物并無對公共健康造成危害的最低濃度,被稱作非閾值污染物(non-threshold pollutant)。這意味著即使停止所有工業活動(或將空氣質量標準降為背景濃度),人類依然面臨健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確立“可接受的健康風險”就成了一個重要而有爭議的話題。環境標準的制定不僅與科學研究的數值有關,更與人類的風險接受程度有關。健康風險具有不確定性,標準制定勢必在“聽從科學”的同時加入裁量權。
環境質量標準的制定可采用多種方法,包括“零風險”方法a如果環境標準值設定在環境背景值水平來最小化風險,由此來消除那些除自然發生以外的全部風險,即為“零風險”方法。參見:COGLIANESE C , MARCHANT G E,流沙:科學在風險標準制定中的局限//金自寧編譯.風險規制與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2。、可接受風險方法b可接受風險是指預期的風險事故的最大損失程度在單位或個人經濟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最大限度之內,具體是指一個具體的組織確定可接受風險依據的最低準則是組織適用的法律法規要求,在此基礎上,組織可依據其方針體現的管理意圖,提出高于法律法規要求的可接受風險界定準則。參見:岑慧賢,等.可接受風險的界定方法探討.重慶環境科學,2000(6)。、避免不可接受的成本方法c這種方法不是只關注收益,而是將規制成本當作關鍵性的因素。換句話說,環保部門可以將環境標準設置得盡可能低,只要使守法成本低于某一可接受的水平。這種方法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不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或造成嚴重經濟混亂就能做到。說一個標準是可行的,意味著其成本是可接受的。參見:COGLIANESE C, MARCHANT G E, 流沙:科學在風險標準制定中的局限//金自寧編譯.風險規制與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2。、成本與收益平衡方法d綜合考慮成本和收益,可以通過分析管理水平的設定來最大化凈收益。已有幾項環境立法要求行政機構在設定分析表中平衡成本和收益。參見: COGLIANESE C, MARCHANT G E,流沙:科學在風險標準制定中的局限//金自寧編譯.風險規制與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12。等。但這些方法應該在何時或者何種條件下使用,并沒有明確的規定。20世紀90年代,聯邦環保局修訂的臭氧和顆粒物標準,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昂貴的規章。環保局估計,到2020年,這些標準可使每年的成本增加450億美元——這比所有其他生效的《清潔空氣法》的年度成本總值還要大[7]。在向國會說明時,聯邦環保局明確地排除了“零風險”方法和“可接受風險方法”,但承認了避免不可接受成本的考慮。在1999—2001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的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 V. EPA案件中,最高法院要求聯邦環保局解釋臭氧濃度標準(0.08ppm)的依據,這是針對非閾值污染物的標志性案件。應法院要求,環保局解釋:針對非閾值污染物,環保局依據健康危害的本質、嚴重程度、易受影響人群及現有知識的不確定性來制定標準。之所以把標準定為0.08ppm,是因為從0.09ppm 到0.08ppm受影響人群顯著減少,而從 0.08ppm到0.07ppm,其健康效益較小且不確定性較大。最高法院在判決中接受了環保局確定空氣質量標準的方法,卻不認為0.08ppm的標準比0.09ppm和0.007ppm更“為公共健康提供了足夠的保護”。換言之,最高法院要求環保局提供“明白易懂的”標準制定原則(intelligible principle)[8]。無論如何,環保局的答案并不讓最高法院滿意,而最高法院也無法根據法案給環保局指出更好的原則。
可見,環境標準的制定并非僅僅依靠科學。環境標準數值的確定總是與經濟、技術條件相聯系,其環境質量標準制定中基于科學和基于裁量權的比例也不明確。因此,美國環保局長經常被環保機構指責標準過于寬松,而被企業界指責標準過于嚴格。有學者指出,環保局在制定環境標準時往往將政策決斷偽裝在科學客觀性的外表下[9],通過夸大科學的作用來規避其為隱含在決策中的價值判斷進行說明的義務。由于價值判斷和政策選擇普遍存在于環境標準制定過程中,如何明確科學在標準制定中的角色,抽離出價值判斷、政策選擇的空間,就成為標準制定的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環境標準是一種預測活動,而所有基于預測而進行的活動,都存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只是相對于已經高度現實化的危險而言,風險的不確定性程度更深[10]。環境標準的制定是一種“面向未知而決策”的風險規制行為,需要設計相應的制度克服其不確定性。為使不確定條件下理性的風險決策成為可能,美國在法律上規定了方法和程序,以增強標準的合法性和效率。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環境法和環境標準的合法性基礎“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結果里”[11]。這些方法大致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3.1 確定性系數和建模
為了平衡和彌補不確定性,在制定空氣質量標準時有必要使用“確定性系數”,以便降低吸入效應可能帶來的風險。其具體做法是,將標準值除以一個或者若干個確定性系數,使得最終確定的空氣質量標準(其實質是可以容忍的風險)比標準值低若干倍,即位于大多數可以觀察到吸入值—效應關系的區間之下。一般來說,下述情況可以使用確定性系數:①將動物實驗的結果轉移到人體;②將在身體健康的人群中實驗的結果轉移到身體虛弱的人群(老、病、幼、孕等),因為空氣質量標準原則上也應該保護這些身體虛弱的人群;③將在特殊的試驗條件(用較高劑量進行的短期試驗)下獲得的結果轉移到真實的暴露條件(長期暴露在較小劑量中);④將由試驗法或者流行病學方法獲得的標準值,外推到一個更低的、未知的吸入值—效應值(“無效應”值)。
為減少不確定性,環境質量標準的制定需要對人類行為和污染物影響方式進行一系列假設。為此,聯邦環保局采用了兩種主要方法。兩種方法都基于對人類日常活動和污染物影響渠道的大量數據采集。第一種方法是根據現有數據估計各種人類活動的暴露系數,確定其對不同污染物的暴露和風險。為此,制定了“暴露評估指南”(guidelines for exposure assessment)和“暴露指數手冊”(exposure factors handbook)。“暴露指數手冊”制定了17個方面影響暴露的系數類別、包括呼吸渠道、皮膚渠道、體重、生命長度、植物食品攝入、肉及奶類攝入、魚類攝入等。這些系數廣泛應用于水質和空氣標準,而各主要環境污染物又有自己更詳細的系數系統。
對于一些復雜污染物,如空氣污染,其傳播渠道和人類暴露方式都難以用簡單的暴露系數來計算。需要用大量數據構建動態模型來模擬人類的暴露風險(humanexposure modeling)。暴露模擬會動用相關數據庫,包括微環境數據庫、通勤暴露數據庫、人口統計數據庫、空氣交換律數據庫等。聯邦環保局在制定空氣質量標準時就使用了空氣污染物暴露模型(air pollutants exposure model,APEX)來模擬光化學污染物和空氣中有毒物質對移動人群在不同微環境(戶外、室內、車內)的暴露程度[12]。就指標空氣污染物的標準制定,環保局采用的是證據—風險結合的方法。若聯邦環保局在草案中提出一個標準的范圍(而非數值):其上限取決于證據,即高于上限,健康危害可信的增強;而下限取決于風險,即低于下限的標準,健康收益會顯著減小,其不確定性會顯著增強。
3.2 注重標準的論證環節
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如何使理性的風險決策成為可能?從社會維度觀察,風險和不確定性不僅是環境管理科學的特征,也源于決策者與公眾之間的視角分歧。對一項風險,即便計算得再合理,對那些沒有參與決策的人而言,也是危險的。因此,不管一個環境標準在專家們(決策者)看來是多么理性,在法律機構、企業和普通公眾眼里,個體永遠是這些專家所做決策后果的波及者,更易對風險決策的理性基礎持懷疑立場。為減少這種“視角分歧”,標準制定機構應注重環境質量標準的論證工作。結合科學研究和大數據模型進行推導和論證,最終形成的空氣質量標準,不僅應包括環境質量標準的數值,還應有闡釋這個數值的推導依據、各種假設和對知識不確定性的審慎處理。讓被管理者、公眾和將來的決策者理解和認同現有的標準。
3.3 標準制定過程的透明化
透明化既包括環境標準的制定過程應遵循相關的程序規章,也包括對這一過程中存在的知識不確定性以及為應對不確定性所采取的措施進行透明化處理。首先是環境標準制定機構的工作流程本身應具有極高的透明性。對待知識的不確定性,理性的態度是反對隱瞞或者縮小,主張“最大限度的透明化”。為此,標準制定機構不僅要重視標準的科學論證,更要做出合理易懂的解釋,讓被管理者和公眾能夠理解,更好地促進社會參與[10]。
透明化的決策過程有助于把分歧消除在政策制定階段,減少執行過程中的各方阻力。在知識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聯邦環保局和科學界、民間和企業的意見交換至關重要。近年來,聯邦環保局改革了指標空氣污染物周期審查程序,將主要文件由兩個分拆為綜合審查計劃、科學評估、風險暴露評估、政策評估四個,科學咨詢委員會(CASAC)和民間/企業可以對每個問題提出質詢并得到聯邦環保局的回復。增強了科學界和各相關利益團體,包括被治理者的參與度,使標準更容易執行。
3.4 標準修訂的動態化
環境標準制定需要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新的知識產生時,及時將其納入標準體系。隨著科學研究的不斷推進,以今天的研究“現狀”為基礎制定的標準,用今后的知識“現狀”來判斷,就可能顯得陳舊和不足。因此,如何使標準回應不斷變化的知識“現狀”,也是空氣清潔委員會合理地應對知識不確定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聯邦環保局對環境標準制定中的公眾參與規則和頻繁的周期審查體現了這種動態的治理方式。
此外,如果社會、企業、立法和執法機構對環境標準或者執法過程有質疑,多會用訴訟和國會調查的方式來解決。比如,聯邦環保局由于種種原因,包括等待新的科學成果而推遲五年一度的周期審查。環保組織可以提起訴訟,讓法院責令環保局在相應時間內完成審查。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也可以環境標準過高或過低為由提起訴訟。法院雖然很少判令環保局修改標準,但常會讓其對標準做出解釋,或者駁回某些爭議標準。
4 美國運用環境標準控制環境與健康風險的啟示
美國的環境標準制度歷經污染物控制—損害后果控制—健康風險控制,由以州控制為主到以聯邦控制為主的過程,逐步建立起了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制度,并賦予其環境與健康風險控制的功能。對環境與健康形勢已十分嚴峻、控制環境與健康風險迫在眉睫的我國,非常具有啟示作用。
4.1 我國環境標準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環境與健康管理實際上處于相互分離狀態,標準的制定也基本上相互獨立,現有的環境標準制度不具備控制環境與健康風險的功能。以美國環境標準制度為鏡,可以發現我國環境標準制度在控制環境與健康風險方面的明顯不足。
(1)價值缺失。環境標準制度沒有確立保障公共健康的核心價值。迄今,我國由各部門、各層級累積制定的各類環境保護標準已達1400余項,但未在法律上明確環境標準制度的核心價值,更未圍繞保障公共健康這個核心來構建環境標準體系,導致我國現有的環境標準不具有環境與健康風險控制的基本功能。
(2)體系割裂。環境標準與衛生標準缺乏關聯。環境與健康監管涉及環保、衛生兩個政府部門,需要有統一的執法依據與執法手段實現協同管理。我國不僅未將公共健康考慮納入環境標準,而且環境標準與衛生標準“各自為政、相互割裂”,沖突之處頗多,無力控制因環境問題引發的公共健康風險。
(3)內容缺失。環境與健康風險控制的指標缺失。許多與人群健康有關的重要指標并未納入環境標準體系。盡管近年來做了一些努力,但由于環境標準制定的基礎薄弱,缺乏環境基準,缺乏建立公共健康指標的基礎數據,我國的環境與健康標準的內容單薄,無法回應頻繁發生的環境污染影響人群健康事件的需求。
4.2 我國環境標準制度的功能再造
可以看到,“十一五”以來,環保部針對環境健康風險管理的實際需要,加強政策引導,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基礎研究,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的環境與健康科學研究基礎十分薄弱,環境與健康科學研究創新能力不強,還不足以支撐我國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體系。為此,我國迫切需要借鑒美國的思路,建立完善的環境標準制度。
(1)確立“保障公共健康”的環境標準制度價值目標。環境標準作為“數字化的法律”,是由法律確立的正式制度。美國的環境標準制定、修改、實施都強調其合法性問題,判斷合法性的尺度就是環境標準制度的價值目標。在這個意義上,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制度價值目標至關重要,它直接決定著污染物界定、指標體系建立、標準實施的合法性。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通過立法方式,明確宣示環境標準制度的價值目標,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體系。
(2)將與環境污染有關的公共衛生指標納入環境標準體系。建立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體系,關鍵在于融公共健康與環境標準于一體。從美國的經驗看,遵循環境與健康風險產生的規律,以公共健康效益主導環境污染物的界定和治理,是有效管控環境與健康風險的成功經驗。我國可以借鑒這個做法,將現有的相互分離的環境標準體系和公共衛生標準體系進行有機融合,根據環境與健康風險控制與管理工作的范圍和需求,建立環境與健康風險控制標準、環境與健康影響評價類標準、環境與健康損害判定類標準三大標準體系。
(3)健全環境標準的內容。完善的指標體系與科學的量值是標準的生命,美國對于指標體系與量值的確定有相對完善的方法。比如,確定“指標空氣污染物”,對有不同健康影響的污染物采取不同的取值方法等,這對于我國環境標準體系實現從“污染源”到“環境介質”再到“風險防范”跨越的意義重大。現階段,我國應著重加強從“人體暴露”到“健康風險”階段的標準體系建設,將現有的環境標準體系延伸到環境與健康標準體系[10]。
(4)完善環境標準的制定程序。科學合理的環境標準制定程序是實現環境標準價值目標的不可或缺環節。美國在環境標準制定、修改和執行過程中,通過不斷完善程序性規定賦予環境標準科學研究以社會功能、實現科學性與民主性的平衡、克服標準不確定性帶來的社會問題等,這些經驗都非常值得學習。我國至少需要建立環境標準制定的科學性保障程序、環境標準制定與修改的審查程序、公眾參與程序、環境標準實施評估程序等。
(5)建立環境標準研究長效機制。環境與健康風險不僅將長期存在,而且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自然環境的變遷而發展變化,環境問題對公共健康的影響也需要長期不間斷的數據積累才可能得出明確的結論,為此,美國在聯邦環保局專門成立的環境與健康風險評估機構,組織長時期、大跨度、廣空間的科學研究,為以保障公共健康為核心的環境標準制度的有效實施提供了堅實的科學研究基礎。我國也應該由國家組建專門的環境與健康風險評價中心,對我國的環境與健康問題進行持續性、大范圍的研究,為環境標準的科學建立與合理適用提供保障。
[1] 保羅·R·伯特尼, 羅伯特·N·史蒂文斯. 環境保護的公共政策[M]. 穆賢清, 方志偉, 譯. 第2版. 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46-250.
[2] 呂忠梅, 劉超. 環境標準的規制能力再造——以對健康的保障為中心[J]. 時代法學, 2008, 6(4): 11-18.
[3] CHOW J, BACHMANN J, HSU Y C, et al. Will the circle be unbroken: a history of the U.S.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J]. Journal of the air & wast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7, 57(10): 1151-1163.
[4]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EB/OL]. https://www.epa.gov/air-research/historyair-pollution.
[5]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Draft integrated review plan for the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for particulate matter[R]. EPA-452/D-16-001. North Carolina: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6.
[6] MCCLELLAN R O. Role of science and judgment in setting national ambient air quality standards: how low is low enough[J]. Air quality, atmosphere & health, 2012, 5(2): 243-258.
[7] 巴魯克·菲施霍夫. 可接受的風險: 一個概念建議[J]. 湯雯雯, 譯. 交大法學, 2011, 2(1): 85-105.
[8] FORMAN A. A call to restore limitations on unbridled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s: American trucking ASS’NS V. EPA[J]. Indiana Law Review, 2001, 34(4): 1477-1505.
[9] 史蒂芬·布雷耶. 打破惡性循環: 政府如何有效規制風險[M]. 宋華琳, 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1-8.
[10] 陳春生. 行政法上之預測決定與司法審查[M]//陳春生. 行政法之學理與體系. 臺北: 三民出版社, 1996: 1-183.
[11] 周志家. 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風險管理——以德國大氣質量標準化為例[J]. 公共管理研究, 2010(8): 19-31.
[12]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uman exposure modeling-air pollutants exposure model[EB/OL]. https://www. epa.gov/fera/human-exposure-modeling-air-pollutantsexposure-model.
Controlling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Risk: Lessons from Environmental Standard-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LV Zhongmei1*, YANG Shiming2
(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2.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90007, USA )
Environment and health have long been treated as separate public policy domain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was among the first countries that suffered from environment-induced health problems. Over the past decades, it has established the public health-oriente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health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effectively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fro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dentifies and categorizes pollutants into two categories by their health impact, and regulates them accordingly. To minimize the effects of uncertainty by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is framework features vigorous and transparent standard making and periodic review, encourag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all stages.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with public health offers a clear mandate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makes public health more implementable. The US approach of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with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gives important insight into solving the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unclear mandate problem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public health risk; environment and health
X321
1674-6252(2017)01-0052-07
A
10.16868/j.cnki.1674-6252.2017.01.052
*責任作者: 呂忠梅(1963—),女,法學博士,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兼職教授,主要從事環境法律與政策研究,E-mail: 250269528@qq.com。
楊詩鳴(1988—),女,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和國際關系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比較環境政策、國際環境治理,E-mail: 3050730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