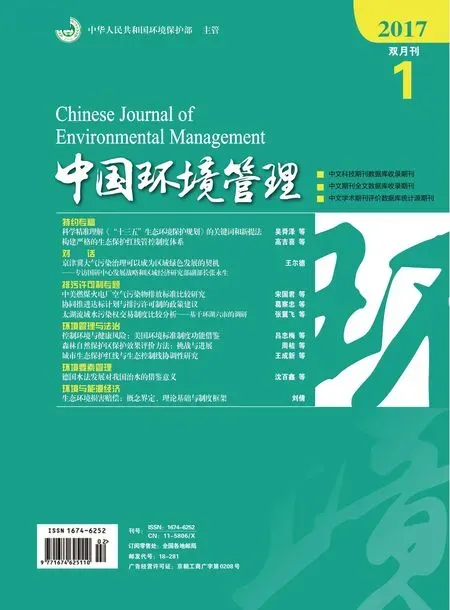德國水法發展對我國治水的借鑒意義
沈百鑫,鄭丙輝,蔡木林,李敏,王海燕*
(1. 亥姆霍茲環境研究中心,德國萊比錫D 04103;2.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12)
德國水法發展對我國治水的借鑒意義
沈百鑫1,鄭丙輝2,蔡木林2,李敏2,王海燕2*
(1. 亥姆霍茲環境研究中心,德國萊比錫D 04103;2.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12)
本文從深受歐盟水政策影響的德國水治理的歷史發展和基礎理念出發,對德國《水平衡管理法》的法規框架和總則進行了闡述、分析與比較。德國經驗表明,在法治框架下,依可根據持續性原則,對水事進行綜合治理。只有根據可持續性原則和通過法治,才能長期確保水安全,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保持水體清潔和維護生態平衡,確保當代及后代人的環境與發展權。水事綜合治理原則不僅要通過協調水體使用與保護之間的關系,來調整環保在相對于經濟和社會的傳統不平衡地位,更要遵循自然水循環的本質特征。建議我國在《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訂中,需要基于我國現實技術支撐的易操作制度,來實踐可持續性原則和水事綜合治理原則,強化法律間的協調。同時,還在立法技術上提出了若干建議。
可持續水治理;綜合水體保護;德國水法;水事法治
引言
本文從考察德國水治理的歷史發展和法規框架及《水平衡管理法》(WHG)(以下簡稱《水法》)的總則規定出發,理解德國水治理理念。為了有助于我國水治理,本文嘗試對我國水治理提出幾點建議。
1 德國涉水法規的框架與發展
自1976年起,德國水法的多次修訂就與轉化歐盟水相關法律緊密聯系在一起。為了更好地適應歐盟水法的發展,理順聯邦與州之間的權限與責任關系, 2006年德國推動了“聯邦制改革”,對聯邦與州之間包括水事領域在內的環境事務管理權,重新予以規范和界定:刪除了《基本法》原第75條規定聯邦政府的框架性立法權限,并將第74條聯邦政府的競爭性立法權限擴展到整個水事管理領域。在自然保護和水事領域,聯邦首次實現了制定完整法規的權限[1]。
德國水事管理主要是源于行政治安法意義上的監管,包括對水體使用進行規范和禁止(水體使用許可制度)、經濟性措施以及規劃機制。在聯邦立法層面,《水平衡管理法》與聯邦《污水征費法》(于1976年制定,其后也同樣經過多次修訂)一起組成水事基本法律。在聯邦法律層面,其他屬于水事治理內容的,還有《洗滌和清潔用品法》和《水協會法》以及《聯邦河道法》;作為行政條例的,包括《污水排放條例》《地下水保護條例》、《地表水保護條例》《飲用水條例》及《工業污水處理設施和水體使用的許可和監管條例》,還包括對水有害物質的規定《關于處理水危害物質設施的條例》。由此,《水法》得到進一步具體化。人類社會生活的錯綜復雜也就決定了法律也必然是相互緊密關聯的網絡體系。除了專門的水事法規,《肥料法》和《循環經濟和固廢法》也有規定污水處理,在《礦產法》中規定了礦區廢水的處理,還有其他特殊性的水體保護法規,如《油污法》《化學品法》和《原子能法》等規定。同樣在聯邦《土壤保護法》《規劃法》《建筑法》《自然保護和景觀維護法》中,也有與不同環境相關部門法之間的銜接,有涉及水體保護相關的規定。
原《水法》在1957年頒布后到2009年共經歷了七次修訂,現行《水法》于2009年重新編排后頒布[2]。這次重新頒布也與德國《環境法法典》編纂努力有關。在20世紀90年代《環境法法典》編纂曾遭遇過一次失敗。2006年又再次被提上立法進程,但2009年年初,因為各州對綜合環境許可的不同認識,法典編纂再次遭到抵抗。作為替代方案,只能對水管理、區域規劃以及自然和景觀保護領域,在現有完整立法權限下制定單行部門環境法。在法典編纂過程已相當成熟的水管理草案基礎上,聯邦政府于2009年3月向聯邦議會提交了新的水管理法草案,并于7月31日頒布。新水管理法主要解決四個任務:①以完整的法規代替原先的聯邦框架法規;②改善復雜和混亂的水事法規,系統化和簡化《水法》,以易于理解和實踐;③以聯邦統一的法規轉化歐盟法規定;④在有必要形成聯邦統一法規的前提下,將原在州法中規定的領域轉移到聯邦法中去[3]。聯邦新《水法》仍然承襲了原法規的大量內容,但也重新表述條文和重新編排結構,而且也大量吸收了各州水法中的內容。這是德國首次制定的直接適用和全國統一的水管理法。總體上,德國水法也沒能超脫于歐盟水事政策與法律,而是日益受到歐盟政策與法律的影響,處于向整個歐盟的水事政策與法律融入的過程。所以,一方面為歐盟輸送德國的經驗與創新,另一方面又融入水治理和環境治理的歐盟框架之中。
整體看德國《水法》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①反映了社會對水治理不斷變化的訴求,體現為立法中不斷妥協的過程;②水法私法特征不斷式微,公法特征不斷增強,公共利益成為優先保護考慮。在水事法律條文上,盡管以公法為主,但私法規定依然包括在其中[3];③在法規層級框架上,形成歐盟—德國—聯邦州這種層次關系,同時為了落實重要規定以行政條例來補充;④雖在具體行政執行上,各州仍然具有壟斷地位,但聯邦政府通過制定相關的詳細規則來影響法律的統一實施,立法權限日益向聯邦層面轉移;⑤從現狀來看,聯邦還需容忍各州在一定范圍內可根據當地實際,制定偏離于聯邦法的州水法規定,但對于設施與物質相關的規范除外;⑥水事管理具有獨特性,水體使用的許可審查,很難予以歸類定性,更是獨成一類。
2 德國《水法》的總則規定
德國《水法》第一章對立法目的、適用范圍、核心概念、水體使用與水體(水資源)所有權和土地所有權之間的關系,以及基本義務做了規定,是對水治理的理念和原則性規定[4]。法律規定是所有表述中最為精確和完整的,考察國外經驗時,對法條明確是很有必要的。《水法》第一章中這五條規定也就為整個水管理明確理念、界定框架奠定了基礎(對這部分法規的深入理解請參見《德國水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水平衡管理法〉總則規定研究》一文)。因此,它被視為《水法》向外與憲法與民法以及其他行政法銜接,向內對具體的水治理規定,指明了路徑,限定了范圍。
對德國《水法》第一章的認識,是理解德國水治理的基礎。第一章共五條規定:第一條立法目的中,有序的多層次立法目的體現了人類涉水利益的優先秩序;第二條是適用范圍,根據綜合水體管理界定了法律的適用范圍和規范客體;第三條是概念定義,集中的概念定義為水事管理提供了統一的知識基礎,為原則、規則和標準的實施提供了明確適用的前提;第四條明確了水體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關系,區分了水事治理的私法秩序和公法秩序;第五條規定了水法中基本的謹慎義務,體現了“水體保護,人人有責”。
第一條規定了立法目的:“本法之目的,是基于可持續水體管理,保護作為生態平衡的組成部分、作為人類生存基礎、作為動植物生存空間以及作為可利用物質之水體。”
第二條是適用范圍:“(1)本法適用于以下水體:1.包括地表水體,2.沿海水體,3.地下水,以及同樣適用于水體之局部。(1a)第23條和第2章第3a節的規定適用于海洋水體。對管理沿海水體適用的規定不受影響。(2)對水體管理次要意義的小型水體,尤其是作為道路組成部分的路邊溝渠,灌溉與排水溝渠以及療養泉,各州可作與本法不同之規定。本款對依第89條和第90條的水體改變之責任不予適用。”
第三條對基本概念進行了明確定義,基于篇幅關系不詳細列舉。可將《水法》的15個基本概念劃分為四類:①法律適用范圍和規范對象:地表水體、沿海水體、地下水、人造水體、顯著改變的水以及水身分為一組;②規范的客體:水體特征、水體狀況和水質分為一組;③規范的手段(管理的途徑):有害的水體改變、先進技術水準和歐盟環境審計為一組;④最后體現流域統一管理理念:流域(集水區)、支流域(支集水區)和流域單元為一組。在新修訂中又補充了“水使用”和“水服務”兩個概念。這些概念定義,其實是整個《水法》的核心點,但又需要與隨后的具體法律相結合,其后的具體條文又正是基于這些概念之上而展開的。
第四條規定水體所有權和土地所有權與水體使用主張的關系。“(1)聯邦河道的所有權,依《聯邦河道法》的規定,置于聯邦政府。只要依本法、基于本法頒布的法規或其他水法規定中對水體所有權之義務,同樣將聯邦作為聯邦河道所有權人。(2)流動的地表水體之水和地下水不具所有權權能(或者屬性)。(3)土地所有權沒有權利實施:1.需要行政審批的水體使用,2.水體建設。(4)只要使用得到行政機關的許可或者不需要行政許可,水體所有權人和使用權人必須容忍第三人的使用。這不適用本法第9條第1款第3項規定情況。(5)其他對水體所有權規定適用州法。”
第五條規定了基本的謹慎義務。“(1)每個人都有義務,在實施可能對水體有影響的措施時,根據情形采取必要之謹慎,以:1. 避免水體狀況的不利變化,2. 確保基于水平衡考慮而采取的節約用水,3. 保持水平衡的效能,4. 避免水流的擴大和加速。(2)可能受洪水影響的每個人,在其可能和合理范圍內,有義務采取相應合適的預防措施,防止洪水的不利后果和減少損失,特別是在利用土地時,要考慮到由洪水可能對人身、環境或財物造成的不利后果。”
3 對我國水事治理的借鑒意義
本文基于德國《水法》的框架和歷史發展情況及《水法》的總則規定,來思考對我國水治理的借鑒意義。要實施可持續水治理,需要更具體的原則來支撐和落實。基于對德國水治理和《水法》的理解中,有幾點值得我國水事治理上思考的地方。
3.1 可持續性理念下的水事法治原則
首先,從國家法治的大背景下[5],水事監管法律是整個法律框架中的一個環節。對此可做多角度理解:①現行法律條文是基于長期歷史發展而形成的,并仍在不斷更新中。在法律的性質和內容上不斷從私法向公法傾斜,在公法范圍內又不斷從經營管理法向現代環境法發展。②水事法規是一個縱向型的獨立部門法,從憲法到民法和刑法,再到主要組成的行政法。并且水事治理同樣還是技術性法律,這意味著除正式法律外,還需要對條例和技術性標準予以細化。③水事治理需要一種有序的法律框架結構。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中,歐盟法、德國法以及州法對水事治理的有序分權與多層次框架合作機制,對我國環境治理上正在討論與實踐轉型中的垂直與橫向管理可能有一定的啟示。
其次,水事法治是可持續理念的組成部分,只有法治才能確保長期穩定與安全,這需要以高質量的水事立法為基礎。確保后代人的環境與發展權,是環境法立法的根本目的。為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可持續性原則要求水事管理長期保持水體清潔和維護生態平衡。現代水事監管,盡管仍保留著一部分傳統經濟法的影子,但重點已經向現代環境法轉型。從德國《水法》的立法目的和其發展過程可以知道,在經歷了現代環境法的綠化后,考慮到生態系統的整體性,水法正在經歷“生態化”的過程,水體保護和自然保護的關系變得日益緊密。這種發展趨勢也正是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所要遵循的。另外,基于水體作為生態平衡的組成部分的認識,并對此加以保護,要求傳統水事監管朝水體環境質量管理導向轉型。在法律原則上,從原來可持續原則作為環境法中預防原則的體現,可持續性原則日益獨立,相對于預防原則主要強調減少對人類和環境的風險,而可持續原則集中在長期維護和改善自然資源的角度[6]。
3.2 水事綜合治理原則
一般而言,在恰當的調控能力保障下,當定位于較大空間、更寬領域、更長時期,就更有行動能力。從歐盟自身的發展、歐盟水治理領域的政策發展以及中國大尺度的調水看,都是這樣的明證。水事綜合治理原則不僅需要調整環境保護相對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傳統不平衡地位,要協調水使用與保護之間的關系,而且要符合水循環的自然特征。通過強化行政區域間水治理上的合作,以流域整體系統性為理念,甚至可把河口和沿海水域統一納入水法體系。
綜合管理首先是多種利益和專業的協調綜合。綜合水體治理理念是對可持續水治理的實施,在基于對水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科學認識的基礎上,協調好經濟、社會與環境之間的利益平衡,即統籌兼顧生活用水、生產用水和生態用水。綜合水體治理理念還要求整合水資源與水環境、利用與治理的分割,統一考慮水量與水質、取水與排水、水面與陸地的問題,只有在確保不會對水體(從水生態綜合的角度)造成明顯影響的情況下才予以批準用水。除非有重要的社會公共利益,但對此需要考慮特定補償性措施。同樣,《水框架指令》立法理由第38項中強調:“各成員國需要將經濟手段作為其措施計劃的一部分。應按照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考慮供水與水處理服務的成本回收問題,包括與對水生環境的破壞和負面影響相關的環境成本與資源成本。為此,有必要在流域區內水資源長期供需預測的基礎上對供水與水處理服務進行經濟分析。”
流域管理需要超越行政區域、實踐流域統一管理理念,包括把沿海水體納入整體考慮。例如,德國很早就把沿海水體的保護引入到《水法》中,我國水法規定沿海水體適用《海洋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但根據流域綜合管理原則,更需要將沿海水資源納入《水法》統一保護范圍。正如歐盟《水框架指令》制定原則第17項中所表明的,“一項有效而統一的水政策,必須考慮鄰近海岸與河口或海灣內或內海的水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因為流入其中的內陸水體質量,對它們的平衡狀態具有很大的影響”。從物質流的角度,自然水循環作為物質的運輸途徑,最后把陸地上的化學品和其他過量物質攜入海洋,尤其是在沿海一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地表徑流其實是作為污染物傳輸途徑,從整個物質循環來看,海洋是過量(有害)物質的最終聚集地,并造成長期不利影響。《海洋環境保護法》是從區域生態系統的角度對海洋水體進行的規范,但不影響水法從對作為環境媒介的水體進行統一管理的角度出發,對沿海水體進行規范。它是相互交叉的,海洋水體的管理同樣有需要適用水法的基礎性規定。
另外,流域管理實質上是綜合治理理念在空間上的體現,它遵從水體本身的自然特征。但針對人類社會的管理在歷史形成的區域管理是根本性的。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的關系,應當這樣來理解:區域管理是基礎,流域管理是一種理念,需要區域管理部門在管理實踐中予以充分考慮。因此,區域管理部門在實踐流域管理的理念中,主要是跨區域與同流域的水管理機構的信息共享與決策協調。在德國《水法》第7條中首先明確劃定了十大流域單元,并且要求各州的水體保護管轄機關,出于流域水體管理利益,不僅在國內還應當與歐盟成員國和非歐盟成員國的管轄機關協調管理規劃和措施計劃。
3.3 適應認知與技術持續更新的水事法治
隨著人類認知的擴展,同時因為水功能的不斷發現,沖突加劇,水在多個層面上突顯有限性。而《水法》必須要解決這種多層面上的利益沖突。在私法和公法都十分發達的德國,在水權統一和系統化進程中,不管是19世紀末《德國民法典》的制定,到1957年德國《水平衡管理法》的頒布,還是20世紀末歐盟《水框架指令》的制定,在與水相關的私法權益領域的規范逐漸收縮,且都側重于公法監管領域,這體現了水治理從私法向公法轉變的趨勢。
我國仍在從公法向私法轉變行進,這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因為我國之前的私權和私法體系仍然很羸弱,沒有明確私權或私法體系不可能有先進的公法體系),但有必要把握發展趨勢。另外,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與歐盟權力體系有很大不同,就像《水框架指令》,它的直接規范對象是成員國,而不是作為歐盟“條例”有對歐盟公民直接的適用效力。其次是歐盟和德國整體上,在經濟、社會和環境保護上都比我國先進,正是因為其在20世紀60年代自發主動地質疑經濟無止盡的增長可能性,才萌生了現代環境保護理念、政策與法律,并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念。而我國的現代環境政策與法治更多的是外生型和精英型,從社會整體上可能只有到了現在這個時刻,才是萌生我國本土內生的環境保護共識時刻。前期發展過程中所引進和催生的我國環境政策與法律,一方面在實踐中因不符合社會現實,不著地氣的法規要求未能真實履行;另一方面當我國工業化進程發展到一定程度、在面對當下比西方國家更大規模和更具威脅性的環境問題時,現有的環境政策與法律卻早已產生了耐藥性。
環境政策與法律是一個實踐導向型的領域,我國正在嘗試的地方環境質量達標和省以下環境垂直管理體制,在根本上來說涉及憲法層面的問題。但政府多層治理的結構變化必然會影響涉水權利和義務的重新分配,而地方立法權限的擴張,會導致權利和義務的區域差異,從而又會影響市場的一體化。除了權利與義務的不斷調整與發展外,在對作為自然現象的水循環的法律干涉上,也在不斷擴展:從點源污染監管向面源污染監管,從排放源頭監管到與整體環境質量達標相結合,從后果歸責到全過程、全社會共同治理,當然這也是需要科技與信息技術發展作為法律證據來支撐的。
所以水治理其實也反映了整個現代社會治理的復雜性。對于環境領域的治理體制與機制改革,需要在整個社會的大框架、大背景的相互協調下發展。對此,頂層設計與實踐創新間需要不斷的螺旋型循環進步。
3.4 在法治框架下的治水一體化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修訂的現實下,尤其是《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發布后,水環境管理從原來的個案監管和總量控制向以水體環境質量導向轉變,這更加突顯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的緊張關系。對這兩者的科學理解是我國水事管理進步的根本所在,流域統一管理和水事綜合管理理念是水事監管的綠化與生態化的基礎。水管理需要科學技術與法律制度的相互促進,水事法律制度只有基于對水事科學的進步認識,才更符合事實,也更有權威和更易執行。同時,法律又為科技提供了頂層設計與框架,《水框架指令》將水管理提升到了生態保護和流域整體保護的高度,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在水事科學上的投入,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并推動了水體治理。
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和200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在水事治理的系統性和生態保護方面的作用都極為有限,甚至需要防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修訂過程中導致進一步分化。促進水治理的系統化,水法法典化可以是一種形式或者框架,也可以是分步驟進行的,尤其是水污染防治作為水治理的核心領域需要有一定準備。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應當同時展開,在可能的條件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事管理綜合法》。在新的修訂中,應盡可能地促使立法過程的透明化,并最大范圍地把水相關利益方納入修訂程序中,只有充分的利益表達和沖突,才能保證充分考慮現實利益沖突,增加法條的執行性。我國在水利工作中很大程度上把水的資源利益與環境利益對立了起來,加劇了水利與環境保護部門的實踐分割。水資源、水環境概念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水法統一綜合進行管理的理念[8]。基于綜合水體保護的理念,水事監管不僅要超越水質與水量的分割,還要增加水體特征與水體狀況這類綜合的概念作為基本的水事治理對象。
在水事治理上,私法與公法的緊密銜接和合理的法律制度設計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國的水事治理,不僅在科技和空間發展上出現了多期迭加的問題,而且在水事法治理論上,傳統私法上的水權制度、向公法為主的現代環境法機制以及在向程序性權和信息權利保障和生態系統性保護的轉型,因為我國私法理論和實踐不足,而現代環境保護政策與法律的外生型早產,形成了一幅錯綜迷茫的圖案。實際上這也是法治的多期迭加。在水事治理上,不僅需要加強私法理論的研究,同時也需要以實踐為導向構建自己的環境法行政執行機制(尤其是以行政許可和行政強制為主的環境行政權限體系),而對于在宣傳上很熱烈的公益訴訟和程序性權利,盡管需要密切關注,但以國家行政權力為核心的行政監管制度建設才是基礎和核心。
3.5 對水事立法技術上的建議
整體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都沒有專門的條款對其法規中的基本概念予以明確定義。一系列規則、原則和標準的適用前提,是有一個可以容納各種情況的權威性范疇的概念體系[7]。二者的統一能有效地避免涉水法規的分裂與矛盾。統一的水法基礎概念能有效地避免部門利益在立法中過于突出。可以明確“水體”是水法的規范對象,而不再是水這種物質,對水體使用的規范要超越水使用,還要包括河岸建設、對水流的影響,而其中核心概念就是“有害的水體改變”。這種有害不再只是水質、水量,還包括水體的水文物理、化學和生態狀況,是指水體特征的改變。水法中的概念體系重構,不僅可借鑒德國及歐盟的水法概念體系,同樣也是基于法律規范的理論要求、水統一管理的事實需要、水法體系性的根本要求以及水體保護與管理的實踐發展的需要[8]。
另外一個立法技術是有關附件。水法作為一種技術性要求很強的法律部門,對于具體技術性的規定很需要有附件來加以明確。另外,在我國水事治理上,對于流域的劃分其實是沒有正式的法律基礎的,對此,德國《水法》附件二明確標示了流域劃分地圖,可以借鑒。
最后還涉及行政法規和地方立法。這方面既是法規一體化的體現,又是立法技術性要求很高的。哪些領域留給行政法規,哪些領域留給地方立法,因為我國水情和水治理的特殊性,這些問題仍然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4 總結
以上,是基于德國水治理法規的發展和組成以及《水法》總則的規定,展開的一部分研究,以及對我國水治理的若干思考。盡管水治理相對整個社會治理只是很小的一個面,但是因為水的重要性、多功能性及流動性,它涉及的方面極其廣泛,水治理體現著國家治理能力的水平。最后以此為結語:“文明是人類力量不斷加以完善的發展,是人類對外在的或物質自然界和對人類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內在的或人類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文明的兩個方面是相互依賴的。如果不是由于人們所已達到的對內在本性的控制,他們就難以征服外在的自然界。”[7]
[1] 沈百鑫. 德國環境保護領域的立法權限[M]//徐祥民. 中國環境法學評論(2010年卷).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0: 199-215.
[2] 沈百鑫. 德國水管理法的變遷[M]//呂忠梅. 湖北水資源可持續發展報告(2010).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189-204.
[3] REINHARDT M. Identit?t und zukunft des wasserrechts als bestandteil eines umweltgesetzbuchs[J]. ZUR, 2008(7-8): 352-357.
[4] 沈百鑫, 鄭丙輝, 王宏洋, 等. 德國水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水平衡管理法》總則規定研究[J]. 環境保護, 2016, 44(12): 65-70.
[5] 沈百鑫. 論中國環境法治的憲法基礎[J]. 國土資源情報, 2015(8): 3-11.
[6] KNOPP. WHG Kommentar, §1[M]. München: Verl. C. H. Beck, 2011: 1-15.
[7] 羅斯科·龐德. 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M]. 沈宗靈,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6: 1-28.
[8] 沈百鑫. 水資源、水環境和水體——建立統一的水法核心概念體系[M]//曾曉東, 周珂. 中國環境法治(下).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2: 99-123.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Water Law for China’s Water Governance
SHEN Baixin1, ZHENG Binghui2, CAI Mulin2, LI Min2, WANG Haiyan2*
( 1. Helmholt UFZ, Leipzig D-04103, Germany; 2.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
Based 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cept of water management in Germany, which was deeply impacted by EU water policy,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general principles of Germany “water balance management law”. The German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water management is made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sustainability. Only thus, people can ensure long-term water security, and maintai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keep the water clean and guarantee the ecological balance, as well as safeguard the righ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water management should not only adjust the unequal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elation to tradi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mely the coordin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use and protection, but also require to follow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 water cycle. It was suggested that in the revision of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law”, it needs to be easy to operate which based on our reality of technical support to practice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water.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law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Moreover, it was made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technology.
sustainable water governance; integrated ecological water protection; the German water law; rule of law in the field of water
D922.66
1674-6252(2017)01-0081-05
A
10.16868/j.cnki.1674-6252.2017.01.081
注: 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修訂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沈百鑫(1975—),男,亥姆霍茲研究聯合會環境研究中心(Helmholtz UFZ)研究員,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德國及歐盟法律比較。
*責任作者:王海燕(1976—),女,博士,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從事環境標準研究,E-mail: wanghaiyan@ crae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