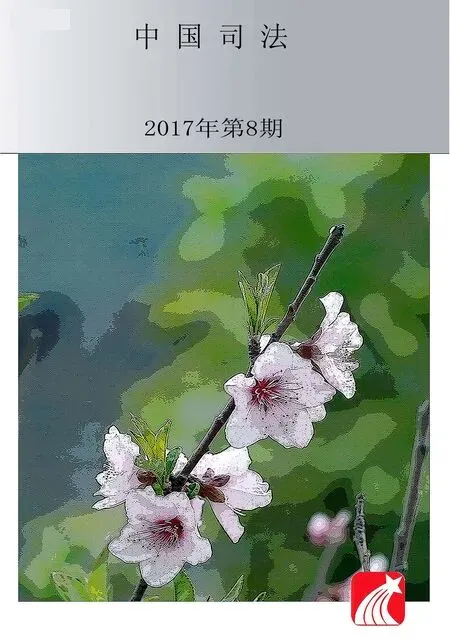美國近年來對重刑主義政策的反思與轉向
梅義征(上海市社區矯正管理局副局長)
美國近年來對重刑主義政策的反思與轉向
梅義征(上海市社區矯正管理局副局長)
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刑事司法政策借鑒和吸收美國經驗的成分越來越多。學界所談論的國際刑事政策的新發展、新趨勢,實際上主要就是美國刑事政策發展的軌跡。不可否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許多國家參考、借鑒、學習的榜樣。本文擬對美國聯邦及各州近年來對刑事政策的反思與調整做一個簡單梳理,以期對我國刑事司法政策調整與完善有所借鑒。
一、重刑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后果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以后,美國從聯邦到各州的刑事政策開始步入被許多美國學者稱為“大實驗”的重刑主義政策周期。其顯著特點就是拋棄原來改造理念,轉而強調公平懲罰、威懾和犯罪控制。突出地表現為擴大監禁刑的適用,加重對涉毒和暴力罪犯的懲處。
1984年,美國聯邦出臺《審判改革法》,明確提出審判的目的是公平懲罰、威懾、使罪犯失去再犯罪能力和改造,改造(rehabilitation)失去了作為刑罰首要目的的地位。該法同時規定:第一,建立聯邦審判委員會,為重罪犯和A級違法行為確定強制性的審判指導標準。標準依據犯罪的嚴重性、犯罪史、受害者的類型、犯罪中的作用以及是否有阻抗司法機關的行為等,確定罪犯的刑期范圍。聯邦法官判案必須依照這個審判指導標準。州級層面,1982年就有37個州頒布了類似的法律。第二,廢除假釋制度,統一規定所有監獄罪犯的在監服刑時間是法院裁定刑期的85%。州級層面,有20個州制定了類似法律。第三,創立了一個不納入刑期的出獄后受監管的釋放期。所有被判定期刑的對象都有一個受監管的釋放期。這一創設,目前已經成為普通法系國家的通例。
1984年美國聯邦《攜帶武器的職業犯罪法案》規定,受聯邦刑事指控的犯“嚴重毒品犯罪”或者是“暴力重罪”的被告人,如果是攜帶武器實施犯罪,應另加處刑罰。一般都需加處5年刑期。為了加重對累犯、再犯的處罰,1994年美國聯邦出臺《暴力犯罪控制與執法法》,俗稱“三振出局法”。該法規定:對于前已犯二次重罪之重罪犯,或者前曾犯一次以上重大犯罪之暴力重罪犯,或者之前有一次以上重大犯罪之毒品犯,將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州級層面,有30多個州頒布了類似的法律。
此外,為加重對毒品犯罪的懲罰,1986年聯邦《反毒品濫用法》將毒品犯罪的起刑標準直接與毒品數量和種類掛鉤,而不考慮犯罪嫌疑人在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及其他相關因素,從而大大增加了適用起刑標準的人數。
重刑主義政策的另一表現就是對社區監管和風險控制的強調。在此前對判處緩刑對象的監管都是比較松散的,一個緩刑官的收案量多在100人以上。到80年代以后,風險管控和危機管理模式在矯正工作中得到不斷推廣,矯正機構著眼的不再是如何改造犯罪人,而是管控風險,預防再犯。風險評估工具得到廣泛適用,以此為基礎,很多州開始對被評估為高風險的緩刑對象實行強化監管計劃,對違反監管規定但還不夠判處監禁刑的緩刑對象實行日報告制度,將緩刑官對此類對象的收案量限制在15到30人之間,通過增加報告和走訪的頻率,加強對此類對象的監管。此外,由于很多原本可判緩刑的對象現轉判短期實刑,造成看守所和監獄擁擠不堪,為解決這個問題,電子監控、居家監禁、震顫監禁、甚至矯正訓練營等被稱為“中間制裁”的刑罰易科措施先后被發明出來,原本以改造和幫扶罪犯為主要目的的社區矯正機構,在維護社區安全方面承擔起越來越重的任務。
重刑主義政策造成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監獄罪犯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迅速增長。從1930年到1980年,美國的監禁率一直保持相對穩定,每10萬人監禁率,最低為1972年的93,最高為1980年的139,但此后就一直猛漲:1980年代平均為200,1990年代就增長到389,到2013年10月,達到創紀錄的716。用另一句話說,美國全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4%,但監獄關押罪犯人數是全世界總數的22%。到2013年,全美處于矯正機構監管下的人數接近700萬,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2%;全年進出看守所的人數達1200多萬。所關押的犯罪群體中,以涉毒罪犯人數增長最快:在1980年,州立監獄所關押的涉毒類罪犯才19000人,占在監服刑罪犯總數的6%;但到2007年,入監服刑的涉毒類罪犯達到253300人,占在監服刑罪犯總數的19.5%。在聯邦監獄中占比則達到53.5%①Todd R. Clear, Gorge F. Cole, Michael D. Reisig, American Corrections,Ninth Edition , Wadsworth,2011, p511.。與之相應的是,從聯邦到各州,自80年代起,所有的監獄都人滿為患。盡管自1990年到2005年新建了超過500座監獄,短短的15年時間,監獄數量增加了42%,但往往一個監獄剛剛投入使用就處于爆滿狀態②American Corrections,p510.。以聯邦為例,從1940年到1980年,聯邦監獄關押的罪犯人數一直不到3萬人,但到2013年,聯邦監獄關押罪犯人數達到22萬人,增加了8倍之多③見 CCTF :Transforming Prisons, Restoring Lives: Final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harles Colson Task Force on Federal Corrections, P.1.。
罪犯人數的迅猛增長和監獄的大量新建,給聯邦和各州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自1986年到2001年,美國聯邦和各州監獄方面開支普遍增長數倍。到2001年,每個美國公民平均每年負擔的監獄開支達到104美元④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tate Prison Expenditures, 200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ne 2004), 1.。這種增長勢頭到現在還沒有得到遏制。以聯邦層面為例,自1981年到2016年35年間,聯邦政府用于監獄方面的年度預算由9.5億美元增長到75億美元,除去通貨膨脹因素,增長了687%,是聯邦司法部其他方面年度預算增長速度的兩倍。目前,聯邦監獄局的年度預算開支占聯邦司法部整個預算的四分之一。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其在聯邦司法部的整個預算中占比還不到8%⑤Transforming Prisons, Restoring Lives,p15.。
重刑主義政策另一個嚴重的后果就是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許多人因進監獄服刑而失去工作和生計,出監后又飽受標簽效應的影響,生活和就業困難重重,大量的家庭因其核心成員被判監禁刑而解體。這方面,黑人受影響最深,拉丁裔次之。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黑人青年進入大學讀書和入監服刑的比率是3:1,但到2010年,這一比例逆轉為3:4,也就是說,在監獄服刑的黑人青年超過了讀大學的黑人青年。在2010年左右,10萬個黑人中,就有5000人處于關押狀態,與之相比,拉丁裔的是2000人,而白人才800人。如果將各類矯正機構監管的對象都算在內,2010年,20多歲的黑人中有三分之一都處于矯正機構的監管之下⑥American Corrections, P524-525.。可以說,刑事政策人為地造就了一個特殊的貧困階層和一個穩定的犯罪群體。
此外,重刑主義政策還深刻影響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格局。在美國,無論是聯邦還是各州,總統、州長和眾議院議員的選舉都是以人口為基數的,按照美國人口調查局的統計標準,入監服刑人員是監獄所在地的“公民”,這樣,那些監獄相對集中的地區不僅在選舉中,尤其在州地方選舉中權重大大增加,而且可以享受到聯邦和州按人口數提供的各項經濟資助和社會服務撥款。在全美,有21個縣,其總人口中監獄人口至少要占到21%,德克薩斯的康楚縣(Concho County),監獄人口占了其總人口的33%。在紐約州,三分之二的罪犯出自紐約縣,但91%的罪犯卻被關押在紐約市北部的各個縣,不僅為這些縣帶來了工作和收入,其政治也為代表監獄職員的工會所左右⑦Brent Staples, “Why Some Politicians Need Their Prisons to Stay Full,”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05, http://query . nytimes.com/mem/tnt.html?oref=login&tntget=2—0/1.。另一方面,美國大部分州都對犯罪人或曾經犯罪者的投票權設定了限制。以2016年的總統選舉為例,有美國學者估計,僅因犯罪或有犯罪史而被剝奪選舉權的黑人就將近600萬,這不僅是對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變相剝奪,也對選舉結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反思與改進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開始檢視重刑主義政策的正當性和效果,通過研究,他們發現了一系列有趣的現象:比如,雖然總體來說,少數族裔、尤其是黑人較多的南部各州入監比率普遍高于北部各州,但即使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基本相同、犯罪率也差不多的兩個州,在入監比率方面卻呈現出很大的差別:2007年,亞利桑那10萬人入監率是554,而與之相鄰的新墨西哥州則只有313;同年明尼蘇達州是181,而與之相鄰的威斯康辛州則為397。因此,有學者通過考察1971~1997年各州監禁率的變化,得出結論,一個州的監禁率的高低,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
——一個州暴力犯罪率越高,監禁率也就越高;
——一個州的財政收入水平與監獄關押人數呈正相關;
——一個州失業人口越多,非裔人口越多,監禁率就會越高;
——一個州的社會福利水平越高,其監禁人口會越少;
——一個州的保守派越多,其監禁率會越高,并且增長速度比那些保守派占少數的州要快許多;
——擴大監禁刑適用的政治動機超越了共和、民主兩黨的政治分野。
又如,有學者通過研究,得出:入監服刑人數的高速擴張并非像表面所顯現的那樣,是犯罪率迅猛增長的結果,而更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驅動的結果。一般來說,公眾普遍痛恨犯罪,贊成強化對犯罪的懲處,且認為最有效的懲處和減少犯罪的方式就是監禁。此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大眾傳媒對犯罪現象的過分關注,有可能使任何一個偶然的犯罪行為引發社會普遍的不安全感,導致從嚴懲處犯罪的呼聲高漲。而對于政治領導人來說,對此作出積極回應,是其傾聽民意,順應民意的最好表現,也是緩解其執政壓力的安全做法。正如有學者所言,加重懲處的要求并不能解決問題,而只是減輕了要“有所作為”的政治壓力⑧American Corrections, P512.。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美國的犯罪率逐年走低,美國學者中對加重對犯罪懲處的刑事政策是否合理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1987年,國家司法研究所一位名叫埃德溫·澤德爾維斯基的經濟學家通過研究全國的犯罪數據,得出囚禁一名罪犯的費用為每年25000美元,而如果放任其犯罪,他一年可能犯罪的次數為187次,導致的社會成本為43萬美元,二者相比是1:17。因此,將重罪犯收監的社會效益遠遠大于成本。這一研究結果引發了美國學者持續數十年的爭論。有學者尖銳地指出,如果澤德爾維斯基的數據準確,那么,美國自1973年入監率就開始增長,到1992年,由此節約的經費不僅可以全部抵消國債,還可以使犯罪率成為負數。到1995年,就有學者指出,目前的刑事政策就其成本與效益而言,已經達到臨界點,如果再任其發展下去,其邊際效益將不斷下降,而成本將會加速攀升。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犯罪率的走低,就是嚴格刑罰的結果,但更多的認為,社會犯罪率的高低與刑事政策的嚴峻與否之間的關聯并沒有想象的那么高。布魯斯·威斯特恩通過分析1971~2001三十年數據后得出,監禁罪犯對于降低犯罪與暴力的作用并不如想象的那樣明顯:1993~2001年,各州監獄關押罪犯人數從72.5萬上升至120萬,牽涉的成本是530億美元。但其對降低嚴重犯罪的貢獻率只有2%~5%之間。
面對重刑主義政策所帶來的日益明顯的負面效應,一些州自90年代開始就有所行動。除了前面所提及的越來越多的州開始用所謂的中間制裁措施替代短期監禁刑外,部分州開始變相恢復了假釋制度,賦予法官和假釋官在確定刑期和釋放時間方面更大的自由裁量權。到2003年,有25個州采取了實質性的步驟減輕了刑罰,修正了刑罰措施和矯正政策,13個州或取消或修正了毒品犯罪的強制性起刑標準,11個州建立或完善了緊急釋放和提前釋放機制。聯邦層面相對而言動作較慢,但到2005年,也將審判指導標準由強制性的變為指導性的,給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但這些局部的變革對不斷攀升的監禁率并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影響。真正促使美國從聯邦到各州重新審視重刑主義刑事政策的是自2008年開始的經濟危機。由不斷擴大監禁刑而產生的沉重經濟負擔成為促使從聯邦到各州改變重刑主義政策的最終動力。
改變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采取切實的措施降低監獄和看守所的擁擠狀況。早在新世紀初,美國的亞利桑那、康涅狄格、內華達、佛蒙特、德克薩斯和威斯康辛等州為解決入監罪犯迅猛增長的問題,啟動了一項稱為“司法再投資”(Justice Reinvestment)的項目,取得了明顯成效。該項目主要致力于通過分析刑事司法數據,找出導致矯正成本大幅上升的因素。以此為基礎,提出為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關者所支持的減少矯正成本的措施;相關司法管轄區再將由減少矯正成本所省下來的部分費用投入到增進公共安全和減少再犯罪的相關項目。2010年,美國聯邦司法部及下屬的司法援助局(Bureau of Justice Assistance)與皮尤慈善信托公司(Pew Charitable Trusts)聯合啟動了一個稱為“司法再投資倡議”(Justice Reinvestment Initiative)的計劃,在各州推廣該項目⑨https://www.bja.gov/programs/justicereinvestment/jri_sites.html.。該計劃為愿意參與的州或司法管轄區運用司法再投資的原則改造它們的矯正體系提供必要的專家和技術支持, 尋求節約成本同時增進公共安全的有效方法。截止2016年11月16日,全美共有33個州參與了該計劃。該計劃的要點在于:第一,將風險級別低、非暴力犯罪的罪犯盡可能交由社區監管;第二,盡量避免將僅違反監管規定(俗稱技術違規)而非再犯新罪的緩刑和假釋對象收監;第三,優化假釋和緩刑監管體系與資源,強化其在管控再犯罪方面的作用;第四,推進矯正項目的科學化,提高其在罪犯矯正方面的針對性⑩http://www.urban.org/urban-wire/justice-reinvestment-using-data-save-dollars.。
為解決看守所擁擠不堪的問題,2007年,國家矯正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與美國知名的非營利組織阿爾本研究所(the Urban Institute)聯合啟動了“從看守所過渡到社區倡議”(the Transition from Jail to Community Initiative)項目,旨在通過應對看守所監管對象社會再融入所面臨的挑戰,著眼于構建多方合作的、以社區為基礎的解決模式,幫助地方司法管轄區改變監管和改造的流程,達到減少看守所的關押人數、增進社會安全的目的。該項目2008~2012年在6個地方司法管轄區進行試點,2012年又啟動了第二輪試點工作?http://www.urban.org/research/publication/transition-jail-community-tjc-initiative-phase-2-summary-implementation-findings/view/full_report.,試點范圍擴大到14個。該項目的要點在于:第一,各關鍵政策制定機構的積極介入、統籌安排與組織領導;第二,構建看守所和社區合作的組織構架,明確共同責任;第三,將客觀實證的數據收集與分析作為決策的基礎;第四,依據監管對象的再犯風險和犯因性需求進行靶向項目干預;第五,基于數據的自我評估和持續性機制的構建。重點在兩個方面,一是優化前端分處(Front-end Diversion)和審前釋放(Pre-trial Release)流程。二是通過科學的工具進行篩查和評估,對高風險對象進行靶向項目干預,優化社區監管措施。
第二,通過立法,弱化重刑主義色彩,從根本上降低收監率。在聯邦層面,2010年通過了《公平審判法》,提高了販賣毒品罪中強制性起刑標準的最低毒品量,取消了持有毒品罪的強制性起刑標準。2013年,聯邦總檢察長埃里克·霍爾德發起“靈活應對犯罪”倡議,指導公訴人專注于最重要的法律實施優先順序,在對毒品犯罪提起公訴時,用好自由裁量權,盡量對那些不是很嚴重的毒品犯罪慎用強制起刑標準。2014年,聯邦審判委員會修改了毒品犯罪的推薦指導標準,降低了絕大多數毒品犯罪的刑期。許多州在此方面也是舉措頻頻。如2011年加利福尼亞通過《公共安全整治法》,具體舉措包括:將非暴力、非性犯罪、情節不嚴重的重罪交由地方看守所而非州監獄關押;對由該法所規定改由地方看守所關押的罪犯實行分割判罰(Split Sentencing),即罪犯在看守所關押一段時間后,繼之以由社區強制監管的緩刑(Suspended Sentence);由監獄釋放的非暴力、犯罪情節不嚴重的罪犯改由縣緩刑機構監管而非由州假釋機構監管;假釋罪犯除非犯新罪,違反假釋規定收監由縣看守所負責而非送到監獄,且看守所關押時間不得超過180天;州級財政對該法所導致的縣級矯正人數的增長給予補貼?Janeen Buck Willison,Transition from Jail to Community (TJC) Initiative: Phase 2 Summary Implementation Findings. http://www.urban.org/research/publication/transition-jail-community-tjc-initiative-phase-2-summary-implementation-findings/view/full_report.。
第三,大力推動循證矯正技術的應用,突出監社合作,不斷挖掘社區矯正在監管改造罪犯和維護社區安全方面的潛力。1974年,社會學家馬丁遜為紐約州長犯罪問題特別委員會所撰寫的報告《什么有效?監獄改革的問題和答案》?參見拙著:《社區矯正制度的移植、嵌入與重構》,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27頁。對改造理念提出全面的質疑,認為,“除了極少數和個別的例外,到目前為止所報告的所有在改造方面的努力在控制罪犯的重犯方面沒有什么可以評估的效果。”這篇報告不僅是美國重刑主義刑事政策的先聲,而且通過否定監獄所有的改造罪犯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使矯正機構變成了一個簡單的懲罰罪犯、使罪犯失去再犯罪能力和管控風險的場所。但到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大數據的出現以及循證理論的興起,對照研究和薈萃分析方法日益廣泛地運用于檢驗各類矯正項目在降低矯正對象再犯風險方面的效度。學者們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并不是所有的矯正項目在降低矯正對象再犯方面都沒有效果,關鍵是項目能否針對矯正對象的犯因性需求;并不是所有的犯罪人都需要采取矯正措施,而只有那些具有再犯風險的對象方才需要干預;對罪犯的矯正需要監社的密切合作。以此為基礎,美國的矯正制度出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深刻變化:
1.風險需求評估的廣泛運用。包括審前評估、判后評估、入監風險篩查、暴力評估、再犯風險和需求評估等等,可以說評估已經滲透到刑事司法程序的各個環節,貫穿矯正的整個過程。
2.注重項目干預。所謂矯正項目,就是針對對象的實際需要、尤其是犯因性需求而設計的集成化的矯正措施,它即可體現在法官的判決中,也可以應用于矯正場所。需求原則是項目干預的基礎,對象需要哪些干預措施,干預的程度如何,是以風險和需求評估的結果為基礎的。為推廣矯正項目的應用,在聯邦司法援助局的資助下,知名犯罪學家法葉·特克斯曼于2014年開發出一套稱為“CJ-TRAK”套裝軟件,幫助矯正機構斷定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和項目是否真正符合其所監管對象的犯因性危險和需求,這種在線工具使用監管對象數量水平數據來評估當前項目的可用度,發現系統水平的差距,并針對監管對象的犯因性需求推薦所必要的項目供給?https://www.gmuace.org/tools/assess-capacity.。
3.注重監獄和社區相互配合,發揮各自所長,包括:強化入監服刑罪犯與家庭之間的聯系,增加罪犯與親人之間接觸的頻率;發揮社區在監管非暴力、惡性程度低的罪犯方面的主陣地作用;通過購買服務、委托監管等方式,廣泛引入社會力量和專業力量參與矯正工作;針對高風險、惡性程度高的罪犯,通過將矯正項目向社區延伸,注重釋放后的監管,構建監獄和社區無縫銜接機制等。
通過幾年的努力,美國罪犯總人數和入監率,自2013年10月份達到頂峰后,開始持續下降。以聯邦監獄關押罪犯數為例,到2016年初,已由最高峰的23萬下降到19萬。從全國看,不僅入監率在逐步下降,犯罪率仍保持了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緩慢下降趨勢,更值得注意的是,再犯率也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刑滿釋放人員4年內的再犯率由原來的42%左右下降到34%左右。
三、初步思考
我國先后頒布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九),雖然減少了死刑的罪名,但在很多方面,進一步嚴格了相關刑罰措施。近兩年,隨著限制三類罪犯(黑社會犯罪、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相關文件的出臺,全國各地的假釋率直線下降,不少省份2016年全年的假釋率還不到1%。各省市近兩年社區矯正對象人數的持續減少就是保外和假釋政策收緊的最直接表現。此外,無論是學界還是司法部門,對于是否應該降低未成年承擔完全刑事責任年齡問題的爭論也日趨激烈。
應該說,無論是從全面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還是從推進刑事一體化的要求看,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還存在許多亟待完善和調整的地方。但一定要防止兩種傾向:
第一,力戒簡單照搬所謂西方的先進經驗和做法。筆者從不反對借鑒和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理性和規則從來就是人類共同體的組織基礎,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要趕超先進,就必須認真學習先進國家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好經驗,總結其失敗的教訓,盡可能少走彎路。但借鑒的前提是切實了解自己和對象,注重系統性和整體性思考,而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否則,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鬧劇會不斷重復。
第二,力戒過分倚重強化刑罰措施來實現預防和減少犯罪、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美國近30年重刑主義實驗充分證明,過分倚重刑罰而忽視其他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不僅會產生過高的政治和社會成本,而且在控制和減少犯罪方面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犯罪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的共生現象,不可能消除,只能將之控制在社會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這種承受度,不是以某些社會成員的感官或媒體報道的單個案例或事件來衡量的,而是以社會秩序的總體正常有序為標志。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犯罪率的上升或下降,受制于多種因素,加重懲罰并不能必然導致犯罪率的下降。尤其是當一個社會在某個時期某一類犯罪問題非常突出的時候,那更加不能僅僅靠嚴格刑罰來解決問題,而應該從制度層面找原因。濫用刑罰實際上等于制度性犯罪,是國家針對某個特定社會群體的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就像美國的黑人群體成為美國重刑主義政策的最大受害者那樣。這時,刑罰實際上已經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所引發的問題,就不僅僅是依靠修改刑事法律制度就能解決的。
(見習編輯:賀 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