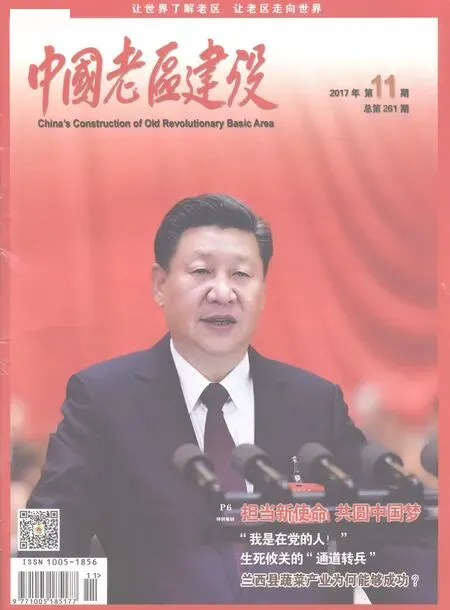教育扶貧中的造假觸目驚心
□ 賀海波
今年回家探親,抽時間到縣城看望楊老師。楊老師是縣高中的校領導,對于教育及其相關社會現象常有感知和思考。這次,他覺得特別有些想不明白的是教育扶貧中反映出來的問題。
在與其交談中,發現目前的教育扶貧確實存在著兩個比較大的問題:一是教育扶貧資源的爭奪現象比較嚴重;一是教育扶貧在分“蛋糕”中誘發的社會之惡。
教育扶貧名額太多了
縣高中每年教育扶貧名額的上限是1000名,不設下限。按楊老師的說法,這個名額太多了,實際上真正需要扶貧的可能就是500名左右的學生。全縣根本就沒有那么多需要教育扶貧的對象。
這其中暗含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國家的教育扶貧政策定位相對來說比較寬松,這種寬松是政府制定政策時難于精準地開展數字管理的反映,既然無法精準,那么就將數額擴大一點,將政策定得活一些,讓學校和基層單位擁有更多的裁量權,也許權利下放到執行單位可以達到精準識別;二是指望學校和基層單位精準識別出教育扶貧對象,從而合理有效分配教育扶貧資源的期望并沒有實現。
那么國家在教育扶貧中的政策意圖為什么不能實現呢?
首先,學校和基層單位沒有意愿或能力做到精準識別。
申請教育扶貧的流程是學生家長找村委會開具家庭貧困證明,然后再到縣民政局開證明,最后上交學校。可見,要想成為教育扶貧對象,學生家長要過村委會、縣民政局和學校三道關口。
照理說,有兩三層把關就足以篩掉那些假貧困戶。但事實是,三道關口都沒有顯示出治理的硬力量。
村兩委與農戶同處一個熟人社會的村莊內部,聯系最為緊密,哪家是什么情況應該很清楚,即使不清楚給小組長打個電話,就很容易搞清楚。但是大多數村兩委只是消極行政,并沒有積極行政的動力。
因為,雖然村干部的報酬近年來有所上漲,一年也有好幾萬元,并由縣鄉發放,而且對他們的要求比較嚴,犯錯了會受到嚴肅處理,但是村干部畢竟還要群眾選舉,還要深植于鄉土社會,為老百姓辦好事、爭取利益還是要放在重要位置,不然下次選舉就有可能被選掉;即使不為了選舉,背上不為村民做好事的罵名也是一件沒有面子的事情,以后在村里就不好混了。
所以,有村民來申請教育扶貧資源,就有充分的理由給個順水人情,反正錢是國家的,也沒有誰會多事來進一步審查,即使有好事者查出來了,受點處分也沒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不當這個干部,自己本就是村莊精英,本就有其他產業,并不完全依靠當干部的報酬。
一旦村兩委干部不負責任,冒充貧困戶的村民找到縣民政局,縣民政局就沒有理由再攔下那些假貧困戶,因為他們實在不了解實際情況,無法分辨,即使可以分辨,村民會說村里都通過了,你為什么不給開證明,你和我有仇嗎?兩個回合下來,縣民政局也實在沒有辦法招架,還是得給出證明。所以民政局只要看見村民拿著村兩委的貧困證明,一般地都給出證明了事。最后,村民將證明交給學校。學校是教學單位,當然更不可能組織人馬逐戶走訪,只能認村里和縣民政局的證明。
其次,大量村民爭奪教育扶貧資源。教育扶貧這兩年力度比較大,一個學期有兩千元的生活補貼,并且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還可以免交八九百元的學雜費。如果得到了教育扶貧資源,就相當于是將孩子交到學校,由國家幫助培養。這確實是一筆很劃得來的生意。
所以很多村民都會去爭取這筆資源,一些家庭比較富裕,開著小車也去跑教育扶貧。這些假貧困戶一般頭腦比較靈活,信息靈通,能夠及時嗅出政策的資源流量,知道采取什么途徑可以通過層層關卡。
比如到村干部那里,他們會裝窮,會隱藏掉家庭中好的一面,專挑那些比較弱勢的方面,說自己家里上有老人要贍養、家里遭了災等;到民政局那里就說,村里已經通過了,我確實是窮困戶,要是不行,就賴著別人,纏著別人;到班主任那里,就直接說反正孩子是交給老師了,不給教育扶貧,出了什么事老師要負責。當然也有一些家長會托關系來通關。一方面是假貧困戶的積極爭奪,一方面是層層把關,層層把不了關。那么國家本來想將政策定得活一些,讓基層單位自由裁量,但結果政策還是成了一個死的政策,以上限為準,直到最后一個名額被瓜分。
造假的底氣
教育扶貧是精準扶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對貧困戶的轉移支付,是對貧困群眾雪中送炭式的幫扶,是救急救貧,讓社會利益最少獲得者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體現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
那么假貧困戶何來的底氣去爭奪這個有很強道德意義的教育扶貧資源呢?
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改革開放以來,市場主義長驅直入,滲透進村民生活與思想的方方面面,村民的思想從最初的致富向獲利轉變,只要是利益就要去爭去搶,只要不違法不受法律懲處,凡多得利益者均是村民眼中的成功者,而無論是否“取之有道”;
其次,村莊喪失了具有道德約束的公共話語。鄂中農村早已原子化,村民之間沒有緊密而可靠的聯系紐帶,舊時的宗族早已解體,新中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也不斷削弱,村莊雖然仍是一個熟人社會,但卻分化為一個個“無公德的個體”。“無公德的個體”是很難生產出具有道德約束力的公共話語的,既然做什么都沒有公共性的約束,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讓“私德”不斷膨脹發酵,以至扯掉了體現出公平正義和遮蔽人性之惡的幕布。
正因如此,教育扶貧資源成為了大家都想吃一口的蛋糕,成為一場歡娛的饕餮盛宴。楊老師擔憂地說,教育扶貧中學生家長爭奪資源的問題很大,絕對不能長期這樣搞下去。
確實,毫無羞恥感爭奪本不應得的教育扶貧資源,會產生一些不良的社會影響,最為重要的是強化了利益至上的市場理性,長期以往,甚至會導致叢林法則的復燃。當下市場理性對于社會的破壞已經到了不得不想辦法治理的地步,但教育扶貧資源卻繼續助長了這種破壞,并且這種滅掉了所有神圣事物的市場理性在教育扶貧中還會發生代際轉移。
其實大多數學生都不愿給自己的家庭貼上貧困戶的標簽,認為那是一件令人恥辱的事情。但是在父母不斷爭奪并最終成為“貧困戶”的事實中,他們建立起來的羞恥感會被不斷消磨掉,最后會成為和他們父母一樣只要利益不顧羞恥的“無公德的個體”。
國家投入越來越多的治理資源,但是這些資源不能準確地運用于國家所圈定的治理對象,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并誘發了更為復雜的治理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