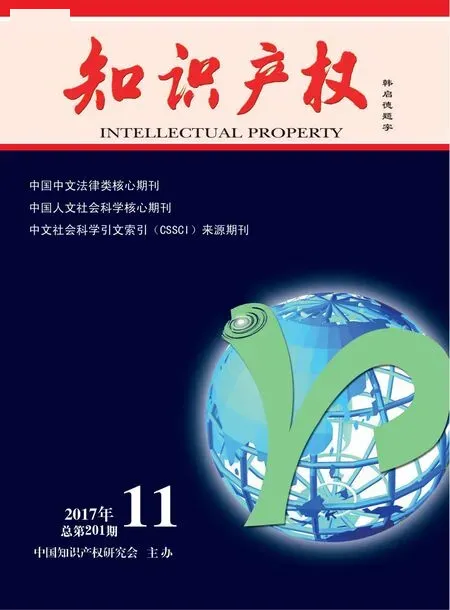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權中的轉播權探析
曹新明 葉 霖
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權中的轉播權探析
曹新明 葉 霖
網絡傳輸技術在豐富廣播電視傳播方式的同時,也給廣播組織權保護帶來了困惑。傳統意義上的廣播電視主要以電磁波信號形式通過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網絡環境下,廣播電視信號不僅可以通過無線傳播,而且可以通過網絡傳輸,由此引發廣播組織與網絡經營者之間的權利沖突。針對轉播權的具體內容,在參與《廣播組織條約(草案)》談判的國家之間存在著明顯分歧。2017年5月,經過各方妥協和讓步,參與談判國家對轉播權的認識漸趨一致,集中體現在初步形成的《條約草案合并文本》之中。我國有關人士對轉播權的具體內容也有不同看法,但隨著《廣播組織條約草案》的推進也基本達成共識。
網絡環境 廣播組織權 廣播電視轉播權
引 言
2017年8月18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署(版權局)版權管理司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廣播組織條約草案》(以下簡稱《條約草案》)主辦專題研討會。①2017年8月17日-19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廣播組織公約》研討會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順利召開。本次《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廣播組織公約》研討會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辦,來自國家版權局的領導、國內高校的學者、歐洲廣播聯盟及中央電視臺的法務工作者,就《廣播組織公約》的制定和廣播組織權制度的完善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引自《張偉君教授參加〈WIPO廣播組織公約〉研討會并作主題發言》,載http://law. tongji. edu. cn/28/3c/c5327a75836/page.htm, 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9日。在這次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圍繞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與相關權常設委員會(WIPO-SCCR)主持起草該《條約草案》的主旨與爭議、廣播組織權的客體與內容、互聯網時代的廣播組織權挑戰與機遇、我國廣播電視行業的探索與實踐以及廣播組織權保護所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等五大主題進行了討論。本次會議的重點之一就是如何正確理解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權中的轉播權。與會者認為,1961年締結的《保護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羅馬公約》(以下簡稱《羅馬公約》)》②《羅馬公約》,即《保護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羅馬公約》(Rom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rformers,Producers of Phonograms and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的簡稱。1961年10月26日,由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及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共同發起,在羅馬締結了本公約。公約于1964年5月18日生效。到2017年為止,我國沒有加入該公約。引自《羅馬公約》,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編:《知識產權國際條約集成》,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90頁。授予廣播組織禁止他人未經許可擅自轉播其廣播節目的權利。③參見《羅馬公約》第13條(甲)項。至今為止,我國沒有加入《羅馬公約》,但因其主要內容被《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④《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簡稱《TRIPS協議》,是世界貿易組織管轄的一項多邊貿易協定。該協定有七個部分,共73條。其中所說的“知識產權”包括:1.版權與相關權;2.商標;3.地理標志;4.工業品外觀設計;5.專利;6.集成電路布線圖設計;7.未披露的信息。引自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中心編:《知識產權國際條約集成》,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370頁。(以下簡稱《TRIPS協議》)吸收,⑤參見《TRIPS協議》第14條“對表演者、錄音制品(唱片)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的保護”。因此,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就必須遵守《TRIPS協議》,即遵守《羅馬公約》關于廣播組織轉播權的規定。然而,在《條約草案》起草過程中,參與談判的國家就廣播組織權所涉及到的許多問題(如轉播權等)一直存在嚴重分歧,導致經過20年馬拉松式的談判未能完成簽訂程序,使之仍然處于擬定過程中。⑥從1997年起, WIPO主持發起該《條約草案》起草工作,現在已經歷經20年,仍然存在著許多爭議,處于起草完善過程中。參見WIPO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hirty-fi fth Session, 載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22169,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7日。因此,關于廣播組織轉播權仍然只能參照《TRIPS協議》的有關規定,依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進行解讀。
一、網絡環境給廣播組織權保護帶來的爭議
眾所周知,互聯網是由網絡技術應用而產生的數據流傳輸通道。當這種數據流傳輸通道運用到廣播電視領域,就將原來以頻率、波段發射的攜帶廣播電視節目信號轉化為廣播電視節目信號數據流,既可以通過信號發射方式播放廣播電視,也可以通過互聯網絡傳輸廣播電視數據流。對廣播組織而言,網絡傳輸方式不僅給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創造了機遇,更對廣播電視權利的保護產生了嚴重沖擊。對網絡經營者而言,網絡環境給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創業機會。在這種新型環境中,廣播組織對廣播電視信號數據流的轉播權與網絡經營者的傳輸行為之間產生了激烈的碰撞。
(一)廣播組織權的客體界定
《羅馬公約》第13條規定的廣播組織權客體就是“廣播電視節目”。⑦《羅馬公約》第13條規定:“廣播組織應當有權授權或禁止:(甲)轉播他們的廣播節目;(乙)錄制他們的廣播節目;(丙)復制:(1)未經他們同意而制作他們的廣播節目的錄音或錄像;(2)根據第十五條的規定而制作他們的廣播節目的錄音和錄像,但復制的目的不符合該條規定的目的。(丁)向公眾傳播電視節目,如果此類傳播是在收門票的公共場所進行的。行使這種權利的條件由被要求保護的締約國的國內法律確定。”《TRIPS協議》對廣播組織權規定使用的是“電視廣播”,⑧參見《TRIPS協議》第14條第3項規定。沒有使用“廣播電視節目或者信號”的字樣。由此規定推知,《TRIPS協議》規定的廣播組織權客體是“電視廣播”。我國是《TRIPS協議》締約方,受《TRIPS協議》約束。與此相對應,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廣播組織權客體是“廣播、電視”,⑨參見我國《著作權法》第45條和第48條規定。和《TRIPS協議》相同。2017年5月擬定的《關于定義、保護對象、所授權利以及其他問題的合并案文》(以下簡稱《條約草案合并文本》)建議的廣播組織權客體就是“廣播的載有節目的信號”,即系指通過電子手段生成、載有最初進行播送并使用任何后續技術格式的節目的載體。⑩引自2017年5月1-5日,WIPO-SCCR在日內瓦召開的第34次會議上的《關于定義、保護對象、所授權利以及其他問題的合并案文》第2條“保護對象”,載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42296,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9日。此處所指的“廣播”包括兩種備選方案:(A)包括“無線廣播”和“有線廣播”;(B)包括“無線廣播”“有線廣播”以及衛星等各種方式傳輸節目信號形式。但是,A、B兩種備選方案都不包括在計算機網絡上進行的播送。[11]備選方案A:(a)(1)“廣播”系指以無線方式播送的供公眾接收的載有節目的信號;通過衛星進行的此種播送亦為“廣播”;播送加密信號,只要廣播組織或經廣播組織同意,向公眾提供解密手段,即為“廣播”。在計算機網絡上進行的播送不構成“廣播”。(2)“有線廣播”系指以有線方式播送的供公眾接收的載有節目的信號。以有線方式播送加密信號,只要有線廣播組織或經有線廣播組織同意,向公眾提供解密手段,即為“有線廣播”。在計算機網絡上進行的播送不構成“廣播”。備選方案B:(a)“廣播”系指或以有線方式,或以無線方式,播送供公眾接收的載有節目的信號;通過衛星進行的此種播送亦為“廣播”;播送加密信號,只要廣播組織或經廣播組織同意,向公眾提供解密手段,即為“廣播”。在計算機網絡上進行的播送不構成“廣播”。引自2017年5月1-5日,WIPO-SCCR在日內瓦召開的第34次會議上的《關于定義、保護對象、所授權利以及其他問題的合并案文》第2條“保護對象”,載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42296,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9日。
由此可知,《條約草案合并文本》提出的兩種備選方案的差別并不大,其共同點比較清晰:即以無線方式和有線方式傳輸的載有廣播電視節目信號就是廣播組織權客體。從WIPO-SCCR推進《條約草案》協商進程來看,這種選擇似乎是參與國比較一致的建議,被通過的可能性非常大。
(二)網絡傳輸廣播電視節目信號的性質
通過網絡傳輸廣播電視節目是否屬于對廣播電視節目信號(數據流)的傳播或者轉播,在知識產權界存在著比較大的爭議。有學者認為網絡傳輸不屬于廣播組織權保護范圍,其理由是我國著作權法關于廣播組織權的規定中沒有使用有線傳播、有線播放、有線轉播的字樣。本文認為,我國著作權法及《著作權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關于廣播組織權的規定雖然沒有使用有線傳播、有線播放、有線轉播的字樣,但也沒有明確規定允許他人未經許可擅自以有線方式傳輸廣播電視。更重要的是我國著作權法第48條第5項規定“未經許可,擅自播放或者復制廣播、電視”即構成對廣播組織權的侵犯,但“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事實上,我國《著作權法》沒有規定“未經許可,擅自以有線方式傳輸、播放廣播、電視屬于不侵犯廣播組織權的例外”。由此可知,通過網絡傳輸廣播、電視(節目信號數據流)在我國本來就屬于廣播組織權所覆蓋范圍內的行為。
2017年5月,WIPO-SCCR擬定的最新《條約草案合并文本》第3條規定:(1)(A)廣播組織(和有線廣播組織)應享有授權以任何方式對其載有節目的信號向公眾轉播的專有權。(B)廣播組織(和有線廣播組織)還應享有授權以公眾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以獲得的方式,對其載有節目的信號進行轉播的專有權。(2)廣播組織(和有線廣播組織)還應當有權禁止未經授權以任何方式轉播其預廣播信號。[12]引自2017年5月1-5日,WIPO-SCCR在日內瓦召開的第34次會議上的《關于定義、保護對象、所授權利以及其他問題的合并案文》第2條“保護對象”,載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42296,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9日。當然,該最新《條約草案合并文本》關于廣播組織轉播權的建議條文,暫時只是一種可能的選擇方案。我國現行著作權法關于廣播組織享有的禁止未經許可擅自轉播其廣播、電視的權利的規定,以及第48條的侵權規定并沒有排除網絡傳輸行為,因此建議我國在《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正案中給予明確規定。
(三)網絡同步傳播廣播電視引發的爭論
網絡環境是廣播電臺、電視臺自誕生以來所遇到的最為重大的技術創新,給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創造了更加便捷的傳播方式。例如,對廣播電視的網絡同步傳播。[13]網絡同步廣播是指除以傳統的有線、無線方式之外,通過計算機網絡向公眾傳播廣播、電視節目信號。中央電視臺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晚會,通過網絡同步傳播,使得其收視率逐年新高。[14]據中央電視臺消息,雞年春晚并機頻道總收視率達到17.64%,相對去年提高0.48個百分點。其中,綜合頻道收視率為7.65%,比上年提高0.67個百分點,綜藝頻道收視率為5.45%,比上年提高0.04個百分點。此外,中文國際頻道、軍事農業頻道、少兒頻道收視率分別達到1.95%、1.11%、1.48%,載http://bj.bendibao.com/news/201724/238080.shtm。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9日。除此之外,由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的其他廣播、電視節目的收視率,得益于網絡同步傳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網絡環境不僅給廣播組織創造了網絡同步傳播的條件,同時還給網絡視頻平臺經營者通過建立視頻網絡平臺對廣播組織播放的廣播、電視進行網絡同步傳播創造了條件,例如IPTV、PPLive等網播平臺。
由此引發這樣的問題:網絡視頻平臺經營者對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的廣播電視進行網絡同步傳播,廣播電臺、電視臺能夠行使廣播組織權予以阻止嗎?面對這種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廣播組織感到十分困惑,一籌莫展。國內傳統廣播組織大多主張廣播組織權應當包括禁止他人未經許可擅自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進行網絡同步傳播的權利,但網絡視頻平臺經營者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兩者針鋒相對的觀點直接影響到法院對此類糾紛案件的判決。例如,2012年3月23日,我國首例涉及網絡轉播的廣播組織權糾紛——嘉興華數電視通信有限公司與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嘉興分公司侵害廣播組織權糾紛案件一審宣判,一審法院認為,嘉興電信公司通過互聯網轉播了黑龍江電視臺的廣播節目,但根據現行法律的規定,尚不能將嘉興電信公司通過網絡轉播黑龍江電視臺節目信號的行為視為《著作權法》第45條規定的轉播行為。[15]引自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載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825/21/31911090_585923804.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7日。原告方不服一審判決,向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該院維持原判,駁回上訴。[16]參見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至此我國第一起廣播電視組織起訴互聯網經營者侵犯其廣播組織權糾紛案件以敗訴告終。
對本案一審法院或者二審法院來說,本來是一個在中國關于廣播組織與網絡視頻平臺經營者因廣播電視通過網絡傳輸引發糾紛開創判例的最佳良機,卻被錯失。我國是成文法系國家,不論哪一個級別的法院先前作出的已經生效的判決,對在后發生的同種類糾紛并不當然具有法律約束力,在后進行裁判的法院不能直接援引先前已經生效的判例作為現在判決的依據。[17]參見曹新明:《我國知識產權判例的規范性探討》,載《知識產權》2016年第1期。盡管如此,倘若針對一起全新的糾紛案件作出了一個具有開拓性判決,既有縝密的法理分析,又有令人信服的正確裁判,這樣的判決可能被最高人民法院收錄成為指導性案例,對此后發生的同種類型糾紛的裁判具有指導作用。這種指導性案例指導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但具有明確的指導性。令人遺憾是,這種創新判例的機遇被“嘉興華數”糾紛案的一、二審法院錯過了,讓廣播組織還得為此繼續迷茫,讓學者們繼續探索,等待機會再次來臨。
關于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享有的轉播權的爭論,在其他國家同樣非常激烈,其典型的事實就是關于由WIPO-SCCR主持起草《廣播組織條約草案》的過程。該項條約草案的發起與WCT[18]《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Copyright Treaty,WCT)的簡稱,是1996年12月20日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持,有120多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外交會議上締結的,主要為解決國際互聯網絡環境下應用數字技術而產生的版權保護新問題。載https://baike.baidu.com/item/,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9日。和WPPT[19]《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WPPT)的簡稱,1996年12月20日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主持,有120多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外交會議上締結的,主要為解決國際互聯網絡環境下應用數字技術而產生的版權保護新問題,實際是“鄰接權”條約。載https://baike.baidu.com/item,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9日。兩個條約的起草的時間差不多,但WCT和WPPT兩個條約1996年就簽署締結了。但是,《廣播組織條約》從1997年起至今已經過去了整整20年,至今不僅還沒有正式簽訂,甚至還有許多基本概念、保護客體、網絡傳輸、權利內容和保護期限等基本問題,需要進一步協商。2017年底,WIPO-SCCR召開的第35次會議進行了專題討論。令人高興的是,2017年5月由WIPO-SCCR擬定的最新《條約草案合并文本》已經將廣播組織權擴展至網絡同步傳播作為唯一選項。這種建議方案被各方接受的可能性非常大。這就意味著很快就會簽署的《廣播組織條約》即將為廣播組織提供更好的保護。[20]參見2017年5月WIPO-SRRC擬定的《關于定義、保護對象、所授權利以及其他問題的合并案文》第3條“所授權利”。載http://www.wipo.int/meetings/en/details.jsp?meeting_id=22169. 最后訪問日期:2017年8月27日。
二、對廣播電視轉播的再認識
“嘉興華數”廣播組織權糾紛案件的一、二審判決都出現了這樣的觀點:1.廣播組織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享有轉播權;[21]根據《著作權法》第45條之規定,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廣播組織享有廣播組織權,有權禁止他人未經其許可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轉播。引自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2.廣播組織權不能擴展到互聯網上;[22]本案爭議法律問題的實質在于廣播組織權項下的轉播權的保護范圍是否能夠擴展至網絡領域。首先,我國著作權法對于此問題的規定并不明確,根據著作權法的規定,廣播組織者享有轉播權,但法律并未將“轉播”的定義擴展至互聯網領域。且從立法體系上分析,我國著作權法將廣播組織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相分離,廣播組織并不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主體,不能控制互聯網領域的廣播電視作品的傳播。引自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3.廣播組織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是分別規定的,對廣播組織提供網絡傳輸廣播電視數據流的行為給予保護,就是妨礙著作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23]從立法體系上分析,我國著作權法將廣播組織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相分離,廣播組織并不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權利主體,不能控制互聯網領域的廣播電視作品的傳播。音、視頻節目在互聯網領域內的權利可由著作權人、表演者、錄音錄像制作者等權利主體進行主張。在立法沒有明確賦予廣播組織在互聯網領域控制傳播權利的法律現狀下,如果將廣播組織權擴大至互聯網領域,可能會縮減著作權人的網絡傳播權的范圍,改變著作權人與鄰接權人的權利分配。引自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4.國際公約還沒有將廣播組織權擴展到網絡空間。[24]從國際公約的立法情況來看,不管是《TRIPS協議》還是《保護表演者、音像制品制作者和廣播組織羅馬公約》,均未將轉播權的保護范圍擴展至網絡領域。再次,在互聯網領域,雖然廣播組織權的權利人不能對“轉播”予以控制,但著作權人或著作權的被許可人、錄音錄像制作者或錄音錄像制作者權的被許可人,仍可以信息網絡傳播權受到侵害為由獲得司法救濟。引自浙江省嘉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浙嘉知終字第7號民事判決書。這幾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理解我國著作權法上使用的“轉播”法律術語。筆者認為,我國著作權法使用的“轉播”應當作如下理解:
(一)我國現行著作權法對“轉播”作以下解釋,即:對廣播電視的轉播方式,既包括傳統的轉播方式(無線轉播),也包括由新技術帶來的轉播方式(有線轉播或者網絡傳輸等),可能更符合著作權法的立法本意。我國《著作權法》第45條第1款第(一)項使用了“轉播”之法律術語,在整部法律中使用了2次(第10條第1款第(十一)項和本條各使用一次),但一直沒有對其作出解釋性規定,這是由于我國著作權法對廣播電視“轉播”概念持開放性立場,并為廣播組織權“轉播”的概念擴展到無線、有線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提供了解釋的空間。2001年10月27日,我國對著作權法進行了第一次修訂。此次修訂有三個主要目的:(1)為加入WTO而符合《TRIPS協議》規定的基本原則、最低保護標準等需要。(2)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同時簽署了WCT和WPPT兩個新的國際條約,其目的是為適應網絡技術發展對著作權保護帶來的沖擊,同時增加了“信息網絡傳播權”,即授權通過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其作品、以錄音制品錄制的表演或者錄音制品,使之可為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得。著作權法通過此次修訂給著作權人、表演者和錄音制品制作者授予了該項權利。(3)我國加入WTO后,尤其是網絡技術的應用,必然對著作權帶來多方面影響。通過此次修訂加以應對。
在此背景下,2001年我國修訂的著作權法只是給著作權人、表演者和錄音錄像制作者授予了信息網絡傳播權。此次修訂著作權法時,立法者考慮到:1.《保護廣播組織條約》尚未通過,廣播組織能否享有通過有線以及網絡傳輸方式傳播廣播電視的權利沒有結論;2.當時的《保護廣播組織條約(草案)》的主要觀點認為廣播組織應當享有通過無線、有線以及網絡傳輸方式播放、轉播廣播電視節目信號的權利;3.《保護廣播組織條約(草案)》可能很快就會通過,到時候馬上修訂著作權法就會導致著作權法的不穩定。因此,我國著作權法采取了開放立場,即:即使《保護廣播組織條約(草案)》很快通過,我國著作權法只需要給予適當的解釋即可,不必重新修訂著作權法中的廣播組織權條款。假如《保護廣播組織條約(草案)》不能馬上通過,我國立法司法機關也完全可以根據技術發展、產業保護訴求以及我國著作權保護實際需要作出相應的解釋,避免因新技術發展給廣播組織保護帶來的沖擊和危害。
(二)將廣播組織權保護通過司法解釋擴張至網絡環境符合我國著作權法遵循的技術中立原則,并充分體現了保護廣播組織行業的初衷。1.雖然現有國際條約中關于廣播組織權的保護僅限于“無線”,[25]《TRIPS協議》第14條第3款:廣播組織有權禁止下列未經其授權的行為:錄制、復制錄制品、以無線廣播方式轉播以及將其電視廣播向公眾傳播。如各成員未授予廣播組織此類權利,則在遵守《伯爾尼公約》(1971)規定的前提下,應給予廣播的客體的版權所有權人阻止上述行為的可能性。我國雖然已加入《TRIPS協議》,該協定第14條規定的是“以無線廣播手段轉播”,并沒有包含有線方式的轉播。但是,《TRIPS協議》所作出的規定只是要求締約方必須履行的最低義務標準,并不能妨礙締約方為其國民提供高于該最低標準的保護。但國際條約中約定的是對廣播組織權保護的最低標準。我國著作權法對廣播電視“轉播”不僅指無線方式,包括有線方式,保護范圍大于國際條約中規定的最低義務。2001年第一次修改著作權法過程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法工委”)于2001年4月24日提出了“廣播電臺、電視臺有權禁止未經許可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以無線方式重播”的建議條文。10月27日,法工委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了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建議:為了應對網絡環境下有線電視的快速發展,著作權法應當對廣播電視的有線播放權作出規定;同時建議將上述建議條文中的“重播”改為“轉播”。在此基礎上,法工委建議將該項修改為“將其播放的廣播、電視轉播”。該項建議被修正案采納。這種立法方案反映了我國保護廣播組織行業的宗旨和技術中立原則。2.隨著技術的發展,廣播電視信號傳播已拓展至網絡環境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給予司法上的公平合理解釋。例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民法研究室主任姚紅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釋解》[26]參見姚紅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釋解》,群眾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頁。就“轉播”給出了清晰的解釋:“‘轉播’不僅指無線方式,也包括有線方式。”此處針對“轉播”作出的解釋就有立法解釋的意味,值得司法審判機關借鑒。
(三)將廣播組織權益保護通過司法解釋擴張至網絡環境符合《條約草案合并文本》的基本精神。1996年12月20日通過的WCT和WPPT分別給著作權人、表演者和錄音制品制作者授予了信息網絡傳播權,將使其著作權和相關權之效力延伸至網絡環境。現在,該《條約草案》雖然仍在商議中,但是,參與談判國家一致認為,廣播組織應當享有通過無線、有線、網絡及其他任何方式傳輸其廣播電視信號的權利,并就相關條文提出建議。例如,2017年5月,《廣播組織條約》最新的合并文本(SCCR/34/3)定義:“‘轉播’系指原廣播組織[原有線廣播組織]以外的任何其他實體,或經原廣播組織[原有線廣播組織]授權者,以任何方式播送載有節目的信號供公眾接收,無論是同時播送、近同時播送[或是滯后播送]。”[27]See WIPO Doc. SCCR/34/3, REVISED CONSOLIDATED TEXT ON DEFINITIONS, OBJECT OF PROTECTION, RIGHTS TO BE GRANTED AND OTHER ISSUES, March 13,2017,p7.注意,“以任何方式”是沒有其他選項的唯一建議條款,已為會議大多數代表團所接受。另根據《條約草案合并文本》第3條(同樣是沒有其他選項的唯一建議條款)規定:“三、所授權利(1)(i)廣播組織[和有線廣播組織]應享有授權以任何方式對其載有節目的信號向公眾轉播的專有權。(ii)廣播組織[和有線廣播組織]還應享有授權以公眾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以獲得的方式,對其載有節目的信號進行轉播的專有權。(2)廣播組織[和有線廣播組織]還應當有權禁止未經授權以任何方式轉播其預廣播信號。”在“所授權利”中同樣規定了“以任何方式對其載有節目的信號向公眾轉播的專有權”,表明了將廣播組織權保護擴展至互聯網及其他“任何方式”的立場。可見,根據SCCR會議已達成的一致意見,轉播概念應該擴展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互聯網)而不應僅局限于無線或者有線方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廣播組織條約草案》現在還沒有被簽訂,但是,該《條約草案》關于在網絡環境下廣播組織轉播權將被延伸至互聯網的建議條款,已經得到了WIPO成員國廣泛的認同。
三、網絡傳輸侵犯廣播組織轉播權分析
眾所周知,針對廣播組織轉播權,《TRIPS協議》第14條所規定的是“以無線廣播手段轉播”,而沒有規定有線方式的轉播。根據該項規定,我國有人從法律實務角度并且在具體審判實踐中(如“嘉興華數”糾紛案件的判決)堅持廣播組織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享有無線轉播權,不能享有網絡傳輸轉播權。這種觀點沒有充分理解《TRIPS協議》的基本旨趣:《TRIPS協議》規定只是各締約方應當遵守的最低標準,并不妨礙締約方為其國民提供更高的保護。[28]參見吳漢東著:《知識產權精要》,法律出版社2017年8月版,第300-302頁。更何況,我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并沒有明確將對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的廣播、電視的轉播局限于無線方式。我國《著作權法》立法者以開放的態度對待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的廣播、電視的轉播,沒有出現無線和有線之類的術語,使得我國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對其播放的廣播、電視,不僅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擅自以無線方式轉播,同樣有權禁止他人未經許可擅自以有線方式轉播。《著作權法》第48條第5項規定,未經許可,播放或者復制其廣播、電視的,就構成對廣播電臺、電視臺依法享有的廣播組織權的侵犯,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9]我國《著作權法》(2010年修訂)第48條規定:有下列侵權行為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同時損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責令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銷毀侵權復制品,并可處以罰款;情節嚴重的,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還可以沒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權復制品的材料、工具、設備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五)未經許可,播放或者復制廣播、電視的,本法另有規定的除外。該條款使用的術語非常簡潔明了:“未經許可,播放其廣播、電視的”,就構成侵權。這里的播放應當包括但不限于首次播放、網絡傳輸、無線轉播和有線轉播等。
從著作權法和侵權行為法基本理論角度看,判斷網絡視頻平臺經營者未經許可傳輸廣播組織的廣播、電視是否構成對廣播組織轉播權的侵犯,需要抓住以下要點:
1.網絡傳輸廣播、電視是否屬于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轉播。如上所述,通過網絡傳輸廣播、電視屬于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轉播行為。實際上,網絡傳輸廣播、電視就是通過有線方式對廣播、電視的轉播。有學者認為我國著作權法禁止他人未經許可,擅自以無線方式對廣播、電視轉播的行為,而不禁止他人以有線方式進行轉播。這種觀點是對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限制性解讀,違背了其立法本意。[30]參見姚紅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釋解》,群眾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頁。
2.網絡傳輸廣播、電視是否侵權?我國《著作權法》第48條第1款第(五)項規定,未經許可,擅自播放廣播組織受著作權法保護的廣播、電視,就構成對其廣播組織轉播權的侵犯。由此規定可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侵犯廣播組織權中的轉播權只須滿足兩個條件:(1)其實施的播放(包括傳播、轉播)廣播、電視的行為,沒有法律依據,并且不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例外或者免責情形;(2)其播放(包括傳播、轉播)的廣播、電視是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對象。特別注意:該條款所規定的“播放”(包括傳播、轉播)行為,并沒有對有線、無線、網絡傳輸或者其他方式的例外性或者排除性規定,即都包括在內。因此,未經許可,任何人擅自通過網絡傳輸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廣播、電視,就構成對廣播組織權中轉播權的侵犯。但是,我國著作權法明確規定的不屬于侵犯廣播組織權的情形除外。事實上,我國《著作權法》及其《實施條例》并沒有規定侵犯廣播組織轉播權的例外。
針對一項傳輸廣播、電視的行為是否侵犯廣播組織轉播權,有關當事人或者司法機關必須同時分析:(1)其行為是否具有合法依據;(2)該行為所涉及到的廣播、電視是否受著作權保護。該行為倘若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就需要進一步檢視其行為是否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例外情形。若是,則不構成侵權;若不是,則構成侵權。構成對廣播組織轉播權的侵犯,不必考慮行為人的主觀因素。針對廣播、電視實施的網絡傳輸行為,若不能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就不構成對廣播組織轉播權的侵犯。
結 語
現在正值兩個重要機遇期,一是WIPO正在積極推進簽訂《廣播組織條約》的外交會議,正式簽訂該條約。從已有的《條約草案合并文本》的建議文本看,未來的《廣播組織條約》很有可能將廣播組織權擴展至網絡環境,為廣播組織提供更加充分合理的保護。我國是WIPO成員國,一直在積極參與該條約的起草和協調工作。二是我國正處于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進程中,其修訂涉及到廣播組織權的條款,希望改變原來關于“轉播”“傳播”或者“播放”是否包括網絡傳輸的模糊性態度,對其作出明晰規定。本文所提出的觀點,希望能夠得到有關方面的關注,對有關立法起到某種參考作用。
Network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which enriching the broadcast modes, brings confus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Traditionally, broadcast and TV mainly communicates to the public by wireless means, such as magnetic signal.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the signals of broadcast and TV can not only communicate through wireless means but also through the Internet, leading to the confl icts between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and network operators. As to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the right to rebroadcast, there is a clear disagreement among the negotiating countries when they participated to draft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Draft Treaty. In May 2017, after the compromise and concessions, all negotiating countries reach a similar cognition of the right to rebroadcast,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newly formed the Draft Treaty Merged Text.Personnel concerned in China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specifi c content of the right to rebroadcast, but managed to reach a basic consensus along with the propelling the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Draft Treaty.
network environment;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 broadcastamp;television rebroadcast right
曹新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葉霖,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2017級博士研究生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15年重點研究項目《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確定標準研究》中期成果,項目編號:15JJD8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