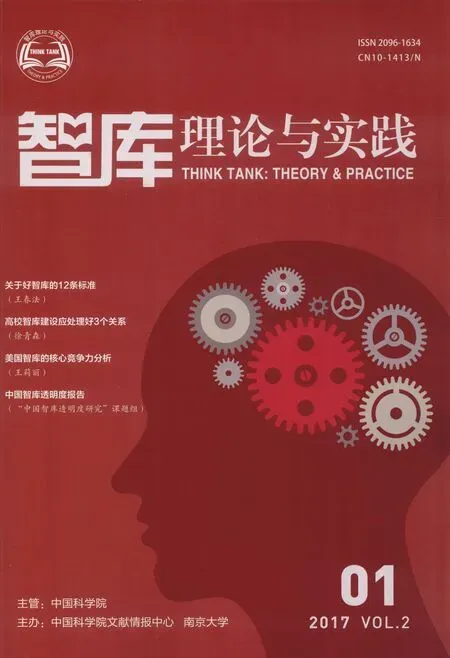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分析
■ 王莉麗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北京 100089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北京 10087
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分析
■ 王莉麗1,21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 北京 1000892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北京 100872
[目的/意義]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庫承擔著知識創新、知識傳播的關鍵作用,是國家和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動力之源。研究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可以為中國智庫的研究和發展提供有益參照。[方法/過程]本文從跨學科的視角切入,以“智力資本”理論和“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為框架,分析指出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源于其強大的智力資本,智力資本由人才資本、傳播資本與制度資本三大要素構成。人才資本是美國智庫思想創新的源泉和基礎,傳播資本是智庫實現影響力的途徑,制度資本則為兩者的實現提供了切實制度保障。制度資本分為宏觀和微觀兩部分,宏觀層面是指智庫所處的政策環境,微觀層面主要是指智庫保持獨立性的機制。[結果/結論]美國智庫的發展興盛及其影響力實現得益于其高素質的人才、全方位的傳播策略、完善的政策環境,正是這些因素為其發展提供了土壤、空間、動力和基礎。
智庫 核心競爭力 智力資本
最近10年來,智庫在全球范圍內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智庫研究也逐漸成為一門重要的跨學科顯學。近年來,對于智庫核心競爭力的探討也成為一個重要議題,目前主要集中在智庫影響力的表現形式、傳播渠道和量化指標的確定和評價上,較為缺乏更深層面的跨學科剖析。本文結合經濟學、傳播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思想,主要運用“智力資本”理論、“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框架對美國智庫進行分析,指出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正是智力資本,相對于一般社會組織而言,智力資本在智庫的發展與創新上更是占據了主要地位。其構成要素主要包括:人才資本、制度資本、傳播資本,三者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智庫的核心競爭力。人才資本主要是指智庫的領導人才和研究人才。制度資本主要指智庫發展所處的宏觀政策環境和微觀運行機制。傳播資本是指智庫在影響決策者和輿論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各種關系與傳播網絡以實現影響力的最大化。
1 智力資本及其要素分析
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智庫相比,美國智庫不僅起源最早、數量最多,而且對政策的影響力也是最大的。究其原因,智庫學界和業界有著不同的觀點。有學者指出,決定各國智庫發展程度和影響力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政治體制、公民社會、言論環境、經濟發展程度、慈善文化、大學的數量和獨立性等[1]。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認為,智庫其實就是聚集眾人之智,創新的思想是智庫的核心競爭力①引自筆者 2014年9月22日在北京對約翰?桑頓教授的訪談。。從輿論學的視角來看,智庫是在一定的政治體制下產生的,其作用的大小以及發揮作用的空間是由所在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決定的。沒有一定的政治民主,智庫的充分發展是不可能的。智庫發展首先需要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環境,充足的資金是它生存的重要條件。智庫與政府機構、社會、特別是媒體之間的平等地位與良好互動, 決定它能否產生好的研究成果和影響力[2]。以上幾種觀點從不同的視角對美國智庫影響力產生的基礎進行了分析,但都未能清晰闡釋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及其構成要素。“智力資本”理論和“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
智力資本理論主要建立在人力資本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智力資本的概念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經典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與物質資本相對應的“精神資本”概念,且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精神資本”與當今經濟學中“人力資本”的概念基本一致,廣義“精神資本”的概念則包括人力資本和所有“外化”的精神存量,即文化藝術、政治制度等等[3]。李斯特所說的“精神資本”正是現代學界所言的智力資本概念的雛形[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提出了多種智力資本概念和要素模型。有學者將智力資本定義為:雇員資本、組織資本和外部關系資本的總和[5]。還有學者把智力資本簡單地歸為“使公司得以運行的所有無形資產的總稱”,并把智力資本的意義體現在一個簡潔的公式中,即“企業=有形資產+智力資本”。它具體包括市場資產、知識產權資產、人才資產、基礎機構資產四大類[6]。目前,學界認同度較高的是將智力資本分為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關系資本三個基本要素[7]。總體而言,目前關于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層面,關于智力資本在非營利組織、在國家和地區層面的戰略作用的研究較少。而美國智庫在機構屬性上是指非營利組織,主要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組成,其產生和存在的主要目的不是營利,而是以是否影響了公共政策和輿論為目標,向全社會提供智力資源和思想產品。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直接套用這個框架來分析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難以清楚闡釋。但是,我們可以結合智庫自身的特點以及其他學科理論,進一步發展這個理論框架。“公共政策輿論場”是建立在傳播學、公共政策學、輿論學基礎上提出的一個理論框架。“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認為,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公共政策的形成是政府、智庫、利益集團、大眾傳媒、公眾通過各種傳播媒介的互動達成的共識。美國智庫的影響力正是在與這些不同輿論因素的互動中得以形成,并通過不同輿論因素所承擔的具體功能得以體現。在“公共政策輿論場”中,智庫處于“輿論聚散核心”的地位。一方面,智庫是輿論生產的“工廠”,是吸引各種各樣的觀點看法、主張、建議,融和、相互碰撞的磁場和聚集地;另一方面,智庫產品是輿論傳播的內容核心,它通過各種傳播策略和傳播渠道影響其他輿論[8]。“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為我們理解美國智庫輿論影響力產生提供了清晰的理論支點。美國智庫的影響力一方面源于其思想創新的能力,另一方面源于其強大的傳播力。
依據“智力資本”理論和“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結合智庫本身的特點,筆者認為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正是智力資本,相對于一般社會組織而言,智力資本在智庫的發展與創新上更是占據了主要地位。其構成要素主要包括:人才資本(人力資本)、制度資本(結構資本)、傳播資本(關系資本),三者相輔相成,共同構建了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在這里,筆者沒有沿用“智力資本”理論框架中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關系資本三個概念。而是結合了“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對智庫傳播力重要性的認識和智庫本身的特點,對智庫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做了新的界定。人才資本主要是指智庫的領導人才和研究人才。制度資本主要指智庫發展所處的宏觀政策環境和微觀運行機制。傳播資本是指智庫在影響決策者和輿論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各種關系與傳播網絡以實現影響力的最大化。接下來,本文就以此為框架,對美國智庫智力資本構成的三要素進行具體分析。
2 人才資本是智庫發展的基礎
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以知識為基礎的智力資本,起主導作用的資源已經不是資金、設備、原材料等自然資源、有形資產,而是以人的智力、知識、信息為主的智力資本、無形資產。智庫作為知識密集型組織,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進行思想創新,人才資本是第一要素。智庫的人力資本由領導人才和研究人才兩部分構成。領導人才需具備政治智慧和政策把握能力、智庫管理和運營能力,并且具有全球意識和傳播意識。在美國,這種智庫領導者也被稱為政策實業家。智庫的研究人才主要是指政策專家。政策專家團隊通常由學者、前任政府官員、媒體和商界精英共同構成,其中學者和前任政府官員是政策專家團隊的核心人物,本文所指的政策專家主要指這兩類人才。在美國智庫界,由于“旋轉門”機制的存在,很多政策專家具備多元化的職業背景,這保證了思想研究與政治實踐之間轉換的可能性。
一支高素質的政策專家隊伍是智庫生存發展的生命力所在。智庫的政策專家具有多重角色,他們既是維護人類基本價值的知識分子,又是政策領域的權威,他們不但是政策理念的生產者,也是思想的傳播者。具體而言,政策專家需要具備的素質分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政策專家須具備深厚的研究功底,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具備一定的政策研究權威。第二,政策專家要具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快速的政策反應力,要對國家戰略和現實政治有相對充分的了解。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于個人的私利之上。第三,政策專家要具備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溝通能力,擅于與媒體打交道,積極營銷自己的思想、引導輿論。除了以上三點外,政策專家需要有道德責任,不但敢盡言責還要善盡言責,考慮和顧及他們的言論和理念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后果。政策專家的這種道德責任有些類似于韋伯所說的政治家應負的責任倫理,它必須考慮和顧及其政治決定將影響到許多人的社會后果。
美國智庫的成功與其強有力的領導者是分不開的,理想而言,一家智庫的領導者需要具備學術和政界的經驗,要與商界和媒體有著良好的關系,既要是一個演說家又要是一個實干家。一般而言,在智庫的組織架構中,設有董事會、總裁、副總裁、中心主任,他們組成智庫的領導層,董事會主席和總裁是最核心的領導者,他們個人的視野和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家智庫的發展方向和影響力范圍。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現任董事會聯席主席是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他是高盛銀行前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現任巴里克黃金集團董事會主席,同時還兼任清華大學教授,負責“全球領導力”項目。因為約翰?桑頓在華爾街乃至全球商界的人脈和影響力,布魯金斯的財政狀況在他擔任董事會主席以來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勢頭。而約翰?桑頓本人對中國的強烈興趣和他希望推動中美關系、推動世界發展的良好愿望,則直接促成了2003年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及其北京辦公室的成立。自2015年以來,美國智庫界展開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在眾聲喧嘩中,以杰弗里?貝德(Jeffrey Bader)、李成為代表的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的學者在這場對華政策大辯論中發揮了理性看待中美關系、推進中美關系繼續和諧發展的重要作用。傳統基金會的總裁艾德溫?福爾納(Edwin Feulner)則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詮釋領導者的力量。擁有MBA學位的艾德溫?福爾納1973年作為董事會成員參與創建了傳統基金會,自1977年開始擔任總裁。他認為傳統基金會不應該成為一個學術研究機構,而應該成為一個商業化運作的、采取各種營銷機制尋求效益最大化的機構。“我們的作用就是要盡力影響華盛頓的公共政策圈,具體的講,最重要的是影響國會山,其次是行政部門,第三是全國性的新聞媒體。[9]”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傳統基金會從1977年只有9個人的小研究機構成為如今擁有220名工作人員的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智庫之一。事實上,每一家具有影響力的美國智庫都可以看到其領導者的理念和影響貫穿于整個機構的運作之中。美國智庫的發展、壯大與其卓越的領導者密切相關。
很顯然,無論是領導人才還是政策專家,都屬于稀缺資源,美國智庫獲取人才資本有賴于“旋轉門”機制。“旋轉門”機制是美國智庫最具特色的現象,其產生和運轉根植于美國的政治體制。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卸任的官員很多會到智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智庫的研究者很多到政府擔任要職,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的流通就是美國的“旋轉門”。一方面,旋轉門機制使得智庫成為政府人才的蓄水池,另一方面,這種機制也為智庫提供了大量政策人才。美國的行政當局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政府部長等高級閣員不是由議會黨團產生,也極少來自公務員,而是來自精英薈萃的智庫,這一點與歐洲國家和中國都很不相同。也因此,每隔4年有很多學者會從智庫進入政府成為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對此,肯特·韋弗(Kent Weaver),認為“智庫作為政府人才供應商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精英滲透的結果”[10]。每當新一屆總統上任之際,除了一大批智庫的學者進入政府之外,同時也會有很多前任政府官員進入智庫從事研究工作。例如在布什政府擔任財長的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離開政府之后進入霍普金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隨后創辦了智庫保爾森基金會。曾于2002—2006年間任美國在臺協會負責人的包道格(Douglas Paal),現在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副總裁。
3 傳播資本構建了影響力網絡
按照“公共政策輿論場”理論,美國智庫的影響力一方面源于其思想創新的能力,另一方面源于其全方位的傳播能力。美國智庫之所以在全球范圍內發揮著重要的思想引領力量正是建立在其強大的傳播資本基礎之上的。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演變,美國智庫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信息傳播模式和全方位的信息傳播機制。具體而言,美國智庫采取的主要傳播方式有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在大多數情況下,3種傳播模式都是同時采用,互為補充和促進。人際傳播有助于智庫的研究成果直接影響決策者,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擔負著議程設置和塑造公共輿論的作用,從而間接影響決策者。
所謂人際傳播方式主要是指智庫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依靠人際關系網影響政策制定,比如“旋轉門”構建的人際傳播網和董事會的信息傳播網。“旋轉門”機制所構建的政府和智庫之間的縱橫交錯的人際關系網絡使得智庫的輿論影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這也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chultz)所說的“著名政治人物和智庫在一起為智庫的專家們開辟了多種渠道”[11]。美國智庫的最高決策和管理機構是董事會,他們通常由著名的政界、商界、學界、非政府組織的社會精英組成。因為這些董事會成員本身都是著名的輿論領袖,而且他們與社會各界都有著密切的關系網絡,他們通過人際傳播所帶來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組織傳播指的是以組織為主體所從事的信息傳播活動,這是美國智庫塑造品牌影響力和機構美譽度的一個重要渠道。通過組織傳播,美國智庫為社會公眾、決策者、專業人士構建了一個意見交流的平臺,同時也為決策者提供了一個接受外交政策教育的基地。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這種傳播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國智庫被稱為沒有學生的大學。
現代社會,大眾傳播是信息環境的主要營造者,是人類感知外部世界和經驗的一扇窗口。大眾傳播通過對信息的大量生產、復制和大面積傳播,能夠在短時間內造成普遍的輿論聲勢。對此,唐納德? 阿貝爾森(Donald Abelson)指出“在國會專門委員會提供立場鮮明的政策主張,出版有爭議的國內或者國際問題的研究報告都可能在某些政策制定領域引起關注,但其所產生的影響力可能遠比不上CBS晚間新聞上的一個畫面或者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上的一篇評論文章”[11]。美國各大智庫都積極鼓勵自己的學者接受廣播、電視媒體的訪問,學者們面向社會公眾分析當前政治局勢,闡述自己的觀點,從而起到了引導公共輿論的作用[12]。在這些多元化的大眾傳播媒介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網絡媒介。當全球化在經濟、政治領域向人類快速逼近時,美國智庫的信息傳播也進入全球意識階段。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智庫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官方網站,并以此為基點,以博客、播客、推特、臉譜各種社交媒體為結點,構建了內容豐富、形式多元、雙向互動的智庫全媒體傳播網絡。新媒體的傳播活動具有開放、多元、瞬時、互動等傳統媒體難以企及的優勢,因此成為表達意見、建立認同、塑造行為的重要媒介。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布魯金斯學會的網站不斷根據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受眾需求的改變調整新媒體傳播策略。2013年6月布魯金斯學會網站推出了類似于《紐約時報》的“雪崩”模式制作的數字化專題,目的在于通過融媒體傳播方式激發受眾對重要議題的興趣和討論。第一期推出后,網頁停留時間提高了125%,其中72%的訪問者為新用戶[13]。一方面,全方位的信息傳播為智庫帶來了市場競爭力和影響力,另一方面卻從某種程度上使得美國智庫的商業化傾向越來越重。雖然美國智庫是一個在思想市場自由競爭的經濟體,但是在具有商業屬性的同時,美國智庫從本質上是一個服務于公共事業的政策研究機構。如何平衡與把握好兩者之間的關系,是目前美國智庫面臨的巨大挑戰。
4 制度資本提供機制保障
人才資本是智庫思想創新的源泉和基礎,傳播資本是智庫實現影響力的途徑,制度則為兩者的實現提供保障。對于智庫而言,擁有人才資本僅僅是成功的第一步,要實現智庫的價值,還必須重視制度資本的培植。美國智庫的制度資本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上主要是完備的決策咨詢機制和完善的稅收制度。微觀層面是指智庫全方位的獨立性和商業化運行機制。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政府的決策更依賴于外部咨詢。廣泛地使用智庫進行外部咨詢參與決策被稱為“美國現象”[14]。美國政府將咨詢作為決策過程的法定程序,要求項目的論證、投資、運作、完成等各個階段,都要有不同的咨詢報告[15]。美國對決策咨詢業的管理實行政府宏觀調控、行業協會微觀約束的機制。政府負責總體規劃,制定決策咨詢發展計劃、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標準,從政府決策的出臺、項目的招標、運作到咨詢機構的資格認定等諸多方面均有相應的規定。美國的決策咨詢體系作為一種較為成熟的制度設計,以《聯邦咨詢委員會法》 (The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為核心和基礎。《聯邦咨詢委員會法》于1972年確立,其目的在于保證各種形式的專家咨詢機構建議的客觀性以及公眾在專家咨詢過程中的知情權[16]。《聯邦咨詢委員會法》從平衡性要求、開放性要求和職能單一要求三方面來確保專家咨詢系統良好運轉。 “平衡性要求”可以“中和”專家由于自身專業原因而產生的利益或觀點上的傾向性,保障專家所代表的各領域專業知識能夠綜合全面進入決策,從而有助于克服專家咨詢組織由于專業知識所限而可能發生的立場偏向,促使咨詢效果實現理性的最大化。同時,平衡性要求也有效限制了行政機關在專家選擇上的利益傾向性。 “開放性要求”規定涉及專家咨詢過程的所有文件、會議,除在立法上獲得豁免情形外,都應無條件向公眾公開。“職能單一性”對咨詢委員會可能發生的超越自身職能范圍和權力范圍的情況實現預防[17]。美國智庫作為非營利機構,其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穩定的資金支撐,而完善的稅收減免制度為智庫募集資金提供了切實保障。肯特?韋弗(Kent Weaver)和安德魯?里奇(Andrew Rich)通過定量分析指出:“影響美國智庫媒介曝光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資金,美國影響力排名前5位的智庫運營資金都不少于1千萬美金。”[18]美國智庫的運營資金一般來自于基金會、企業、個人捐款和政府合同,多元化的資金來源避免了智庫對某一資金源的過度依賴所帶來的弊端,有利于保持研究的獨立和客觀。
以上是從宏觀層面對制度資本的分析,從微觀層面,美國智庫的制度資本是指其全方位的獨立性和商業化的運行機制。美國智庫大都宣稱自己是非黨派、非政府的獨立政策研究機構。其獨立性包括思想的獨立、資金的獨立和政治的獨立。所謂思想的獨立是指智庫專家們研究的獨立性,學者以開放的思維來開始他們的研究項目,并通過對事實的客觀分析獲得結論。研究的獨立性保證了智庫產品的高質量和創新性。為了保證思想的獨立性,美國智庫在機構設置上以研究人員為核心,一般分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兩大塊,政策研究是核心,行政管理服務于政策研究。資金的獨立是指智庫雖然接受基金會、企業、個人的資助以及政府的合同項目資金,但是智庫的研究不受資金來源的影響。美國智庫大都是企業化運作、商業化管理。資金的來源直接決定和影響了美國智庫研究選題設置和研究方向,每家智庫在接受資金捐贈時都力圖保證自己的研究過程和結論不受資金來源的影響。但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是,金錢總是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思想的走向。為了保證資金的獨立性,美國智庫的資金來源大都保持盡可能的多元化,包括大量公共和私人的資助方。政治的獨立是指美國智庫追求獨立于政黨之外,在研究過程中遵循客觀、獨立,不受任何黨派政治和利益的影響。對于這一點,很多智庫的研究者們不以為然,經常把智庫的研究傾向和觀點按照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中立來劃分,并以此為依據判斷智庫與政黨的關系。由于這種根植于美國政治傳統的偏見,使得美國智庫很難對某一具體問題的研究產生絕對客觀、中立的思想。事實上,大多數美國智庫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黨派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智庫都力圖保持自己研究成果的獨立和高品質;另一方面,美國智庫的多樣性和競爭性使得不同的觀點和聲音得以表達,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種偏見所帶來的危害。美國智庫的獨立也只是有限的獨立,它不可能脫離其生存的政治、經濟、文化土壤。不同的智庫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也總是會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同的傾向性和偏見。
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庫承擔著知識創新、知識傳播的關鍵作用,是國家和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動力之源。美國智庫的發展興盛及其影響力實現得益于其高素質的人才、全方位的傳播策略,與其所處的文化、經濟、政治環境及其本身的運行機制有著密切關系,正是這些智力資本因素為其提供了土壤、空間、動力和基礎。研究美國智庫的智力資本及其要素,可以為中國智庫的研究和發展提供有益參照。
[1] James McGann. Comparative Think Tank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M]. Edward Elgar: Northampton, 2005.
[2] 劉建明, 紀忠慧, 王莉麗. 輿論學概論[M]. 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009: 205.
[3]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M]. 北京: 華夏出版社, 2009.
[4] TA Stewart. Your Company’s Most Valuable Asset: Intellectual Capital[J]. Fortune 1994(13): 68-76.
[5] Saint-Onge, Hubert. Tacit Knowledge: The Key to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J].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1996(2): 10-14.
[6] 安妮?布魯金. 第三資源智力資本及其管理[M]. 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8.
[7] Edvinsson. L, Michael S. Malone. Intellectual Capital: Realizing Your Company’s True Value by Finding Its Hidden Brainpower[J]. Harper Business: New York 1997.
[8] 王莉麗. 論美國智庫輿論影響力的形成機制[J]. 國外社會科學, 2014(3): 51-55.
[9] Abelson, Donald.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M].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96: 114.
[10] Weaver, Kent.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J].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89(22): 563-578.
[11] Abelson, Donald. A Capitol Idea[M].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2006.
[12] Rich, Andrew.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4: 68.
[13] 王莉麗. 以史為鑒: 提升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N]. 學習時報, 2014-11-10(06).
[14] Dye, Thomas.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M]. Prentice-Hall: New Jersey, 1987.
[15] 郝佳芬. 國外決策咨詢研究綜述[J]. 新世紀圖書館, 2003(6): 60-63.
[16] 楊誠虎, 李文才. 發達國家決策咨詢制度[M]. 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1: 36.
[17] 王錫鋅. 我國公共決策專家咨詢制度的悖論及其克服[J]. 法商研究, 2007(2): 113-121.
[18] Abelson, Donald. Do Think Tanks Matte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M].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2002: 90-92.
Analysis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Wang Lili1,21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9
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conomy, think tan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and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for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the core competency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growth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Method/proces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cluded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of public policy” that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came from their strong intellectual capital, which consisted of talents,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 capitals. Talents capital was the source of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for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communication capital served as the way to exert think tanks’ influence, while the realization of these two relied on the institution capital. Institutional capital could be analyzed from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The macrolevel referred to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micro-level was mainly about the mechanism for think tanks to remain their independency. [Result/conclusion] The prosperity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influence are attributed to high quality talents, the all-rou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nd developed policy environment, all of which provide the source, space, impetus and foundation for their growth.
think tank core competency intellectual capital
G311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7.01.03
2016-12-05
2017-01-11 本文責任編輯:欒瑞英
王莉麗,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新聞學院副教授,E-mail: wlltsinghua@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