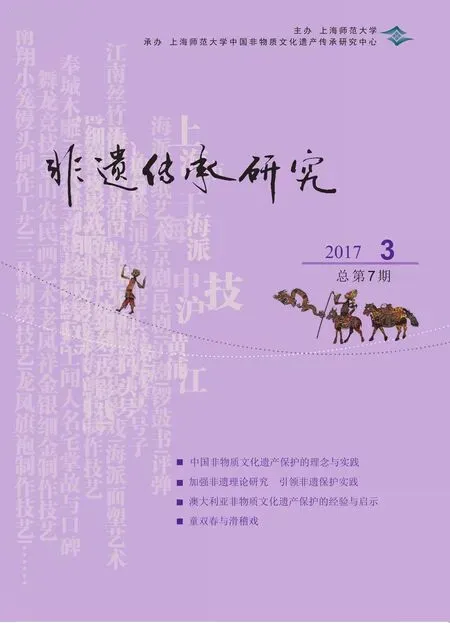加強非遺理論研究 引領非遺保護實踐
蔡豐明
自1997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人類口頭與非物質(zhì)遺產(chǎn)”保護的命題以來,整個世界的非遺保護事業(yè)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在中國,隨著非遺保護體系的日益完善、非遺傳承機制的逐漸建立,以及非遺項目推廣、宣傳活動的廣泛開展,非遺保護這項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文化事業(yè)已經(jīng)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但是相對大量的非遺保護實踐工作而言,有關非遺保護的理論研究卻較為滯后,具體表現(xiàn)在非遺保護的理論體系還不夠完善,非遺保護的理論成果還較為缺乏,非遺保護的理論隊伍還較為薄弱等方面,這勢必會對快速發(fā)展的非遺保護實踐產(chǎn)生不利影響。因此,當前我們很有必要加強對于非遺保護的理論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理論體系,以對當前紅火興盛的非遺保護實踐起到較好的引領與指導作用。
筆者主要從非遺的本質(zhì)內(nèi)涵與基本特征、非遺保護的方法、非遺保護的價值等一些基本理論方面出發(fā),提出一些思考。
1.有關非遺的本質(zhì)內(nèi)涵與基本特征
“非遺”作為一個20世紀后期開始由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學術命題,在理論上最為重要,也是最需要闡釋清楚的就是它的本質(zhì)內(nèi)涵與基本特征。什么叫做“非遺”?“非遺”本身又包含哪些最基本的特點?這是每一個從事非遺理論研究或者實踐工作的人所必須認識的。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制定的《保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中,對非遺作了明確定義:“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指被各社區(qū)、群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xiàn)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在這個定義中,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重點強調(diào)了創(chuàng)造非遺的主體,即“各社區(qū)、群體、有時為個人”;以及非遺的主要內(nèi)涵,即“各種實踐、表演、表現(xiàn)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在同一個文本中,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對非遺的內(nèi)容類型作了具體的闡述,指出“非遺”的內(nèi)容主要包括了“口頭傳說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jié)慶”“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tǒng)手工藝技能”等5個方面。這種對于非遺內(nèi)容的表述,體現(xiàn)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非遺概念宏觀且前沿的認識,它大大突破了原來的“民間文藝”“民間知識”“民間創(chuàng)作”以及“民間工藝”之類較為單一的層面,將非遺的對象拓展到了與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相對應的所有以口頭與行為方式體現(xiàn)的人類文化遺產(chǎn)領域。這一定義的提出,不僅拓展了人類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范疇,而且也使人們對于“文化遺產(chǎn)”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出的這種既具有宏觀性,又具有前沿性的非遺理念,得到了世界上很多國家的認同,我國作為一個歷史資源豐富、文化遺產(chǎn)眾多的文明古國,于2004年就已經(jīng)成為這一公約的締約國之一,并且在非遺保護的事業(yè)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值得重視的是,我國在對于非遺概念的闡釋上除了遵循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基本內(nèi)容以外,又創(chuàng)造性地形成了一個更加具有中國本土話語特色的定義,那就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指各種以非物質(zhì)形態(tài)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包括口頭傳統(tǒng)、傳統(tǒng)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jié)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知識和實踐、傳統(tǒng)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見《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通知》,2005年第42號]這一定義中所闡述的內(nèi)容,與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中的表述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更加強調(diào)了“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等這些非遺所具有的基本屬性,使得非遺的本質(zhì)內(nèi)涵更容易為中國本土的民眾所理解。
在清楚非遺的概念、定義以及本質(zhì)內(nèi)涵以后,接下來是關于非遺的基本特征問題。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我國所規(guī)定的非遺定義,筆者認為非遺最為重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無形性。所謂無形性,是指“以非物態(tài)的方式”而存在的、主要以口頭與行為方式進行表達與傳承的文化遺產(chǎn)形式,它與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表現(xiàn)方式上有很大區(qū)別。“遺產(chǎn)”一詞最早是指私人遺留下來的財產(chǎn),后來被逐漸推廣引申到社會文化領域,于是便出現(xiàn)了所謂的“文化遺產(chǎn)”以及“文化遺產(chǎn)保護”。法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對“文化遺產(chǎn)”進行保護的國家,1840年,法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部文化建筑保護法——《歷史性建筑法案》,此后,又先后制定了《紀念物保護法》《歷史古跡法》等相關的文化遺產(chǎn)保護法律。尤其在《歷史古跡法》這部法律中,法國在原來具體的“建筑物”“紀念物”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概念,并且進一步擴大了保護的范圍。1984年,法國又正式設立了“文化遺產(chǎn)日”,并規(guī)定每年9月的第三個周日為“文化遺產(chǎn)日”。法國這種對于文化遺產(chǎn)的理念以及有關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做法,后來也得到了歐洲許多國家的認同與響應。但是當時法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提出的文化遺產(chǎn)保護,重點主要是在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方面,包括古遺址、建筑物、街區(qū)、歷史紀念物等等,而對于那些包括各種以非物態(tài)形式出現(xiàn)的,即現(xiàn)在所謂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方面的內(nèi)容則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相比較而言,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把文化遺產(chǎn)分為“有形文化財”與“無形文化財”的國家,早在1950年5月,日本就制定了《文化財保護法》,把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建筑物、紀念物等文化遺產(chǎn)同時列入了國家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范疇。隨后,韓國于1962年1月也把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chǎn)分為“有形文化財”與“無形文化財”,這是非遺概念產(chǎn)生的最早源頭。
在這些文化遺產(chǎn)法中,已經(jīng)明確提出了“無形文化遺產(chǎn)”的概念,這一概念后來被翻譯成英文就是“intangible heritage”,也就是“沒有形的”“看不見的”文化遺產(chǎn)。從日本、韓國“無形文化財”的具體內(nèi)容來看,主要指的是那些具有較高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的傳統(tǒng)戲劇、音樂、工藝技術等文化成果。另外,在日本、韓國的《文化財保護法》中,還涉及到“民俗文化財”一項,包括衣食住、職(行)業(yè)、信仰、例行節(jié)日等風俗習慣等等,其實也是屬于現(xiàn)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范疇。結合英文對于無形文化遺產(chǎn)的翻譯以及其實際所指的具體內(nèi)容可以看出,所謂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其最為本質(zhì)的特征就是“無形性”,也就是不以物質(zhì)形態(tài)存在的,主要以語言、行為、技藝等各種以非物態(tài)形式出現(xiàn)的,以人的活動、傳承為載體的文化遺產(chǎn)形式。
(2)公共性。非遺是一種具有公共性的文化遺產(chǎn),它與私人的遺產(chǎn)有很大不同。非遺的這種公共性特點具體表現(xiàn)在如下三個方面:①非遺事象創(chuàng)作主體的公共性。②非遺精神價值的公共性。③非遺享有權利的公共性。所有非遺事象都是由社區(qū)民眾所創(chuàng)造,并且為社區(qū)民眾所共享,這就是非遺公共性特征最為重要的內(nèi)涵。
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非遺定義的表述中,對非遺創(chuàng)作主體的公共性以及非遺精神價值的公共性問題有著許多方面的強調(diào)。例如在1989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保護民間創(chuàng)作建議案》(這一文件現(xiàn)已被視為國際社會提出非遺保護理念的前身)指出:“民間創(chuàng)作(與現(xiàn)在的非遺概念相似)是指來自某一文化社區(qū)的全部創(chuàng)作,這些創(chuàng)作以傳統(tǒng)為依據(jù),由某一群體或一些個體所表達,并被認為是符合社區(qū)希望的,作為其文化和社會特性的表達形式。”在這里,有關“來自某一文化社區(qū)的全部創(chuàng)作”“由某一群體所表達”“符合社區(qū)希望的,作為其文化和社會特性的”等一些文句的表述,都重點強調(diào)了非遺與民眾及其所生活的社區(qū)之間的緊密關系。非遺事象大多是在民眾的社區(qū)生活中所創(chuàng)制的,并且反映了社區(qū)民眾的共同價值追求、思想情感與審美情趣,這是對非遺公共性問題的最好詮釋。這就要求我們在非遺保護的實際工作中,要盡量避免拍腦袋、主觀臆斷的現(xiàn)象,真正注重對于那些符合社會民眾需要、愿望與利益的非遺資源與項目的保護。
除了非遺事象創(chuàng)作主體的公共性以及非遺精神價值的公共性以外,非遺的公共性還表現(xiàn)在它享有權利的公共性方面。非遺既是由廣大的社會民眾創(chuàng)造的,又是為廣大的社會民眾所共享的,因此,所有與非遺有關的權利與利益,都應該建立在社會公共性這樣一個廣闊的平臺之上。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公共性問題,是非物質(zhì)文化在該傳承社區(qū)的當代社會發(fā)展和可持續(xù)的問題;是文化傳統(tǒng)生生不息、不斷發(fā)展創(chuàng)造的問題;是不同社區(qū)民族傳承群體文化自信、自覺性提升增強的問題;是文化資本向文化創(chuàng)造轉換延伸的問題。非物質(zhì)文化其社會的公共性,必然超越個人及地方本位的利益。國家作為社會的主體意識,首先應當確定文化權益和文化利益的基本歸屬性,和文化在社會價值認同中的公民所屬權益的平等性。國家應當在社會公共領域不斷完善、兌現(xiàn)公民文化權益應有的法律、法規(guī)、文化政策及產(chǎn)業(yè)化管理規(guī)劃,以及文化公共性所需的社會交流、傳播等信息使用方面的基礎設施。”在這里,作者把非遺保護與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從維護公民文化權益的高度闡述了非遺享有權利的公共性問題,這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總之,非遺是一種有著鮮明的民眾性特點的文化遺產(chǎn)形式,有著深厚的民間性、民眾性等與“民”相關的基本屬性,說得直白一些,也就是說非遺姓的是“民”。
(3)生活性。任何非遺的形式,實際上都是一種一定區(qū)域中人的生活方式,它來自生活,取自生活,體現(xiàn)了人們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與生存智慧。需要強調(diào)的是,非遺本身不僅僅是一種歷史留存的文化遺產(chǎn),同時也是一種活態(tài)的生活方式,是人們在長期的日常生活中所習得、所形成的一種活動樣式。它與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生活場景緊密結合在一起,沒有了生活活動,非遺事象就失去了依托,失去了自身的本質(zhì)。因此,非遺可以說就是一種“活著”的遺產(chǎn),“動態(tài)”的遺產(chǎn),與實際生活緊密結合的遺產(chǎn),在這方面,非遺與那些傳統(tǒng)建筑物、紀念物等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有著很大的不同。例如,民間剪紙作為一種民間美術類的非遺形式,是中國非遺門類中十分普遍的形態(tài),盡管民間剪紙的形式眾多,但是它們都與各個地區(qū)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有的是為了刺繡花樣,有的是為了美化環(huán)境,也有的是為了祈吉求祥等。總之,所有的民間剪紙,都有著豐富的生活涵義,它們是傳統(tǒng)社會民間生活方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間生活情趣表達與民間生活實踐和體驗的一種重要形式。非遺事象總是與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任何一種脫離了生活的非遺事象都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我們在對非遺進行保護的時候,不能夠把非遺事象與現(xiàn)實生活割裂開來,或者將其從生活中剝離出來,而是要從生活方式的整體性上去認識非遺保護的意義,讓非遺事象繼續(xù)生活化、活態(tài)化,并與現(xiàn)代人的生活方式融為一體。
2.有關非遺的保護方法
隨著非遺保護實踐的深入推進,當今世界已經(jīng)在非遺保護的領域中形成了諸多方法,其中有些方法與理念已經(jīng)被國際學界認為是特別重要的,應當在今后的非遺理論研究中予以充分重視。
(1)本真性方法
本真性是英文“Authenticity”的譯名,本意是指真實的而非虛假的,原本的而非復制的(事物)。20世紀60年代,“本真性”被引入遺產(chǎn)保護的領域,并逐漸在世界范圍內(nèi)達成了理解與共識。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奠定了本真性對于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重要意義,在這部憲章中,明確提出“將文化遺產(chǎn)真實地、完整地傳下去是我們的責任”。
本真性應該是非遺保護最為重要的方法與原則。我們必須保護真實的非遺財產(chǎn)而不是虛假的非遺財產(chǎn),即要保護那些原生的、本來的、真實的、完整的非遺信息,這是非遺保護的基本前提。這一點對于當前非遺保護的工作實踐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如今,由于年代久遠,許多產(chǎn)生于古代社會的非遺形式,如手工紡織技藝、傳統(tǒng)民俗廟會等等已經(jīng)很難在當代社會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形態(tài),留下來的只是一些殘存的、不完整的歷史印跡。因此,我們在對這些文化遺產(chǎn)進行保護時,很可能會產(chǎn)生一定的偏差,只是保護了它們的一些旁枝末節(jié),而把其中最為核心的內(nèi)容丟掉了。這就需要我們對這些非遺事象進行深入細致的挖掘與研究,認真考察它們的來龍去脈,力求還原它們的本來面貌,從而將這些非遺事象妥善、完整地保護與傳承下去。提倡本真性的保護方法與保護原則,更是為了防止那些珍貴的、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價值的非遺資源的異化、泛化與虛假化現(xiàn)象。在當代社會中,由于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以及一小部分人出于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一些歷史文化遺產(chǎn)被模仿、假冒,或者被改頭換面、移花接木,嚴重破壞了文化遺產(chǎn)的價值,同時也嚴重影響了人們對這些文化遺產(chǎn)的崇尚感與認同度。例如上海的杏花樓月餅、老鳳祥金銀細工首飾、老飯店本幫菜、龍鳳旗袍等等老字號品牌,它們的技藝都被列入了上海非遺保護的名錄之中,但是當前社會上對這些老字號的產(chǎn)品也有一些假冒仿造的現(xiàn)象,以致影響了這些老字號本身的聲譽。因此,在對大量的非遺資源與項目進行保護時,必須堅持本真性的方法與原則,力求運用科學的保護手段,維護非遺資源中那些能夠代表其本質(zhì)內(nèi)涵與基本特征的成分,去除那些以假亂真,或者似是而非的“假遺產(chǎn)”“偽文化”,以維持非遺形象的純潔性與神圣性。
為了較好地實現(xiàn)對于非遺本真性的維護,我國政府在近10多年來所采取的相應的保護措施主要有“非遺資源普查”“非遺資源存檔”“非遺數(shù)據(jù)庫建設”等等。通過這些方法與手段,較好地實現(xiàn)了對非遺資源進行客觀、全面、真實記錄以及保護保存的目的,其歷史功績值得充分肯定。
(2)整體性方法
所謂整體性方法,就是在對非遺資源與非遺項目進行保護時,不但要保護這些非遺事象的本體,而且還要保護與這些非遺事象本體有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其他諸多相關因素,如社會生產(chǎn)方式、歷史人文資源、傳承人群及其活動等等。這些因素雖然不是非遺事象的本體,但是卻對非遺對象的形成、發(fā)展、傳承,乃至風格特點等等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有的甚至會直接影響到非遺事象的生命延續(xù)。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對(非遺)具體文化事象的保護,要尊重其內(nèi)在的豐富性和生命特點。不但要保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自身及其有形外觀,更要注意它們所依賴、所因應的構造性環(huán)境。”因此,我們在進行非遺保護的具體實踐時,并不能將非遺本體與整體的文化形態(tài)及其相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完全割裂開來,使其成為一張張文化碎片,而必須同時注重對非遺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其他諸多內(nèi)容因素的保護,并將它們與非遺事象一起列入專門制定的保護體系之中。
整體性保護的方法在當前我國非遺保護的工作實踐中有著大量的運用。例如,在對上海的民俗類非遺項目——哭喪哭嫁歌實行保護時,我們不僅僅需要對這些歌謠的唱詞、音樂進行保護,同時也需要對這些歌謠演唱時的場景、風俗、儀式進行保護;又如在對上海的民間舞蹈類非遺項目——舞草龍實行保護時,我們不僅僅需要對這種舞龍形式的動作、音樂、表演形式進行保護,而且也需要對與這種舞龍形式相關的一些重要的民俗活動以及宗教儀式,如祭祀、求雨、巡游等實行保護。總之,對于像哭喪哭嫁歌、舞草龍等之類具有較為深厚的民俗內(nèi)涵的非遺項目,只有同時實行了對其事象的本體以及與這些事象相關的各種民俗活動與宗教活動的整體性保護,這些非遺事象的信息才能稱得上是完整的與全面的。
整體性保護的方法更多的是體現(xiàn)在非遺文化生態(tài)園區(qū)保護的這種保護模式之中。所謂非遺文化生態(tài)園區(qū),就是指非遺資源較為集中,并能以整體性的文化生態(tài)形式呈現(xiàn)的非遺文化區(qū)域。在這些非遺文化區(qū)域中,非遺的各種形式、內(nèi)容、場景以及相關的展示與活動被集中地聚集在一起,整體性地呈現(xiàn)了非遺形態(tài)的特色與風格。這種通過建立非遺生態(tài)園區(qū)的形式來實現(xiàn)對非遺資源進行整體性保護的辦法,目前已經(jīng)在我國許多地區(qū)推廣,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3)傳承性方法
在對非遺資源實行保護時,還有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傳承性保護。因為所有非遺事象與非遺形式都是通過人的傳承而得以存在與延續(xù)的,只有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傳承,非遺的內(nèi)容與形式才能得以保持,非遺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續(xù)。因此,在非遺保護實踐中,必須堅持以人為載體的活態(tài)傳承原則,強調(diào)傳承機制的完善以及積極發(fā)揮傳承人的作用,并通過各種能夠促進非遺事象進行有效傳承的方法與途徑使非遺在當今人們的生活中更好地“活起來”。
我國較為主要的非遺傳承方式,主要有家族傳承、師徒傳承和學校傳承等幾種。其中家族傳承與師徒傳承是較為傳統(tǒng)的非遺傳承形式,它們主要是通過某個家族或者某些師傅與徒弟之間的關系來實現(xiàn)非遺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與延續(xù)目的。相對而言,這兩種傳承模式傳承范圍較為狹隘,社會影響較為有限,但其優(yōu)點是能夠形成較為穩(wěn)定的傳承關系,傳承人之間的情感與關系較為密切,往往能較好地達到傳承效果。學校傳承是當代社會中采取的較為常見的非遺傳承方式,它引入了現(xiàn)代教育的教學方式,即通過規(guī)范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以及專業(yè)教師講授等方式在學校中開展非遺傳承與教育,社會影響面廣,系統(tǒng)性強,對當代的非遺傳承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傳承的范圍與廣度方面,與傳統(tǒng)的家族傳承與師徒傳承相比有著很大優(yōu)勢。但學校傳承的方式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主要在于其傳承關系不像家族傳承與師徒傳承那樣穩(wěn)固,難以維持非遺傳承的持久性。因此,在開展非遺傳承工作時,必須幾種方法并用,根據(jù)實際情況發(fā)揮家族傳承、師徒傳承與學校傳承的各自優(yōu)勢,以達到最好的非遺傳承效果。
(4)分類性方法
分類性方法是針對我國非遺資源與非遺項目形式豐富、門類眾多的特點而提出的一種可行性方法。非遺作為一種獨特的具有較強民間文化特點的文化遺產(chǎn)形式,不同的非遺形式與非遺門類在內(nèi)容特點、表現(xiàn)形式、生存條件、發(fā)展前景等方面都有一定差異,因此,對所有的非遺形式與門類僅僅采取一種統(tǒng)一的保護模式是不科學的,必須根據(jù)不同的非遺類型與特點制定不同的保護方法與保護措施,實行分類性保護。
就目前我國非遺資源與項目的實際情況來看,究竟應該如何來確定這些不同的非遺分類方法呢?有關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形成較為完善和統(tǒng)一的意見。其中一種較為有效和現(xiàn)成的做法,就是根據(jù)現(xiàn)有的非遺分類體系來確定不同的非遺保護方法。例如,對口頭文學類的非遺形式采用具有符合口頭文學類非遺形式所具有的特點與規(guī)律制定相應的保護方法,對手工技藝類的非遺形式采用具有符合手工技藝類非遺形式所具有的特點與規(guī)律制定相應的保護方法,對民俗類的非遺形式采用具有符合民俗類非遺形式所具有的特點與規(guī)律制定相應的保護方法等等。當然,除了這種分類性保護方法以外,還可以有其他的分類性保護方法。例如按照非遺保護的不同保護取向,可分為“搶救性非遺保護方法”“整體性非遺保護方法”“生產(chǎn)性非遺保護方法”“傳承性非遺保護方法”等等;按照非遺具體的表現(xiàn)形式,可分為“戲曲類非遺保護方法”“民歌類非遺保護方法”“剪紙類非遺保護方法”“工藝類非遺保護方法”等等。總之,應當對不同類型的非遺制定不同的保護措施,進行有針對性的分類保護,這樣才能使非遺保護工作更為科學、有效地實施與推進。[從中國非遺的特點來看,筆者認為將其分為“文藝類非遺”“民俗類非遺”“手工技藝類非遺”“自然知識類非遺”等這樣幾類是較為合適的。]
3.有關非遺的保護價值
經(jīng)過10多年來的努力,我國在政府與知識界的層面對非遺的保護價值已經(jīng)有了較為統(tǒng)一的認識,但是,要想進一步形成廣大民眾對于非遺保護的自覺,使非遺的保護工作成為一項為整個中華民族所重視的事業(yè),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此,在當前,加強對于非遺保護價值的認識以及從理論思想上加以闡述與研究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認為,在有關非遺的保護價值問題上,應該強調(diào)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理念:
(1)維護文化生態(tài)多樣性理念
維護文化生態(tài)多樣性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2001年11月2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第1條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這種多樣性的具體表現(xiàn)是構成人類的各群體和各社會的特性所具有的獨特性和多樣化。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chuàng)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chǎn),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第2條又指出:“在日益走向多樣化的當今社會中必須確保屬于多元的、不同的和發(fā)展的文化特性的個人和群體的和睦關系和共處。主張所有公民的融入和參與的政策是增強社會凝聚力、民間社會活力及維護和平的可靠保障。因此,這種文化多元化是與文化多樣性這—客觀現(xiàn)實相應的一套政策。文化多元化與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它有利于文化交流和能夠充實公眾生活的創(chuàng)作能力的發(fā)揮。”由此可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很早就認識到了世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意義,并用官方文本的形式對其作了十分具體的闡述。這種文化理念充分闡明:世界上的文化生態(tài)應該是多樣化和多元化的,這是世界文化繁榮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前提。只有有了各種文化的多樣化、多元化存在,人類世界才能夠繁榮與進步。在世界文化多樣性這種理論的背后,實際上蘊藏著的思想基礎是生態(tài)平衡理論與文化共生理論。它主張文化生態(tài)應該是平衡的而不是沖突的,文化機制應該是共生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很顯然,這種思想理念為非遺保護事業(yè)的提出與發(fā)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文化多樣性的理論不但對于文化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促進民族尊重、社會和諧、世界和平等當前重大的世界性話題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充分體現(xiàn)了對于各種文化的尊重、平等,以及相互理解的思想,而不是讓整個世界陷入一種對抗、爭執(zhí)和沖突的泥潭。現(xiàn)在我們將非遺保護事業(yè)提高到這種高度來認識,其意義也就顯得更為重要與深遠。在當今社會中實行對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實際上正是維護與體現(xiàn)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需要,它不但能夠促進世界文化的繁榮與發(fā)展,同時也能夠促進各個民族之間的溝通與理解,以及人類世界和諧大家庭的建構。
(2)提高民族文化認同感理念
非遺是一個民族的符號,體現(xiàn)了深厚的民族基因。在非遺的各種形態(tài)中,蘊藏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與精神特質(zhì),包含了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念、心理特征、氣質(zhì)情感,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與文化核心。因此,對大量的具有民族基因特色的非遺資源進行全面的保護與傳承,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認同感,進一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與發(fā)展奠定重要的基礎。這一點尤其重要的是體現(xiàn)在青少年教育的方面。非遺作為一種歷史文化遺產(chǎn),主要產(chǎn)生于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社會與農(nóng)業(yè)文明時代,與當前社會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思想情感、審美情趣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距離,對當代青少年而言,缺乏對非遺的了解、興趣與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并不等于說非遺對當代青少年是沒有意義的,恰恰相反,非遺內(nèi)涵中所蘊藏的許多優(yōu)秀的思想精神,例如和諧精神、群體意識、誠信觀念等等對于當代社會的青少年來說是十分需要的。因此,必須通過各種有效的方法與形式,讓我們的青少年更好地了解、熟悉、喜愛非遺,以增強他們對于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提高他們對于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3)促進當代文化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
當代文化代表了一種時代的新型文化,反映了當代人的價值追求、情感方式與審美理想,與傳統(tǒng)文化有著很大的區(qū)別。但是這并不等于說當代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之間就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當代文化的發(fā)展,必須以傳統(tǒng)文化作為基礎。只有以傳統(tǒng)文化為基礎,并充分利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各種有利因素來充實、完善當代文化的內(nèi)容與形式,才能使當代文化更好地彰顯民族文化的特性,具有更為持久與強大的生命力。
具體到非遺領域,我國現(xiàn)有的各種具有傳統(tǒng)文化特點的非遺形式,正可以在當代文化的發(fā)展與探索之中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并為當代文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增加更多斑斕的色彩與獨特的風格。目前,我國已有很多地方進行了將非遺項目引入當代文化領域的實踐,如利用非遺項目中的某些內(nèi)容與形式來舉辦各種文化節(jié)、文化展覽、文化大賽、文化表演以及娛樂游戲等等,它們對促進當代文化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在像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中,利用非遺資源來發(fā)展當代文化,豐富市民文化生活,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文化的常態(tài)。僅以非遺節(jié)慶活動為例,就有南匯桃花節(jié)、徐匯桂花節(jié)、奉賢菜花節(jié)、崇明灶花節(jié)、奉賢羊肉燒酒節(jié)等各種形式。它們無不以其濃厚的地方特色與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充實了當代上海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為當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繁榮發(fā)展增添了諸多亮色。
當然,在論及非遺對促進當代文化發(fā)展重要作用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強調(diào)非遺事象本身在這一過程中的創(chuàng)新與重塑的重要性。非遺事象大多是傳統(tǒng)社會的產(chǎn)物,具有較為鮮明的農(nóng)業(yè)文明與傳統(tǒng)時代的印記,因此,當它們被利用來為當代社會的文化發(fā)展服務時,必須要經(jīng)過一定的創(chuàng)新與重塑,使之更符合當代人的價值追求與審美情趣,為更多的當代民眾所接受、所喜愛,而不可原封不動地完全照搬或者模仿原來的樣式,否則就很難在當代的文化環(huán)境中充分地發(fā)揮自身的作用。這樣的做法并不是為了讓非遺拋棄自身的核心價值而去迎合社會的需要,而是為了讓非遺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fā)展,使非遺更好地融入當代社會發(fā)展的潮流之中。一方面要保護本真,一方面要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就是我們當代社會對于非遺的辯證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