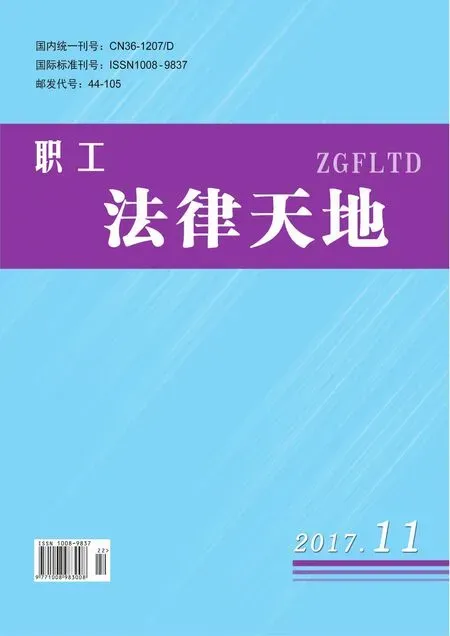淺談虛假訴訟的表象
王美俐 王 濤
(317200 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 浙江 天臺)
淺談虛假訴訟的表象
王美俐 王 濤
(317200 浙江省天臺縣人民法院 浙江 天臺)
虛假訴訟入刑在法律人的千呼萬喚中塵埃落定,但相比事后救濟,如何甄別虛假訴訟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為此,筆者通過實踐中虛假訴訟的案例,掀開虛假訴訟的表象.
虛假訴訟;表象;甄別
一、從三則案例說起
1.案 例一
陳某指使他人以到王甲店里做生意聯系為由,騙取王甲在一張空白紙上寫上姓名和聯系電話。后陳某在該紙條上偽造了“我于1991年12月中旬向王乙(系陳某家人)借到人民幣五千五百元整,約定月息(按三分計算)因當時沒寫借條,現在補寫”的借條。后陳某憑借借條以王乙名義向法院起訴,導致法院支持其訴訟請求,并經執行完畢。后經公安偵查,檢察院指控陳某、王乙等涉嫌敲詐勒索罪提起公訴,經審理,法院以詐騙罪判處陳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3萬元。其余涉案人員也被判處有期徒刑。
2.案 例二
許某讓他人為其存積分準備貸款,他人陸續將265萬元打入許某在某銀行的賬戶。許某的債權人朱某及高某等人遂向法院申請訴訟保全,法院即凍結了賬戶中的229萬元,因許某外債有400多萬元,為減少自己損失,許某就指使朱某找幾個朋友并由許某出具假借條給朋友,再由朋友起訴許某,等法院執行拿到錢后可從中拿回部分錢。爾后,朱某叫來三個人幫忙起訴并虛構了許某借款的借條。法院以妨害作證罪判處許某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以幫助偽造證件罪判處朱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其余人也受到相應的處罰。
3.案 例三
許某因經營不善將某公司轉讓給包某,在簽訂轉讓協議時,雙方約定公司債務由包某等人承擔。后許某、吳甲伙同林某偽造許某以公司名義向林某借款21.6萬元、68萬元的借條。許某、吳甲伙同吳乙偽造以公司名義向吳乙借款20萬元、40萬元的借條。后由林某、吳乙持假借條作為憑證分別起訴許某以及某公司。法院支持了其訴訟請求。后包某向公安機關報案。法院以詐騙罪判處許某、吳甲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10萬元。以詐騙罪判處林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6萬元。以詐騙罪判處吳乙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5萬元。
二、問題的引出
從上述三則案例不難看出,虛假訴訟的形式各異,有雙方自編、自導、自演的,有單方借助親朋,“友情”出演或自帶群眾演員的,但不管“虛假訴訟”這出“鬧劇”怎么出演,法院最終變成了非法“出演”的場所,法官成為了當事人愚弄的對象。“鬧劇”被揭穿后,“出演者”雖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被揭穿的“鬧劇”僅僅是所有發生的虛假訴訟中的冰山一角,正在上演的,或僥幸逃脫的,又該如何預防、識破?這正是本文需要探討的問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深在此山中”,欲破“虛假訴訟”之冰,必先“識”之。
三、“虛假訴訟”內涵體系梳理
虛假訴訟究竟指什么?理論界眾說紛紜,司法實踐的處理莫衷一是。理論界類似虛假訴訟概念有,濫用訴權、惡意訴訟、訴訟欺詐等。筆者特意在中國知網期刊網輸入上述關鍵詞搜索了一下,發現“濫用訴權”“惡意訴訟”“訴訟欺詐”等概念的內涵相互穿插、交織,沒有明確的界線與區分標準。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在民事審判中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案件的若干意見中將“虛假訴訟”定義為:“民事訴訟各方當事人惡意串通,采取虛構法律關系,捏造案件事實方式提起民事訴訟,或者利用虛假仲裁裁決、公證文書申請執行,使法院作出錯誤裁判或執行,以獲取非法利益的行為。
司法實踐中,虛假訴訟早已突破了民事訴訟各方當事人惡意串通的情形,原告單方惡意或者與案外第三人串通的情形也常有之。為此,筆者認為,無論是當事人雙方惡意串通的情形,還是原告單方惡意提起,只要在訴訟的虛假性上是相同的,都是以虛假訴訟騙取法院有利判決,無論受害人是誰,均應歸入虛假訴訟的研究范疇,否則,既不利于法學概念的統一,也會給立法帶來障礙。綜上,筆者認為,可以將虛假訴訟定義為:為獲取非法利益,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偽造證據等方式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者利用欺詐手段騙取仲裁裁決、公證文書等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法律文書申請法院執行,使法院作出錯誤裁判、調解或執行的行為。
四、“虛假訴訟”的外衣
經過各地的司法實踐,“虛假訴訟”的廬山面目逐漸暴露,雖若隱若現,虛實交替,但為識破虛假訴訟開辟了前進道路。在此,筆者,不厭其煩的站在司法同仁的肩膀上,再次對虛假訴訟普遍表現形態進行分析與總結。
1.組 團訴訟,魚目混珠
虛假訴訟多發于民間借貸案件、已經資不抵債的企業、其他組織、自然人為被告的財產糾紛案件,拆遷區劃范圍內的自然人作為訴訟主體的分家析產、繼承、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離婚案件一方當事人為被告的財產糾紛案件等。這些案件一旦爆發或進入破產“程序”,關聯案件會不斷送到法院,一段時間內同一被告或同一利害集團的案件數量激增,真、假案件交織,魚目混珠,案件的迷惑性增加,法官很難識別。考慮到該類案件涉及人數眾多,地區影響之大,針對該來案件,法院通常會集中安排開庭或應各方當事人要求進行集中調解,而此時法官識別虛假訴訟的時間、精力被無限壓縮,或惰性或麻痹,常有霧里看花之感。這種組團式的訴訟,也是虛假訴訟最常見的偽裝方式。
2.兩 級“對抗”,防不勝防
在虛假訴訟中,尤其是雙方當事人合謀串通的案件中,由于當事人已經就相關的法律關系、法律事實和證據進行了共謀,訴訟中通常不存在激烈對抗的場面,當事人一般不作抗辯或不作實質性抗辯,或者表面上抗辯,但對其抗辯事由不提供證據,導致法院作出對對方有利的裁判。或者,雙方為了不讓更多人參與、了解訴訟情況,一般會主動放棄舉證、答辯時間,要求適用簡易程序,“自愿”要求調解。實踐中,有些“涉嫌”集資類犯罪的債務人,打著“逃避”刑事法律追究,爭取債權人“諒解”的旗號,會積極“配合”調解,在當事人“調解目的”“合情合理”化后,法官對虛假訴訟的提防與敏感會被當事人“潛移默化”的架空,虛假訴訟的發生防不勝防。
綜上,筆者或杞人憂天,或未雨綢繆,結合立案登記制的大背景,站在司法同仁們的肩膀上,對虛假訴訟行為再次進行梳理與分析,掀開虛假訴訟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