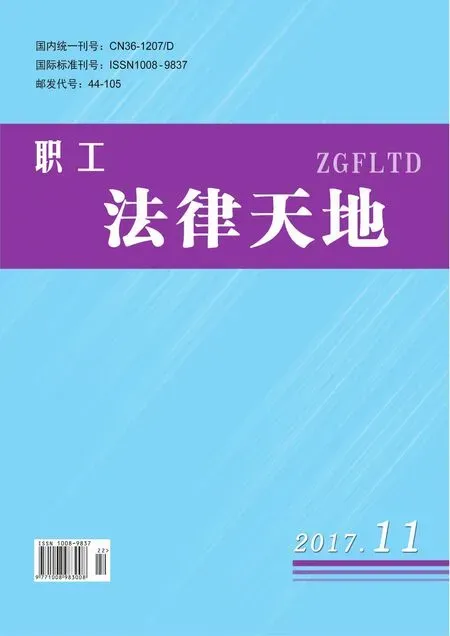刑事被害人訴訟現狀及對策分析
金曉東 李鑒振
(201800 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 上海)
刑事被害人訴訟現狀及對策分析
金曉東 李鑒振
(201800 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 上海)
以刑事被害人在訴訟中的角色現狀為關注視角可以發現,由于法律傳統的影響、立法技術的制約、司法實踐的阻卻等因素影響,當前我國在刑事被害人訴訟權利保障程序上和實體上存在問題,建議樹立被告人和被害人權利并重的刑事司法理念,完善被害人的庭審控訴權利,落實法律文書中被害人的主體地位。
刑事被害人;訴訟角色;權利保障
一、刑事被害人當前訴訟境遇的現狀與特征
1.出 庭權不受重視
刑訴法182條規定:“……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人民法院確定開庭日期后,應當將開庭的時間、地點通知人民檢察院,傳喚當事人,通知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證人、鑒定人和翻譯人員,傳票和通知書至遲在開庭三日以前送達。……”顯然,這里的當事人應當包括被害人。但實踐中被害人的這個權利常常被司法機關及被害者本人所漠視,刑事被害人的出庭率極低。數據顯示,部分基層法院涉及刑事被害人的公訴案件被害人出庭率僅為3%左右,個別法院甚至僅為1%左右。[1]
2.代 理權相對失衡
刑訴法第33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作了規定,第44條對被害人委托訴訟代理人作了規定。但通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辯護人及辯護人享有的權利與被害人委托訴訟代理人及訴訟代理人享有的權利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對被害人訴訟代理人訴訟地位、訴訟權利的描述均過于簡化,這也直接導致了被害人與被告人相比在權利的完善上還有一定的差距。如刑訴法對被告人因為法定條件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①但卻沒有規定被害人在法定條件下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司法機關應當為其提供怎么樣的法律援助。
3.知 情權難以落實
被害人是直接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是直接受害者,為了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被害人理應享有對訴前、訴中、訴后的整個過程充分了解的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也賦予了被害人一定的知情權和規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告知義務,但司法實務中的現狀卻并不盡如人意。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完全成為被害人的代理人,偵查機關只在必要的時候詢問被害人有關情況或指認犯罪嫌疑人等;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人員只在證據不明確的情況下才偶爾通知被害人陳述意見;即使進入審判階段,雖然刑訴法確立了被害人庭審參與質證的權利,獲得了與被告人同等的訴訟參與權,但這一權利確因被害人的缺席而形同虛設,也使《刑事訴訟法》修改中人權保障內容大打折扣。
4.陳 述權遭受限制
實踐中,如果不是公訴機關要求被害人當庭陳述,法院一般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參與訴訟,否則只在法庭宣讀被害人的書面陳述。并且被害人的陳述并不是由其主動發動的,它常要基于審判長的同意或者是依附于法官、檢察官、辯方律師的提問,時時處于被動狀態,其陳述的內容也多是為了和檢察機關的觀點相印證,起補充說明的作用,而并非從維護自身權益的目的出發。可以說,與被告人在庭審中的權利相比,被害人的陳述權受到極大限制,被害人即使出庭參與庭審,也極易淪為刑事審理部分的“局外人”。②
三、刑事被害人訴訟境遇現狀之原因探究
1.法 律傳統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長期受社會本位觀念的影響、政治刑法觀的束縛以及刑法工具主義的制約,缺乏“國家刑罰權自我制約的意識”[2],被害人的個別救濟被淹沒在了國家追究、懲罰犯罪的過程中。刑事司法制度更加注重的是解決“誰違反了法律”、“違反了什么法律”、“違法者應處以何種刑罰”之類的問題。這種國家追訴主義、追求實體的真實主義導致了保護社會和國家的利益遠遠高于被害人索回財產和恢復身心健康的需要,表現出的直接后果即為對如何恢復犯罪造成的損失關注甚少,被害人的賠償在刑事訴訟中實際居于次要地位。
2.立 法技術的制約
當前我國立法技術更注重的是對應然權利的規定,而對權利實現的可能性加以忽略,導致有些權利雖然做出了規定,但由于與實踐脫節而不具備實然性。如從立法內容來看,缺乏被害人國家救助的立法,在刑事訴訟法中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內容較多,造成與被害人權利救濟不對等之現象。③又如從立法配套來看,有關被害人相關權利的規定散見于多部法律中,對于法律之間的相互聯系、銜接及競合的情況,目前尚缺乏通盤的兼顧與考慮。[3]
3.司 法實踐的阻卻
拋卻宏觀環境及客觀因素,影響被害人訴訟參與權行使的直接原因還在于司法實踐的阻卻,典型表現即為當前法律文書中并沒有對被害人的當事人身份予以充分體現。盡管刑訴法將被害人規定為當事人,卻沒有為其準備進入刑事訴訟的通道,也沒有給他以當事人的載體。從偵查終結的法律文書——起訴意見書,到審查起訴終結的法律文書——起訴書,直至審理終結的法律文書——判決書,這些法律文書除了把被害人當作人證之外,根本沒有體現其當事人的地位。由此帶來的后果是,法律文書上沒有列明的當事人理論上并不存在,也無法以當事人的身份進入到訴訟程序中。[4]
四、落實被害人應然訴訟角色的現實路徑
1.樹 立被告人和被害人權利并重的刑事司法理念
一種新的犯罪觀認為,犯罪不僅是犯罪人和國家之間的對抗,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更主要的是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侵權,這種新的犯罪觀和被告人與被害人權利并重的刑事司法理念體現了刑事訴訟中的主體性原則和參與性原則,有助于司法公正化解糾紛,有利于克服正式刑事司法制度的弊端,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無疑會更加重視當事人作用的發揮,重視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和賠償,增強被害人與司法機關的合作,促進恢復性司法這種非正式司法模式的建立。
2.完 善被害人的庭審控訴權利
一是落實出庭權,從立法上規定法院負有告知被害人參與審判、出庭的義務,并明確規定在法庭上應設置被害人的單獨席位,以確保被害人出席整個庭審的權利。當然,被害人實在不愿意出庭,以書面形式做出不出庭決定的,可以被允許。二是保障知情權,明確法院開庭前應當送達被害人起訴書副本的義務,明確被害人閱卷權利,賦予被害人與被告方辯護律師同等的查閱、摘抄、復制有關犯罪事實材料的權利,明確其會見被告人的權利。三是強化陳述權,可在現階段引入被害人影響陳述,既能保障被害人在法院量刑中所起到的一定影響作用,也有利于他們因為被犯罪侵害而產生的報復心理逐漸緩解;賦予被害人最后陳述權。建議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三條中的“被告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修改為“被告人、被害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四是完善被害人代理制度,不斷完善被害人代理制度的相關規定,尤其是對被害人代理制度的基本內容作出明確的規定,應保障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獨立的訴訟地位,構建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3.落 實法律文書中被害人的主體地位
首先,應當在法律文書的當事人中明確載明被害人。從偵查階段開始,就在法定訴訟文書中載明所有的訴訟參與人,其中被害人為當事人。如果被害人需要保護隱私或安全而隱名的,可以在法定訴訟文書中指向在附件中載明而不是用非法定訴訟文書移送。其次,法律文書明確載明已告知被害人的各項權利及被害人對權利的處置情況。對被害人參與的各項程序有書面的記載,偵控法律文書必須對被害人如何處置自身的訴訟權利或義務有明確的說明。再次,法律文書中有公示權利的記載。各個階段的法律文書必須送達被害人,無法確定被害人的應當公告送達。
注釋:
①與1996年刑訴法相比,修改后的刑訴法擴大了法律援助對象的范圍,將適用對象擴大至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情形,而且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改為均“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②《關于公權力凌駕下的被害人權利保護》,載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6416 ,于 2012 年 5月26日訪問.
③這一現象從《刑事訴訟法》中有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相關權利規定的章節篇幅的對比中可見一斑.
[1]魏少永,魏偉.刑事被害人出庭率低的現象應引起重視,人民法院報,2008年12月10日第7版.
[2]梁根林.二十世紀的中國刑法學(中)——反思與展望,中外法學,1999年第3期,第3頁.
[3]王大為.中國有關被害人權利保護問題研究,公安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
[4]王繼青,李秀霞.被遺忘的當事人——被害人刑事訴訟程序缺席的實證分析.山東審判,2010年第1期.
金曉東,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科長。
李鑒振,上海市嘉定區人民檢察院公訴科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