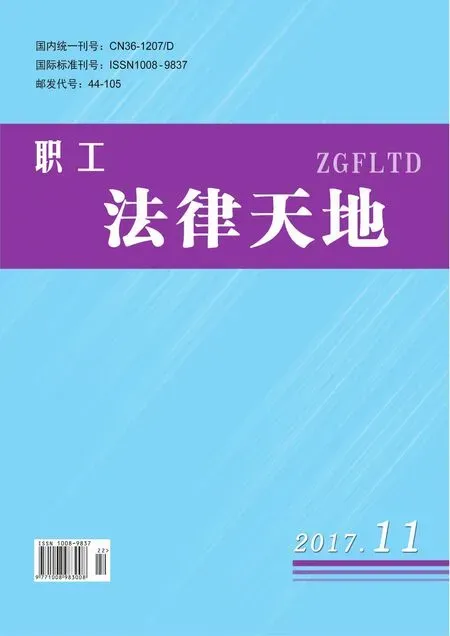我國侵權法上的權益區分保護模式
瞿曉麗
(210093 南京大學 江蘇 南京)
我國侵權法上的權益區分保護模式
瞿曉麗
(210093 南京大學 江蘇 南京)
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有限。社會生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侵權法難以對其保護范圍進行準確地界定,因此構建侵權法保護范圍的基本 框架是侵權法發揮保護功能的第一步。從對我國侵權法的現有條文進行文義解釋來看,對一切民事權益均予以同等保護,具有明顯的不合理性。在侵權法保護模式上,有具體列舉式和抽象概括式以及概括全部請求權式三種立法例。具體列舉式的德國法通過三個“小的一般條款”對權利和權益進行區分保護,相對于籠統保護權益的法國法而言,更具有合理性。我國侵權法沒有明確采權益區分保護模式,但從理論分析和司法實踐來看,仍具有肯定并采該種模式的傾向和空間。
權益區分保護;保護性法律;權益
一、問題的提出
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為民事權利或利益,但并非法律中所有的民事權利和利益都能夠受到或者有必要得到侵權法的保護,其原因在于,侵權法要平衡權益保護和行為自由這兩種基本價值。為了避免對任何一方的偏袒和損害,界定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的民事權利和權益的范圍可以方便社會公眾明晰他人權利的范圍和自己行為的邊界,預測行為后果,進而合理安排自己的行為。權利的認定是侵權法思考和判斷的基礎,是平衡權利救濟和行為自由的第一道閘門。[1]因此,明確侵權法的保護范圍就成為學界一項重要的任務。但是由于社會生活處于不斷變化發展的狀態中,我們無法做到將現有的以及將來可能具有的每一種權利都窮盡列舉,受保護的權益同樣也在增加甚至可能上升為權利,例如早期人格權的種類并不包括姓名權、肖像權等類型,隱私在我國最初是被放在名譽權中加以保護,后來才被定型化和普遍化為隱私權。因此,構建侵權法保護范圍的基本框架是侵權法發揮保護功能的第一步。
與其他法律相比,侵權法保護對象的范圍更加寬泛,從對現有條文進行文義解釋來看,似乎對一切民事權益予以同等保護,更容易引起爭議,這在司法實踐中表現極為突出。例如,移動公司通過免費短信發送信息給用戶的行為是否侵害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和“生活安寧權”?[2]如果構成侵權,對于該種權益,我國侵權法體系能否提供救濟?實踐中經常發生類似的侵害“一般人格權”的糾紛,受害人的主張是否均能得到支持?侵權法對于這一類型的“權利”的保護與明文規定的權利有何不同?回答這些問題,還需要對我國侵權法體系的保護模式進行分析,從中歸納出權益區分保護的可行路徑。
二、比較法觀察
由于還沒有出臺一部統一的《歐洲民法典》,從《法國民法典》的施行到新的《荷蘭民法典》的誕生,出現了不同模式的民法典,調整侵權行為法的條文的數量不斷增多,導致了歐洲侵權法條文異乎尋常的細密。在各國民事立法中,哪些民事權利和權益應當受到侵權法的保護,從形式上看,存在三種不同的立法例:德國具體列舉模式、法國抽象概括模式、歐洲的概括全部請求權的模式。
(一)德國模式
《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規定“因故意或者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者其他權利者,對他人因此而產生的損害負賠償義務。”該款之所以只列舉了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這四項人格法益以及所有權等絕對權,是因為絕對權之外的權利以及那些雖然受到法律保護但尚未達到權利保護高度的利益,因其不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或者內容并不確定,權益享有者之外的人往往難以知悉此等權利或利益之存在或確切內容,法律上也無法要求人們對之給予如同絕對權那樣的尊重。[3]為了避免社會公眾的行為自由受到突然的侵害或者不正當干預,需要區別于權利予以保護。因此,823條第2款就對違反保護性法律的侵權行為進行了規范:“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的法律者,負相同的義務。如果根據法律的內容并無過失也可能違反此種法律的,僅在有過失的情況下,始負賠償義務。”換言之,無論保護性法律是否以過錯為條件,侵權人只有在有過錯且違反保護性法律的情形下負賠償責任。同時,該法第826條對以故意背俗的方式侵權做出了規定:“以違反善良風俗的方式故意對他人施加損害的人,對他人負有損害賠償義務。” 它將責任因違反善良風俗而造成的損害聯系起來,對于法官對法律的發展,補充違法行為,保護那些尚未由法律確認為權利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4]德國通過這三個“小的一般條款”構建起區別保護權利和權益的途徑,被稱為“權益區分保護模式”。除此之外,還有基于推定過錯的責任。由于823條第1款規定的過錯責任要求受害人就加害人的過錯和因果關系舉證,在簡單(直接)侵害過程中,其外在過程受害人是可見的,但是在某些情形如受害人死亡或者間接侵害中,這一侵權過程雖可見但無濟于事甚至不可見,針對這些困難,判例法上創設了推定證明和舉證責任的轉移,《德國民法典》831-837條和《道路交通法》18條也規定了法定證明責任倒置。[5]
(二)法國模式
《法國民法典》規定的侵權責任被認為是世界上范圍最廣、射程最遠的侵權責任制度。[6]在所有的歐洲民法典中,《法國民法典》給法院的指示最少。該法第1382-1383規定的是自己責任,1384-1386規定的是對他人行為和物的損害的責任,這5個條文高度概括了法國早期侵權法的全部規則。1382條規定“任何行為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自己的過失而致行為發生之人對該他人負賠償的責任。”1383條規定:“任何人不僅對于因自己故意行為所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而且還對因自己的懈怠或者疏忽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前者是“故意的過錯”,后者是“非故意(懈怠或疏忽)的過錯”。從條文來看,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只有三個:過錯(faute)、損害和因果關系,法院只能根據這三個要素構建侵權責任,而核心要素是“過錯”這一主觀性判斷標準,它是區別于其他責任的根本標志。他們只是對規定“對任何人的損害”一類的原則感興趣,這樣的原則很難作為可以適用的法律規則,它們只能被歸入有限的適用范圍。法國民法典的起草者認為,不需要另外的規定調整個人不當行為的責任。[7]隨后,法國學者又對過錯的主觀性判斷標準提出不同的理論依據,并逐漸采客觀的判斷標準,即過錯是對謹慎與注意之一般義務的違反,不再考慮行為的個體特征和個體的主觀可責難性,[8]但是對主觀性判斷標準的完全拋棄是通過司法判例來完成的。
如上所述,《法國民法典》關注的重點是致損事件而不是受害人所享有的特定權利的性質和范圍,不管是廣義上的財產損害(包括純經濟損失)、人身損害還是精神損害,只要因他人的過錯而造成,都可以主張損害賠償。除此之外,法國還通過一系列的判例明確某些對特殊利益的保護,如純經濟損失、胎兒所遭受的損害、植物狀態中的原告、人格權與隱私權的保護、對法定利益的保護、第三人干預他人契約關系。[9]就法定利益的保護而言,最高法院民事庭確立這樣一項原則:當損害是對法定保護利益的損害時,則此種損害可予以賠償,反之則不可。此種規則的確立是為了拒絕原告所提出的違法法律、違反公共秩序或者違反善良風俗的損害賠償要求。[10]換言之,此種利益必須是合法利益,既不違反法律,也不違反公序良俗。
(三)歐洲侵權法草案模式
《歐洲侵權行為法草案》第1條[11]規定使得侵權法的一般條款不僅是過錯侵權的責任依據,也是無過錯侵權的責任依據;它不僅是自己侵權行為的責任依據而且也是對他人或物造成損害承擔責任的依據,因此它是一切侵權損害之法律救濟請求權的基礎。可以說,此種規定是最符合一般條款的固有含義的,而且最充分地表現了一般條款的作用。此外,《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2027條也被認為屬于該模式的典型,[12]但有學者認為,認真研究可以發現其實它是用一個條文分別規定了三個一般條款, 即過錯責任的一般條款、無過錯責任的一般條款、替代責任的一般條款,實際上是用一個條文區分不同的侵權責任分別加以概括, 而不是將全部侵權責任概括于一個一般條款之中。[13]筆者認為,如果將2027條的整體看成一個一般條款, 也不妨將其認定為概括全部侵權責任的一般條款。
(四)立法例之比較
具體列舉模式可以方便人們知曉他人和自己權利的邊界,明確侵權法保護的范圍,但是具體列舉有限,不能涵蓋所有的權利類型,需要通過司法實踐不斷擴展保護范圍。《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時,立法者希望通過826條故意背俗的規定來補充823條列舉之外的其他權益,或者適用更后面的規定中的補充性規則,“獨立的法官制定的侵權行為法”的權力盡可能地受到民法典的限制。但它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如遺漏了對個人榮譽、名譽和隱私的保護,也沒有給司法部門在純粹經濟損失領域作出獨立判決劃定范圍。于是德國立法者為阻止侵權行為法這樣的進一步發展所建立的藩籬很快就被打破了。[14]德國后來仍然是通過大量判例來拓展第823條的保護范圍的,[15]進而發展出“一般人格權”、“營業權”以應對規范體系的漏洞和司法實踐的挑戰。法國模式和歐洲侵權法草案模式雖然可以高度概括各項受侵權法保護的權益,但是不能確定具體權益范圍的邊界,司法實踐中很難掌握和操作。《德國民法典》把門關的太緊,就如同《法國民法典》把門開的太大一樣。但從本質上看,法國模式和德國模式的差別并不在于保護范圍有何區別,而在于對不同的利益的保護程度有所區別。[16]德國法模式充分考慮到法國法模式的不足,在區分權益的保護程度上,限定法官的自由裁量等方面,德國民法典中侵權法保護模式的確具有一定的優點。因此,在一般條款的設計上,德國模式具有更大的借鑒意義。
三、我國侵權法的權益區分保護模式
(一)現行法規定
1.《民法通則》:概括式
即將失效的《民法通則》第5條和第106條第2款均規定保護公民的“財產、人身”和“民事權益”,但未指明具體何種權利和利益受保護。由于《民法通則》措辭寬泛,為學理留下了很大的解釋空間。從上述規定來看,似乎可以認為,只要有過錯、損害和因果關系就可以第106條第2款為請求權基礎,主張民事責任。在這種意義上,《民法通則》模式與法國模式相同。
2.《精神損害賠償解釋》:列舉+權益區分保護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1條列舉了因遭受非法侵害而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格權利的類型,同時也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可以主張賠償精神損害。相比較于《民法通則》而言,對人格權利做了豐富列舉,但仍是不完全性列舉。值得注意的是,該條第2款對人格利益的保護要求以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或社會公德為條件,這種對權利和權益給予不同程度的保護,與德國法規定的權益區分保護模式相同,為建立類似于德國法的第三條保護路徑留下解釋空間。但是由于《侵權法》的出臺,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精神損害賠償解釋》這一規定。
3.《侵權法》:概括+具體列舉式
《侵權法》借鑒了一般概括加具體列舉的立法經驗,其第2條規定了受保護的民事權利的具體種類以及明確保護民事權益。有學者質疑這18種權利的列舉是否完全,很多重要的權利如身體權、債權、配偶權沒有被包括在內,而且這18種權利并非一個邏輯層次上的權利,有具體權利,也有權利類型。[17]很顯然,此處并非是對權利的封閉性列舉,法條中的“等人身、財產權益”即起到了兜底條款的作用,表明其不僅保護權利,而且對利益的保護也做了明確規定。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條款設計,法官可據以對法律未明文規定的權益進行保護,或者根據侵權責任特別法和司法解釋的補充規定來進行救濟。但是該條沒有指明對權利和權益如何進行區別保護,而且由于第2條第1款有“依照本法”表述的存在,有不少學者認為該條沒有規范價值,僅具有宣誓意義,不能作為裁判依據。[18]同時,該法第6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從文義解釋來看,不論因故意還是過失,侵害他人的任何民事權益,均應承擔侵權責任。換言之,該款并沒有像德國法那樣將絕對權和其他利益區分開來并給予不同程度的保護。此外,該法第22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申言之,只要一個人的人身權益遭受侵害,并受到了嚴重精神損害,他就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無論這種人身權益是姓名權、肖像權,還是親吻權[19]、貞操權[20],而不再要求以故意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方式侵害人身權益。對于侵害人身權益,要求必須造成嚴重精神損害才能獲得保護,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區別保護的傾向。
在我國《侵權法》起草過程中,有不少學者主張采取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立法模式,在區分權利與利益的基礎上適用不同的條款規定不同的侵權責任構成要件,[21]但是立法機關未予采納,并認為“權利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其落腳點實際上還是利益,很難把權利和利益劃分清楚。從權利的形式來看,法律明確規定某權利的當然屬于權利,但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某權而又需要保護的,不一定就不是權利。而且權利和權益本身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有些利益隨著社會發展糾紛增多,法院通過判例將原來認定為利益的轉而認定為權利,即將利益‘權利化’。”[22]筆者認為,試圖對侵權法所保護的權益類型進行窮盡列舉、對其保護范圍作出明確具體的界定,既不可能也不科學,具體列舉是有必要的,但是設立兜底條款也必不可少,如此才能滿足民法時刻跟進社會生活變化的需要,探討的重點在于如何給予權利和利益不同路徑的保護。
4.《民法總則》:概括+具體列舉+特殊保護式
新訂《民法總則》第3條概括性規定:“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在第五章“民事權利”中對民事主體享有的各種具體權利和權益進行了列舉,第126條則為對法律未列明的權利和利益的兜底條款。值得關注的是,第128條明確其他法律規定對其有特別保護規定的權利,按照該法的特別規定予以保護。[23]從這個角度來看,《民法總則》對《民法通則》做了很大改動,修改之后與德國模式有諸多相似之處。
(二)我國侵權法的權益區分保護模式
雖然《侵權法》沒有區分民事權利和民事利益在保護程度和侵權構成要件上的不同,[24]也沒有明顯采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使用三個小的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但是這并不代表我國侵權法沒有區分權利和權益并用不同條款來對其給予不同保護的空間。如果文義解釋和歷史解釋不能得出合理的結論,那么目的解釋就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毋庸置疑,民事權利和利益因輕重緩急不同,在保護力度上應當有所區別,從現有規定和目的解釋來看,我國新訂《民法總則》和《侵權法》實際上也對權利和權益做了區別保護。值得一提的是,司法機關也傾向于區別權利和權益的保護并為何種利益應受保護提供了參考標準:“雖然《侵權責任法》原則上將民事權利與利益均列入保護范圍,但是由于民事利益的特殊性,并不能不加區分地一概予以保護,在界定哪些民事利益受到侵權法保護時,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民事利益是否被一些特別的保護性法規予以保護;侵權人侵犯民事利益時的主觀狀態等。”[25]結合侵權法體系來看,我國侵權法的保護體系同樣也可以分為三個路徑:
1.第一條路徑
對比《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和我國《民法總則》“民事權利”一章及《侵權法》第2條可以看出,二者均對絕對權進行明確列舉,但這種列舉又是不完全列舉,仍然留有解釋的空間,如823條第1款中的“其他權利”就被解釋為限定物權、先占權和其他絕對地位。[26]此外,我國《侵權法》和明確首先保護人身權,其次保護物權,最后是保護知識產權,這完全符合“人的保護最為優先、所有權的保護次之、財富(經濟上的利益)又次之,僅在嚴格條件下才受保護”的現代侵權法的發展趨勢,[27]糾正了一直以來都為臺灣學者所詬病的《民法通則》中將“財產”置于“人身”之前的做法,突出了人身權益的優越地位,宣示了生命健康權是最重要的法益,這在《民法總則》也有明顯體現。據此,可以認為這是侵權法第一條保護路徑,即對民法規定的基本權利的保護。
2.第二條路徑
《德國民法典》823條第2款是用以規范違反保護性法律的侵權行為,雖然《侵權法》沒有違反保護性法律的明文規定,但是《民法總則》第128條已經明確了這一保護路徑,而且我國有《婦女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一系列保護性法律,這些法律均是侵權責任的特別法。由于一部《侵權法》解決不了所有民事侵權問題,世界上也沒有一部侵權責任法囊括所有民事侵權內容,[28]因此,保護性法律的存在就顯得很有必要。而且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多遵循違反保護性法律的思路審理案件。如在著名的“燒傷兒童狀告《喜羊羊與灰太狼》制作人案”中一審法院在認定“模仿情節”與喜羊羊動畫片存在因果關系的前提下,認為制作公司未能遵守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相關法律,未嚴格審查、過濾未成年人不宜的情節和畫面,也并未做出風險提示、警戒模仿,因此判其承擔侵權責任。本案中,制作公司違反的是《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4條有關禁止向未成年人以其他方式傳播暴力、兇殺、恐怖、等毒害未成年人的音像制品的規定。雖然該案經二審調解結案,但是一審法院的判決理由足以說明,法院在處理受法律保護但未在《侵權法》中明文列舉的權利遭到侵害時的救濟途徑。
在曾經的青島法院關于“果凍噎死人”的侵權案件中也有類似判決。當時廠家認為自己執行了國家標準,而國家標準并沒要求生產果凍廠家有警示說明和警示標志,因此堅稱自己沒有任何不當,但法院依據《產品質量法》第27條第1款“產品或者其包裝上的標識必須真實,并符合下列要求:……(五)使用不當,容易造成產品本身損壞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財產安全的產品,應當有警示標志或者中文警示說明”的規定,仍然判定廠家敗訴。
雖然有學者認為,對于已基本確定的侵權類型,可明確規定,而不必如德國民法典第326條第2款,確立“違反保護性法律”的一般性規范。[29]但是基于上述分析,這并不妨礙我們對我國侵權法體系實際上存在第二條保護路徑的認定,即對保護他人之法律所保護的利益的保護。
3.第三條路徑
《德國民法典》第826條是對以故意背俗的方式侵害權益的行為進行的調整,而我國《侵權法》第22條規定了于此不同的路徑: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這是侵權法第三條保護路徑,即對產生嚴重精神損害后果的人身利益的保護,它區別于財產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結合《侵權法》第20條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財產損失并予以賠償的規定來看,不管是具體人格權還是一般人格權,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保護,獲得財產或者精神賠償的救濟。
在前文中提到的用戶訴移動公司短信騷擾案件中,法院認為,雖然我國民法目前明文規定的具體人格權只有健康權、身體權、肖像權、隱私權等,并未明確將自主選擇權和生活安寧權作為具體人格權。但原告主張的自主選擇權和生活安寧權應當包含在關于人之存在價值、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獨立、平等的一般人格權利益當中,屬于“其他人格利益”,因此移動公司構成侵權。但是由于被告已停止了侵權行為,就信息發送的時間、內容、次數等綜合因素考慮,未給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嚴重后果,對其精神損失的主張不予支持。除此之外,還有諸如“祭奠權”[30]、“遺體告別權”等被法院納入“其他人格利益”的范疇,均應適用《侵權法》第22條的規定。原則上,侵權責任法是保護權利而不是創造權利的法,但是如果僅根據一般條款來判斷權益的可保護性,可能導致其保護范圍漫無邊際。同時也應當看到,這種一定程度的創設權利的功能要受到嚴格的限制,“親吻權”的主張不被支持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四、結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體系對于民事權益存在三條保護路徑,分別是對民法基本權利的保護、對保護性法律所保護的利益的保護、對人身權益的保護。這三個路徑并不是無縫鏈接的關系,而是互有交叉,例如人身權益中的具體人格權屬于民法規定的基本權利,第三路徑保護的存在使得其受侵害時精神損害賠償成為可能。至于哪些權利和利益應歸入第一、第二、第三路徑保護,則屬于另一重要問題,需在一般條款的模式建成后,將受保護權益的范圍具體化、類型化。
[31]誠如拉倫茨教授所言,沒有一種體系可以通過純粹的演繹推理和邏輯結構來規范全部問題,體系必須維持其開放性,它只是暫時概括總結。[32]
[1]王成:《侵權責任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頁.
[2]阮益泳訴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侵權案,(2011)茂南法民初字第1604號.
[3]程嘯:《侵權責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4]Karl-Heinz Gursky, 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S. 217.轉引自王成:《侵權責任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頁.
[5]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90頁.
[6]王成:《侵權責任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頁.
[7][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上冊),張新寶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頁.
[8]劉海鷗:《大陸法系侵權法歷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頁.
[9]張民安:《現代法國侵權責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7年版,第56-71頁.
[10]Gerard Legier,droit civil, les obligations, quatorzieme edition,1993, Dalloz. p.95.轉引自:張民安:《現代法國侵權責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7年版,第66頁.
[11]《歐洲侵權行為法草案》第1 條規定:“(1)任何人遭受具有法律相關性的損害,有權依據本法之規定請求故意或過失造成損害的人或者對損害依法負有責任的其他人賠償。(2)損害或進一步的損害以及權利侵害的發生處于緊急情勢時,將遭受損害的人享有本法賦予的防止損害發生的權利。”
[12]《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2027條規定:“(1)任何人應對因過犯給他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而不論他為自己設定的責任如何。(2)在法律有規定的情形,一個人應對因其從事的活動或所占有的物給他人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3)如果某人根據法律應對第三人負責, 他應對該第三人因過犯或依法律規定發生的責任負責。”
[13]房紹坤:《論侵權責任立法中的一般條款與類型化及其適用》,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第14頁.
[14][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上冊),張新寶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頁.
[15][德]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權行為法》,齊曉琨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
[16]葛云松:《〈侵權責任法〉保護的民事權益》,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3期,第39頁.
[17]楊立新:《侵權責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4頁.
[18]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立法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0頁 .
[19]陶莉萍訴吳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2001)廣漢民初字第832號.
[20]段勇馮鼎臣:《對貞操權應給予民法保護》載《人民司法·案例》2008年第12期,(2006)東法民一初字第10746號.
[21]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侵權責任法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頁.
[22]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解釋與立法背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23]《民法總則》第126條規定:“民事主體享有法律規定的其他民事權利和利益。”第128條規定:“法律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婦女、消費者等的民事權利保護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24]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
[25]最高人民法院侵權責任法研究小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頁.
[26][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 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59-660頁.
[27]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7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頁.
[28]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
[29]王利明:《侵權法一般條款的保護范圍》,載《法學家》2009年第3期,第22頁.
[30](2011)新法民一初字第356號.
[31]王利明教授對此也有相同論述,參見王利明:《侵權法一般條款的保護范圍》,載《法學家》2009年第3期,第27頁.
[32]拉倫茨:《法學方法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9頁.
瞿曉麗(1993~ ),女,漢族,安徽滁州人,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