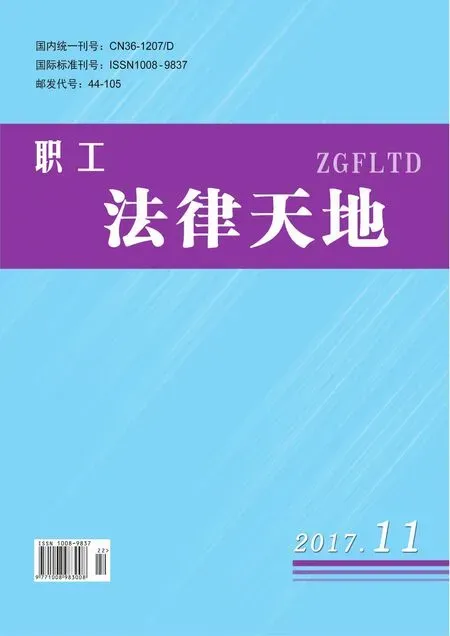淺析《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條
王 翔
(100088 中國政法大學 北京)
淺析《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條
王 翔
(100088 中國政法大學 北京)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第9條規定了法官處理普通動產多重買賣履行順序的適用規則,這條為多個有效的買賣合同之間標的物交付和多有權歸屬的問題提供了一條有效的解決途徑,然而這種看似為司法實踐操作提供便利的規則,其實質上存在著諸多問題,不論是自身邏輯構造還是內在合理性方面都存在缺陷。
多重買賣;合理性;必要性
一、法條解讀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9條規定:出賣人就同一普通動產訂立多重買賣合同,在買賣合同均有效的情況下,買受人均要求實際履行合同的,應當按照以下情形分別處理:(一)先行受領交付的買受人請求確認所有權已經轉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二)均未受領交付,先行支付價款的買受人請求出賣人履行交付標的物等合同義務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三)均未受領交付,也未支付價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買受人請求出賣人履行交付標的物等合同義務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此條適用的情形是普通動產的買賣合同。首先,合同標的物是普通動產。其次,數個買賣合同均為有效合同。買賣雙方之間關于動產物權變動的合意是合法有效的,作為物權變動的原因,買賣合同有法律效力是物權變動的根本前提,否則不生物權變動的法律效果。
由上述的文義解釋我們能得到這樣的結論:《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條的規范意指在于解決在數個有效的債權請求權中如何擇一履行的問題。
二、履行順序標準的正當性探析
《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條的履行順序標準由三款組成,就依此順序逐一分析:
(一)受領交付者優先
先行受領交付的買受人請求確認所有權已經轉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條規定適用的前提條件是出賣人就同一普通動產訂立多重買賣合同,在買賣合同均有效的情況下,買受人均要求實際履行合同的,由此可見,將先行受領交付的買受人列進請求給付之列實為謬誤。
(二)先支付價款者優先
先行支付價款的買受人請求出賣人履行交付標的物等合同義務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經過上述論斷,價款交付者優先是立法者認可的第一順位的標準,其中又可以推到出兩個具體的小標準:
第一,支付價款者和未支付價款者同時請求實際履行合同的,支付價款者優先;
第二,數個支付價款者同時請求實際履行合同的,最先支付價款者優先。
不得不提的是,在此標準中,價款是核心界定因素,那價款具體含義為何?價款是指買合同標的物的全部價款還是部分價款,若是指部分價款,那先付部分價款的買受人優先于后支付全部價款的買受人的合理性何存。
(三)先合同成立者優先
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買受人請求出賣人履行交付標的物等合同義務的。這是立法者認可的第二順位的標準,這種“先到先得”的標準設計似乎正中普通民眾傳統觀念的下懷,順應了民意。令人扼腕的是,“先到先得”的履行標準設定與民法物債二分的體系背道而馳:債權平等原則是由債權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具有堅實而鞏固的法理基礎。債權作為一種請求權,以請求力為基礎的債權之間具有相容性和平等性;而物權作為一種支配權,具有絕對性,表現為它的排他性和優先性。
三、第9條必要性之探討
依據《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條的規定,當買受人訴諸法院要求出賣人實際履行交付標的物時,最高人民法院將決定選擇哪個合同實際履行的權利從出賣人手中奪走轉而交給了法官,為何本來屬于出賣人擁有的權利,就因司法程序的介入而讓渡于法官,其法律依據何在?
司法解釋起草者提供的理由為:“多重買賣通常是在出賣人因標的物價格上漲后、后買受人支付的價金更加有利可圖的場合發生。出賣人本應履行前一買賣合同,交付標的物于先買受人;但其卻不履行該義務而將同一標的物出賣給后買受人,明顯違反誠實信用原則。”進而,出賣人在經過一番權衡利弊后一般會選擇出價較高的后買賣合同來履行,自愿承受對先買受人的違約責任。有鑒于此,《買賣合同司法解釋》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否定了出賣人自主決定說,采取了先支付價款說與合同成立在先說。
筆者當然不否認維護誠實信用原則的重要性,但是剝奪出賣人自主決定權(出賣人自行選擇履行哪個合同的權利)是否就能一定達到維護交易安全,保障誠實信用的效果呢?如果這種立法安排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的話自然不必多說,但現實是《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條所設計的履行順序標準根本不能保證防止出賣人背信棄義,也不能有效地保護先買受人的權益。詳細理由闡述如下:
(一)先支付價款的買受人不一定就是先成立買賣合同的
按照司法解釋起草者的觀點,先成立合同的買受人肯定就是誠實守信的買受人,后成立合同的被推行為非誠實信用的買受人,但是先支付價款者就一定是先成立合同者嗎?價款支付時間本來就是買賣雙方約定而成的,怎能想當然地認為先成立合同者必會先支付價款。照這樣說來,只要出賣人要求后出高價的買受人在先買受人之前付價款就可以輕易規避此條的規制。
(二)后成立合同的買受人并不一定均為惡意
以合同成立先后作為確定履行順序的第二種標準,暗含著這樣一種觀點,即后成立合同的買受人是惡意的,在明知有先合同存在的情形下仍然和出賣人訂立合同,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這種“有罪推定”無疑是欠妥的。畢竟,合同作為買賣雙方之間的契約并不能像登記那樣公諸于眾,易被查詢,其公示范圍極其有限,要求后買受人盡悉出賣人所涉買賣合同關系是極其不現實的,而就此推定其為惡意的就更不合理了。
(三)誠實信用原則的維護不一定非要以剝奪出賣人自主選擇權為代價
普通動產多重買賣的出賣人是否實際履行合同和選擇哪個買賣合同來實際履行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不能混淆。出賣人是否按照合同約定來交付標的物是履行合同義務的問題,在我國交付被視為是一種事實行為,不包含行為人的意思表示,同時并非僵硬地固守此觀點,例如學界普遍認為認為非自愿的交付根本不構成交付。而出賣人選擇多個合同中的哪個來履行則是屬于出賣人自身意思自治的范圍內,有選擇的余地。
[1]張新寶,王偉國.《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司法解釋溯及力問題探討》.《法律科學》,2010年第6期.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劉保玉.《論多重買賣的法律規制——兼評〈買賣合同司法解釋〉第9、10條》.《民商法學》,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