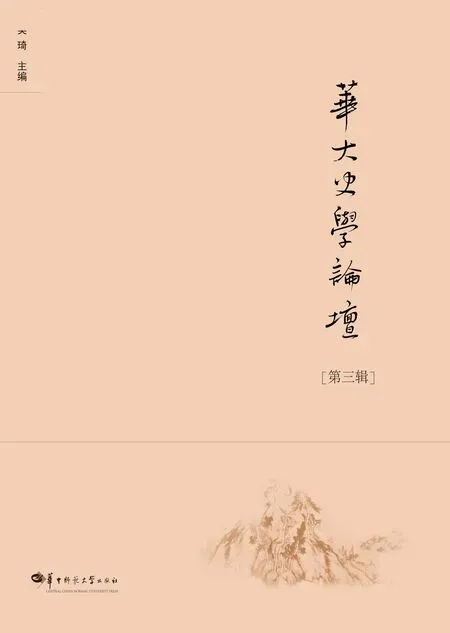二戰(zhàn)前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納粹大屠殺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研究
苗思雨
希特勒上臺(tái)之后建立獨(dú)裁統(tǒng)治,在二戰(zhàn)期間實(shí)施了種族清洗式的納粹屠猶行動(dòng),將近600萬(wàn)猶太人被屠殺。有國(guó)外學(xué)者將大屠殺中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角色分為Perpetrator(迫害者)、victim(受害者)和bystander(旁觀者),這三類角色對(duì)大屠殺分別有不同的態(tài)度。知識(shí)分子通常被稱為文明理性的代言人,當(dāng)年德國(guó)納粹大屠殺卻順利進(jìn)行并得到多數(shù)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默許和支持。大屠殺發(fā)生之后,隨著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自身身份的轉(zhuǎn)變和內(nèi)心覺(jué)醒,思想界又率先提出“反思民族歷史”的舉措[注]王雪:《19世紀(jì)德國(guó)猶太知識(shí)分子身份認(rèn)同問(wèn)題研究》,《北方論叢》2013年第2期,第23頁(yè)。。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納粹大屠殺發(fā)生前后的態(tài)度變化及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國(guó)外學(xu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就開(kāi)始了對(duì)猶太人的歷史及大屠殺的追溯與反思研究。比較著名的有《德國(guó)問(wèn)題與猶太問(wèn)題:從康德到瓦格納的革命性反猶主義》[注]Paul Lawrence Rose,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from Kant to Wagn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和《不自由的學(xué)者:德國(guó)律師、教師和工程師,1900—1950》[注]Konrad H.Jarausch,The Unfree Professions:German Lawyers,Teachers and Engineers,1900-19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德國(guó)學(xué)者克勞斯·費(fèi)舍爾近年出版的《德國(guó)反猶史》[注]克勞斯·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及齊格蒙·鮑曼教授的著作《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注]齊·鮑曼:《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也都是對(duì)納粹大屠殺的警示之作。國(guó)內(nèi)對(duì)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與納粹大屠殺的研究中,河南大學(xué)張倩紅教授的《德國(guó)社會(huì)民眾與“大屠殺”——讀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注]張倩紅:《德國(guó)社會(huì)民眾與“大屠殺”——讀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史學(xué)理論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具有代表意義,文章從德國(guó)知識(shí)界與“大屠殺”、德國(guó)普通民眾與戰(zhàn)爭(zhēng)罪責(zé)、德國(guó)猶太人為何坐以待斃三個(gè)方面論述了《德國(guó)反猶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問(wèn)題。鄭州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劉麗娟的《納粹德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與大屠殺——以醫(yī)學(xué)界為視角》[注]劉麗娟:《納粹德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與大屠殺——以醫(yī)學(xué)界為視角》,《鄭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3年第5期。一文從醫(yī)學(xué)視角探討了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與大屠殺的關(guān)系。
Intellectual一詞來(lái)自法國(guó),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案件。當(dāng)時(shí)德國(guó)正處于德意志帝國(guó)時(shí)期。德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呈現(xiàn)的并不是一種勇于承擔(dān)社會(huì)責(zé)任的形象,他們對(duì)社會(huì)表示懷疑,并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學(xué)院知識(shí)分子,馬克斯·韋伯是主要人物。而到了魏瑪共和國(guó)時(shí)期,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不問(wèn)政治的立場(chǎng)沒(méi)有改變,其疏遠(yuǎn)政治和社會(huì)的態(tài)度直接導(dǎo)致了之后20世紀(jì)30年代德國(guó)的意識(shí)形態(tài)領(lǐng)域被納粹主義所占據(jù)。在1948年之前產(chǎn)生了空想的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他們對(duì)制度體系進(jìn)行批判,這類知識(shí)分子后來(lái)受到了排擠,開(kāi)始尋求封閉的世界觀和政治任務(wù)[注]李大雪:《現(xiàn)代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形象的轉(zhuǎn)變》,《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年第4期,第45頁(yè)。。1960年代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開(kāi)始擺脫長(zhǎng)期代表保守文化的階級(jí)特征,成為一個(gè)語(yǔ)言共同體,共同發(fā)聲。八九十年代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逐漸認(rèn)識(shí)到未來(lái)的工作更多的是面臨現(xiàn)實(shí),成為“行動(dòng)的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注]李大雪:《現(xiàn)代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形象的轉(zhuǎn)變》,《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年第4期,第46頁(yè)。。本達(dá)在《知識(shí)分子的背叛》中指出:知識(shí)分子被理解為精神的指引者、民眾的教育者,其文化上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來(lái)源于道德上的合法地位[注]李大雪:《現(xiàn)代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形象的轉(zhuǎn)變》,《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年第4期,第46頁(yè)。。然而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20世紀(jì)所經(jīng)歷的身份變化卻印證了德國(guó)不同社會(huì)角色的價(jià)值觀念變化。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已經(jīng)成為研究德國(guó)某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jiàn)證人。在此,筆者從知識(shí)分子的身份認(rèn)同角度,選取律師、醫(yī)生、工程師等具有知識(shí)分子屬性的職業(yè)人物作為研究對(duì)象,探討二戰(zhàn)前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納粹屠猶展現(xiàn)出的社會(huì)行為及情感,并就其背后的原因進(jìn)行探討與反思。
一、戰(zhàn)前和戰(zhàn)時(shí)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納粹大屠殺的態(tài)度
納粹政府實(shí)施大屠殺可分三個(gè)階段:從1933年希特勒政府上臺(tái)到1939年納粹政府的法律排猶階段,是納粹大屠殺的序幕;1939年到1941年是納粹政府隔離猶太人時(shí)期,集中營(yíng)和毒氣室的建造為納粹屠猶做了準(zhǔn)備;1941年到1945年是納粹政府對(duì)猶太人的最終解決階段,600多萬(wàn)名猶太人在將近三年的時(shí)間里幾乎消失殆盡,是納粹大屠殺進(jìn)行的主要階段。律師、醫(yī)生、工程師、大學(xué)教授等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納粹大屠殺中扮演了支持與默許的角色,從大屠殺的旁觀者到最終參與到納粹屠猶過(guò)程中,充當(dāng)了納粹大屠殺的見(jiàn)證者。
(一)法律排猶階段:律師助推排猶法案的出臺(tái)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guó)政府中權(quán)力最大的總理,做出此任命的是年事已高的德國(guó)總統(tǒng)興登堡。希特勒是右翼德國(guó)國(guó)家社會(huì)主義工人黨(簡(jiǎn)稱納粹黨)的領(lǐng)袖。到1933年,納粹黨已是德國(guó)勢(shì)力最大的政黨之一。1933年3月23日,《授權(quán)法》在議會(huì)中獲得通過(guò),授予希特勒實(shí)行獨(dú)裁統(tǒng)治的權(quán)力。
當(dāng)時(shí)德國(guó)境內(nèi)的猶太人約為60萬(wàn)人(不足1933年德國(guó)總?cè)藬?shù)的1%),然而,納粹政府卻開(kāi)始宣傳種族主義思想,將猶太人視為一個(gè)種族,并將其定義為“劣等”。1933年,希特勒政府著手制定并實(shí)施一系列歧視猶太人的法律,禁止猶太人從事政府部門、大學(xué)與法院的工作,禁止猶太兒童進(jìn)入公立學(xué)校。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仍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內(nèi)運(yùn)作的納粹政府而言,排猶需要司法程序的支持,因此負(fù)責(zé)立法和執(zhí)法的司法部門和內(nèi)政部門也都參與了排猶活動(dòng)。
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在紐倫堡文化協(xié)會(huì)的大廳召開(kāi)了德國(guó)議會(huì)特別會(huì)議,參加會(huì)議的有德國(guó)的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司法人員,他們商議通過(guò)了極為重要的法律:帝國(guó)旗幟法、公民法和保護(hù)德國(guó)血統(tǒng)及德國(guó)榮譽(yù)法。希特勒對(duì)軍隊(duì)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重新武裝,希望新的德國(guó)軍隊(duì)成為民族社會(huì)主義工人黨的軍隊(duì),從此確立了納粹黨是民族的旗幟。法律宣布猶太人為二等公民。《紐倫堡法》規(guī)定,對(duì)猶太人的定義不再按照本人的宗教信仰或自身的選擇,而是以其祖父母輩的宗教信仰為準(zhǔn);有關(guān)異族通婚的法律被稱為“保護(hù)民族血統(tǒng)和德國(guó)榮譽(yù)法”,它禁止德國(guó)人和猶太人之間通婚及發(fā)生性關(guān)系,禁止猶太人雇傭年齡在45歲以下的德國(guó)女性公民,無(wú)論在德國(guó)境內(nèi)或境外蔑視這個(gè)法律的婚姻合同都被宣布無(wú)效,禁止猶太人升德國(guó)國(guó)旗,而懲罰的手段更是千奇百怪。這些極為荒謬的法律大部分都得到了會(huì)議的通過(guò)。
為了給德國(guó)人享有高高在上的優(yōu)越權(quán)找一個(gè)正當(dāng)?shù)睦碛桑に沟峡藠W特和他的法律顧問(wèn)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之后以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個(gè)身份重新露面,提供以下官方注解:
國(guó)家社會(huì)主義都平等及個(gè)人擁有無(wú)限自由的理論,政府認(rèn)識(shí)到基于法律本質(zhì)基礎(chǔ)上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差異。權(quán)利和職責(zé)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來(lái)自種族、國(guó)籍和民族上的差異。[注]克勞斯·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5頁(yè)。
納粹同時(shí)期也迫害被他們視為種族和心理“劣等”的其他民族,如1933—1935年間德國(guó)通過(guò)的一系列法律就旨在采用強(qiáng)制性的絕育手段以減少“劣等”人的數(shù)量。德國(guó)3萬(wàn)名吉卜賽人中許多人與黑人一樣,最終被實(shí)施絕育手術(shù)并禁止與德國(guó)人通婚。根據(jù)1935年司法部法令高級(jí)軍官修改了治罪標(biāo)準(zhǔn),僅僅是對(duì)一個(gè)男子同性戀的指控就可以將他逮捕、收審,乃至定罪。
(二)隔離猶太人階段:醫(yī)生扮演了合作者角色
1938年,針對(duì)德國(guó)和奧地利猶太人的經(jīng)濟(jì)攻擊演變成摧毀猶太人會(huì)堂和商店、逮捕猶太男子、摧毀猶太家庭、殺害個(gè)人的行為。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便是著名的水晶之夜行動(dòng)。水晶之夜后,德國(guó)和奧地利猶太人第一次遭到大規(guī)模的逮捕,大約有3萬(wàn)名猶太男子被送到達(dá)豪及其他集中營(yíng)關(guān)押。從1939年到1941年是納粹政府隔離猶太人時(shí)期,集中營(yíng)和毒氣室的建造為納粹屠猶準(zhǔn)備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此時(shí)醫(yī)生在屠殺猶太人的活動(dòng)中扮演了合作者角色,設(shè)計(jì)毒氣室迫害猶太人以及使用一些其他醫(yī)學(xué)手段給猶太人帶來(lái)了深重苦難,其中包括著名的安樂(lè)死計(jì)劃。
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不久,希特勒親自頒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將所有“無(wú)藥可救”的精神病人和殘疾人處死。特別醫(yī)生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審查由所有國(guó)立醫(yī)院填寫的問(wèn)卷,以決定某個(gè)病人是否該被處死。確定應(yīng)該被處死的人隨后被轉(zhuǎn)移到位于德國(guó)和奧地利的6家醫(yī)院,在那里搭建起的毒氣室中遭到暗殺。1941年這個(gè)計(jì)劃遭到了公眾抗議之后,納粹頭目仍然在暗中執(zhí)行這項(xiàng)被委婉稱為“安樂(lè)死”的計(jì)劃[注]克勞斯·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9頁(yè)。。許多嬰兒和其他受害者也因毒液注射、毒藥及強(qiáng)制性饑餓而死亡。安樂(lè)死計(jì)劃為浩大的種族凈化拉開(kāi)了序幕,然而希特勒書(shū)面授權(quán)殺死不符合納粹種族標(biāo)準(zhǔn)的人——這里只是他個(gè)人簽署的一個(gè)謀殺性文件,并不具備法律效力——幾乎沒(méi)有醫(yī)師對(duì)希特勒的授權(quán)書(shū)提出質(zhì)疑或公然反抗。在納粹德國(guó),醫(yī)生受到了納粹種族觀念的深刻影響,在大屠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德國(guó)的一流學(xué)府也參與了安樂(lè)死計(jì)劃,40個(gè)在大屠殺中扮演領(lǐng)導(dǎo)性角色的科學(xué)家,有9個(gè)是大學(xué)教授。希特勒政府將此計(jì)劃編造成一個(gè)組織名稱——嚴(yán)重遺傳病科學(xué)登記帝國(guó)委員會(huì)。“安樂(lè)死”小組用一個(gè)郵局信箱作為寄信地址,給它的成員分派編號(hào),以沒(méi)收的猶太公寓(簡(jiǎn)稱T-4)作為辦公地點(diǎn)。在整個(gè)過(guò)程中,很多機(jī)構(gòu)或醫(yī)師介入其中,他們中有些人給予謀殺計(jì)劃以熱忱的幫助。其中之一是赫爾曼·普凡米勒(Hermann Pfannmuller)博士,他是靠近慕尼黑的巴伐利亞艾格芬-哈爾醫(yī)院的院長(zhǎng),他被稱為是“由醫(yī)生轉(zhuǎn)變?yōu)闅埧釀W邮值牡湫腿宋铩盵注]陳恒、耿相新:《新史學(xué)第八輯 納粹屠猶:歷史與記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69頁(yè)。。
1939年希特勒啟動(dòng)了屠殺成年殘疾人計(jì)劃。納粹醫(yī)生和醫(yī)院院長(zhǎng)公然叫囂:“解決精神衛(wèi)生領(lǐng)域問(wèn)題的方案必須是一個(gè)能夠消滅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們醫(yī)院的病人太多,把他們打死好了,這樣你們就會(huì)有地方了”[注]克勞斯·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頁(yè)。。到1941年夏季為止,安樂(lè)死計(jì)劃共殺死了70273人。安樂(lè)死計(jì)劃已經(jīng)被正常化了。安樂(lè)死計(jì)劃的最后一名受害者是一個(gè)名叫里夏德·延內(nèi)的四歲兒童,她于1945年5月29日在美軍占領(lǐng)區(qū)的考夫博伊倫被殺害。
(三)最終解決階段:知識(shí)分子充當(dāng)了旁觀者角色
殘疾人安樂(lè)死的計(jì)劃進(jìn)一步在德國(guó)占領(lǐng)區(qū)擴(kuò)大實(shí)施,大規(guī)模屠殺吉卜賽人和猶太人,這就是所謂的“最終解決計(jì)劃”,在整個(gè)計(jì)劃執(zhí)行的過(guò)程中,被納粹殺害的無(wú)辜平民達(dá)600萬(wàn)人以上。1941年,德國(guó)撕毀互不侵犯條約,進(jìn)攻蘇聯(lián)。德國(guó)軍隊(duì)開(kāi)始以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對(duì)待500萬(wàn)名蘇聯(lián)猶太人,隨后希特勒和他的內(nèi)閣跨國(guó)迫害和攻擊,進(jìn)一步采取系統(tǒng)消滅猶太人的措施。納粹軍團(tuán)建立起特別的組織尾隨正規(guī)軍進(jìn)入蘇聯(lián)。這種軍團(tuán)叫做別動(dòng)隊(duì)(Einsatzgruppen),每隊(duì)由500到1000人組成,其中很多人受過(guò)高等教育,有律師、神學(xué)家及其他專業(yè)人員,他們的任務(wù)是殺掉知名的共產(chǎn)主義者和任何被懷疑暗中破壞或反對(duì)德軍行動(dòng)的人。很快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解釋為對(duì)所有猶太人的滅絕,包括婦女和兒童。在死亡集中營(yíng)和毒氣室建造之前,德軍就槍殺了大約150萬(wàn)名猶太人。
1941年年底,第一個(gè)滅絕營(yíng)在盧布林附近的貝烏熱茨建立,在1942年春季開(kāi)始運(yùn)作。正是在這個(gè)地方產(chǎn)生了第一個(gè)用毒氣殺人的毒氣室。貝烏熱茨集中營(yíng)的設(shè)計(jì)者和首席終結(jié)者是克里斯蒂安·維爾特,他曾效力于安樂(lè)死計(jì)劃,是數(shù)百名從安樂(lè)死計(jì)劃轉(zhuǎn)向波蘭的滅絕集中營(yíng)的專家之一。第二個(gè)死亡集中營(yíng)于同月在波蘭東部的索比布爾開(kāi)始運(yùn)作,第三個(gè)在特雷布林卡,第四個(gè)在離盧布林1英里遠(yuǎn)的馬伊達(dá)內(nèi)克。第五個(gè)也是最具爭(zhēng)議的、最可怕的奧斯威辛集中營(yíng),在上西里西亞?wèn)|部,即前波蘭奧斯威辛鎮(zhèn)建立。由于集體槍殺的延續(xù)和新的死亡集中營(yíng)的出現(xiàn),最終方案需要一套更協(xié)調(diào)的戰(zhàn)略,為此納粹領(lǐng)導(dǎo)人召開(kāi)了一次會(huì)議,商討殺掉歐洲剩余猶太人的技術(shù)細(xì)節(jié)。而出席會(huì)議的15位領(lǐng)導(dǎo)層中有8人具有博士學(xué)位。與會(huì)者都贊成必須對(duì)猶太人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
從1942年春天開(kāi)始,設(shè)在波蘭西里西亞和總督區(qū)內(nèi)的海烏姆諾、貝烏熱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個(gè)勞動(dòng)營(yíng)裝備了專門的殺人毒氣室和焚尸場(chǎng)后,調(diào)來(lái)一大批曾專門從事T-4行動(dòng)的醫(yī)務(wù)人員和工程技術(shù)人員,搖身一變成為第三帝國(guó)的四大滅絕營(yíng)。四個(gè)滅絕營(yíng)的幸存者總共只有82人,其中沒(méi)有一個(gè)是兒童。因此,運(yùn)抵滅絕營(yíng)的人數(shù)即等于該滅絕營(yíng)殺害的人數(shù)。因此,1942年以來(lái)納粹使用毒氣室殺害了來(lái)自德國(guó)、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萬(wàn)名猶太人。而整個(gè)屠殺過(guò)程中,除了參與大屠殺過(guò)程中的集中營(yíng)頭目、領(lǐng)導(dǎo)階層狂熱殺戮,更多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階層的態(tài)度是冷漠處之,在強(qiáng)大且專制的納粹政權(quán)面前,鮮有反抗。
德國(guó)傳統(tǒng)的精英在希特勒的滅絕猶太人的瘋狂念頭面前喪失了判斷力,在執(zhí)行大屠殺命令時(shí)并沒(méi)有愧疚之心;而參加大屠殺的這一代人是在社會(huì)進(jìn)化論和科學(xué)至上精神的熏陶下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且不說(shuō)要反抗滅絕人性的種族屠殺,就是質(zhì)疑種族主義科學(xué)性的聲音他們都沒(méi)有發(fā)出,這才是德國(guó)知識(shí)界和教育體系的悲哀。
二、戰(zhàn)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反思
1945年大屠殺結(jié)束之后,隨著戰(zhàn)爭(zhēng)罪行的不斷揭露和德國(guó)人自身的內(nèi)心反思,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經(jīng)歷了從“沉默的文化”[注]孫燕:《理性釋讀瘋狂——評(píng)〈德國(guó)反猶史〉》,《文教資料》2011年第19期,第68頁(yè)。到勇敢面對(duì)的過(guò)程,其中兩次歷史學(xué)家的辯論使得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將納粹大屠殺這段歷史逐漸帶入公眾視野。
(一)戰(zhàn)后初期德國(guó)知識(shí)界對(duì)納粹罪行的反思
戰(zhàn)后初期,德國(guó)遭受重大創(chuàng)傷,納粹大屠殺成為德國(guó)戰(zhàn)爭(zhēng)罪行的主要符號(hào),多數(shù)人主張以禁忌的方式來(lái)保全德意志應(yīng)有的榮譽(yù),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注]洪郵生:《誰(shuí)是屠殺猶太人的真正元兇——西方大屠殺研究述論》,《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7年第1期,第35頁(yè)。,然而,德國(guó)知識(shí)界很快認(rèn)識(shí)到戰(zhàn)爭(zhēng)罪責(zé)問(wèn)題是德國(guó)人無(wú)法掩飾的過(guò)去。20世紀(jì)40年代,《德國(guó)的浩劫》與《德國(guó)人的罪責(zé)問(wèn)題》成為戰(zhàn)后反省納粹歷史的開(kāi)山之作,分別由歷史學(xué)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和思想家雅斯貝爾斯于1946年撰寫。梅尼克作為一個(g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希特勒的反對(duì)者,將希特勒奪取政權(quán)看作德國(guó)最大的一場(chǎng)不幸的開(kāi)端。20世紀(jì)50年代之后,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社會(huì)批判理論的奠基者西奧多·阿多諾寫了一篇評(píng)論,題為《完成過(guò)去的工作意義何在?》,阿多諾通過(guò)這一問(wèn)題想要闡明的是,一個(gè)人如何和過(guò)去達(dá)成真正的和解。他的回答是德國(guó)人沒(méi)有完成這一任務(wù),在他看來(lái),“德國(guó)人壓制了過(guò)去,就是在背叛未來(lái)”[注]張倩紅、艾仁貴:《德國(guó)對(duì)納粹大屠殺歷史的反思與悔悟》,《光明日?qǐng)?bào)》2014年2月26日,第16版。。德國(guó)學(xué)術(shù)界開(kāi)始沖破大屠殺的種種禁忌,探討災(zāi)難發(fā)生的內(nèi)在根源。
從20世紀(jì)60年代開(kāi)始,一批年輕的歷史學(xué)家開(kāi)始重新定位史學(xué)的功能,對(duì)歷史過(guò)程中的政治結(jié)構(gòu)、民族傳統(tǒng)以及社會(huì)背景進(jìn)行批判性分析。代表人物有漢斯·羅森堡(Hans Rosenberg)、漢斯-烏爾里希·維勒(Hans-Ulrich Wehler)等,他們被稱為批判史學(xué)派。此后,更多的知識(shí)分子從不同角度來(lái)解讀歷史,知識(shí)界對(duì)納粹罪行的反思研究逐漸演變?yōu)橐淮未瓮磸氐乃枷胂炊Y過(guò)程。1968年,曾經(jīng)的反法西斯戰(zhàn)士勃蘭特出任德國(guó)聯(lián)邦總理,兩年后他做出了感動(dòng)世界的“勃蘭特之跪”以示謝罪,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以其實(shí)際行動(dòng)贏得了國(guó)際社會(huì)的尊重。
(二)兩次歷史學(xué)家論戰(zhàn)
二戰(zhàn)結(jié)束40年后,大屠殺的陰影仍在德國(guó)民眾心頭揮散不去,一種希望消解罪責(zé)的呼聲悄然發(fā)出,1986年6月6日,歷史學(xué)家恩斯特·諾爾特在《法蘭克福匯報(bào)》上發(fā)表題為《過(guò)去將不會(huì)遠(yuǎn)去》的文章,認(rèn)為納粹集中營(yíng)中的“種族殺戮”是對(duì)斯大林“階級(jí)殺戮”的防衛(wèi)性反應(yīng)[注]張倩紅:《戰(zhàn)后德國(guó)史學(xué)界對(duì)納粹大屠殺罪行的反思》,《世界歷史》2014年第4期,第36頁(yè)。。諾爾特駁斥大屠殺是獨(dú)一無(wú)二的罪行的見(jiàn)解,認(rèn)為納粹屠殺只是20世紀(jì)諸多種族集團(tuán)滅絕屠殺中的一起。這種試圖消解罪責(zé),實(shí)質(zhì)上為納粹罪行開(kāi)脫的行為遭到了社會(huì)學(xué)家、法蘭克福學(xué)派第二代學(xué)者哈貝馬斯的抨擊,從而引發(fā)了左派與右派的大辯論,史稱“歷史學(xué)家之爭(zhēng)”。爭(zhēng)論的焦點(diǎn)有:大屠殺的獨(dú)一性或相對(duì)性、歷史學(xué)的公共用途、大屠殺記憶與德意志民族記憶等,這場(chǎng)論戰(zhàn)成為二戰(zhàn)后聯(lián)邦德國(guó)最為重要的思想論戰(zhàn)。
在歷史學(xué)家論戰(zhàn)10年后,1996年《希特勒心甘樂(lè)意的劊子手》一書(shū)引發(fā)了新一波有關(guān)猶太人屠殺罪責(zé)與第三帝國(guó)歷史定位議題的論戰(zhàn),它由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政治學(xué)教授高哈登以其博士學(xué)位論文為基礎(chǔ)出版。該書(shū)強(qiáng)調(diào),反猶太主義導(dǎo)致數(shù)以萬(wàn)計(jì)的普通德國(guó)人成為冷血?dú)⒑Κq太人的屠夫,反猶太主義乃是德國(guó)人集體精神狀態(tài)中的一部分體現(xiàn),因此,換做其他百萬(wàn)計(jì)的德國(guó)人處于上述人士一樣的位置,也將會(huì)做出同樣的暴行。高哈登對(duì)“普通民眾”作為謀殺者的認(rèn)定,直接拷問(wèn)德國(guó)民眾的人性,在德國(guó)史學(xué)界引發(fā)了眾多討論。作為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挑起者與法西斯主義的策源地,戰(zhàn)后德國(guó)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罪責(zé)問(wèn)題進(jìn)行了較為徹底的反省,并贏得了外部世界的積極肯定,這在根本上與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階層的努力密不可分。
三、二戰(zhàn)前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納粹大屠殺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原因
猶太文化在歐洲已經(jīng)存在了兩千年,然而希特勒納粹政權(quán)在僅僅幾年的時(shí)間里對(duì)猶太民族進(jìn)行迫害、驅(qū)趕以及“最終解決”。很難想象納粹大屠殺這樣的慘劇會(huì)發(fā)生在給人類文化寶庫(kù)孕育出康德、馬克思、貝多芬、歌德等巨人的德國(guó),并且得到了當(dāng)時(shí)大部分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支持與默許。而二戰(zhàn)后德國(guó)知識(shí)界又首先扛起了反思?xì)v史的旗幟,找到了德國(guó)自我救贖之路。
(一)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大屠殺過(guò)程中對(duì)其支持與默許的原因
首先,恐猶癥的歷史在德由來(lái)已久,通過(guò)知識(shí)界精英在思想領(lǐng)域不斷發(fā)揚(yáng),繼而成為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支持納粹屠殺的基礎(chǔ);其次,一戰(zhàn)之后德國(guó)社會(huì)狀況惡化,魏瑪共和國(guó)根基不牢,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其失去信心;希特勒上臺(tái)之后的文化政策導(dǎo)向,既包括民族主義的種族優(yōu)越論,也包括容克軍國(guó)主義背景以及希特勒自身獨(dú)裁集權(quán)體制的實(shí)行;最后,德國(guó)的教育體系、希特勒政府以科學(xué)的名義進(jìn)行種族滅絕,都使個(gè)人要面對(duì)的屠殺道德問(wèn)題變成生產(chǎn)線上純粹的技術(shù)活。
1.恐猶癥的歷史因素
當(dāng)猶太人被基督教指責(zé)為殺害耶穌的兇手和阻撓上帝拯救人類的絆腳石時(shí),基督教社會(huì)對(duì)猶太人的憎恨開(kāi)始加劇,從中世紀(jì)以來(lái)德國(guó)文化中就存在反猶現(xiàn)象,猶太人與德國(guó)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種方面的差異有歷史淵源。十字軍與宗教裁判所的大肆殺戮就是例證。費(fèi)舍爾在《德國(guó)反猶史》中尖銳地指出:“僅是恐猶癥的泛濫并不能構(gòu)成在納粹德國(guó)發(fā)生大屠殺的充分原因。”[注]張倩紅:《德國(guó)社會(huì)民眾與“大屠殺”——讀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世界歷史》2014年第4期,第19頁(yè)。但正是由于恐猶癥的歷史由來(lái)已久,它在德國(guó)走向屠殺的過(guò)程中給予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根深蒂固的影響。
從中世紀(jì)開(kāi)始,德國(guó)恐猶癥的積聚經(jīng)歷了一個(gè)過(guò)程,主要包括中世紀(jì)時(shí)期以宗教分歧為特征的反猶主義、近代德國(guó)統(tǒng)一之前以“反對(duì)解放,拒絕同化”為基調(diào)的反猶主義、德意志帝國(guó)時(shí)期以“種族主義”為主旨的反猶主義、魏瑪共和國(guó)時(shí)期作為“政治思想”出現(xiàn)的病態(tài)反猶主義四個(gè)階段。這些反猶主義的漩渦包括:揮之不去的基督教徒的反猶太人歧視——指責(zé)猶太人殺害了耶穌基督,并對(duì)基督教社會(huì)犯下了諸多罪行;國(guó)家的偏見(jiàn)——說(shuō)他們是“異端存在”,一個(gè)國(guó)家中的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方面的利己主義——控告猶太人是剝削者,欺騙誠(chéng)實(shí)的德國(guó)人;普遍存在的歧視——直接針對(duì)單個(gè)猶太人的羞辱性的方式;種族生物學(xué)方面的理論——污蔑猶太人不僅種族低劣,而且從生物健康學(xué)方面來(lái)看也對(duì)社會(huì)有危害。這些歧視和偏見(jiàn)絕不是單一的,而是在許多情況下連接成有機(jī)的整體,作用于單個(gè)猶太人或更大的猶太團(tuán)體。正是由于恐猶癥的慢慢積聚,反猶情結(jié)能夠迅速成為新的社會(huì)潮流并被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接納就不足為奇了。
上述內(nèi)容表明,在大屠殺發(fā)生之前,恐猶癥已經(jīng)融入德國(guó)知識(shí)界精英的頭腦中,“猶太人是低下人種”、“猶太人太精明”等種種恐猶觀念在他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有許多平民相信傳統(tǒng)的猶太人所犯罪行的陳詞濫調(diào),但恐猶癥更被具有相當(dāng)意義數(shù)量的專業(yè)人士所接受——大學(xué)教授和他們的學(xué)生、教師、律師、記者、軍官和士兵、商人——他們都相信猶太人是德國(guó)的不幸。恐猶癥的蔓延是從社會(huì)上層往下層滲透的。
2.一戰(zhàn)戰(zhàn)敗的現(xiàn)實(shí)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德國(guó)戰(zhàn)敗對(duì)德國(guó)納粹法西斯的產(chǎn)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戰(zhàn)爭(zhēng)造成通貨膨脹和物價(jià)上漲,而戰(zhàn)敗和賠償?shù)呢?fù)擔(dān)大部分轉(zhuǎn)嫁到下層人民身上。而在德國(guó)這個(gè)充滿軍國(guó)主義的國(guó)家內(nèi),軍人一向處于受人敬慕和向往的地位,但是由于戰(zhàn)后裁軍,為數(shù)眾多的退伍軍人流向社會(huì),滑入無(wú)產(chǎn)者的行列,成為社會(huì)的破壞力量。
德意志民族從公元10世紀(jì)起曾多次侵占和掠奪其他民族而形成的某種民族自負(fù)和民族優(yōu)越感引導(dǎo)了德國(guó)志民族主義情緒的某種畸形發(fā)展,形成一種所謂雅利安種族優(yōu)越論。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以沙文主義為實(shí)質(zhì)的“愛(ài)國(guó)主義”教育普遍推行,德國(guó)各階層民眾尤其知識(shí)分子深受影響。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fā)展,追求歐洲和世界霸權(quán)的容克資產(chǎn)階級(jí)把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義推到頂峰,然而一戰(zhàn)戰(zhàn)敗非但把德意志民族爭(zhēng)霸世界的迷夢(mèng)打碎,而且使德國(guó)又套上了凡爾賽條約的沉重枷鎖。這樣,德國(guó)民族復(fù)仇主義情緒惡性發(fā)展起來(lái)。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也帶來(lái)了全世界的國(guó)際共產(chǎn)主義革命,德國(guó)建立了魏瑪共和國(guó)。由于德國(guó)根深蒂固的軍國(guó)主義和專制主義思想,共和國(guó)從一開(kāi)始就根基不穩(wěn)。從1918年到1923年之間,德國(guó)經(jīng)歷了舊統(tǒng)治力量崩潰、新的統(tǒng)治權(quán)力分裂時(shí)期,也經(jīng)歷了劇烈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文化方面的動(dòng)亂,就在民主領(lǐng)袖致力于打下新民主根基時(shí),德國(guó)出現(xiàn)了德國(guó)保護(hù)和抵抗聯(lián)盟——一個(gè)反民主、排猶的行動(dòng)組織。德國(guó)保護(hù)和抵抗聯(lián)盟在1920年散發(fā)了764.2萬(wàn)份傳單,聯(lián)盟還擁有自己的報(bào)紙《德國(guó)種族報(bào)》和“科學(xué)的”種族雜志《政治人類學(xué)月刊》。許多德國(guó)著名學(xué)者在反猶雜志擔(dān)任總編輯。他們指責(zé)猶太人逃避服役,指責(zé)猶太人向革命者和具有報(bào)復(fù)性的政客提供幫助和撫恤,恐猶者幾乎就每一個(gè)負(fù)面影響對(duì)猶太人加以指責(zé),從現(xiàn)代思想的頹廢到折磨廣大人民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方面的災(zāi)難。
3.文化政策因素
納粹時(shí)期德國(guó)的政治文化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而是具有深刻的歷史和政治因素。希特勒利用一戰(zhàn)后人們的復(fù)仇主義觀念以及狂熱的種族激情上臺(tái),結(jié)束了魏瑪共和國(guó)的統(tǒng)治,德國(guó)知識(shí)精英階層成為種族優(yōu)越論的狂熱推崇者。德國(guó)的文化政策是促使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從“恐猶”轉(zhuǎn)為“屠猶”的重要因素,這一時(shí)期的德國(guó)政治文化更多的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法西斯意識(shí)形態(tài)的反映。種族主義思想——“種族優(yōu)越論”、“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以及希特勒推行的領(lǐng)袖原則是文化政策中的主要內(nèi)容。種族主義以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chǔ),宣揚(yáng)生存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勝劣汰,認(rèn)為人類發(fā)展的歷史就是一部種族斗爭(zhēng)的歷史;認(rèn)為作為雅利安人的后代,德意志人是優(yōu)等民族,理應(yīng)得到推崇和贊美;而作為“低劣”民族的猶太人理應(yīng)被驅(qū)逐和唾棄。種族主義在納粹政府統(tǒng)治時(shí)期發(fā)展成極端的反猶主義,最終為推行種族滅絕政策奠定了基礎(chǔ)。
“民族共同體”[注]孫東方、傅安洲:《二戰(zhàn)后德國(guó)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變遷中的作用研究》,《比較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3頁(yè)。的德文原文是Volksgemeinsehaft,德文“Volk”一詞除了表示“民眾”、“民族”、“人民”外,還包含一種以血統(tǒng)和鄉(xiāng)土為基礎(chǔ)的原始部落集團(tuán)的意思。民族共同體是希特勒為建立法西斯集權(quán)獨(dú)裁統(tǒng)治而建立的社會(huì)聯(lián)盟。民族共同體強(qiáng)調(diào)德意志民族的整體利益,同舟共濟(jì),復(fù)興德意志民族。這種民族榮譽(yù)感對(duì)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意識(shí)形態(tài)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領(lǐng)袖原則與民族共同體思想是緊密相連的。希特勒把尼采的超人哲學(xué)運(yùn)用到了政治領(lǐng)域,提出由種族精英統(tǒng)治國(guó)家。希特勒政府宣揚(yáng)領(lǐng)袖是德意志民族共同體的代表,推崇強(qiáng)烈的種族主義。當(dāng)時(shí)建立了許多嚴(yán)密的組織,培養(yǎng)具有納粹特色的“新的世界觀”[注]傅聰:《歐洲反猶主義的根源》,《國(guó)外理論動(dòng)態(tài)》2005年第5期,第82-87頁(yè)。的人。德國(guó)具有特有的“道德冷漠”,既包括德國(guó)民族主義思想中的種族優(yōu)越論、生物種族觀和猶太惡魔化的主題,又包括容克軍國(guó)主義的背景。在此觀念的長(zhǎng)期滲透下,德國(guó)軍官變成了執(zhí)行命令的機(jī)器。
4.德國(guó)納粹政府教育體系
此時(shí)德國(guó)的教育體系建立在獨(dú)裁的、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基礎(chǔ)之上。在德國(guó)的學(xué)校里教唆學(xué)生憎恨猶太人是極為普通的事情。德國(guó)納粹執(zhí)行的專制政府教育體系,成為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根深蒂固種族優(yōu)劣思想的根源。
當(dāng)時(shí)德國(guó)年輕一代的知識(shí)分子仇恨猶太人,與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密切相關(guān)。納粹政府統(tǒng)治時(shí)期,學(xué)校從兒童入學(xué)起就開(kāi)始灌輸種族意識(shí),并且要求青少年必須具備有關(guān)血液純潔的意義和必要性的完備知識(shí)。希特勒的文化政策也時(shí)時(shí)刻刻地宣傳種族主義和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這些意識(shí)從青少年時(shí)期開(kāi)始形成,繼而成為德國(guó)教育體系的重要的理論依據(jù)。在希特勒的統(tǒng)治下,科學(xué)、文化也被貼上了種族主義的標(biāo)簽,區(qū)分為德意志科學(xué)文化與非德意志科學(xué)文化。以科學(xué)進(jìn)行的種族滅絕和滅絕行動(dòng)的技術(shù)化和工廠化,使得每個(gè)人要面對(duì)屠殺的道德問(wèn)題變成了生產(chǎn)線上純粹的技術(shù)活[注]克勞斯·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頁(yè)。。在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這一群體的身上,體現(xiàn)出更多的是平庸的惡。在像第三帝國(guó)時(shí)期的德國(guó)這樣的極權(quán)社會(huì)中,人們對(duì)權(quán)威采取了服從的態(tài)度,用權(quán)威的判斷代替自己的判斷,平庸得喪失了獨(dú)立思想的能力,無(wú)法意識(shí)到自己行為的本質(zhì)和意義,無(wú)法在服從中從個(gè)人價(jià)值方面進(jìn)行判斷,因而也成了一些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面對(duì)納粹政府屠猶行動(dòng)時(shí)“無(wú)能為力”的借口。
(二)戰(zhàn)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進(jìn)行反思的原因
戰(zhàn)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之所以能夠比較深刻地反思以大屠殺為標(biāo)志的納粹罪行,對(duì)其采取不回避和正視的態(tài)度,也有著深刻的社會(huì)與文化背景。
1.悠久的知識(shí)分子傳統(tǒng)
兩次歷史學(xué)家之爭(zhēng)是整個(gè)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以及全社會(huì)反思戰(zhàn)爭(zhēng)罪責(zé)的一個(gè)縮影。德國(guó)是一個(gè)具有知識(shí)分子傳統(tǒng)的國(guó)家,二戰(zhàn)后,德國(guó)戰(zhàn)敗,知識(shí)分子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濟(jì)世情懷,力圖在大屠殺廢墟之上營(yíng)造精神的共同體。德國(guó)的歷史學(xué)家首先擔(dān)當(dāng)起了反思?xì)v史的重任,強(qiáng)化國(guó)家應(yīng)該擔(dān)當(dāng)?shù)臍v史責(zé)任。而知識(shí)分子具有的思辨態(tài)度也在此時(shí)發(fā)揮了極大的作用。首先,歷史上德國(guó)學(xué)者康德、萊布尼茨等思想家都從不同角度探討過(guò)反思的哲學(xué)思想,出版了相關(guān)書(shū)籍。二戰(zhàn)之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延續(xù)了此傳統(tǒng),繼續(xù)反思自己國(guó)家的歷史。其次,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的知識(shí)素養(yǎng)本身較高,德國(guó)人普遍的閱讀量也居于世界前列,這使得反思納粹大屠殺的過(guò)程變得更加徹底。再次,反思傳統(tǒng)是與批判性聯(lián)系在一起的。20世紀(jì)50年代之后批判史學(xué)派的出現(xiàn)使得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反思?xì)v史的熱潮更加高漲。最后,戰(zhàn)后哲學(xué)家一直致力于引導(dǎo)德國(guó)人進(jìn)行反思,如雅斯貝爾斯提出罪責(zé)的四種分類,阿倫特提出“平庸的惡”[注]陳恒、耿相新:《新史學(xué)第八輯,納粹屠猶:歷史與記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45頁(yè)。,哈貝馬斯提出商談民主等等,知識(shí)分子成了引導(dǎo)德國(guó)民眾反思納粹大屠殺的主要力量。
2.政治文化與宗教因素
知識(shí)分子反思?xì)v史是德國(guó)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政治文化語(yǔ)境的體現(xiàn)。德國(guó)的“贖罪文化”[注]金莎:《德國(guó)戰(zhàn)后公民教育中的“反思”探析》,《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年第6期,第9頁(yè)。對(duì)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反思納粹大屠殺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戰(zhàn)后德國(guó)民生凋敝,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大不如前,如何回歸民主世界、回歸正常化以及建構(gòu)新的國(guó)民認(rèn)同成為最主要的訴求,也是民眾的期盼。承載著德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的知識(shí)分子通過(guò)對(duì)納粹罪行的反思,促使德國(guó)認(rèn)同了悲劇的歷史,承認(rèn)了德國(guó)給世界帶來(lái)戰(zhàn)爭(zhēng)的罪責(zé),并努力修復(fù)德國(guó)與曾經(jīng)遭受納粹侵略和迫害的戰(zhàn)爭(zhēng)受害國(guó)之間的關(guān)系。反思?xì)v史以及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納粹歷史的認(rèn)識(shí)成為國(guó)際檢驗(yàn)德國(guó)的度量尺。納粹政府執(zhí)政時(shí)期,希特勒將宗教與政治混為一談,將種族優(yōu)越論發(fā)展到了極致,戰(zhàn)后,《基本法》規(guī)定德國(guó)實(shí)行政教分離,然而由于濃厚的種族主義影響,宗教仍然在德國(guó)政治文化中發(fā)揮著重要影響,二戰(zhàn)之后,德國(guó)教會(huì)對(duì)“罪”有了更全面的強(qiáng)調(diào),提出了上帝的兩條誡命——“要盡心盡性盡意愛(ài)主,你的上帝”,“要愛(ài)人如己”。二戰(zhàn)結(jié)束后,德國(guó)神學(xué)家和牧師弗里德里希·馬丁·尼莫拉起草的斯加特悔罪書(shū)指出:“我們給世界人民和國(guó)家?guī)?lái)了無(wú)窮的災(zāi)難,我們譴責(zé)自己。我們沒(méi)有更勇敢地去承認(rèn)過(guò)錯(cuò),沒(méi)有更虔誠(chéng)地祈禱,沒(méi)有更樂(lè)觀地信神,沒(méi)有更熱烈地去愛(ài)。”從德國(guó)的“贖罪文化”中,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更加清晰地找到了反思?xì)v史的原因。
3.歷史的延續(xù)
尼釆曾說(shuō):“只有強(qiáng)壯的個(gè)性才能承受歷史,弱者會(huì)被它消滅。當(dāng)感情沒(méi)有強(qiáng)大到用自己來(lái)衡量過(guò)去時(shí),歷史就會(huì)讓它們感到不安。”[注]弗里德里希·尼采:《歷史的用途與濫用》,陳濤、周輝榮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其實(shí)這對(duì)于一個(gè)民族也是同樣的道理,沒(méi)有強(qiáng)大的民族自信就不可能承受如此悲痛的歷史。從戰(zhàn)后初期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納粹大屠殺的淺顯反思道路,之后阿登納時(shí)代的歷史反思與集體回憶,60年代反省歷史的意識(shí)初步形成,到八九十年代的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批判性自我反省,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對(duì)納粹大屠殺的反思?xì)v程印證了一個(gè)道理:為了歷史的延續(xù)以及獲得世界的尊重和信任,民族反思?xì)v史是必不可少的道路。它直接影響普通民眾對(duì)過(guò)去歷史的態(tài)度,引導(dǎo)著德國(guó)未來(lái)的前進(jìn)方向。
結(jié) 語(yǔ)
希特勒政府對(duì)歐洲猶太人的種族清洗罪行,在20世紀(jì)于人類歷史和良知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嘆息之余,我們更驚異于作為知識(shí)分子的律師、醫(yī)生、工程師們對(duì)納粹大屠殺的屈從,大部分知識(shí)分子被德國(guó)法西斯鍛造成訓(xùn)練有素的“殺手”,狂熱地追隨并積極支持種族優(yōu)越的理念,終將大屠殺演變?yōu)椴豢赡孓D(zhuǎn)的過(guò)程。相比于狂熱追隨者,一部分知識(shí)分子是無(wú)動(dòng)于衷的執(zhí)行者,他們將狹隘的道德觀僅僅應(yīng)用于自己的民族,對(duì)于從自己的國(guó)家驅(qū)逐出去的猶太人深深的苦難,更多的是視而不見(jiàn)與無(wú)動(dòng)于衷。除此之外,少數(shù)抵抗者在德國(guó)整個(gè)納粹統(tǒng)治時(shí)期顯得那么微不足道,在無(wú)法改變的屠殺慘劇面前,他們被迫選擇了沉默與逃避[注]劉麗娟:《納粹德國(guó)的知識(shí)分子與大屠殺——以醫(yī)學(xué)界為視角》,《鄭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3年第5期,第31頁(yè)。。二戰(zhàn)結(jié)束,德國(guó)知識(shí)界又最早認(rèn)識(shí)到德國(guó)無(wú)法掩飾的戰(zhàn)爭(zhēng)罪責(zé),由沉默逃避走向積極反思的道路。1970年的“勃蘭特之跪”震驚了世界的同時(shí),讓世界感受到了德國(guó)勇于承擔(dān)歷史罪責(zé),并真誠(chéng)懺悔對(duì)猶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國(guó)在政治中心的心臟位置建立了龐大的碑林,上面記載著納粹當(dāng)年殘暴的罪行,這在世界歷史中是極為罕見(jiàn)的自省與贖罪之舉。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歷史。柏林建成猶太人大屠殺紀(jì)念碑,不僅是德國(guó)人反思過(guò)去的象征,也是德國(guó)真正面對(duì)歷史的開(kāi)端。雖然時(shí)至今日,人們?cè)噲D從理性的角度探討大屠殺產(chǎn)生的成因與機(jī)制,不過(guò)更重要的是,唯有重新樹(shù)立起對(duì)人性尊嚴(yán)與民主價(jià)值的尊重,才能防止人類悲劇的重演,有效遏制世界上類似的獨(dú)裁政權(quán)再度利用種族主義涂炭生靈。對(duì)生命的重視和民主政治的追求是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經(jīng)歷角色轉(zhuǎn)變后所感悟的重要內(nèi)涵。
人們常把知識(shí)分子作為一個(gè)國(guó)家、一個(gè)民族思想精華的載體,代表著社會(huì)的正確的價(jià)值導(dǎo)向,可是納粹德國(guó)的歷史卻證明了如果謬見(jiàn)加上學(xué)識(shí),會(huì)使一個(gè)虛擬、荒誕的世界變得有板有眼、有血有肉[注]張倩紅:《德國(guó)社會(huì)民眾與“大屠殺”——讀費(fèi)舍爾〈德國(guó)反猶史〉》,《史學(xué)理論研究》2009年第1期,第8頁(yè)。。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在納粹屠猶過(guò)程中扮演了幫兇甚至迫害者的身份,但是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仍是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率先開(kāi)始醒悟,積極反思戰(zhàn)爭(zhēng)罪責(zé)。回顧戰(zhàn)后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反思大屠殺罪行的曲折歷程,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迪是:應(yīng)尊重歷史與事實(shí),正確對(duì)待歷史。正確的歷史態(tài)度不僅是對(duì)本國(guó)家歷史的尊重,更是一種對(duì)國(guó)際社會(huì)的歷史擔(dān)當(dāng),是國(guó)家實(shí)現(xiàn)自我救贖、重建民族自豪感的必經(jīng)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