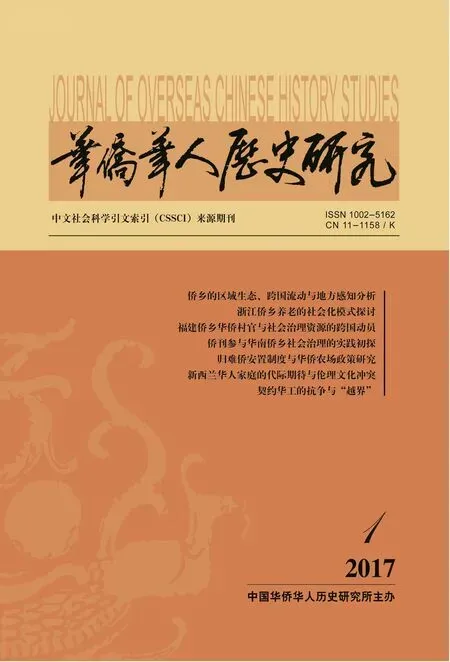國家需求、治理邏輯與績效*
——歸難僑安置制度與華僑農(nóng)場政策研究
黎相宜
(中山大學(xué) 國際關(guān)系學(xué)院/南海戰(zhàn)略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275)
分析探討
國家需求、治理邏輯與績效*
——歸難僑安置制度與華僑農(nóng)場政策研究
黎相宜
(中山大學(xué) 國際關(guān)系學(xué)院/南海戰(zhàn)略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275)
僑務(wù)政策;華僑農(nóng)場;歸難僑安置;歸僑;難僑;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和諧
論文梳理了中國政府在設(shè)立歸難僑的安置制度以及制定相應(yīng)的華僑農(nóng)場政策中的治理邏輯及其治理績效。研究發(fā)現(xiàn),政府對華僑農(nóng)場及歸難僑的治理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從設(shè)立之初強調(diào)“政治任務(wù)”,到體制改革后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再到后來對“社會和諧”的重視。華僑農(nóng)場的設(shè)立具有安置歸難僑、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屬性。但是,政府對華僑農(nóng)場以及歸難僑長期的特殊照顧導(dǎo)致了國家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dān)。出于提高生產(chǎn)效率、改善歸難僑生活的目標,政府對華僑農(nóng)場進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這一政策給華僑農(nóng)場及其社區(qū)內(nèi)的歸難僑群體的生產(chǎn)、生活帶來較大沖擊,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面臨著平衡“經(jīng)濟發(fā)展”與“社會和諧”之間張力的兩難。國家的這種二元需求與社會結(jié)構(gòu)、中央—地方關(guān)系等因素互動,共同影響了歸難僑安置制度與華僑農(nóng)場治理政策的變革軌跡以及治理績效。
華僑農(nóng)場①目前,全國大部分華僑農(nóng)場已經(jīng)開始向鎮(zhèn)、街道辦事處以及開發(fā)區(qū)等模式轉(zhuǎn)變,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不能再稱之為“華僑農(nóng)場”。但由于本文涉及農(nóng)場的體制改革歷史,為了還原當時的歷史變遷過程及突出社區(qū)內(nèi)擁有眾多歸難僑群體的特征,本文大體上仍沿用“華僑農(nóng)場”的表述。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國家為安置被迫回國的大批歸難僑設(shè)立的特殊社區(qū)。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在“體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會,經(jīng)濟融入市場”(簡稱“三融入”)的轉(zhuǎn)型大背景下,作為計劃經(jīng)濟產(chǎn)物的華僑農(nóng)場遭遇了空前強烈的沖擊。[1]目前,一些華僑農(nóng)場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實現(xiàn)政企分開,逐漸下放歸地方政府管理,由此進入“后華僑農(nóng)場時代”。②“后華僑農(nóng)場時代”用于描述目前全國華僑農(nóng)場基本告別計劃經(jīng)濟體制、逐漸融入地方,同時華僑農(nóng)場的管理體制也逐漸融入社會,經(jīng)濟功能逐漸融入市場的狀況。上述劇烈的轉(zhuǎn)型深刻地影響了華僑農(nóng)場內(nèi)的歸難僑及其子女在安置地的多元適應(yīng)與融入狀況。
學(xué)界對歸難僑安置制度以及華僑農(nóng)場政策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尤其關(guān)注華僑農(nóng)場從計劃經(jīng)濟過渡到市場經(jīng)濟中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涉及歸難僑安置、華僑農(nóng)場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問題、農(nóng)場下放地方政府管理的政治體制問題以及農(nóng)場的發(fā)展與轉(zhuǎn)型等問題。[2]但以往研究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這些研究基本上以對政策的歸納、實施過程的描述與政策效果的評論為主,并沒有深度挖掘隱藏在歸難僑安置制度以及華僑農(nóng)場政策背后的深層邏輯,無法更深入地理解制度與政策的變遷。其次,很多研究簡單地將1985年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作為分界點,但是沒有考慮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對歸難僑的安置以及華僑農(nóng)場的政策一直都在變動中。第三,以往研究主要分析中央政策與基層實踐之間的關(guān)系,既忽略了地方政府出臺的政策在基層實踐中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忽視了地方實踐對于中央政策調(diào)整的作用。第四,在解釋歸難僑安置制度與華僑農(nóng)場政策時,沒有太多考慮到國家需求、社會結(jié)構(gòu)、中央—地方關(guān)系等政治和社會變量的影響。
本文試圖從國家需求③國家需求的討論散見于眾多著作中,比如吉登斯(Giddens)將國家所需的資源劃分為“權(quán)威型資源”和“分配型資源”,蒂利(Tilly)則分為“威壓”和“資金”。國家需求在中國的國家政策中被表述成為“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和諧”以及“經(jīng)濟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都要硬”。參見陳那波:《國家、市場和農(nóng)民生活機遇——廣東三鎮(zhèn)的經(jīng)驗對比》,《社會學(xué)研究》2009年第6期。的角度,結(jié)合社區(qū)治理及社會建設(shè)、國際難民安置的相關(guān)理論與經(jīng)驗,對20世紀50年代初到現(xiàn)在的華僑農(nóng)場治理的制度背景進行分析,具體探討國家建立歸難僑安置制度與制定華僑農(nóng)場政策的邏輯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轉(zhuǎn)變。本文將主要采用政府政策文獻分析法,①為了說明治理績效,文中會涉及有少量的田野調(diào)查材料,但僅為輔助,不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對僑務(wù)政策、具體的歸難僑安置以及華僑農(nóng)場政策、國家及省級領(lǐng)導(dǎo)人有關(guān)華僑農(nóng)場和歸難僑的談話、各級僑辦及華僑農(nóng)場的總結(jié)報告、檔案文獻等進行內(nèi)容分析,理清不同層次的政策、制度對華僑農(nóng)場治理的社會過程以及績效的影響。內(nèi)容分析將采取“情境分析法”,“聯(lián)系政策制定的社會情境,分析政策選擇背后的邏輯脈絡(luò)和路徑”。[3]
本研究涉及省政府層面的材料主要集中于廣東省,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方面是由于筆者所搜集到的與廣東省相關(guān)的政策文件較為豐富;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廣東省本身就是華僑農(nóng)場以及安置歸難僑最多的省份:全省華僑農(nóng)場有23個;安置的歸難僑人數(shù)為6.9萬人,來自24個國家,占全國華僑農(nóng)場歸難僑總數(shù)的43%;[4]三是廣東省一直積極調(diào)整華僑農(nóng)場政策,在全國形成較好的示范效應(yīng)。上述因素為我們以廣東省為例去理解華僑農(nóng)場治理政策及其變遷邏輯提供了很好的基礎(chǔ)。
一、安置歸難僑:華僑農(nóng)場治理政策的確立
中國的華僑農(nóng)場政策以及針對歸難僑建立起來的一系列制度,實際上反映出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以及歸難僑的治理邏輯。這個治理邏輯的轉(zhuǎn)型受到國家需求以及總體社會結(jié)構(gòu)的影響。下面筆者將分析20世紀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邏輯及其變遷。
(一)歸難僑安置制度的建立
華僑農(nóng)場的出現(xiàn)本身就是計劃經(jīng)濟的特殊產(chǎn)物。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家動用了各種行政資源、采取了強制性措施,將從不同國家、不同時間回國的歸難僑安排在華僑農(nóng)場里。先后在全國建立的華僑農(nóng)場有84個,分布在廣東、廣西、福建、云南、海南、江西和吉林,安置來自馬來西亞、越南、印度尼西亞、緬甸、印度等國的歸難僑及其家屬將近24萬人。[5]其中,有41個華僑農(nóng)場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有43個是在20世紀70年代為安置越南難僑建立的。雖然華僑農(nóng)場的性質(zhì)是國有農(nóng)業(yè)企業(yè),但是它的設(shè)置主要不是為了獲得經(jīng)濟績效,而是以改善歸難僑生產(chǎn)、生活為目標。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設(shè)立華僑農(nóng)場與當時的冷戰(zhàn)格局、東南亞的排華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中國所處的安全環(huán)境,尤其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的威脅,使這些戰(zhàn)略文化的核心得以強化。[6]基于上述歷史背景,中國政府對于受排華風(fēng)潮影響而回歸到社會主義新中國懷抱的歸難僑進行特殊化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充分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同時也構(gòu)成“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20世紀70年代中期建立的華僑農(nóng)場主要是為了配合國家當時改革開放的政策。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受到南北越統(tǒng)一、越南排華、中越戰(zhàn)爭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影響,大量印支難民向外流散。其中,有不少越南難僑以國際印支難民的身份陸續(xù)回到中國。中國政府將一部分越南歸難僑安置在原有的華僑農(nóng)場的同時,又建立了43個華僑農(nóng)場用以安置這些越南歸難僑。在對內(nèi)執(zhí)政上,中國已經(jīng)開始放棄了“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tài)目標,轉(zhuǎn)而進行經(jīng)濟建設(shè)。在對外政策上,中國也試圖去重新融入世界,重新建立與世界的聯(lián)系。中國政府對這些從越南來的難民雖然也稱之為“歸難僑”,但其性質(zhì)與五六十年代回國的歸僑群體存在本質(zhì)的區(qū)別。中國當時是作為國際難民接收國的身份接收了這些越南歸難僑,為此聯(lián)合國難民署還撥款給中國政府,以實現(xiàn)對這些印支難民的安置。國家對越南歸難僑進行安置,除了因為保護中越戰(zhàn)爭中的僑民外,更多的是基于人道主義援助。而接收國際難民,樹立了中國作為負責(zé)任大國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這對于當時急需世界接納的中國來說是尤其重要的。
(二)治理績效的后果:特殊照顧與經(jīng)濟虧損
盡管不同歷史時期建立的華僑農(nóng)場所要實現(xiàn)的政治目標存在一定差異,但是歸難僑的安置制度以及華僑農(nóng)場政策在這個時期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國家通過制度安排建立起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針對華僑農(nóng)場與歸難僑的管理體系。這一時期的華僑農(nóng)場政策以及隨之建立的歸難僑集中安置的制度安排對歸難僑、華僑農(nóng)場以及國家有著不同的影響。
從歸難僑群體來說,國家通過集體性制度安排歸難僑的生產(chǎn)、生活,提供終身就業(yè)與享有社會福利的保障,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fā)了歸難僑的勞動積極性(起碼在一段時間內(nèi))與對于國家的感恩心理。此外,華僑農(nóng)場的歸難僑由于受到國家層面的特殊照顧與扶持,其生活水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普遍高于周邊的農(nóng)民群體,這也無形中塑造了歸難僑的“相對優(yōu)越感”以及依賴特殊照顧的習(xí)慣。
從華僑農(nóng)場來說,國家通過嚴密的科層體系對華僑農(nóng)場在資源分配上進行傾斜,華僑農(nóng)場生產(chǎn)設(shè)備和物資供應(yīng)列入國家計劃,產(chǎn)品由省統(tǒng)購統(tǒng)銷。這些都造成了華僑農(nóng)場“大鍋飯”體制的固化以及對于國家更進一步的依賴。當然,華僑農(nóng)場作為“單位制”的一種特殊類型,在國家與歸難僑之間也發(fā)揮著積極的中介組織的功能:當歸難僑出現(xiàn)了訴求和“怨氣”會向“組織”即農(nóng)場匯報,農(nóng)場會進行及時有效地疏導(dǎo)或是將意見“上傳”,而國家的意圖也容易通過農(nóng)場“下達”。
從國家及地方政府來說,國家長期減免各地華僑農(nóng)場的農(nóng)業(yè)、企業(yè)稅收,承擔(dān)起農(nóng)場的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等財政負擔(dān),省級政府還動用財政大量補貼農(nóng)場由于經(jīng)營不善導(dǎo)致的經(jīng)濟虧損,這造成了國家以及省級政府層面沉重的財政負擔(dān)。截至1984年,虧損的華僑農(nóng)場有62個,占總數(shù)的72%。[7]
二、促發(fā)展:華僑農(nóng)場治理政策的轉(zhuǎn)向
國家通過華僑農(nóng)場安排歸難僑的生產(chǎn)、生活,初步建立了歸難僑安置制度。這一國家政策給不同行動者所帶來的影響不盡相同,進一步影響了后續(xù)政策的變遷以及制度的轉(zhuǎn)型。下面筆者將梳理1986—2006年國家的華僑農(nóng)場政策及其績效情況。
(一)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實施
1978年,“經(jīng)濟體制改革”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為重點被明確提出,國企改革由此拉開序幕。然而,考慮到華僑農(nóng)場的特殊性,國家當時并沒有立即對作為國有農(nóng)業(yè)企業(yè)的華僑農(nóng)場立即進行改革。1979年7月,國家通過擴大企業(yè)自主權(quán)的改革,讓企業(yè)有了一定的生產(chǎn)自主權(quán)。企業(yè)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后,企業(yè)和職工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政企分開,所有權(quán)與經(jīng)營權(quán)相分離,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yè)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jīng)濟實體。
在國有企業(yè)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后,國家為了改善華僑農(nóng)場逐年虧損的狀況,減輕中央及省級政府財政負擔(dān),打破“吃大鍋飯”的經(jīng)濟體制,提高農(nóng)場本身的“造血”功能,改善歸難僑生活,最終決定對華僑農(nóng)場進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wù)院頒布了《關(guān)于國營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開頭就提到了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進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原因:“經(jīng)濟效益差”與“農(nóng)場虧損”。這表明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更加側(cè)重于滿足“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求,即效率邏輯成為國家在華僑農(nóng)場推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首要原則,“經(jīng)濟發(fā)展”也成為解決群眾生活困難的良方。
歸難僑安置制度與華僑農(nóng)場政策的轉(zhuǎn)向?qū)嶋H上涉及到國家與華僑農(nóng)場及歸難僑關(guān)系的根本性變革。一方面,國家試圖剝離華僑農(nóng)場的行政與社會功能并將之下放至地方政府,由原有的中央和省級僑務(wù)部門主管(以省為主)的領(lǐng)導(dǎo)體制改為由地方人民政府領(lǐng)導(dǎo);同時,剝離其經(jīng)濟功能,使其“政企分開”,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jīng)營、自負盈虧的經(jīng)濟實體。另一方面,國家也試圖改變對農(nóng)場歸難僑的管理模式,從原來“大包大攬”的直接管理轉(zhuǎn)變成間接管理。國家宣布不再安置新的歸難僑,鼓勵歸難僑自謀職業(yè)、投親靠友甚至出國定居,并且對歸難僑的子女取消“統(tǒng)包分配”政策。這意味著從1986年開始,華僑農(nóng)場職工子女成年以后,不再自動轉(zhuǎn)成農(nóng)場職工,他們生活在“農(nóng)場”,卻不擁有“農(nóng)場的正式成員”的資格。[8]這實際上也就是把華僑農(nóng)場社區(qū)內(nèi)的歸難僑直接推向市場。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歸難僑經(jīng)歷了非自愿個體化(involuntary individualization)的過程。[9]
(二)治理績效的復(fù)雜性:“三融入”與民生問題
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政策的出臺標志著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治理邏輯的轉(zhuǎn)向。這一政策給華僑農(nóng)場及其歸難僑群體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其治理績效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首先,不同地區(qū)的華僑農(nóng)場基本完成了經(jīng)濟體制改革。在《決定》出臺后,全國華僑農(nóng)場先后開始了政企分開、下放地方的過程。以廣東省為例,1988年8月,全省23個華僑農(nóng)場中有22個下放至地方政府管理,設(shè)立管理區(qū)或設(shè)鎮(zhèn)。花都華僑農(nóng)場的改制最遲,于1991年1月設(shè)鎮(zhèn)。隨后有7個華僑農(nóng)場陸續(xù)撤區(qū)設(shè)鎮(zhèn),1個華僑農(nóng)場撤區(qū)設(shè)街道辦事處。截至2016年12月,廣東有13個場設(shè)為華僑(經(jīng)濟)管理區(qū),9個場建立了鎮(zhèn)級建制,1個場設(shè)立街道辦事處,基本實現(xiàn)了“體制融入地方”。[10]與此同時,農(nóng)場辦社會職能分離基本完成,歷史上的金融債務(wù)基本得到了處置。
其次,歸難僑的生產(chǎn)、生活受到了較大沖擊。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后,部分農(nóng)場的歸難僑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有相當比例的歸難僑尤其是越南歸難僑在急速轉(zhuǎn)型的過程中成為最不受益的群體之一。導(dǎo)致上述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家取消統(tǒng)包分配政策,這導(dǎo)致歸難僑尤其是越南歸難僑的就業(yè)問題凸顯。根據(jù)筆者在廣東華僑農(nóng)場的調(diào)查,部分越南難僑在20世紀70年代末回國時尚年幼,80年代末面臨就業(yè)就碰到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無法轉(zhuǎn)成農(nóng)場職工。而且,由于這些歸難僑教育背景比較低,難以在市場中找到合適的工作,長期處于失業(yè)或無業(yè)的狀態(tài)。此外,國家針對國有企業(yè)以及農(nóng)業(yè)雖然均有一些優(yōu)惠政策,但在政策具體執(zhí)行過程中,華僑農(nóng)場作為國有農(nóng)業(yè)企業(yè)很多時候兩邊的政策均享受不到。上述兩個因素導(dǎo)致不少農(nóng)場職工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原本生活要好于周邊農(nóng)民群體的歸難僑開始出現(xiàn)了“相對失落感”:“其實呢,我們剛回來的時候,國家還是給了不少優(yōu)惠政策,對于我們還是很照顧的。但是農(nóng)場改制之后,這種政策就越來越少了。”①2016年9月25日,筆者在廣州南涌華僑農(nóng)場(化名)對越南歸僑李先生的訪談。在經(jīng)歷十幾年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后,華僑農(nóng)場內(nèi)歸難僑與本地農(nóng)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漸拉大。廣東經(jīng)濟條件最好的深圳光明華僑畜牧場,2000年歸難僑人均收入僅為3336元,不及周邊農(nóng)民人均純收入9270元的一半。[11]即使在廣東省初步采取了一些改善民生的措施(后面會論及)后,2006年廣東華僑農(nóng)場歸難僑的年人均收入反為6631.39元,低于農(nóng)場所在市縣的農(nóng)民人均總收入8339元。[12]經(jīng)濟因素導(dǎo)致了華僑農(nóng)場在基層治理中出現(xiàn)了一些不穩(wěn)定因素。
再次,地方政府在華僑農(nóng)場治理中的角色凸顯。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就是將華僑農(nóng)場的行政功能下放至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的運作邏輯除了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還受制于所在地區(qū)的經(jīng)濟與社會條件。[13]一些經(jīng)濟欠發(fā)地區(qū)的地方政府本身財政經(jīng)費有限,為了實現(xiàn)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的目標,有不少地方政府拖欠國家下發(fā)給華僑農(nóng)場的職工工資、退休金和醫(yī)療費,形成了“三拖欠”問題,導(dǎo)致一些農(nóng)場基層出現(xiàn)了沖突與對抗的因素。此外,地方政府接管華僑農(nóng)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農(nóng)場原本在治理中扮演的“上傳下達”的中介角色并沒有立即由地方政府承擔(dān)。這導(dǎo)致基層治理出現(xiàn)了應(yīng)責(zé)主體缺失的狀況,群眾的訴求無法得到及時的舒緩與解答,加劇了底層不滿的累積。在實地調(diào)研中,一位歸僑說:“以前感覺和國家很近,平常農(nóng)場領(lǐng)導(dǎo)都會下來關(guān)心我們歸難僑,讓我們覺得自己是受國家重視的。改制后,這種機會就少了很多。也就是過節(jié)才會有,而且也不會每家每戶都去。”②2014年8月9日,筆者在廣州南涌華僑農(nóng)場(化名)對越南歸僑陳先生的訪談。
由此可見,華僑農(nóng)場的政策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績效十分復(fù)雜,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政策制定者所意想不到的負面后果。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開始逐漸調(diào)整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政策。
三、重民生:華僑農(nóng)場治理政策的調(diào)整
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徹底改變了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與歸難僑的治理方式,其所產(chǎn)生的治理績效既有積極影響,也有負面后果。下面筆者將討論國家是如何根據(jù)其政策績效來調(diào)整華僑農(nóng)場政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是如何互動并最終影響華僑農(nóng)場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的。
(一)政策調(diào)整的契機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jīng)歷了高速的經(jīng)濟發(fā)展,加上1994年的稅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的稅收不斷提高。國家的需求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其更重要的目標逐漸從“經(jīng)濟發(fā)展”轉(zhuǎn)向到保持“社會穩(wěn)定與和諧”。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科學(xué)發(fā)展觀。在此基礎(chǔ)上,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dǎo)思想。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邏輯發(fā)生再次轉(zhuǎn)向。國家開始注意到,華僑農(nóng)場在經(jīng)歷了20年的體制改革后,行政管理體制逐漸融入地方,經(jīng)濟長期虧損的局面得到了很大遏制。但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中所出現(xiàn)的負面績效開始浮現(xiàn)出來,比如部分歸難僑生活困難,甚至基層出現(xiàn)了一些不和諧聲音。
2006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來自廣西容縣僑鄉(xiāng)的全國人大代表李漢金聯(lián)合其他9名人大代表在會上建議,中央在“十一五”規(guī)劃期間對口安排專項資金加大扶持力度,并盡快制定扶持歸難僑、安置農(nóng)林場發(fā)展的優(yōu)惠政策。2006年5月,針對李漢金等代表提出的關(guān)于加大華僑農(nóng)場扶持力度的建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盛華仁視察廣西華僑農(nóng)場。同年8月1日至5日,國務(wù)委員唐家璇率領(lǐng)國務(wù)院辦公廳、勞動保障部、農(nóng)業(yè)部等9個部門負責(zé)人組成調(diào)研組,赴廣西防城港、崇左、百色和南寧四市下屬的華僑農(nóng)林場調(diào)研。調(diào)研組深入困難職工的家庭,向他們表示慰問,并詳細察看了這些農(nóng)場的生產(chǎn)、生活條件,隨后在南寧召開華僑農(nóng)場工作座談會。唐家璇在會上將歸難僑困難歸咎于外在的結(jié)構(gòu)性因素,即華僑農(nóng)場被嚴重邊緣化,而不是歸難僑自身,而且黨和政府有責(zé)任、有義務(wù)解決好華僑農(nóng)場問題。①2008年12月15日,國務(wù)院僑辦國內(nèi)司司長程鐵生在廣東省華僑農(nóng)場改革發(fā)展工作經(jīng)驗交流會上的講話中,提到唐家璇此次視察廣西華僑農(nóng)場發(fā)表的重要觀點。從這段時期的一系列政策文獻與領(lǐng)導(dǎo)講話可以清楚看出,中央層面對于華僑農(nóng)場存在的一些問題有著敏銳的感知。
而地方層面的一些先行措施也為中央調(diào)整政策奠定了實踐基礎(chǔ)。廣東是最早試圖解決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中出現(xiàn)的民生問題的省份之一。早在2001年,廣東省政府就出臺了《廣東省人民政府批轉(zhuǎn)省發(fā)展計劃委員會關(guān)于加快華僑農(nóng)場與發(fā)展意見的通知》(粵府【2001】62號文)。此文件出臺后,廣東省通過省市兩級籌措資金,基本解決了17個困難華僑農(nóng)場職工養(yǎng)老保險納入地方統(tǒng)籌的一次性補繳統(tǒng)籌金和解除勞動關(guān)系后的一次性經(jīng)濟補償金。同時,廣東省政府還出臺了歸難僑危房改造、加快基礎(chǔ)建設(shè)等扶持性政策。廣東省之所以先于中央小范圍內(nèi)調(diào)整政策與廣東省本身的經(jīng)濟與社會條件密不可分。廣東省作為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其政府首要的績效已經(jīng)不是發(fā)展“物質(zhì)文明”,而是發(fā)展“精神文明”、保持“社會和諧”與注重“民生問題”。
華僑農(nóng)場長期出現(xiàn)的不和諧聲音、各級精英的不斷呼吁與奔走、中央思想層面的松動與基層調(diào)研、地方政府的積極實踐,為國家重新調(diào)整華僑農(nóng)場政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二)政策調(diào)整中的中央與地方
2007年,國家出臺了《關(guān)于推進華僑農(nóng)場改革和發(fā)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標志著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治理邏輯的第二次重大調(diào)整。盡管在此文件中仍然提倡“三融入”,但“華僑農(nóng)場人員的就業(yè)培訓(xùn)、勞動關(guān)系處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參加基本養(yǎng)老保險和醫(yī)療保障”等民生議題在文件中被重點強調(diào),這標志著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邏輯開始從原先的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轉(zhuǎn)向更強調(diào)“社會和諧”上。
《意見》下發(fā)后,廣東省積極響應(yīng),并根據(jù)文件精神,于2008年出臺了《廣東省推進華僑農(nóng)場改革和發(fā)展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實施方案》在《意見》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細化了具體實施細則,提出要加快歸難僑的危房改造、統(tǒng)籌規(guī)劃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完善農(nóng)場職工養(yǎng)老與醫(yī)療保險和處理歷史債務(wù)。在此文件中,重點強調(diào)要認真應(yīng)對農(nóng)場在改革發(fā)展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突發(fā)事件。隨后根據(jù)《實施方案》,廣東省僑務(wù)辦公室先后出臺《廣東省華僑農(nóng)場歸難僑安居工程實施方案(修訂稿)》《關(guān)于做好困難歸僑扶貧救助工作的通知》,廣東省財政廳出臺《關(guān)于下達華僑農(nóng)場清償“三拖欠”債務(wù)獎補資金的通知》《關(guān)于安排華僑農(nóng)場改革解困發(fā)展專項補助資金的通知》。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廣東省針對華僑農(nóng)場與歸難僑進行傾斜與扶持的政策痕跡。這與廣東省本身的經(jīng)濟與社會條件密不可分。廣東省作為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其首要的績效已經(jīng)不是發(fā)展“物質(zhì)文明”,而是發(fā)展“精神文明”,保持“社會和諧”。
在上述政策的指導(dǎo)下,自2008年以來,廣東省配合中央下?lián)艿饺A僑農(nóng)場的資金得到了迅速增長。從2007年至2011年9月,廣東省財政先后下?lián)?億多元專項資金,用于解決歸難僑危房改造、分離辦社會職能、清償債務(wù)處置;有關(guān)部門還傾斜安排超過6億元資金,重點解決華僑農(nóng)場基礎(chǔ)設(shè)施、社保基金缺口和民生社會事業(yè)問題;同時,每年安排17個困難華僑農(nóng)場財政轉(zhuǎn)移支付4850萬元。[14]廣東省一方面希望通過制定政策解決華僑農(nóng)場下放地方后所帶來的“三拖欠”(拖欠職工工資、職工及離退休人員醫(yī)療費和離退休金)等歷史遺留問題,另一方面試圖重建社會福利導(dǎo)向的集體消費制度,如出臺歸難僑危房改造政策、統(tǒng)籌歸難僑的醫(yī)療及保險費用等。
此后,廣東省還定期檢查上述政策的執(zhí)行情況,完善華僑農(nóng)場治理中的問責(zé)與應(yīng)責(zé)機制。2009年11月30日,廣東省政府辦公廳下發(fā)《關(guān)于開展華僑農(nóng)場改革和發(fā)展工作檢查的通知》,由廣東省僑辦牽頭,省發(fā)改委、民政廳等七部門參加,圍繞華僑農(nóng)場歸難僑危房改造、土地確權(quán)登記發(fā)證、金融債務(wù)處置、清償“三拖欠”、華僑農(nóng)場職工參加城鎮(zhèn)職工基本醫(yī)療保險、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六大項20個內(nèi)容進行檢查。
2011年3—5月,廣東省為了進一步摸清省內(nèi)華僑農(nóng)場改革以及民生方面存在的問題,廣東省委辦公廳會同省直屬有關(guān)單位對全省華僑農(nóng)場改革解困發(fā)展問題進行專題調(diào)研。8月18日,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調(diào)研華農(nóng)(林)場改革解困發(fā)展情況時發(fā)表講話,指出華僑農(nóng)場與歸難僑的“解困發(fā)展問題”直接關(guān)系到“國家形象”,華僑農(nóng)場改革不能單純立足于追求經(jīng)濟總量和財政收入謀劃發(fā)展,而必須堅持以人為本,防止出現(xiàn)經(jīng)濟總量雖然增加了,但這些歸難僑并沒有得到好處的情況出現(xiàn)。汪洋此次講話第一次將“民生問題”提到了比“經(jīng)濟發(fā)展”更重要的位置上。2011年12月,廣東省財政廳出臺《關(guān)于安排華僑農(nóng)場改革解困發(fā)展專項補助資金的通知》,安排2189萬元專項補助資金用于華僑農(nóng)場改革解困。
廣東省作為僑務(wù)大省,其對于華僑農(nóng)場與歸難僑的重視,也進一步增強了中央徹底解決歸難僑民生問題的信心。華僑農(nóng)場的基層實踐也為國家進一步的政策調(diào)整提供了參考依據(jù)。
2012年7月23日,國務(wù)院僑務(wù)辦公室等10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了《關(guān)于進一步推進華僑農(nóng)場改革和發(fā)展工作的意見》。文件中體現(xiàn)出中央層面對于華僑農(nóng)場改革過程中的民生問題的重視。7月26日,全國華僑農(nóng)場改革和發(fā)展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僑辦主任李海峰在會上指出,華僑農(nóng)場體制改革不僅是重大的經(jīng)濟任務(wù),也是嚴肅的政治任務(wù),關(guān)系到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對外形象,要從講政治、講大局的高度來認識解決華僑農(nóng)場問題。這些都體現(xiàn)了國家需求以及對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目標發(fā)生了一定的轉(zhuǎn)變,已經(jīng)從主要關(guān)注“經(jīng)濟發(fā)展”轉(zhuǎn)向到了更注重“民生問題”與“社會和諧”。
根據(jù)中央精神以及全國華僑農(nóng)場會議的精神,2013年,廣東省政府出臺《關(guān)于進一步推進華僑農(nóng)場地區(qū)改革發(fā)展的若干意見》。文件中將原本針對歸難僑群體的特殊照顧延伸至華僑農(nóng)場職工以及非職工,比如對新增歸難僑以及非歸難僑危房進行改造,對農(nóng)場內(nèi)困難人員提供“一對一”免費就業(yè)援助、優(yōu)先安置到公益性崗位就業(yè),統(tǒng)籌“4050”①“4050”人員是指由于年齡較大、自身就業(yè)條件較差、技能單一等原因,難以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yè)的勞動者,年齡界定為女性40歲以上,男性50歲以上,因此稱為“4050”人員。農(nóng)場人員參加城鎮(zhèn)醫(yī)保費用等。文件還提出要全力維護華僑農(nóng)場的和諧穩(wěn)定,及時排查化解矛盾糾紛,加強華僑農(nóng)場地區(qū)社會管理,做好涉僑信訪工作,維護歸難僑合法權(quán)益。
由此可見,隨著國家需求的變化,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邏輯從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轉(zhuǎn)變?yōu)閺娬{(diào)“社會和諧”。從中央至地方政府層面都試圖通過構(gòu)建完善的福利制度來改善農(nóng)場基層的民生問題。而華僑農(nóng)場的歸難僑及其他居民借此獲得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新機遇,也出現(xiàn)了“逆?zhèn)€體化”[15]的過程。這一“逆?zhèn)€體化”作為政策調(diào)整后所產(chǎn)生的非預(yù)期績效,會進一步影響國家政策的落實以及農(nóng)場的基層治理。當然,每個華僑農(nóng)場因此而產(chǎn)生的治理績效不盡相同,這需要結(jié)合華僑農(nóng)場的具體情況深入分析,在此不作過多討論。
四、結(jié)論與討論
本文在分析政府政策文獻的基礎(chǔ)上,梳理了國家在設(shè)立歸難僑安置制度以及制定相應(yīng)的華僑農(nóng)場政策中的治理邏輯及其治理績效。研究發(fā)現(xiàn),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及歸難僑的治理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的變遷:從設(shè)立之初強調(diào)“政治任務(wù)”,到體制改革后注重“經(jīng)濟發(fā)展”,再到后來對于“社會和諧”的重視。華僑農(nóng)場的設(shè)立具有安置歸難僑、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屬性,但是國家對華僑農(nóng)場以及歸難僑長期的特殊照顧導(dǎo)致了國家沉重的經(jīng)濟負擔(dān)。國家出于提高生產(chǎn)效率、改善歸難僑生活的目的,對華僑農(nóng)場進行經(jīng)濟體制改革。這一政策給華僑農(nóng)場及其社區(qū)內(nèi)的歸難僑群體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華僑農(nóng)場在不同程度上實現(xiàn)了“三融入”,但同時部分歸難僑的生產(chǎn)、生活受到了較大沖擊,加上“三拖欠”問題以及中介組織的空缺,導(dǎo)致華僑農(nóng)場在基層治理中出現(xiàn)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再次進行政策調(diào)整。其中,廣東省作為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積極響應(yīng)國家政策,建立一系列的社會保障制度與集體消費制度,試圖解決華僑農(nóng)場的民生問題。
從上述過程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國家既要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又要保持“社會和諧”的二元需求實際上造成華僑農(nóng)場在治理過程中的兩難:一方面,在經(jīng)濟轉(zhuǎn)型的大背景下需要促進華僑農(nóng)場的“體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會,經(jīng)濟融入市場”,但無視僑務(wù)及安置政策的歷史以及歸難僑的特殊性,“三融入”會面臨一定的風(fēng)險;另一方面,給予歸難僑群體適當?shù)膬A斜與優(yōu)惠政策,在保證民生的同時,實際上卻延緩了華僑農(nóng)場與當?shù)匾惑w化的過程,尤其是原本被迫“個體化”的歸難僑又面臨“逆?zhèn)€體化”的趨勢。國家的這種二元需求以及基層治理的困境,進一步增加了治理績效的復(fù)雜性與不確定性。
本文有幾點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首先,華僑農(nóng)場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并不完全是由中央自上而下貫徹的,有時也受到地方層面或響應(yīng)或推諉的影響,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互動中不斷形成的。因此,不同省、市政府對國家政策的執(zhí)行情況是存在差異的。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廣東省華僑農(nóng)場,因此本文所涉及到的地方政府層面的結(jié)論不能直接推論至其他省份。其次,國家的治理目標在層層下達基層時受到具體情境的種種限制,即使都在廣東省內(nèi),由于不同華僑農(nóng)場自身的地理區(qū)位、經(jīng)濟基礎(chǔ)以及社會結(jié)構(gòu)均存在差異,因此國家目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下達至具體農(nóng)場,在這個過程中會不會出現(xiàn)目標扭曲甚至完全改變政策目標的情況,基層治理又是如何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的,這些問題均需做進一步研究。第三,本文所討論的治理績效只是從宏觀層面對廣東省華僑農(nóng)場的基本情況進行分析,但不否認個別華僑農(nóng)場的治理績效比文中分析的更好或更差。
因此,筆者計劃在梳理國家對于華僑農(nóng)場治理邏輯及其績效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具體個案研究,討論在國家的二元治理邏輯之下,基層的治理實踐是如何展開并且又是如何影響到中觀、宏觀政策的邏輯演變的。
[注釋]
[1] 李明歡:《社會人類學(xué)視野中的松坪華僑農(nóng)場》,《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
[2] 張賽群:《福建省華僑農(nóng)場養(yǎng)老保險改革評析》,《社會保障研究》2013年第3期;張小欣:《“九三零”事件后中國對印尼歸難僑救濟安置工作論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1年第2期;賈大明:《華僑農(nóng)場體制改革探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4年第10期;周聿峨、鄭建成:《在華印支難民與國際合作:一種歷史的分析與思考》,《南洋問題研究》2014年第3期;俞云平:《一個特殊社區(qū)的歷史軌跡:松坪華僑農(nóng)場發(fā)展史》,《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鄭少智:《國營華僑農(nóng)場改革與資產(chǎn)營運模式探討》,《暨南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3年第4期;何靜,農(nóng)新貴:《關(guān)于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思考》,《福建論壇(經(jīng)濟社會版)》1999年第6期;鐘大球:《“小政府”催長了大經(jīng)濟——對珠江華僑農(nóng)場成立管理區(qū)后的調(diào)查》,《中國農(nóng)墾經(jīng)濟》1994年第10期;楊英、傅漢章、鄭少智、王兵:《廣東省國有華僑農(nóng)場體制改革基本思路探索》,《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2003年第2期。
[3] 王寧:《消費制度、勞動激勵與合法性資源——圍繞城鎮(zhèn)職工消費生活與勞動動機的制度安排及轉(zhuǎn)型邏輯》《社會學(xué)研究》2007年第3期。
[4] 數(shù)據(jù)參見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wù)辦公室編:《關(guān)于我省華僑農(nóng)場改革發(fā)展情況的報告》,內(nèi)部資料,廣東省僑辦提供。
[5] 參見國務(wù)院僑務(wù)辦公室編:《全國華僑農(nóng)場基本情況》,內(nèi)部資料,廣東省僑辦提供。
[6]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zhàn)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guān)于中國與國際社會關(guān)系的三種假設(shè)》,《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
[7] 國務(wù)院辦公廳編:《關(guān)于國營華僑農(nóng)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26號),廣東省僑辦提供,內(nèi)部資料。
[8] 李明歡:《群體象征與個體選擇:華僑農(nóng)場的改革歷程與歸僑職工的訴求》,賀美德、魯納編:《“自我”中國:現(xiàn)代中國社會中個體的崛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出,第279頁。
[9] Li Minghuan, “Collective Symbols and Individual Options: Life on a State Farm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fter Decollectivization”,How Chinese Migrants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05.
[10] 參見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wù)辦公室編:《廣東華僑農(nóng)場主要歷史沿革表》,內(nèi)部資料,廣東省僑辦提供。
[11] 參見鄭少智:《國營華僑農(nóng)場改革與資產(chǎn)營運模式探討》,《暨南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3年第4期。
[12] 參見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wù)辦公室編:《廣東華僑農(nóng)場各指標總表(2006)》,內(nèi)部資料,廣東省僑辦提供;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wù)辦公室編:《廣東省華僑農(nóng)場職工、人均收入及低保情況》,內(nèi)部資料,廣東省僑辦提供。[13] 參見陳那波:《國家、市場和農(nóng)民生活機遇——廣東三鎮(zhèn)的經(jīng)驗對比》,《社會學(xué)研究》2009年第6期; David S. G. Goodman, , “The Localism of Local Leadership Cadres in Reform Shanx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9, No.24, 2000, pp.171-172.
[14] 參見廣東省人民政府僑務(wù)辦公室編:《關(guān)于我省華僑農(nóng)場改革發(fā)展情況的報告》,2011年10月8日,內(nèi)部資料,廣東省僑辦提供。
[15] Li Minghuan, “Collective Symbols and Individual Options: Life on a State Farm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fter Decollectivization”, How Chinese Migrants Make Their Dreams Come True,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07.
[責(zé)任編輯:密素敏]
National Demand, Governance Logic and Performance Efficiency:The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Policies on Overseas Chinese Farms
LI Xiang-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itute of South China Sea Strategic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policies of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rrangement of persecute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economy development; social harmony
This paper reviewes the governance logic and performance efficiency in the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 of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on overseas Chinese farm which were develop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hases for the arrangement of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related policies on overseas Chinese farm: emphasize the “the political tas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rrangement, emphasize “economy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ystem, then focus on “social harmony”after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farms has the political features of the arrangement of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and improvement of their lives. But the long-term special care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nd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became a heavy burden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aim of increasing productive efficiency, improving lives of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reform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farms. This policy brought relative big impact to lives and productivities of the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farm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government from other levels faced the dilemma of balanc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ual goal of the nation and the factors such as social structure and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hip were both influencing the reform trajectory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returned persecuted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policies on overseas Chinese farms.
D634.2
A
1002-5162(2017)01-0050-09
2016-12-13;
2017-02-02
黎相宜,(1985-),女,中山大學(xué)國際關(guān)系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中山大學(xué)南海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華僑華人研究、僑鄉(xiāng)研究、國際移民。
*本研究受到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比較視角下的移民安置聚集區(qū)治理模式及其績效研究”(16CSH017)、廣東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十二五”規(guī)劃2014年度特別委托項目“廣州新移民與僑鄉(xiāng)社會的互動”(項目批準號:GD14TW01-12)、2015年度中國僑聯(lián)課題“廣州珠江華僑農(nóng)場歸難僑群體的多向分層融入模式研究”(15CZQK214)的資助。感謝匿名評審人、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張秀明女士以及廣州市社會科學(xué)院陳杰副研究員提出的寶貴批評意見!文責(zé)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