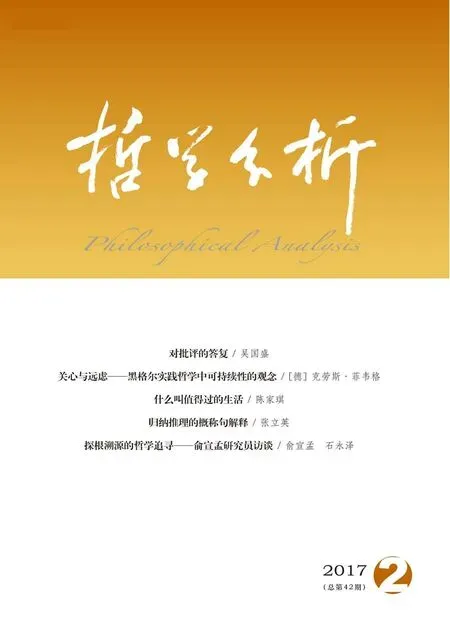2016年維也納海德格爾年會紀要
王宏健
2016年維也納海德格爾年會紀要
王宏健
2016年5月6日至8日,海德格爾年會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奧托·摩爾中心(Otto-Mauer-Zentrum)舉行。6日上午10點15分,海德格爾協會主席、奧地利現象學家維特教授(Helmuth Vetter)宣布大會開始,并且向大家介紹了會議的緣起。近年來,由于黑皮書的出版,海德格爾的人格和思想遭受了巨大的質疑,似乎海德格爾要被歐洲人拋棄了。但是,因為其某些反猶言論就否定海德格爾的全部思想,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對于海德格爾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理解海德格爾,從實質上澄清這一問題,而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對海德格爾展開批判性研究。在致辭中,維特教授進一步介紹了海德格爾與維也納的關系以及這次會議的名稱——hermeneia(詮釋)。
隨后,來自歐洲各國的海德格爾研究者就不同的專題展開了報告。大會的兩個大主題分別是海德格爾與神學的關系、海德格爾的反猶問題。諸報告或者圍繞這兩大專題,或者是與海德格爾相關的其他主題。
一、 海德格爾與神學
第一個專題是海德格爾與神學(宗教)的關系。來自瑞士洛桑大學的許思勒教授(Ingeborg Schü?ler)的報告題目是《觀看、全能與暗示:海德格爾論上帝問題》。報告伊始,她提出了上帝概念的三個面向,分別是形而上學的上帝概念(作為存在者的最高根據)、基督教的創世神以及海德格爾那里的最后的神。其中,前兩者是互不可分的,兩者共同構成了傳統哲學和宗教思想的基礎。而海德格爾則在存在歷史思想的框架內提出了最后的神,以對抗傳統思想的上帝概念。
在古希臘哲學中,“神”的原意是“觀看”。柏拉圖的理念(idea, idein)也是從“觀看”一詞演變而來,最高善就是最高的觀看。而這一形而上學的上帝概念逐漸與基督教的全能神結合在一起。精通哲學史的海德格爾追溯了希臘思想的羅馬化進程,在那里,亞里士多德的“隱德萊希”變成了“現實性”這一范疇,與之相隨的是,作為顯現和消散之雙重統一的自然(physis)演變成了謀制(Machenschaft)和支配(Herrschaft)。
為了克服這一趨向,需要借助于最后的神。在海德格爾那里,最后的神是暗示著的(winkend)神,這意味著,它是存在之本質現身,而非對象性的思辨。存在現身于暗示之中(Wesung in Wink)。事實上,海德格爾在20世紀30年代所提出的這一思想在其1928年的教授就職演說中就有所體現。他在該演說中提出了無化的“無”(Nichts nichtet),這意味著,存在不是某種靜態的存在者,毋寧說,存在“現身于此”(Sein west)。
來自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的費赫教授(Istvan M. Feher)的報告題目是《海德格爾的神學起源》。他指出,海德格爾曾在寫給洛維特的一封信中寫道,他不是一個哲學家,毋寧說,他是一個基督教神學家。這意味著,從神學起源來理解海德格爾的思想,并非一個完全錯誤的視角。值得指出的是,海德格爾的神學起源與他對詮釋學的研究密不可分,例如,他在學生時代對施萊爾馬赫的研究就表明了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恰恰是克服和綜合兩種基督教傳統的結果——一方面是天主教對存在論的強調(布賴格、布倫塔諾),另一方面是新教對主體經驗亦即此在的重視(路德、保羅、奧古斯丁、克爾凱郭爾)。對于后期海德格爾而言,他揭示了形而上學的存在—神—邏輯學機制,并且提出了神學的另一種樣式,亦即非對象化地對諸神的道說。這意味著,要拋棄形而上學的語言,挖掘出原始的神學經驗,從而確認神學的本質和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費赫教授認為,要區分信仰、宗教和神學三個范疇。宗教是對信仰的實施,而神學則是關于信仰的科學,但這種科學,不是理論和學科意義上的,毋寧說,在海德格爾看來,神學是一種人生實存論。信仰是神學的源頭,而神學的任務則是將信仰以特定的概念機制和語言表達出來,這意味著,神學乃是對宗教之體驗、實行要素的概念把握。在這個意義上,神學——作為某種哲學——是此在的某種存在方式,是某種伴隨性的理解(begleitender Nachvollzug)。神學是關于最高存在者(神)的哲學,它以詮釋學的方式展開自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可以被看作一個神學家。
來自維也納大學的波爾特納教授(Günter P?ltner)的報告則涉及海德格爾對中世紀哲學家和神學家阿奎那的闡釋。在海德格爾看來,中世紀對希臘哲學的接受伴隨著希臘的原始生活經驗的遺失。在中世紀神學家那里,存在成為了被創造存在(Geschaffensein),這就意味著制作性行為(herstellendes Verhalten)的支配地位。相反,在海德格爾那里,存在乃是實行,是發生事件。然而,波爾納教授向我們表明,阿奎那將存在作為某種完善者和富足者,在這個意義上,他對存在的理解并不是像傳統形而上學那樣,將其理解為實體和現成存在者。海德格爾對阿奎那的解讀是片面的。盡管如此,海德格爾的闡釋還是深刻而富有啟發的,因為他給阿奎那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和可能性。
二、 海德格爾的反猶問題
大會的第二個專題關乎海德格爾的反猶立場。來自海德堡師范大學的卡爾·施米特研究專家梅林(Reinhard Mehring)教授從形而上學批判的角度對海德格爾的猶太人問題展開了論述。首先,從文本上看,學界認為,海德格爾全集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密不可分。其第三部分的核心內容乃是存在歷史思想,而第四部分則是對存在歷史思想在政治和教育領域的具體運用。一方面,盡管全集第三部分沒有明確提到猶太人問題,但是,這些筆記對研究海德格爾的猶太人問題同樣意義重大。另一方面,全集第四部分也不能還原為單純的政治性筆記,而要聯系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批判這一核心主題。
梅林教授的主要觀點是,在黑皮書中,海德格爾的關注焦點從形而上學批判轉換到一神論批判。誠如尼采所說,德意志觀念論者也都是神學家。對猶太人及猶太精神的批判,就是對其所代表的創世神亦即一神論的批判。而對猶太人的批判并不意味著海德格爾對納粹的支持。在某種意義上,納粹是“無神的猶太教”。誠然,海德格爾反對猶太精神,但在類似的意義上,海德格爾同樣批判納粹。
來自因斯布魯克大學的圖恩赫爾(Rainer Thurnher)教授則試圖挖掘海德格爾的黑色筆記與存在歷史思想的關聯。他認為,不應該只看到黑色筆記中令人驚訝的、丑聞性質的表述,而應該將黑色筆記看作詳細刻畫海德格爾思想發展的材料,因為它提供了對海德格爾思想結構的直接洞見。其次,黑色筆記也讓我們能夠看到海德格爾對于圍繞著他所發生的現實世界的評論。
在報告中,圖恩赫爾教授按照黑色筆記的時間順序,考察了海德格爾存在歷史思想的不同階段,分別是:1931—1933年的產生階段;1933—1934年的納粹校長時期;1934—1938年的反省期;1938—1948年的轉折期。在反省期,海德格爾致力于“思想之作品”,并且提出了此之奠基(Da-Gründung)的思想。而在最后的轉折期,海德格爾開始了道路和過渡的思想。
三、 其他主題
除了上述兩大主題之外,相關學者還做了其他主題的報告。來自圖賓根大學的諾威亞努(Alina Noveanu)博士的報告涉及海德格爾與文學理論家斯泰格(Emil Staiger)的關系。她首先點明了一個文本詮釋的原理:我們所能把握的,乃是我們已經把握的東西。而這個“已經把握的東西”,乃是直接給予我們的,是一種直接的情感和情調。她還著重分析了斯泰格20世紀50年代的作品《闡釋之藝術》。有兩種把握真的方式:科學、知識(Wissenschaft)的方式和知道(Wissen)的方式。后者不以邏輯為基礎,而是以情感為標準。在藝術經驗、生活本身和人的行動中,“知道”較之知識更為根本。在這個意義上,斯泰格的文本詮釋學可以在海德格爾的哲學中找到深厚的淵源。
來自馬堡德意志文獻檔案館的比洛(Ulrich von Bülow)博士的報告是關于海德格爾的遺稿。他指出,不同于尼采、胡塞爾等哲學家,海德格爾對自己的遺稿出版有所規劃,海德格爾的遺稿是有條理的、經過整理的。海德格爾的哲學是一種書寫的哲學,對于海德格爾自身而言,他經常閱讀自己所寫的東西,并且通過做筆記的方式與自己對話。其次,海德格爾的文本可以區分為私人性質和公開性質的,并且,私人性質的文本更為本質。總體而言,海德格爾的遺稿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27年《存在與時間》發表之前,作為哲學教師的海德格爾以口傳的方式推進其哲學工作;第二階段是《存在與時間》發表之后的若干年,海德格爾通過自我閱讀和自我反思的方式與自己爭辯;第三階段是“二戰”結束之后,海德格爾的思想發生了轉向,他不再與自己的早期哲學爭辯,而是與存在本身進行爭辯。最后,比洛指出,《海德格爾全集》不會出版批判版(kritische Ausgabe),但是,目前有可能的是,在原計劃102卷全集之后出版一個補充版(Erg?nzungsausgabe),亦即所謂的“第五部分”。
(責任編輯:韋海波)
王宏健,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