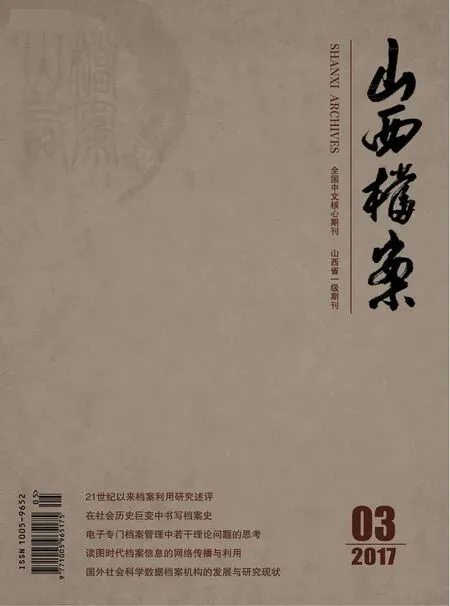論西晉詩歌中的“兒女”之情
——以傅玄、張華為中心
文 / 馮源
論西晉詩歌中的“兒女”之情
——以傅玄、張華為中心
文 / 馮源
受魏晉時期崇情思潮的啟引,西晉詩壇創作出大量的“緣情”之作。其中,傅玄、張華的言“兒女”之情詩作比較突出。傅玄現存詩歌73首,言“兒女”之情者有20余首,約占其詩歌總量的三分之一,此類詩作著意摹寫女子的心理、情狀,突出女子的情真、情深、情美,委婉動人;張華現存的《情詩》《雜詩》和《感婚詩》,集中體現著“兒女情多”的特色。以傅玄、張華為代表的西晉“兒女”情詩,變魏風而為晉調,引領詩歌由建安的多氣向西晉的多情轉變;確立情詩之情感內涵,情真、情深、情持重;情詩清虛之意境為唐詩之祖。
西晉詩歌;兒女之情;傅玄;張華
魏晉學界如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人于“情”的探討,深化了其時詩人對情感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西晉的“緣情”詩學觀;而“緣情”詩學觀又啟引著其時的詩歌創作,西晉詩壇逐漸呈現出重情的態勢,創作出大量的“緣情”詩作。在魏晉洛下清談中,人們可以就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情分別討論,而在實際的詩作中,七情往往不會單獨呈現,而是多種情感混合在一起。因此,對西晉“緣情”詩的考察,尚無法精準地以七情的分類標準,只能以某種情感為主,如“兒女”之情多以愛情為主,“傷逝”之情多以哀情為主。兒女之情,是指青年男女之情,西晉“緣情”詩中此種題材較為突出,學界鮮有結合魏晉崇情思潮來探討者,且對此類詩作的詩歌史意義闡發不足,為此,本文擬以傅玄、張華的詩歌為中心,具體探究西晉詩歌中的“兒女”之情。
一、傅玄的“善言兒女”
傅玄字休奕,身仕曹魏和西晉兩朝,其活動及創作地域主要在洛陽,是曹魏詩壇向西晉詩壇的過渡性詩人。逯欽立先生輯得傅玄現存詩作71首,駱玉明、陳尚君先生輯得2首[1]125,共計73首。其中,“新溫婉麗,善言兒女”[2]138者有20余首,約占全部詩歌的三分之一。
在傅玄言兒女之情的詩中,一部分是樂府舊題,如《秋胡行》、《艷歌行》、《青青河邊草》等,傅玄在因襲固有題材的同時,又賦予其新的內涵。如《秋胡行》,本事為仕宦他鄉的魯國男子秋胡,于返鄉途中戲妻,妻有節,自投長河。傅玄在肯定秋胡妻美好婦節的同時,又有“此婦亦太剛”[3]556之嘆,表明傅玄不贊成秋胡妻為節舍命,不希望以倫理綱常來壓制女性的生命,流露出魏晉人強烈的生命意識,具有時代特色。
除樂府舊題外,傅玄用大量篇幅摹寫女子對夫君的思念,深情綿邈。如《車遙遙篇》,清人張玉谷評曰:“賦閨情也。前四,追敘別景,正述離懷,猶是夫人能道。妙在后二竟接‘影’字,懼其在陰而不得隨,愿其依光而得長隨。反覆模擬以搖曳之,真傳得一片癡情出。”[4]243《雜言詩》,寫得“悠然情長”[5]283;《秋蘭篇》中的女子亦癡情一片;《西長安行》尤其寫得極富特色,苦苦思念意中人的女子,聞意中人變心后,表現得相當克制,對方所贈之物,并不舍得毀棄,免得日后斷了念想,體現出對女子用情的專深。試對比漢樂府鼓吹曲辭收錄的《有所思》,此中女子聞聽所愛之人有他心,便毅然燒掉要送給對方的雙珠玳瑁簪,當風揚其灰,并非常決絕地表示“從今以往,勿復相思”[6]230。《有所思》與《西長安行》中女子對待愛情態度的差異,即漢代與魏晉時代風尚的差別。魏晉以來的崇情風尚,使得傅玄筆下的女子呈現出一往情深的風貌,女子情深得甚至有點癡。
《歷九秋篇》十二章的篇幅,繁衍鋪寫,從新婚的歡娛著筆,直至女子因色衰而愛減,時令的推移,物色與境遇的變遷形成一種同構關系。從詩的內容來看,“前六章追溯‘初醮結發’時歡樂的場面,杯觴交接,樂舞翩翩,從新婚妻子的感受角度,寫出婚姻的美滿幸福;后六章刻畫眼前‘盛時忽逝’后的凄涼情景”[7]334-335。傅玄大篇幅的鋪衍敘寫,展示出女主人公心境的變化過程,“具敘夫婦別離之思”[6]505,詩尾歸結為“妾心結意丹青”,丹青色艷而不易泯滅,故往往被借以比喻對情感的始終不渝,女子以“蘭桂踐霜逾馨”自勵,以明丹青之信。春去秋來,歷盡寒暑,女子矢志不渝,對情的堅守依然不變。
二、張華的“兒女情多”
張華是西晉詩壇的領軍人物,其詩歌的“緣情”風貌特別突出。鐘嶸《詩品》品評張華:“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云氣少。”[8]11“兒女情多”是張華詩歌的主要特色,其《情詩》《雜詩》和《感婚詩》較為集中地體現著這種特色。
張華的《情詩》為組詩,共有五首。從該組詩的整體命意來看,當以《玉臺新詠》的編排方式為是,即“北方”、“明月”、“清風”、“君居”、“游目”。
“北方”以鼓琴的佳人開端,顯示佳人具有較高的才學素養,整首詩在裊裊的琴音之中氤氳開來,清雅脫俗,茂先可謂善發詩端。詩中的佳人思念服役遠行的君子,觸目所見成雙的翔鳥、相和的草蟲,皆令她感激流淚。在詩的結尾,女子突發奇想,愿托晨風之翼以與夫君相會。此處有一細節,即“束帶”侍衣衾,“束帶”為整飾衣服、以示端莊之意,透露出女子多情而又持重的性格特點。游子思婦,是中國古代詩人慣用的詩歌主題,然不同時代的詩人,筆下的思婦卻有著不同的風致。如曹植的《雜詩·西北有織婦》,詩中的女子性格豪放,思念丈夫時“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云”[3]457,帶有戰爭時代的風云氣,而張華這首情詩中塑造的女子形象,既體中和之質,又懷至深之情,有含蘊不盡之美。
“明月”展現的是月夜下的一幅場景:幽人獨守空帷,因相思入夢與佳人相會,醒后形單影只,倍添思念之苦。在中國古典詩歌中,靜謐的月夜往往與情人間的相思相關聯,月亮的清輝,給人以無限的遐想。張華此詩亦有物外傳心、空中造色之妙,玲瓏明凈的詩歌境界,透出清虛寥廓之美。
“清風”以清風、晨月發端,物色與情人之間悠遠的懷思正相契合。從時間安排來看,其一、二首是由晨到晚,此首是由晚到晨;從場景的設計看,其一、二首分別自佳人、君子的處境著筆,此首綜寫佳人與君子共同懷思的況味。
“君居”以空間展開,佳人自述懷抱,不懼山川阻隔,“微心”一片,忠貞不二。
“游目”抒發君子對佳人的懷想,以“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作結,進一步突出夫妻間的相思之苦。此詩與古詩《涉江采芙蓉》同為懷思主題,《涉江采芙蓉》結語為“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彌漫著濃重的悲觀情緒;與古詩相比,離別如一,苦思如一,而此詩結語則有了新的境界,詩人不抱怨、不悲觀,依然熱切地執著于相思,具有一種輕倩之美,誠如王闿運所評“結二句則意新苦語也”,這著重指出了此詩的新意所在。在結撰方法上,這首詩與古詩亦有很大的不同,張華將《涉江采芙蓉》中詩句鋪衍開來,如將“蘭澤多芳草”鋪衍為“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將“采之欲遺誰”鋪衍為“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將“還顧望舊鄉”鋪衍為“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與古詩相比,張華這首詩寫得舒緩從容,且辭彩蔥倩,正所謂“秾麗之作,油然入人”[9]127。
三、以傅玄、張華為代表的西晉“兒女”情詩的意義
首先,變魏風而為晉調,引領詩歌由建安的多氣向西晉的多情轉變。尚氣尚勢為建安文學的特質,如曹植詩發端矯健,選詞偏愛富有力度者,情詩亦寫得風云氣十足。由魏至晉,詩風由多氣向多情轉變,即由剛健之氣向柔靡之情轉變。在此進程中,傅玄堪稱承上啟下的詩人。一方面,傅玄開始大量創作兒女情詩;另一方面,建安詩風中的骨力亦在傅玄詩中時有體現。陳祚明曾云傅玄樂府詩的特點,情長是晉調,矯健、質澀則屬于魏風。及至張華《情詩》等“兒女情多”詩作問世,始一掃曹植等人的樸澀,變建安矯健之氣為西晉柔靡之情,詩歌呈現出深情綿邈、辭彩蔥倩、清綺靡曼的特點。
其次,確立“情詩”之情感內涵,情真、情深、情持重。情真,是指張華《情詩》所言之“情”為純粹的兒女之真情。在張華之前的《情詩》中,如曹植、徐幹的《情詩》,多為托寓之作;如傅玄的言“兒女”情詩,有些篇章顯然有托寓成分;而張華的《情詩》五首則專注于言夫妻離思之情,情思真摯,且無興托在里面,此點為歷來論者所共識。情深,是指傅玄、張華之“兒女”情詩深情綿邈,懇摯、濃郁的情感,深切感人,如傅玄《西長安行》中的情感,專一、執著,不怨不怒,可謂“溫柔敦厚”,有《古詩十九首》之遺風;情持重,是指張華《情詩》所言之情本為夫妻之情,不違人倫,雖懇摯、纏綿,但發乎情、不逾禮,任憑道學家亦無可指摘。
再次,清虛之意境為唐詩之祖。意境自唐人始才著重予以關注,而張華情詩之境界已出音聲之外,有含蘊不盡之美。鐘嶸與劉勰對張華詩歌評價較為一致的詞語是“清”。清字本義為水清,《說文》曰:“清,朖也,徵水之皃。從水,青聲。段玉裁注:朖者,明也。”[10]550老莊之學推崇“清”,漢末以來,玄學興起, “清”逐漸用于對人物的品評和文學批評。張華作為清談名士,亦喜用“清”字,在《情詩》五首中,其二用“清景”,其三用“清風”,其五用“清渠”;不僅如此,他在物象的選擇上,亦多與“清”境有關,如其一的“晨風”,其二的“明月”、“靜夜”,其三的“虛景”等。張華以清虛之景入詩,詩之美已超出物象之外,含蘊不盡。王夫之對張華詩歌歷史地位的深入思考,即“茂先……欲開宋、齊之先,作唐人之祖。”[11]167,可謂知言。
四、結語
西晉詩歌中言“兒女之情”詩作不限于文中所論,其顯著特點是集中于對私我化的兒女之情的抒發,反映出西晉詩壇關注“小我”的創作趨向。此種現象,折射出詩歌創作由魏風向晉調的轉變。而在此進程中,傅玄、張華無疑起到了引領作用。傅玄之所以“善言兒女”,張華之所以“兒女情多”,當緣于魏晉時期崇情思潮的啟引。尤其是張華,堪為“晉調”的領軍人物。張華之所以能去曹植、王粲之煩重,主要在于他能守虛沖;之所以不同于孫楚、夏侯湛之鹵莽,則在于其造次以禮。在張華的身上,名教與自然已經融合無間,體現著晉人的風流。張華的《情詩》,在對情感的崇尚及寫作成就上,皆有界碑意義,其詩歌中呈現出的面貌,即是其胸襟、氣度、素養以及審美情趣的外化,反映出晉初崇情思潮與儒教的高度融合。
[1]駱玉明,陳尚君.《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補遺[J].文學遺產,1987,(1).
[2](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傅鶉觚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7.
[3]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清)張玉谷.古詩賞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宋)郭茂倩.樂府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7]魏明安,趙以武.傅玄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8](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1.
[9](清)沈德潛.古詩源[M].北京:中華書局,2006.
[10](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1](明)王夫之.古詩評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I206.2
A
1005-9652(2017)03-0147-03
本文為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杜佑《通典》與中原文化(2014BLS001)”、河南工程學院博士基金(D2014030)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虞志堅)
馮源(1974-),女,河南方城人,河南工程學院人文社科學院講師,鄭州大學文學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