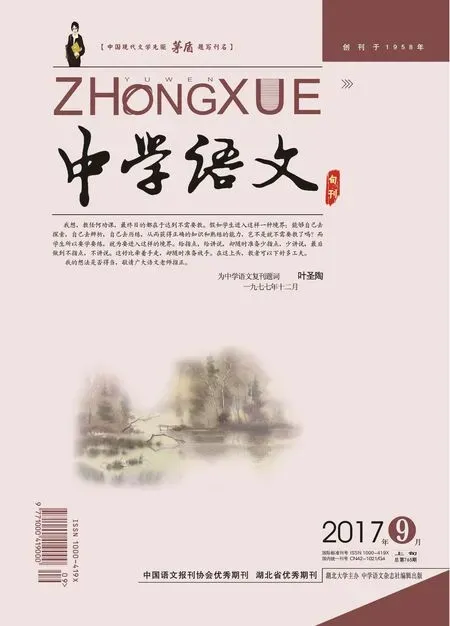突破線性語文教學觀
——《一棵小桃樹》文本解讀與教學創新
李 艷 陳尚達
突破線性語文教學觀
——《一棵小桃樹》文本解讀與教學創新
李 艷 陳尚達
李政濤教授曾指出,“不要把師生割裂開來,作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考,我們要把課堂變成師生共生共長的生命場,成為師生共生共長的家園,它的背后是關聯式思維、整體融通式思維和綜合滲透式思維。”①“共生共長”一詞,道出了語文教學的“課堂”作為“生命場”所蘊涵的師生交互和相互關切,這種“共生共長”暗含著師生相互作用過程充滿變化的生生不息和種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好奇心和緊張感。遺憾的是,很多語文教學滿載著教師對學生關于課文文本的意義限定與思想控制,一些教師依據教師用書并參考他人教學設計來劃定學生的語文學習進程,包括問題由教師拋出和答案由教師提供,整個教學路線由教師單方面劃定,學生只能俯首稱臣。有的閱讀教學中,對大一統式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熱衷取代了語言的發散性思維訓練,修辭運用讓位于邏輯歸納。從一定程度上講,這種線性語文教學觀是造成語文味淡薄的一大根本原因。本文試以《一棵小桃樹》為例,談談語文教學的關聯性思維,以及線性語文教學觀的突破與超越問題。
一、《一棵小桃樹》的線性教學框架及其問題分析
《一棵小桃樹》新入選人教版七年級語文下冊,作者是賈平凹。無論是語文教師用書,還是網上關于《一棵小桃樹》的教學設計與教學反思,都把側重點放在小桃樹的形象探究上,很多老師都會涉及到作者介紹、字詞掌握、結構分析、主題歸納和寫法總結等。其中,“我”和小桃樹的相互關系被凸顯出來,老師們又主要會圍繞三個問題來展開討論:這是一棵怎樣的小桃樹?作者對小桃樹有著怎樣的感情?小桃樹對于作者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形象、感情和意義成為本文教學的三個關鍵詞。
這是一篇托物言志的散文,因此關于小桃樹形象的理解,認為小桃樹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小桃樹的遭遇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境遇,這大體是不錯的,托物言志的寫法也因此會被強調。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提及的線性并不是指問題與答案之間的線性對應關系,雖然它也可能構成線性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而是指整個教學過程都是由教師設計、發起、推進和結束的,并沒有提供學生超越教師教學框架的機會與自由。這種線性教學框架的最大問題在于,它過多體現出教師教學的知識單向流動性及其所顯現出來的強制性意味,并導致學生在語文學習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被思考”與“失語”現象。或許有老師會以教師主導為自己辯護,但教師主導不能以犧牲學生的主體地位與扼殺學生的差異思考為代價,更不能憑著自己的狹隘偏見而將文本意義的豐富性加以簡單裁剪,或故作高深理解并凌駕于學生經驗之上。一句話,學生有超越教師預定教學框架和預設問題理解的自由。“自由能促進個人生長。當我們否定人們為自己作出判斷和決定的權利時,我們就是在否定他們生長的權利。只有在自由地參與反省、論證、審思、評價的過程中,才能提高參與者的理解力和判斷力。”②教師要通過課堂開放吸引學生主動參與,感知捕捉到自己備課中沒能發現的問題和意義。稍加反思就能感悟到,上述關于《一棵小桃樹》的線性教學框架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文本意義被窄化。作者與小桃樹的關系只是其中之一,奶奶與小桃樹的關系被忽略了,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單就小桃樹而言,看不上它的爺爺、看著它長大的姐姐弟弟乃至拱過它的豬都和它的生命成長有關,都是不可忽視的存在者。文本意義并不僅僅限于作者賦予的意義,還包括讀者參與所生成的意義。雖然過度闡釋和強制闡釋都是應該反對和抵制的,但文本文字引發和作者并不一致的理解和想象,是很容易發生的。正如課文所揭示出來的,同樣一棵小桃樹,對于不同的家庭成員而言,顯然表現出并不相同的意義。
第二,學生經驗被弱化。很多老師都圍繞著作者和小桃樹的關系來組織教學,這顯然是強調作者中心論,作者的思想意圖被放大了,所提問題的客觀性被強化了。他們沒有意識到,學生作為讀者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建構中來,問題答案其實是讀者和作者協商的產物,是讀者經驗語境和作者文本語境的疊合互滲,是讀者主觀性理解對文本客觀性意義的一種動態把握。如果是開放性問題,它的答案就不是恒定不變的。就閱讀教學而言,課文文本的意義正在于積極調動學生的生活經驗,并通過教師的機智協調,順利轉變學生的生活經驗。教師如果將教師用書和參考來的答案視為優先的存在物而凌駕于學生思維之上,這種現成結論對學生而言,就形同“不生育的癟籽或死道”。③導致學生經驗被弱化的另一個原因在于,教師引導學生過多關注課文文本本身,沒有將文本與生活、歷史與當下、作者與學生聯系起來,以致學生生活經驗處于被壓抑甚至屏蔽狀態。課文并不僅僅在寫桃樹,也在寫自己,寫親人,寫親情,寫人生。學習這篇課文,不僅僅是讓學生理解作者筆下的桃樹、親人、親情和人生,也要讓學生理解屬于自己的桃樹、親人、親情和人生。在這里,桃樹是一個隱喻,是情感與精神上的重要支撐物。
第三,語文味被淡化。由課文教學的線性框架所決定,教師對問題設計及答案理解的先在性和優先性,使得學生在語文教學過程中明顯處于極為不利的被動地位,尤其是對課文結構的邏輯分析,學生思維明顯帶有一種“繭縛”特征,它顯然是教師提供的。語文味必定和語言的修辭運用密切相關,優秀作品的語文味形成也一定要得益于作者的積極語用過程。不難發現,語文課語文味淡化可能主要與以下三個因素高度相關:首先是教師的線性教學框架和提供現成結論導致的,學生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和主動性缺乏,從而帶來語文思維的扁平化。尤其是提供現成結論,這樣的語文知識教學對學生而言,“就無異于看到水果攤上的水果”,卻難以感受到“它的生命過程中曾經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一樣。④其次是過多邏輯分析,學生的形象思維沒有得到調動和發揮。最后是教師本身的語言貧乏,缺少一定的修辭性色彩,以致學生感受不到語文味。
二、《一棵小桃樹》文本解讀創新
毋庸置疑,小桃樹形象本身的確值得大力關注,小桃樹生長環境所隱喻的不利生存環境意義,小桃樹生長開花不顧偏僻不畏風雨所隱喻的堅強個性,小桃樹身上負載著夢想的和現實的人生理解等,這也是一棵小桃樹命名的真正緣由所在。不少教學資料提及“文革”這個特殊寫作背景,由此聯想到小桃樹成長環境所象征的社會環境意味。這種聯想和象征或許無法否定,但是作者關于山里和城里的鮮明對比表述:“山外的天地這般兒大,城里的好景這般兒多”,是否包含有對社會發展不平衡的政策公平問題的批判呢,肯定是有的。作者學習奮斗進城要干一番事業卻發現自己的幼稚和天真,讀不懂人世大書。結果,“我漸漸地長大了,脾性兒也一天一天地壞了,常常一個人坐著發呆,心境似乎是垂垂老了。”作者在城里生活的水土不服不正暗示出內心對鄉土的精神依戀么,作者的懺悔也源于此,“身漂異鄉”,作為漂泊在外的游子,小桃樹、故土和親人,才是思想精神得以安頓的重要支柱。
擺脫小桃樹即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和托物言志歌頌勇于和困難做斗爭的頑強不屈精神品質的簡單理解,《一棵小桃樹》文本解讀創新,可以從以下三個視角進行開拓。
第一,文學視角。作者筆下的小桃樹為讀者提供了無盡想象的空間,小桃樹承載著作者兒時的夢,是作者的夢種兒長的。小桃樹的誕生和生長其實緣于奶奶為孩子們編織的美麗故事:含仙桃桃核夢桃花盛開,就會幸福一生。有關仙桃的傳說故事也因此能被喚起,如孫悟空大鬧天宮中王母娘娘的蟠桃大會等。小桃樹在這里可以是一個替代物,學生和自己的親人之間也一定有種種難以忘懷的美好故事。或者說,小桃樹可以作為一種起興的對象物來處理。不言而喻,對小桃樹本身的細膩描繪是值得關注和玩味的。春雨讓作者喜憂參半,春雨淅淅瀝瀝,作者吟詩想踏青;春雨噼里啪啦下大了,作者看桃花落陷,老瘦許多,而無可奈何,讓人頓生“零落成泥碾作塵”(陸游《卜算子·詠梅》)的哀嘆。作者對桃花的描繪,可以引起共鳴性聯想與想象,如作者在課文結尾的發問,“你會開嗎?你開的是灼灼的嗎?”就暗含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詩句(《詩經·桃夭》)。可以結合關于桃花的詩詞這種互文性文本來渲染學生的詩情,并引發學生的詩意聯想,增強語言表達的審美游戲性。“‘互文性’說到底是文本之間的某種相互依存、彼此對釋、意義共生的條件與環境。”⑤如“滿樹如嬌爛漫紅,萬枝丹彩灼春融”(吳融《桃花》),“可憐地僻無人賞,拋擲深山亂木中”(李九齡《山舍南溪小桃花》),“日暮風吹紅滿地,無人解惜為誰開”(白居易《下邽莊南桃花》)等。
第二,倫理學視角。作者寫小桃樹其實是寫人際關系的,那不只是“我”的小桃樹,也是奶奶的乃至整個家庭的小桃樹,小桃樹因而是表達親情倫理的關系之樹。形同史鐵生筆下的合歡樹富含他和母親之間的幸福與悲傷故事,小桃樹也負載著作者和奶奶之間的快樂和苦痛。與之不同的是,前者是兒子傷殘而引發的母親擔憂,后者是孫兒別離而生發的奶奶掛念,作者的懺悔和愛都是傾注其中的。小桃樹因奶奶的美好囑托而生,因作者的堅定信念而長,并因奶奶的細心呵護而成。“他們曾嫌長的不是地方,又不好看,想砍掉它,奶奶卻不同意,常常護著給它澆水。”想砍掉它,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們是誰?作者沒有明說,可能是爸媽吧。因為奶奶的不同意,他們也就放棄了砍掉的打算,體現出對奶奶的尊重與理解。作者這樣寫,是否有著某種避諱之意,從而溢出親切明朗的倫理意味。從這個意義上說,小桃樹是一棵親情倫理之樹,一家人的和諧和美其樂融融都在這棵樹上,充滿無限的善意。另外,如同前文曾指出的,作者將鄉村和城市加以對比,自己脾氣變壞,其實就是對故鄉和親情的眷戀,也就是對小桃樹的想念和迷戀,小桃樹就是故鄉和親情的縮影與化身。
第三,哲學視角。從這個角度看,作者明寫小桃樹,暗道人生哲理。小桃樹從桃核入土到發芽生長,陪伴了作者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作者走出大山,來到城里,知道自己的渺小,慢慢發現自己的幼稚與天真。小桃樹雖然不能陪伴,但是深深扎根在作者的心田。小桃樹寄托著作者的人生夢想,它的不利生長環境如同農村孩子的成長環境,“它長得很委屈,是彎了頭,緊抱著身子的。第二天才舒開身來,瘦瘦兒的,黃黃兒的,似乎一碰,便立即會斷了去”,作者這樣描繪小桃樹,可能是對城市和農村生存環境的巨大反差有了鮮明印象之后的產物。“雨還在下著,我的小桃樹千百次地俯下身去,又千百次地掙扎起來”,“小桃樹”雖然營養不良而顯得孱弱,沒有見過世面,但那種對生活不屈不撓、勇于抗爭的堅強個性充分顯現出來了,這正是和作者一樣的在農村長大的有為青年的典型性格。然而作者在城里生活的脾氣變壞,又隱喻作者的靈魂是迷戀著鄉村和大地的,課文表達出親近傳統文化精神的一面,與沈從文的《邊城》在思想精神上有著某種相通之處。作者對奶奶和小桃樹的懺悔和自責似乎并非僅僅是情感意義上的表達,而是對鄉土和親情的精神皈依。
以上從語言的美、倫理的善和哲理的真三個維度對課文文本加以解讀,文本解讀視角當然不止這三種,這里只是側重解釋和揭示復雜關聯中的文本意義的豐富性。
三、《一棵小桃樹》教學創新
課文解讀和課文教學顯然不是一回事,其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關注:一是課文解讀只是解決了教師的學,而無法解決教師的教。盡管教師的學與教存在著關聯,但不能說教師學什么就教什么,因為教師學本身主要是與教師的經驗視域有關的,教師教則主要是要基于學生的經驗視域來實施的。就像上文提及作者獨到的人生感悟,是需要豐富的人生閱歷作為支撐的,對初一學生而言恐是難以理解的,因而就不需要教。二是課文教學是要解決語文知識和學生經驗之間的思維距離,也就是杜威曾指出的,教師需要精通課文,但是他的注意力,必須放在學生的態度和反應上。⑥這就意味著,教師要關注的不是語文知識本身,而是要幫助學生解決他們在主動學習語文知識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問題。這決不僅僅是解決教的針對性,而且是激發與培養學生學語文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三是教學的意義主要體現為積極作用于學生的思維過程,促成學生思維的積極變化。這就是孔子啟發教學所強調的,讓學生思(憤、悱),助學生思(啟、發)和擴學生思(舉一反三)。從讓思到助思再到擴思,這種積極作用于學生思維的三部曲就體現出孔子教的循循善誘特征,體現出教育生活的鮮明兒童立場。“教育生活中的兒童立場最終還是要在理解兒童世界的內在邏輯、尊重兒童的各種念想、給予兒童嘗試錯誤的空間、讓他們在失敗中學習之后,切實地轉化成兒童的發展。”⑦以此來觀照《一棵小桃樹》教學,以下三個環節可以嘗試關注和實施,它有利于不斷提升學生的積極語用能力,并加強師生的相互作用過程。
1.設置自由說環節,讓學生經驗得以出場
教師安排學生課前預習,課文教學伊始可安排5-8分鐘讓學生大膽陳述自己的閱讀理解。教師不霸道施教,不對學生的課文學習進程包括學習內容和方法進行限定與控制。設置自由說環節,不僅是語文教學一個極其必要的民主程序,也是為了讓學生的閱讀經驗得以出場和在場。教師要善于在學生自由說環節積極回應,捕捉問題,巧妙應對。教師向學生講述教師用書上的觀點,或者主動發問后進行解答的串講串問,都不是一種接地氣的教學,極有可能讓學生因不知所云而走神,思想逃離出語文課堂,出現教學空場現象。很多語文課堂都是知識本位的教學,用這種凌駕于學生經驗之上的知識符號強迫學生接受與理解,遏制了學生語文學習本該具有的欲望和沖動,這實在是本末倒置了。讓學生經驗出場,教師傾聽學生原汁原味的感受、體驗與理解,在此基礎上激勵幫助學生,教學才能有的放矢。這個環節,可以稱之為關注學生經驗,行進在朝向文本意義目標的路上。
2.安排討論環節,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
小桃樹其實是極其平常的,在作者筆下實在是一棵不怎么樣的樹,“長得委屈,”“瘦瘦的,黃黃的,”“彎彎的身子,”開的花兒也“弱小,”“骨朵兒也不見繁,”“太白,”“苦澀地笑著,”連奶奶也說“這種桃樹兒是沒出息的”,然而作者為什么要寫它呢?家人“想砍掉它”,奶奶又為什么要護著它呢?小桃樹、“我”和奶奶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內在原因的關鍵點,對這兩個問題的討論其實就涉及到小桃樹的不同尋常處。包括前面提及的小桃樹的形象、感情和意義三個方面,都是可以讓學生獨立思考與自由表達的。教師要關注答案的正確性,但同時也要關注學生話語表述的自由度。在這里,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主要是指能夠用自己的話語表達自己的思考,并在相互補充過程中豐富和完善問題所包含的意義。不是說一提批判性思維能力就是跟人作對,故意走向他人觀點的對立面,而是說不簡單重復他人的觀點,在與他人求同存異中積極語用,勇敢做自己。小桃樹因奶奶而生,凝結著“我”的綠色幸福夢,“我”走出大山來到城里發展而“沒去思想”小桃樹,奶奶對小桃樹的愛護也就是對“我”的惦念,奶奶去世后“我”對桃樹的懺悔等。可見,小桃樹身上存在著奶孫之間愛的呼應和交織。在這個討論環節,要讓學生的語文思維花朵自由綻放,但也要讓教學審美理性歸位與在場,而不是放任自流,以讓學生的思想在正確的思維軌道上運行。這個環節,可以稱之為鑿開學生經驗與文本意義之間的通道。
3.關注兩個拓展,提升學生思維的融通能力
尋求課文意義與語文知識及學生經驗的一種關聯與融通,在拓展學生知識視野基礎上,謀求文本意義在學生語文經驗中生根和生長。誠如斯蘭特瑞所言,“世界是我的教室,而藝術則是我探究此場域的載體,我的目標是督促學生將課程的學科材料與周遭社群的生活世界經驗進行聯結。”⑧這種學科與經驗之間的審美聯結其實就是尋求互文性,也就是關注兩個拓展,提升學生的思維融通能力,近乎孔子提及的舉一反三。一是橫向拓展:尋求此文本與他文本之間的豐富意義關聯;二是縱向拓展,是指歷史文本意義向當下學生生活的一種延伸與滲透。將兩者結合起來看,小桃樹作為一種關聯生命成長的回憶物,一種重要的文本符號表征,都是指向著經驗的,包括專家學者意義上的他者經驗,教師經驗和學生經驗,目的就在于讓文本意義將學生的生活世界照亮,并促成學生語文經驗審美化。教師引導學生由作者筆下的桃樹,聯想到歷史名人有關詩詞傳說中的桃樹,以及當下自我生活世界中的桃樹,甚至包括其作為隱喻的發散性聯想,構成小桃樹意象極為豐富的立體化意義世界。在這個過程中,師生經驗能夠不斷被喚起,積極語用能力得到訓練。這個環節,可以稱之為引領學生在教材文本和生活經驗構成的特殊地理世界中旅行。
①李政濤.《重建我們的思維方式》,《人民教育》,2016年第 3-4期。
②夏正江.《教育理論哲學基礎的反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頁。
③張祥龍.《邊緣處的理解:中西思想對話中的“印跡”》,《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④楊 義.《韓非子還原》,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9頁。
⑤陳定家.《互文性與開放的文本》,《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第4期。
⑥約翰·杜威著,王承緒譯.《民主主義與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頁。
⑦劉鐵芳.《日常教育生活中兒童立場如何可能》,《中國教育學刊》,2011年第11期。
⑧楊 曉.《讓 “身體”回到教學》,《全球教育展望》,2015年第 2期。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項目《啟發教學中的對話關系及其意蘊研究》(批準號:SK2016A096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通聯:李艷,安徽六安市第九中學;陳尚達,安徽皖西學院教師教育實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