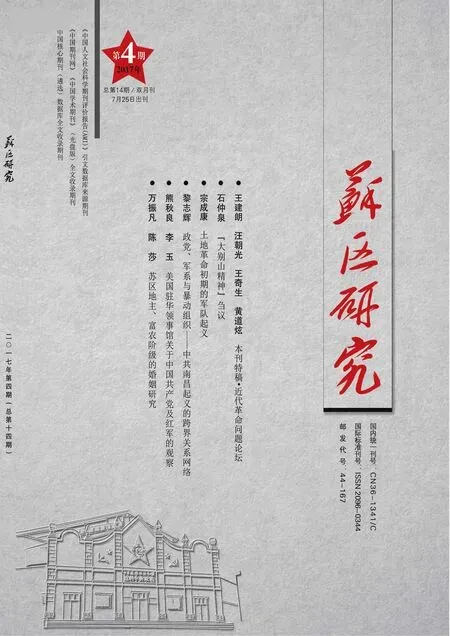蘇區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研究
萬振凡 陳 莎
蘇區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研究
萬振凡 陳 莎
蘇區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進行全國執政的探索時期,在如何處理敵對階級的婚姻問題上,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中共從“階級斗爭”理論和現實出發,對革命階級的婚姻給予強力支持和保護,同時剝奪敵對階級從婚姻中獲得幸福的權力,盡可能從地主、富農階級手中奪取“女性”資源,把它送到農民手中。由此形成獨特的“階級成份婚姻”現象,使蘇區時期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婚姻觀念對解放后很長一段時期中國人的婚姻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蘇區;地主;富農;婚姻
蘇區時期的婚姻問題,已引起了有關學者的關注。李奎原等從社會治理的視角,就中國共產黨對中央蘇區封建婚姻的治理策略和績效進行了探討。*李奎原、齊霽:《中國共產黨對中央蘇區封建落后婚姻的治理》,《蘇區研究》2017年第1期,第90-105頁。湯水清對蘇區有關婚姻法律法規的頒布和實施進行了考察。*湯水清:《蘇區新式婚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黨的文獻》2010年第4期,第62-67頁。吳小衛等從婦女解放的視角,對蘇區婚姻制度變革進行了研究。*吳小衛、楊雙雙:《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與婦女解放》,《南昌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第102-105頁。黃東從社會改造的角度,對蘇區婚姻自由、保護女性等進行了分析。*黃東:《紅色蘇區婚姻改造述論》,《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第26-30頁。郭靜《蘇區的階級與婚姻研究》,對蘇區《婚姻法》賦予不同階級的婚姻權利以及各階級的婚姻狀況作了初步的梳理。*郭靜:《蘇區的階級與婚姻研究》,江西師范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4-41頁。然而,現有成果并沒有對蘇區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問題進行過多的討論。本文擬從探討蘇區時期地主、富農階級所處政治、經濟地位入手,分析蘇區《婚姻法》對地主、富農婚姻權益的限止及剝奪,考察蘇區時期在階級斗爭沖擊之下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境況,剖析蘇區時期這一制度安排對后來中國婚姻問題所產生的長遠影響,旨在進一步推進蘇區婚姻史研究,并為人們觀察、理解現當代中國婚姻現象提供一個窗口。
一、被專政、制裁的反動階級
按照黨的理論,農村中的地主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代表中國最落后的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是革命的對象。富農對農民既有地租剝削,也有雇傭剝削和高利貸剝削,他們“對革命表現出極大的惶惑”,態度“始終是消極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20頁。,是農村革命“限制”的對象。土地革命目的,不僅要在經濟上摧毀封建經濟制度,而且要在政治上推翻地主、富農幾千年來在農村的統治。
蘇區對地主的政策是毫不含糊、毫不寬容的,這個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打倒地主階級,從各方面對地主階級“施行嚴厲的制裁與鎮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24日),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頁。,在經濟上用土地革命的辦法,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房屋等分給農民,徹底摧毀農村封建制度存在的經濟基礎;政治上通過對地主實行清算、戴高帽子游鄉、關監獄、驅逐、槍斃等措施,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4-26頁。據毛澤東《興國調查》,革命初期興國第十區四個鄉地主的命運是:第一鄉,地主不在本鄉,都住外地,但田地均在本鄉,被沒收和分掉了。第二鄉,有三家地主,一家在革命中被殺了兩個兒子,另兩家自動拿出田契來燒,把自己的田分給了農民。第三鄉,有兩家地主,兩家房屋都被人燒了,人則逃亡在外。第四鄉,三家地主,一家逃亡在外,一家被殺,一家被政府看押,家財被抄。*《興國調查》(1930年10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212頁。蘇維埃政府對留在蘇區的地主則加緊對其進行剝奪和鎮壓。1933年6月查田運動開展后,蘇區對地主政策的“左傾”化逐步升級,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將豪紳地主階級,不論大小,全部抓起來,“編為永久的勞役隊”*張聞天:《是堅決的鎮壓反革命還是在反革前面的狂亂》,《紅色中華》1934年6月28日,第1版。;有的地方把所有的地主,“不論大小都捉起來,一律殺盡”*張聞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斗爭》第67期(1934年7月10日),第1版。,采取了從肉體上消滅地主的做法。
對富農,蘇區在革命初期實行“限制政策”,即沒收富農多余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但在實踐中限制政策逐步升級,演變為反對甚至消滅富農的政策。1931年9月5日,中共贛東北省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關于蘇維埃工作決議案》對富農提出了以下政策:“堅決的反對富農。政治上剝奪他們參加政權的機會,肅清富農的反動,經濟上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限制其發展,組織上拒絕他們參加一切群眾武裝組織的權利。同時,要發動雇農反富農剝削的階級斗爭。”*江西財經學院經濟研究所、江西省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編:《閩浙贛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料選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9頁。1932年中共中央決定在蘇區黨政機構中發起“清洗富農”運動,把原來參加革命的富農,從黨政軍組織中徹底“清洗”出去,征發富農組織勞役隊,在赤衛軍監督下,承擔蘇區的各項勞役。*《中央人民委員會第35號命令——征發富農組織勞役隊》,《紅色中華》1932年11月28日,第6版。毛澤東《興國調查》為我們展現了革命初期興國第十區實施富農政策的具體情況:第一鄉共有十二家富農,其中被殺了家長的有兩家,壯丁逃亡在外的有五家,被認為是AB團遭到逮捕的有兩家,“捐了款子,平了田”的有三家。第二鄉一共有九家富農,其中被殺的有六家,被政府“捉起了”的有一家,自動焚燒田契,把田地分給農民的有兩家。第三鄉一共有九家富農,其中抄家被殺的有一家,逃亡在外的有三家,被認為是AB團成員被捉起來了的有兩家,捐了田和錢的有三家。第四鄉一共有兩家富農,兩家均被殺。*《興國調查》(1930年10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13-215頁。從興國第十區的情況看,32家富農中,被殺的11家,逃亡在外的8家,被政府“捉起了”的5家,捐出田和錢的8家,被殺和逃亡的富農占總數的60%。
可見,在土地革命的沖擊下,蘇區的地主、富農,相當一部分逃不過被殺或外逃的命運。國民黨方面的材料也證實了這一點。如1930年11月,在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向南京政府呈送的報告中就提到:蘇區“稍有資產者,或已遠循,或已被殺”,“居留之人大半為農工階級”*《匪共禍贛概況》(電訊),《大公報》1930年11月20日,第3版。。戰后國民黨方面的有關人員在江西農村調查、考察時也發現:江西蘇區“稍有……財產者,未遭殘害,亦相率逃亡”*汪浩:《收復匪區之土地問題》,正中書局1935年7月印行,第28頁。;“稍有知識或財產者,未遭殘害,亦相率逃亡,不敢返鄉”*江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江西經濟問題》,臺灣學生書局1971年6月影印版,第50頁。;崇仁“居民中上產者,多逃至南昌,余亦惶惶惚惚,大有朝不保夕之慨”*陳賡雅:《贛皖湘鄂視察記》,上海申報月刊社1936年12月編印,第14頁。;南豐“略有資產土地的地主、富農、商人,甚至中農均被殺害”*愛伯夏:《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江西銘記印刷所1935年10月編印,第34頁。;南城農村稍有積蓄者“跑的跑、躲的躲,沒跑沒躲的就遭了殺戮”*劉哲署:《東北大學豫鄂皖贛收復匪區經濟考察團報告書》,東北大學編輯部1934年12月編印,第55頁。;臨川“麋集此間之難民,……數共五千……惟細詢之,則無一而非拋財產、棄田園之中產以上者”*陳賡雅:《贛皖湘鄂視察記》,第5頁。。這類史料比比皆是,它說明當時農村地主、富農階級的被殺和外逃的確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即使沒有外逃或被殺,在蘇區留下來的地主、富農,也受到了嚴厲的專政。正如1934年1月2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所指出:蘇維埃對地主和剝削階級實施“嚴厲的制裁與鎮壓”,“第一件是拒絕他們于政權之外。完全取消他們的選舉權,取消他們在紅軍中在地方部隊中服兵役的權利。……第二件,是剝奪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與革命法庭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311頁。。在經濟上蘇區對地主、富農也實行嚴厲的剝奪政策。1931年夏,蘇區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政策,同時蘇區政府把捐稅重點放在富農身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關于頒布暫行稅則的決議》(1931年11月28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566頁。,對富農進行沒收、罰款、派捐、征發谷物等剝奪。*劉哲署:《東北大學豫鄂皖贛收復匪區經濟考察團報告書》,第137-139頁。1932年秋,中共中央決定對蘇區地主殘余與其家屬,實行“絕不能分得土地”,其“所有田地、山林、房屋、池塘通通沒收外,其家中一切糧食、衣物、牲畜、農具、家私、銀錢等一概沒收”的政策。*中央土地人民委員部:《中央土地人民委員部訓令——為深入土地斗爭,徹底沒收地主階級財產》(1932年12月28日),見廈門大學法律系、福建省檔案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法律文件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頁。1933年夏“查田運動”開始后,各地實行“消滅富農的路線”,以至發生“從肉體上消滅富農的現象”。*張聞天:《是堅決的鎮壓反革命還是在反革前面的狂亂》,《紅色中華》1934年6月28日,第1版。可見,蘇區地主、富農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其生存條件徹底惡化。
總之,在蘇區地主、富農階級是革命的對象,受到革命階級的嚴厲專政和制裁,不僅土地、房屋、財產被沒收,而且政治上成為被專政、被鎮壓的階級,在社會上成為最受孤立、鄙視的階級。地主富農階級這種政治、經濟地位的變化,為蘇區推行剝奪、限止地主、富農婚姻權益的法律和政策奠定了基礎。
二、《婚姻法》對地主、富農階級婚姻權益的剝奪
與上述政治、經濟領域的革命斗爭相配合,在婚姻家庭領域,蘇區也實施了反“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法。從法理上看,法律作為國家統治的工具,具有很強的階級性,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當統治階級需要超越道德來維護自身統治和利益時,就會通過法律保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和地位,對敵對階級的權力和利益則進行最大限度的限止和剝奪。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兵政權,工農兵是國家的主人,地主富農是敵對階級,因此蘇維埃政府毫無疑問要實行保護工農兵婚姻權力,剝奪地主富農婚姻權益的婚姻法律和政策。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前,蘇區各地方性法律建設中,就已經出現了限止和剝奪地主、富農階級婚姻權力的婚姻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930年4月頒布的《閩西婚姻法》,現將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82-83頁。
一、男女結婚以雙方同意為原則,不受任何人干涉。
二、取消聘金及禮物。
三、寡婦任其自由結婚,有借端阻止者嚴辦。
四、夫婦離婚后婦女田地不得歸夫家沒收。
五、夫婦離婚后子女歸夫家養育,但婦女愿意負責者除外。
六、男女結婚須向區鄉政府登記。
七、有下列條件之一者準其離婚:①反動豪紳的妻妾媳婦要求離婚者,準予自由。②如有妻妾者,無論妻或妾,要求離婚者,準予離婚。③婢女準其離婚自由。④如有乘白色恐怖來時,將女子嫁有錢者嚴辦。⑤丈夫出外二年以上不通音訊者,準予離婚。⑥婦女離婚后,尚未與人結婚時,男子應幫助其生活。
除閩西外,同時期蘇區各地關于婚姻問題大都有類似的條文和規定。如1932年2月公布的《湘贛蘇區婚姻條例》,其中涉及地主、富農婚姻的條例主要有:第五條規定“男女因政治意見不和或階級地位不同,無論男女可以提出離婚”;第六條規定“有妻妾者無論妻或妾都可以提出離婚,政府得隨時批準之”。*江西省婦女聯合會、江西省檔案館選編:《江西蘇區婦女運動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頁。再如贛南蘇區其他縣份也出臺了諸如“離婚結婚有絕對自由”“禁止虐待童養媳”“富農及富農以上的老婆實行離婚之后,在未結婚之前,其間的生活應由男子負責”“在離婚時,其中的財產雜物和牲畜有享受平均分配之權”等等政策。*《江西蘇區婦女運動史料選編》,236頁。這些政策的基本精神同《閩西婚姻法》差不多,明顯具有鼓勵地富妻妾同地富離婚的意圖。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以國家的名義先后頒布了兩部婚姻法,一是1931年11月28日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二是1934年4月8日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為了分析問題起見,現將兩部婚姻法的有關內容摘錄如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共7章23條,涉及地主、富農婚姻的條款,主要有以下幾條,其大意如下:*《紅色中華》1931年12月18日,第4版。
第一條:男女婚姻必須以自由為原則,廢除任何形式的包辦、強迫、買賣婚姻,嚴禁養育童養媳。
第二條: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禁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
第八條:男女結婚雙方必須到鄉蘇維埃或城市蘇維埃進行登記,領取結婚證,沒有登記的婚姻將不受蘇維埃婚姻法保護。
第九條:離婚自由,凡男女雙方同意離婚的或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即可辦理離婚手續。
第十一條:離婚前子女撫養權的歸屬,如果男女雙方都要求撫養,則撫養權歸女方,如果女方不愿撫養,則男方必須撫養離婚前子女。
第十四條:離婚后女方撫養的小孩,男方必須承擔小孩三分之二的生活費用,直到16歲為止。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共7章21條,涉及地主、富農婚姻問題的條款包括總則在內共有九條,這些條文的基本精神如下:*韓延龍、常兆儒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4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90-795頁。
總則:確定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廢除一切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
第一條: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禁行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
第十條:離婚自由,男女雙方同意離婚的或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即可辦理離婚手續。
第十一條:紅軍戰士的老婆提出離婚,必須得到紅軍戰士本人的同意,才能辦理離婚。
第十二條:男女結婚雙方必須到鄉蘇維埃或城市蘇維埃進行登記。
第十三條:在結婚滿一年,男女共同經營所增加的財產,男女平分。
第十五條:離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結婚,并缺乏勞動力,或沒有固定職業,因而不能維持生活者,男子須幫助女子耕種土地,或維持其生活。
第十六條:離婚前所生的小孩及懷孕的小孩均歸女子撫養。如女子不愿撫養,則歸男子撫養。
第十七條:所有歸女子撫養的小孩,由男子擔負小孩必需的生活費的三分之二,直至十六歲為止。
從上述史料來看,從1930年地區性的《閩西婚姻法》到1934年全國性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關于結婚條件、離婚條件和離婚后的子女財產分割的表述基本相同,其剝奪地主、富農婚姻權益的基本精神一脈相承。下面以《閩西婚姻法》為例對此作些分析。《閩西婚姻法》雖然是閩西蘇區所有的居民在婚姻問題上都必須遵循的規范,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似乎是一個專門針對地主、富農階級婚姻問題的婚姻法。七條內容,每條都與限止、剝奪地主、富農的婚姻權益有關,具有明顯的革命性、階級性。
從結婚方面看:由于革命前地主、富農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相對于普通農民有絕對優勢,經常出現有錢有勢的人利用權勢強搶民女、民妻,或買賣婚姻現象,《條例》通過肯定結婚“自愿”、“自由”及“取消聘金及禮物”等原則,取消了地主、富農在這方面的優勢;《條例》規定“男女結婚須向區鄉政府登記”,這條規定便于蘇區政府對地主、富農階級婚姻進行監管,如果發現地主、富農違反蘇區《婚姻法》,則不但不批準其結婚,還會進行嚴厲的制裁。條例規定“如有乘白色恐怖來時,將女子嫁有錢者嚴辦”,是為了防止局勢不穩定時期,人們把女子嫁給有錢的地主、富農。
從離婚方面看:《條例》規定離婚條件包括:“反動豪紳的妻妾媳婦要求離婚者,準予自由”,“如有妻妾者,無論妻或妾要求離婚者,準予離婚”,“婢女準其離婚自由”,“丈夫出外二年以上不通音訊者,準予離婚”。這里的“有妻妾者”、有“婢女”者,都是指有權有勢的地主、富農;因在革命的沖擊之下,原蘇區的地主、富農大量的逃亡在外,所以《條例》提到的“出外二年以上不通音訊者”也包括這些逃亡在外的地主、富農。可見,所有的條文給予了地主、富農的妻妾離婚的便利條件,都在支持、鼓勵地主、富農的妻妾與地主、富農離婚,以便嫁與革命階級為妻。
從婚后子女和財產分割方面看:《條例》規定“夫婦離婚后婦女田地不得歸夫家沒收”,“夫婦離婚后子女歸夫家養育,但婦女愿負責者除外”,“婦女離婚后,尚未與人結婚時,男子應幫助其生活”等等,這些條款不僅為地主、富農的妻、妾離婚解決了后顧之憂,而且還使她們在離婚時能帶走一部分地主、富農的財產,地主、富農不僅要失去妻、妾,還要失去財產。
總之,蘇區通過頒布和實施上述婚姻條例和婚姻法,對地主、富農的婚姻權益進行了全新的規范和強制性的剝奪,并以蘇維埃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如有違犯則會受到蘇維埃國家執法組織如法院、監獄、軍隊等的嚴厲懲罰。
三、階級斗爭沖擊下的地主、富農階級婚姻
階級劃分和階級斗爭不僅打破了傳統鄉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而且極大地改變了傳統鄉村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境況。
土地革命前由于地主、富農階級具有政治和經濟上的優越條件,因此他們的婚姻較之一般農民具有很大的優勢。在革命之前,蘇區的地主富農階級中一夫多妻制普遍存在。經過蘇區革命的滌蕩,地富階級的土地、財產、房屋大都被沒收,經濟上還不如一般農民。加上政治上地主、富農被打入另冊,成為反動階級,被打擊的對象,他們在婚姻方面的優勢蕩然無存,其婚姻生態變得非常惡劣,婚姻變得十分艱難。
1.地主、富農本人的婚姻。如前所述,蘇區地主、富農分三種情況,一是被殺,一是逃亡在外,一是留在蘇區。被殺的地主、富農,其本人不存在婚姻問題,只是留下了他們妻妾的婚姻問題,對此后文進行分析。
攜家逃亡在外的地主、富農,除了那些特別有錢、在外特別有勢的大地主的婚姻狀況比較穩定外,其他的地主、富農的婚姻都面臨極大的困境。許多中小地主在外花光了所有財產后,逼迫自己的妻、妾、媳、女去賣淫來養活他們,這種婚姻關系名存實亡。如1930年4月5日,《張懷萬巡視贛西南報告》就提到“大豪紳已離開吉安而跑往滬寧,下焉者生活無計……則迫令媳女妻室賣淫”。*《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182頁。1930年10月7日,《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也提到“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風凜凜的,現在大半在吉安、贛州當娼妓,土劣則挑水做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361頁。可見,同以前相比,逃亡在外的地主、富農本人的婚姻生活非常悲慘。
留在蘇區的地主、富農,由于政治、經濟地位的下降,其婚姻也岌岌可危。如上所述,蘇維埃頒布的婚姻條例和婚姻法,旗幟鮮明地鼓勵地主、富農的妻妾與其夫離婚再嫁他人。在蘇維埃政府的鼓勵下,為了擺脫困境,許多地、富的妻妾紛紛同地主、富農離婚。史料記載蘇維埃政府“對地富的婦女要求離婚是很容易批準的,因為離了婚可以和農民結婚了,而且在運動中不少地方發現把婦女當果實分配給農民做老婆”的情況。*梁紅:《認真檢討婦女工作嚴格批判錯誤觀點》,《新華日報》1948年12月31日,第2版。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革命時期“女人的身體就會和土地一樣被重新加以分配,總的流向是從富人家到窮人家”。*金惠敏:《身體的文化政治學》,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頁。顯然,地主、富農本人的婚姻陷入了危機,女性“資源”日益流失。
2.地主、富農妻妾的婚姻。被殺、外逃的地主、富農多為家長和壯年男子,除了隨同地富老公被殺、外逃之外,其他地主、富農的妻妾則留在了蘇區。她們如果不同地主富農離婚,同樣要受到嚴厲的鎮壓和打擊。《紅色中華》第59期發文號召:要無情的嚴厲打擊“對于地主富農家屬的憐憫現象”。*劉祥文:《對于地主富農的“憐憫”》,《紅色中華》1933年3月9日,第3版。有些地方因為“地主婆每日笑罵群眾”便由群眾大會決定將其槍斃了。*邵式平:《閩贛省查田突擊運動的總結》,《紅色中華》1934年4月28日,第3版。有的堅持反動階級立場的地主、富農妻妾,被編入“勞役隊”,開墾荒山荒地和做苦工。有些地主婆表面不對抗革命,但心存不服,同樣也遭到打擊。《紅色中華》第185期一篇題為《好厲害的地主婆》文章,揭露地主婆在蘇維埃政府籌款時,“總是堅決的拒絕,最后他便冒充乞丐,以圖掩飾群眾的耳目……始終不肯拿出分文”,后來把她幾個女兒抓起來審問,才在“地主婆家里挖出金子一兩四錢,現洋三百四十九元,銀子三十余兩,羊皮三件,還有鴉片煙一碗,衣服多件”,文章提出地主婆“是非常頑硬的、機詐的”,必須對她們進行無情的斗爭。*張仁賢:《好厲害的地主婆》,《紅色中華》1934年5月7日,第3版。
經過革命的再三剝奪,留在蘇區的地主、富農妻妾,不僅政治上抬不起頭,而且基本上沒有了經濟來源,迫于生活的重擔和社會的壓力,許多地富妻妾只好另尋出路。有的跟了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員,比如有史料提到“區政府打土豪捉來一個土豪婆(靖衛團總的媳婦)罰了大洋四十元,結果未交款,便由一個委員拿去做了老婆”。*朱權:《西岡區的嚴重現象》,《紅色中華》1932年2月24日,第7版。有的則主動尋求出路,如1932年3月23日《紅色中華》第15期記載,在閩西南的選舉運動中,就出現了“地主富農家之女子因沒有選舉權,紛紛到政府要求離婚,不愿做地主富農老婆”的現象。*口城:《閩西南選舉運動中的成績》,《紅色中華》1932年3月23日,第7版。以致1933年12月15日蘇維埃政府不得不出臺“未結婚的黨團員應教育他不能同地主富農結婚”的規定。*《江西省女工農婦代表大會第四天——閉幕》(1933年12月15日),《江西蘇區婦女運動史料選編》,第133頁。這說明蘇區存在比較多的地主、富農妻妾同地、富離婚,而與革命階級結婚的事實。
3.地主、富農女兒的婚姻。地富的女兒由于生活條件優越,保養得好,較之一般農民的女兒更加漂亮。那些從未碰過女人、“苦大仇深”的農民認為,以前我們受盡地主富農的剝削、欺凌,娶不到老婆,現在天天革命,搞個把地主富農女兒算得了什么。因此,革命中地富的女兒(包括部分地主富農年輕漂亮的妻妾)被強奸以至輪奸的應當不在少數,只是事發后不敢報案,因為即使報案,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也是殘酷無情地打擊地主富農,不可能站在地主富農一邊。有不少地富的女兒被蘇維埃政府的地方干部強迫嫁娶。有的地方“強迫地富的女兒與未婚農民成婚,而不問其本人是否愿意”。*《中央局滕代遠巡視湘鄂贛蘇區的報告》(1931年7月12日),張叔復等編:《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1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6頁。宜黃縣東陂區在1932年9月捉拿了一個地主的女兒,年輕漂亮,蘇維埃政府答應只要女子家里湊足105元大洋來保這位年輕婦女,就可以把她放回家。但是區蘇維埃裁判部部長李衣祿“公開把這個女子放出來弄去同他一床睡覺”,一個月后這個土豪女子家里送來了105元,然而“裁判部長李衣祿還是把她留在身邊快活”。*熊珍:《貪污與腐化》,《紅色中華》1932年11月14日,第8版。當然,與地主富農女兒結婚或有染的人,后來其政治前途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響,許多人還受到清查。
也有不少地方,地主富農主動將女兒嫁給鄉村蘇維埃政府干部或革命農民為妻,希望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有所改善。*陳賡雅:《贛皖湘鄂視察記》,第120頁。對此,蘇維埃政府進行了干涉和限止。1931年12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出臺了《對于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條例》,規定“豪紳地主及加入反革命組織和自動領導群眾反水的富農的老婆、媳婦、女兒同工人、雇農、貧農、中農結婚的,本條例頒布以后,不得分配土地”,“以招郎形式試圖保住財產的豪紳地主富農家庭的財產、房屋仍一律沒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4卷,第124頁。1933年9月30日頒布的蘇區“查田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查田運動中的階級分析》也指出:“地主富農的妻女媳婦與貧苦工農結婚后,他的階級成分是不能改變的,她們過著地主富農剝削的生活,革命后或者是革命前不久,同貧苦工農結婚,他的成分不因嫁了一個貧苦工農的老公而變改。當然不能和貧苦工農一樣分田。”*欣:《查田運動中的階級分析》,《紅色中華》1933年9月30日,第6版。黨和政府認為地富階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地主女兒剝削階級思想是不易改變的,娶她們做老婆會影響老公的革命工作。所以,盡管許多地富女兒愿意嫁給革命農民,卻不被接納,以至出現“地富女孩子因找不到老公而自殺”的現象。*李六如:《談湘贛蘇區土地革命》,《回憶湘贛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頁。
4.地主富農兒子的婚姻。革命前由于家庭條件優越,地主富農的兒子一般都能娶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齡姑娘為妻,有的還會三妻四妾。經過革命的沖擊,地主富農兒子娶不到老婆則成為常態。首先,一般女孩不會主動跟地主富農的兒子結婚。因為蘇區時期地主、富農是“反革命階級”,不僅在政治上沒有政治權力、經濟上沒有分配土地和財產的權力,沒有任何政治經濟前途,而且還要經常受批斗、受鎮壓。一個女子如果與地主富農兒子結婚了,這個女子就成了地富婆,就成了階級敵人,成為革命打倒的對象。而且蘇區政府規定“不論何時與何種成份結婚,所生子女的成份與父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1933年10月10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頁。就是說其子子孫孫都逃不脫“反動階級”的命運。因此,家庭成分是貧下中農、工人的女孩,往往不會選擇地主、富農的兒子作為戀愛和結婚的對象。
其次,蘇區黨和政府,對地主富農兒子的婚姻權力進行了種種限止和剝奪,基本精神就是“將對革命有危險的人踢出局,剝奪這些人從婚姻中得到幸福的權利”。*金惠敏:《身體的文化政治學》,第62頁。前述蘇區婚姻法,不僅在結婚條件上對地主富農兒子的婚姻權力有種種限止,而且即使地主富農兒子娶了老婆,蘇區政府也積極支持、鼓勵她們離婚。許多嫁到地主富農家做媳婦的女人,為了和地主、富農家庭劃清界限紛紛離婚。一頂地富帽子會讓地主富農兒子終身抬不起頭來,“地富”作為一個被打倒的階級,過著比“貧下中農”還苦的日子,在社會上遭受敵對和孤立,地主富農兒子是不敢奢望從婚姻中得到幸福的。他們同以前的貧苦農民一樣,很難娶到老婆,最好情況是娶到一些“低檔次”的女人為妻,比如同樣是階級成份不好的女人、智力有問題的女人、身體有問題的女人或離過婚的女人等。部分地主富農兒子開始品嘗“光棍”生活滋味,有的甚至一輩子都沒有“碰”過女人。
四、結論
蘇區時期,為了推翻封建統治、打倒地主富農階級,中共把階級斗爭引入到蘇區社會的各個層面,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對地主富農階級進行嚴厲制裁與鎮壓。在婚姻家庭方面,蘇區同樣實施了剝奪地主富農婚姻權益的政策和法律,在結婚條件、離婚條件和離婚后的子女、財產分割等方面對地主富農的婚姻進行嚴苛的限止和剝奪,基本上否定了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權力,使地主富農階級的婚姻生態極端惡化。在階級斗爭的沖擊下,地富本人處于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境地;地富的妻妾雖然大量同地富離婚,而嫁入革命階級家庭,但同樣受到了歧視和打擊;地富的女兒有的被強迫與農民成婚,有的主動嫁給革命階級為妻,希望改善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但這種希望因蘇維埃政府關于嫁與革命階級為妻的女人其“階級成分不能改變”的規定而破滅;在蘇區,地主富農兒子娶不到老婆成為常態,他們最好情況是娶到一些“低檔次”的女人為妻,有的甚至一輩子打“光棍”。
蘇區在地主富農婚姻問題上的這些做法,在當時對于打擊地主富農階級囂張氣焰、削弱敵對階級力量、鞏固蘇維埃政權、推動革命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形成的“階級成份”婚姻觀念,為后來的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所繼承,并對建國后中國人的婚姻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依然可見它的歷史痕跡。但是這種建立在階級斗爭化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婚姻觀念和制度,使婚姻離它的“兩情相悅而結合”的本質相距甚遠,兩性關系中的感情已不再是婚姻的基礎,男女婚姻具有功利化的特征。盡管這種做法在革命戰爭年代無可厚非,但在和平年代,人們要做的應該是讓婚姻回歸它的本真。
責任編輯:魏烈剛
A study of the Marriage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Rich Peasant Class in the Soviet Area
Wan Zhenfan Chen Sha
The Soviet area was the period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rried out the national power. Therefore, there was no ready-made experience to draw upon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marriage of the hostile class.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reality of "class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ongly supported and protected the marriage of revolutionary class, whereas deprived the hostile class of the power to derive happiness from marriage. The party seized the "female" resources from the landlords and the rich peasants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delivered them to the peasants. Because of this policy, an unusual phenomenon of "blended-class marriage" was then shaped, not only bringing upside-down change to the marriage between the landlord and the rich peasant class in the Soviet area, but also exerting a significant and long-last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people's marriage and marital life.
Soviet area; landlord; the rich peasant; marriage
10.16623/j.cnki.36-1341/c.2017.04.011
萬振凡,男,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陳莎,女,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3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