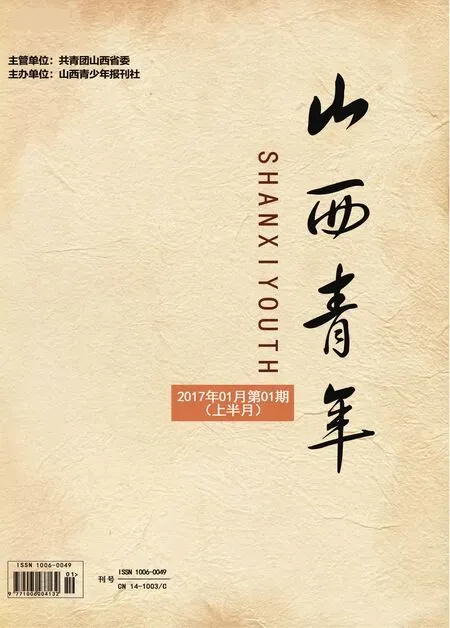金毓黼《遼東文獻征略》的文獻價值
胡 石 趙秀敏 劉 戀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吉林 長春 130033
金毓黼《遼東文獻征略》的文獻價值
胡 石 趙秀敏 劉 戀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吉林 長春 130033
金毓黻是我國二十世紀上半葉著名的歷史學家,是近代以來東北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金先生的《遼東文獻征略》是一部意義非凡的文獻,它是近現代以來我國第一部論述東北古代文獻的著作,為東北史的學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礎,資料的源頭,是深入東北史研究的門徑之一,筆者在論述其體例與內容的基礎上,將其文獻價值升華為一個新的高度,以期對相關研究有所貢獻。
金毓黻;《遼東文獻征略》;文獻價值
金毓黻是我國二十世紀上半葉著名的歷史學家,是近代以來東北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他將東北史置于中國史和世界史的研究背景中,并將史學、文獻學、考古學等學科融入其中,學術視野之寬廣可見一斑。金先生愛國憂鄉,著書立說;愛書情切,搶救古籍;史家風范,上書諫言,搶救、保存、輯錄了大量的文獻典籍,為后世學者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研究史料,體現了中國文人的愛國情懷與責任擔當。
金毓黼先生一生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其1927年出版的《遼東文獻征略》尤其具有標志性,它標志著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學科——中國東北地方古文獻學的發軔,東北古文獻學不僅屬于國學,而且是國學研究的基礎之一,從前我們經常說:治學要有根,根深才能葉茂,東北古文獻學正是東北史研究之根。《遼東文獻征略》敘錄中是這樣描述本書的“北游以來,從公余晷,博稽古書,參以目驗,歲月不居,得若干事次,為八卷,題曰《遼東文獻征略》,文謂典籍,獻謂賢者,凡所甄采必有依據,故曰征也,隨筆摭拾,不成條貫,故曰略也。”
一、《遼東文獻征略》的史學價值
金毓黼的《遼東文獻征略》是一部意義非凡的文獻,它是近現代以來我國第一部論述東北古代文獻的著作,為東北史的學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礎,資料的源頭,是深入東北史研究的門徑之一。
最早有關東北地理的論述出現在《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鄭注云“醫巫閭”,即今遼寧北鎮的醫巫閭山。“遼東”這個名詞最早見于《史記燕世家》及《匈奴列傳》中,具體語言不詳。金先生在《遼東文獻征略》敘錄中說:“自東晉以后,遼東一隅淪于異族燕慕容氏、渤海大氏,亡也忽焉,無足述己。金、清兩代奮跡東北,前者則橫厲中原,后者則統一區夏,以遼東為豐沛舊鄉,崇隆備至,然考之《金史地理志》、《盛京通志》皆因書闕,有間紀載多疏,蓋考求東北地理之難,有如此者。”于此,金先生秉承著憂鄉情懷及學者的責任擔當進行著東北文獻的輯錄與研究。
金先生較為全面系統的歸納了東北史研究的文獻著作,不僅包括學者經常參引的《金史·地理志》、《盛京通志》等,還包括前人罕見引用的文獻,如唐賈耽的《邊州道里記》,賈耽一生喜愛地理,尤勤于搜集地理方面的資料,該書記載東北方隅里到甚為精確可據,只可惜寥寥短篇少之;宋許充宗的《奉使行程記》為許充宗奉使出使金國所記;洪皓的《松漠紀聞》,該書為洪皓留金所記見聞雜事,是一部全面敘寫東北的專著;清楊賓的《柳邊紀略》是清康熙四十六年編寫的一部全面敘述東北的地理學專著,給當時國人揭開了關東神秘的面紗,給后來史家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史料,這些都是考證東北地理必讀之書。關于東北人文著作的記載,在官修史志中也是不全面的,如《盛京通志》所錄遼東人詩寥寥,而金人元好問撰的《中州集》錄遼東人之詩達百余首,鐵保《熙朝雅頌集》、盛昱《八旗文經》所錄八旗人之詩文大半也都為遼東人之作。除此之外,李桂林等所撰的《吉林通志考究》、《東北地理持論精覈》,近人景明久的《考證東北地理之答記》,沈陽世仁甫先生撰的《靜觀齋叢錄》等都是金毓黼先生極力推介的研究遼東先正作品的書籍。
二、《遼東文獻征略》的編撰體例及內容概述
藩鎮割據時多數地區以方隅自號,遼東則稱東北,漢時的遼東郡有奉天一省之地,此明代設遼東都司的依據,《方輿紀要》中將東北諸城附于遼東城邑之后也是取此意,《遼東文獻征略》所述以奉天省舊事為多,故以遼東命名,以黑龍江、吉林兩省及東蒙故實作為附益和補充。本書共有八卷,分別為郡邑、山川、金石上、金石下、人物上、人物下、典籍及雜錄,每一門類都有帶著自身特點的編纂體例;同時,《遼東文獻征略》的主要內容在每一門類下以主題的方式展現,從目錄可知其概貌.本文因篇幅所限,僅選取門類列舉其中一小節概述其內容,以便了解其內容特點及展開方式等。
(一)《遼東文獻征略》中郡邑一門,辨析前人考論東北地理之疏舛,指出遼金二史地理志中存在諸多錯誤之處,《盛京通志》因訛傳訛,遺誤后學匪淺,如挹婁國忽汗城黃龍府皆在吉林省境內,而舊志云皆在奉天省;清始祖所居之地本在長白山附近,而舊志以吉林省之敖東城,這些錯誤可謂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本門對此述論詳盡。“前人已考見及此而引證,未備者亦復不憚辭費,一一辨之。”為學者研究東北提供了準確、詳盡的文獻資料。
郡邑門類下第一個主題為“遼東”,金先生在書中對遼東名字的來源作了追溯,引用了充分的文獻資料進行佐證,具體文字如下:
“《漢書·地理志》:遼東遼西二郡皆秦置,讀史《方與紀要》:遼東為古冀、青二州地,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廣寧以西地,青東北為營周即今廣寧以東地,春秋戰國并屬燕,秦置遼東、遼西二郡,漢初因之。毓黼按遼東遼西之名,初不以在遼水之東西而分,漢之無慮縣在遼水西仍隸遼東郡。《周禮·職方氏》、《鄭注》:醫巫閭在遼東,巫閭與無慮同音,無慮以為閭山所在得名,今奉天省北鎮錦義等縣皆漢無慮縣地,亦皆在遼水西即其明證,況前乎此者遼東地方實兼賅遼西在內,初無東西之分。《史記·蘇秦傳》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此遼東之名初見于古籍者,又《燕世家》燕王喜二十九年秦攻拔薊燕王亡徙居之遼東,蓋在遼水以西,去薊都近,故徙居之,若去薊都千于里,而遠徙于遼水之東,恐非當日情實,項籍分封諸侯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無終為漢右北平縣治,今之直隸玉田縣,去薊甚邇非遼西郡所屬,猶曰遼東,則知其所包之地廣矣。明代因元遼陽等處中書行省之舊域置遼東都指揮司東至鴨綠江,南至旅順海口,西至山海關,西北至大寧廢衛,東北置建州衛,斥地千里跨遼水東西兩岸,概名之曰遼東,從其朔也。蓋古帝王宅京于冀、幽并雍遼地,適當其東故以幽薊以東之地,被以是名非以在遼水之東而名之也,故渝關以東三省之地及熱河東部或稱東北或稱滿洲皆非是名從其朔,宜名遼東。”
(二)《遼東文獻征略》山川一門也具有較強的史料引導性,古人考論東北山川者,未身履其地殊多,鑿空之論,如長白山本因終年為積雪所掩一望皆白得名,而論者乃謂此山為白衣觀音所居,草木禽獸皆白色,則意訛矣;又如黑水本為松花江之別稱,洪忠宣謂以掬其水色微黑得名,于是唐人置黑水府之言始有依據,而論者以今黑龍江當之,實為不當。本門相關東北山川的辨析甚為詳盡。山川與郡邑門類展開體例類似,此處不贅述。
(三)《遼東文獻征略》中金石一門,仿青浦王氏《金石萃編》之體例,考論前代碑版首列原文,次系證義,使讀者不必覓求原拓而本末兼具。分析疏舉多為從前未見之本,足補史乘之闕,致足珍貴。
(四)《遼東文獻征略》中人物一門,列舉諸氏多為文人逸士或其行誼學術為世人不盡知者,博考諸書,有見必錄,只字不遺。文獻間相互考證、補遺,如邴原所居之三山、趙至所居之遼東皆為疏舉多證,務求其實;《金史》闕王遵古傳,可用元遺山所撰《王黃華墓志》及《中州集遵古小傳》補之;遼東三老忠之戴亨行誼無考,可以金兆燕所撰《戴梓傳》補之,類此者甚多。
人物一門中,筆者以“趙至”這一主題為例子,分析展示該門類特點,在對趙至這一人物論述中,除了簡單的介紹人物外,金先生還將《文選》中的《與稽茂齊書》全文摘錄,而本主題的重點是對《與稽茂齊書》的作者與趙至的占戶地進行辨析,具體文字如下:
“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安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子太子舍人藩,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文選》四十三,李善注。《嵇紹集》。
毓黼按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稽康書。《嵇紹集》以為至與茂齊書。李善注《文選》時不能定其適從,故兩存之。唐修《晉書》從《嵇紹集》故附至傳,又《文選》注謂至詣遼東州,辟為從事,而《晉書》則謂占戶遼西幽州,辟部從事,亦有歧疑,晉遼西郡為今渝官以內,舊永平府地,至雖占戶,其間與吾遼東不相涉也。愚從《嵇紹集》詣遼東之文,故以趙至入錄,而定其占戶遼東焉。《晉·地理志》:遼西郡屬幽州,故幽州辟至為從事。”
(五)《遼東文獻征略》中典籍一門,甄敘終始,粗明條貫,補遺輯佚。最早記述遼東文獻的書籍屈指可數,唐賈耽的《邊州道里記》、宋許充宗的《奉使行程記》僅僅記錄奉使道里故實,筆墨不多,只有洪忠宣居東北最久,記載在金國見聞,內容頗多,然以出境有禁不得攜帶回南方,所以大都散佚,現在流傳的《松漠紀聞》二卷,是其晚年回憶之著,只是大略而已,但現在考論史實仍然以此書為依據,因為該書所記都為親眼目睹之事,實屬可貴。遼東先正自著之書可考見者不下數百種,乃從無一人為之捘剔爬疏撰列一表,以資來學之訪求者。于此,本書特列典籍一門。
典籍一門中對《拙軒集》的敘述也較為精彩,在輯錄作者及書籍始末的同時還對相關的疏舛之處做了引證,筆者僅摘錄如下:
“《拙軒集》六卷,金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登天德二年進士,累官中都,轉運使,謚文肅,《金史》不為立傳,元遺山《中州集》載其詩入乙集而仕履亦敘其梗概,《中州集》稱元寂著有《拙軒集》、《北遷錄》諸書,今《北遷錄》已無傳本,而元氏所選寂詩僅七首即附件《姚孝錫傳》一首,其他亦久佚不見。乾隆四十一年,四庫館總纂紀昀、陸錫熊,纂修汪如藻等自《永樂大典》中輯出寂詩文若干首,厘為六卷,仍署曰《拙軒集》,既佚而復得,遂非完璧亦十存七八,良可寶貴矣。…………余被命提點遼東等路刑獄事,閱再歲會以公集飯素于大清安禪寺,偶于稠人中得故人李仲佐,握臂道舊,又贈仲佐詩,序云李仲佐,遼東之豪士也,初識于大元帥席上,怪其議論英發,坐客盡傾,至于通練事物,商較人物,雖宿星老儒或有所不及,仲佐為何人?《金史》及《中州集》皆不載,既為寂所盛稱,必為杰士,設無此集,其姓氏亦湮沒,不傳矣。
《盛京通志》歷朝藝文錄寂詩僅七首,皆在遼東之作,與《中州集》所載者頗有出入,蓋其時《拙軒集》已經館臣輯出,故輯者得以采入,王氏父子兩世皆官,遼東為名宦一門,卓異之選,而《盛京通志》僅錄其詩而不為立傳,亦百密一疏也。”
(六)《遼東文獻征略》中雜錄一門,為不能入以上諸門者,內容涉獵多樣,因此取名為雜錄,以免偏失。
該書體例明晰,指導、引見性較強,金先生意在供他日修志者具漁獵采伐之資,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
三、結語
綜上,金毓黼先生的《遼東文獻征略》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為東北史學者開展研究提供相關資料,筆者對《遼東文獻征略》的研究現狀進行調查,在中國知網(CNKI)中,以《遼東文獻征略》為主題進行檢索,得到五篇文章,但這五篇論文沒有對《遼東文獻征略》進行內容研究與論述的文章,都是引用其內容進行相關東北史研究的論文,如傅郎云的《<好太王碑>所載相關問題的思考》、張韜的《“詵王之印”小考》,由此可見,對《遼東文獻征略》的開發與研究是必要的。
[1]金毓黼.遼東文獻征略[M].吉林:吉林永衡印書局,1927.
[2]霍明琨.金毓黼《靜晤室日記》文獻學價值述略[J].歷史文獻研究,2012(3).
[3]傅朗云.《好太王碑》所載相關問題的思考[J].社會科學戰線,1996(4).
[4]王禹浪,蘆珊珊.遼東地名考[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1(1).
G256;K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