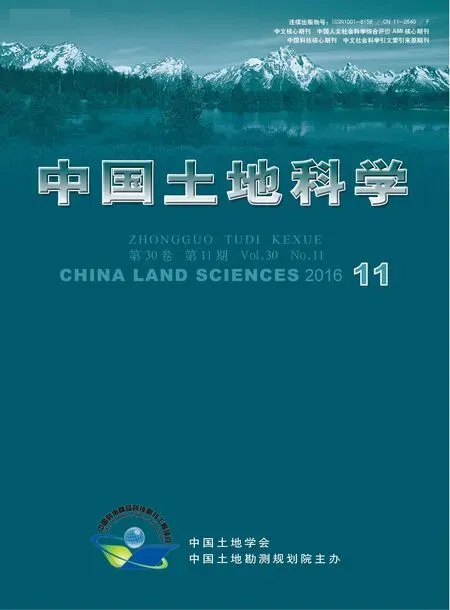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與影響因素計量經濟研究
——基于廣東省南海區1872份市場交易及398份調研數據需求側的實證分析
張 婷,張安錄,鄧松林,胡 越
(1.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2.江西省水利規劃設計研究院,江西 南昌330029;3.農業部管理干部學院,北京102208)
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與影響因素計量經濟研究
——基于廣東省南海區1872份市場交易及398份調研數據需求側的實證分析
張 婷1,張安錄1,鄧松林2,胡 越3
(1.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2.江西省水利規劃設計研究院,江西 南昌330029;3.農業部管理干部學院,北京102208)
研究目的:利用2010—2015年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數據歸納出市場發展特征,在此基礎上利用398份問卷調研數據分析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及影響因素,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提供建議。研究方法:Tobit模型,二值選擇的Probit模型。研究結果:(1)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特征表現為集體經濟組織的高度自組織性;市場交易的高頻率;市場客體為存量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波動性大。(2)資產專用性正向影響契約期限、交易對象的選擇,威廉姆斯交易成本理論認為長期契約有利于給予投資者進行投資的信心;集體經濟組織化水平是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關鍵因素。(3)交易的不確定性越強,企業越傾向于選擇短期契約,以降低企業的預期風險;市場交易“買進”戰略存在風險,企業傾向于選擇與集體經濟組織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交易的有效性。研究結論:為提高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有效性和效率,明晰土地和房屋產權是前提和保障,其次應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的第三方規制。
土地經濟;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特征;影響因素;市場效率;計量經濟研究
1 引言
在追求GDP快速發展的壓力下和城鎮化進程不斷加速的現實中,中國經濟發達地區普遍經歷了劇烈的土地利用結構變化過程,土地供需矛盾問題成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瓶頸[1-2],也刺激了鄉村工業化的發展。改革開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地區正是憑借豐富的土地資源以及低廉的建設用地擴張成本,吸引了大量“三來一補”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確立了外向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迅速推進,珠江三角洲的建設用地進入高速擴展時期[3-5],并且以鎮、村兩級為主要投資載體,從而促進了建制鎮以及村鎮級工礦用地的迅速擴展,造成了建設用地擴展的小城鎮傾向[3]。
南海區作為珠三角地區中農村城鎮化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6],在改革開放30年間經歷了多次集體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熱點試驗區。20世紀80年代的“三權分立”制度格局促進了鄉村工業化的開端及建設用地的大量增加[7];20世紀90年代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加速了土地利用非農化的發展,形成破碎的鄉村工業化格局,發展成為了早期無序的、“隱形”的農村建設用地市場;隨著集體建設用地的無序擴張,國家開始思考實施規范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土地政策,2001年后土地緊縮政策促進了集體產權的國有化,建設用地增長變緩,并逐漸呈現集聚與破碎共存的特點[8]。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所謂的“南海模式”,這一模式主要是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創新,在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背景下,出租土地或修建廠房出租進行土地非農化,進而實現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和集體土地的集中經營,形成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9]。
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從無序、“隱形”的土地市場發展成為有序、“可見”的土地市場,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已經成為和國有土地市場平行的農村土地市場。然而,這種土地市場的發展情況如何?如何去衡量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情況?這些是學術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以往對土地市場發展的研究主要是針對農地流轉市場,并從參與土地市場的農戶比例、參與土地市場的土地面積比例以及交易契約期限的角度進行分析[10-13]。本文在借鑒以往土地市場研究經驗的基礎上,從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屬性和交易流程出發,采用市場交易的契約期限、交易的場所、交易對象等來分析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及其影響因素,探析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有效性,為建設高效率、低成本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提供意見和建議。
2 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及其特點
根據對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調研,對南海區公共資產交易平臺、各鎮(街)公共資產交易平臺的訪談,以及集體資產交易平臺和國土局備案中記載的2010—2015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的1872份數據,歸納出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以下特點:
(1)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供給方)的高度自組織性,降低了市場需求方和個人產權細碎化的締約和履約成本。集體建設用地空間上分散,產權方面屬于農村集體共有而非個人所有,如果集體建設用地像西方私有土地市場那樣進行交易將面臨巨大的交易費用。因此,在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過程中需要進行制度的創新,而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1992年南海區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這一改革的重大突破點是農村集體的政經分離,建立了經濟社和經聯社并行使集體經濟組織的權利,將原來行政的、松散的組織變成經濟的、統一的組織,形成了沒有政府干預、以市場為導向的交易。2010年南海區在各鄉鎮(街道)建立鎮(街道)、村兩級集體資產交易平臺,第一宗集體建設用地在鎮級平臺交易;2014年南海區集體土地交易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定位為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交易場所,2015年南海區大瀝鎮的一宗地正式在區級交易中心掛牌交易。根據區、鎮(街)、村三級交易平臺的數據記錄,2010—2015年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共交易1872宗,其中出租1855宗,出讓17宗。南海區這些制度創新和機構的建立最大程度地消除交易過程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同時也有利于消除需求方(企業)在交易場所選擇方面的不確定性,為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提供安全、可靠的交易場所,降低需求方在交易過程中的交易費用,提高市場交易的有效性。
(2)市場主體交易預期的長期性、締約的短期性帶來市場較高的交易頻率。集體建設用地是集體共有資產而不是單個私有資產,農村集體的個體知道土地歸屬于某一集體,因而對集體建設用地交易的利益分享會有持續的、強烈的預期。而需求方(企業)對于企業的經營狀況以及盈利也存在一定的預期,再加上企業的生命周期相對于土地利用周期較短,因而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呈現交易周期相對較短、契約期限較短(大部分低于20年)、交易頻率較高的特點。交易數據顯示,2010—2015年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以出租方式進行的交易其契約期限小于等于5年的有1305宗,在5—10年間(含10年)的有91宗,契約期限在10—15年間(含15年)的宗地數量是85宗,在15—20年間(含20年)的宗地數是96宗,而契約期限長于20年的宗地數量是278宗;以出讓方式進行的交易其契約期限只有1宗地小于等于5年,其余16宗地的契約期限都長于20年。由此可見,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締約的短期性將給市場交易帶來較高的交易頻率,并帶來相對較高的交易費用,并進一步影響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效率。
(3)市場的客體是存量建設用地,而非增量,供給有限而需求上升使得價格有較大的上升空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進行交易的都是存量建設用地,這些存量建設用地來源于20世紀80、90年代“三資”企業入駐珠三角地區對于建設用地需求的增加,改革開放初期地方政府“零地價”、“零門檻”的招商引資,將大量農用地越過土地征收過程直接轉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以及20世紀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面臨的企業轉型,使得大量技術粗放型企業被技術密集型企業替代,粗放型企業面臨破產,從而留下了大量的存量建設用地。南海區建設用地總面積為536.93 km2,其中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面積為250.68 km2,國有建設用地面積為286.25 km2,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面積占全區總面積的比例為46.69%。這些集體建設用地的區位往往是分散的、插花分布,土地規模相對來說較小、較破碎,而對于企業的用地需求而言,企業傾向于選擇地塊相對集中的、區位較好的土地,以減少市場交易過程中信息搜集等的交易費用。因此,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特征會影響企業市場交易的交易費用,從而影響市場交易的有效性。
(4)公開市場交易的歷史較短,相應的市場監管、調控制度滯后,市場交易波動性大。2010—2015年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數量呈現先上漲后下降的趨勢,2010年交易的宗地數為317宗,2011年交易宗地數為723宗,達到了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的峰值,2012年交易了361宗,2013年交易的宗地數為256宗,2014年交易的集體建設用地數量是150宗,2015年交易了65宗。2010年南海區開始在各鎮(街)逐步建立交易平臺,2011年南海區政府出臺了《佛山市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出租管理辦法》,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進一步規范,使得市場交易數量在2011年達到了峰值。然而由于存量集體建設用地的有限性,交易數量開始下降,特別是在2012年,集體建設用地交易的數量只有2011年的一半。這反映了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尚缺乏一套系統的市場監管、調節機制,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負反饋機制較弱,市場的波動大,會導致集體主體產權容易受到侵犯、利益被侵占,這就使得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環境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此外,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借鑒國有建設用地市場的稅收體系,向承租方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稅、廠房租金稅等,然而由于集體建設用地交易出現很多二次轉租、多次轉租的行為,稅費繳納并非是當前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者,這種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將影響承租方的交易費用。
3 理論分析框架
Williamson引入了“比較制度視角”或稱“分立的結構選擇分析法”,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交易費用經濟學這一得到廣泛經驗檢驗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支[14-17]。本文對于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效率的分析沿用威廉姆斯交易成本理論。根據前文對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狀況的分析可知,市場的交易主體中供給方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需求方是用地企業,交易客體是集體建設用地。然而課題組的調研發現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普遍存在二次轉租和多次轉租的行為,即用地企業從集體經濟組織承租土地或者物業之后會將其轉租給其他用地企業,因而本文只考慮其提供的交易環境。根據威廉姆斯交易費用理論,資產專用性是指用于某種特定用途后資產被鎖定在這一用途上,改作他用可能會使資產價值降低甚至毫無價值,且資產在不同行業中進行再配置將產生費用(成本),資產專用性越高再配置產生的費用越高,其包括人力資產專用性、物質資產專用性、地理位置資產專用性[14-18]。人力資產專用性包括承租方(企業)是否本地人、承租方(企業)受教育程度兩個因子,人力資產專用性越高越容易被鎖定在某一行業中,對集體建設用地的需求也將被鎖定,因而會使得市場交易費用較高,這將影響承租方在集體建設用地交易時對契約期限、交易對象選擇的預期,人力資本專用性越強,承租方傾向于進行長期契約交易,并愿意選擇與村集體交易,以降低交易費用。物質資產專用性是指企業的資產狀況、企業規模等,表現為企業投入資本及企業年總產值。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在選擇集體建設用地時需要根據企業自身的狀況和規模來衡量,因而企業資產專用性越高,會被“束縛”在某一行業中,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費用較高,這就使得承租方對于契約期限預期越長,且傾向于選擇規范化的交易場所及有保障的交易對象。地理位置專用性在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中主要是受集體建設用地的區位和規模的影響,通過交易地塊規模和區位屬性表示,由于土地的位置固定性,因而企業在選擇集體建設用地后將會被固定在某一區位,改變位置將產生高交易費用。位置專用性越強,承租方越傾向于選擇長期契約以減少市場多次交易產生的費用。資產專用性越高,企業在契約期限選擇、交易場所和交易對象的選擇方面會衡量資產投資以及收益回報的均衡,以降低交易過程中的風險,從而達到提高市場效率的目的。
交易的不確定性主要包括在兩個方面:交易行為的不確定性和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1)交易的不確定性越高,其產生的交易費用越高[14-17]。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中交易行為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簽訂的合同公證情況、政府干預、中介參與,反應其可能發生的機會主義行為[18],市場交易行為的不確定性越強,市場可能存在越多的機會主義行為,這將會導致市場失靈和市場交易效率降低,承租方將更愿意選擇短期契約以降低不確定性帶來的交易費用,并通過選擇交易平臺來減少交易過程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可在集體建設用地交易中得到更高的收益預期。(2)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表現在辦理《土地使用證》、辦理《房屋產權證》、繳納土地使用稅、繳納廠房租金稅,反應制度變化以及信息不對稱、不透明帶來的交易費用[18]。交易環境不確定性帶來的交易費用會使得交易雙方在接受信息以及實際信息之間的失衡,使得市場的運行存在較多風險,因此,承租方傾向于選擇交易平臺來保障交易的公開、公正、公平,選擇與村集體進行交易可以減少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以提高市場交易效率和運行的有效性。由此可見,影響交易行為和交易環境不確定性的因素同時也是影響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從這個理論框架對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與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對于探究市場運行效率影響原因具有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提出提高市場高效率、低成本發展的建議有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集體建設用地市場。
4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數據來源于華中農業大學“建設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課題組于2015年12月、2016年6月和8月3次在南海區的調研和問卷調查,主要針對南海區桂城街道、西樵鎮、獅山鎮、大瀝鎮、里水鎮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進行調查。調查過程中采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調查樣本,走訪發生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行為的企業。分層包括3個階段:第一階段根據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交易的統計數據對各鎮、街進行分層隨機抽取樣本(鎮、街);第二階段從鎮、街隨機抽取村、社區的樣本;第三階段從村、社區隨機抽取企業樣本。對于村、社區樣本的末端抽樣規則是,每個樣本村、社區隨機選取15個企業作為受訪樣本,受訪對象一般為企業負責人,即參與了地塊交易過程的負責人。調查共計發放問卷420份,隨機挑選企業面對面完成問卷400份,其中有效問卷398份。
根據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特點,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進行研究,研究思路是選擇市場交易契約、交易場所的選擇、交易對象的選擇這3個指標來衡量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質量并分析其影響因素,變量的選擇見表1。
回歸模型能夠成立的重要條件是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并解釋與擾動項不相關,因此,接下來對解釋變量直接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選擇使用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19]①結果表明VIF最大的為2.44,遠低于10(VIF超過10,則存在較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5 模型選擇與實證分析
本文采用Tobit模型對交易契約期限進行估計,采用二值選擇的Probit模型對交易場所、交易對象進行估計,分析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發展情況,結果見表3。
Tobit模型(模型一)的計量結果表明,企業投入資本在1%水平上正向顯著影響交易契約期限,即企業投入資本越多,交易契約期限越長。企業投入資本可以表現為企業規模,企業規模越大,其承載的成本越大,企業容易被“束縛”在某一行業中,企業作為“理性經濟人”在選擇地塊或者廠房時更多地考慮長期投資,并會根據企業自身的資產狀況以及企業發展狀態做決定,且這是一種減少企業搬遷成本、人力成本等交易費用的有效方式,過高的交易成本對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不利;而且如果企業交易契約期限較短,出租方未必會繼續續租給現在的承租方,這意味著承租者的長期投資會存在一個概率無法收回,將可能使得企業的盈利較少甚至無法盈利[13],這會導致企業發展風險較高,不利于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地塊規模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交易契約期限,即地塊規模越大,交易契約期限越長。企業在交易過程中選擇地塊的規模越大,其對于地塊的專用性要求交易契約期限較長[20];地塊規模越大說明地塊的細碎化程度越低,這就降低了企業在轉入地塊過程中談判的交易成本[21],并進一步提高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有效性和效率。簽訂的合同是否公證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的契約期限。簽訂的合同公證是為了確保合同的切實履行所進行的一種法律審核行為,這對于企業來說是法律上保障。交易契約期限長的企業為了降低風險會選擇將合同進行公證,簽訂的合同公證有助于提升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規范化。辦理了《土地使用證》對交易契約期限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辦理《土地使用證》對于企業來說是一項權益的法律基本保障[22-23],為其在后續企業辦理相關營業證件減少了不確定性及履約風險、降低其未來的費用,因而企業更愿意簽訂長期契約。是否辦理《房屋產權證》在1%的水平上對交易契約期限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辦理了《房屋產權證》的集體建設用地不能輕易對其進行房屋或廠房進行改建,某種程度上限制企業的發展,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可能要面臨因更換廠房等帶來的投資成本、交易成本等,因而企業在選擇交易集體建設用地時更傾向于沒有辦理《房屋產權證》。承租人是否繳納廠房租金稅對交易契約期限呈現出顯著正向影響。廠房租金稅的繳納分為兩種,一種是由承租人繳納,另一種是由出租人繳納。調研發現,如果需要出租人繳納稅費,交易雙方簽訂的契約期限不會太長,因為出租方不愿意承擔過長時間的稅費壓力,增加經濟壓力,減少自己的經濟收入來源。

表1 變量設定、說明及賦值Tab.1 The setting, defnition and assignment of the variables
Probit模型(模型二)對交易場所選擇的計量結果表明,企業投入資本、企業年總產值、地塊規模、簽訂的合同是否公證、是否有中介介入、政府干預、是否辦理《房屋產權證》,這些變量均顯著影響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場所的選擇。
Probit模型(模型三)對交易對象選擇的計量結果表明,對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對象的選擇產生影響的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企業投入資本、地塊規模、地塊區位屬性、是否有中介介入、是否繳納廠房租金稅。在調研過程中發現,企業即使選擇和現在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持有者(個人、房東)進行交易,在辦理企業或工廠相關營業證件時,還需要和村集體之間簽訂一份合同,而且南海區已經建立了鎮、村兩個級別的農村集體資產交易平臺以規范化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根據科斯關于一體化的理論,南海區農村集體在1992年實行了土地股份制改革,農村集體已經成為了一體化的經濟實體,經濟體內部的交易要比與外部的交易成本低[24]。因此,本文認為選擇在村集體進行交易,與村集體進行交易、簽訂的合同進行公證可以減少市場交易費用,提高市場交易效率,能夠提高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質量。從模型結果可以發現,企業投入資本、地塊規模、簽訂的合同是否公證、政府干預這些變量都顯著正向影響企業交易場所的選擇,受教育程度、企業投入資本、地塊規模、地塊區位屬性正向顯著影響交易對象的選擇。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企業主傾向于選擇與村集體進行交易,受教育程度越高,市場規范化、程序規范化的意識更強,對未來風險預期的分析能力相對更強,因而為了降低交易費用、減少市場風險,會選擇的交易場所是村集體。對企業投入資本越多(企業規模越大)的企業選擇了與村集體交易,企業規模越大越重視長遠收益和風險的均衡,因而會選擇交易場所為村集體、交易對象為村集體,這也有利于有效建立和發展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地塊規模大企業面臨的資金回收風險更大,因而選擇與村集體進行交易以降低市場風險。簽訂的合同是否公證、政府干預表示的是交易行為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企業簽訂的合同進行公證、政府干預是降低風險、減少不確定性的有效方式。企業選擇交易場所時,傾向于在村集體對簽訂的合同進行公證,南海區村集體有相關負責人進行合同簽訂和見證,政府干預是政府相關人員監控和引導的過程,這些都是為了保證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的質量。而中介介入對交易場所和交易對象的影響均是顯著負向的,中介公司介入的交易一般發生在企業和個體之間,這是因為個體發布消息的途徑有限,只能通過依賴中介公司,而且這種第三方規制有助于出租方單位成本的減少[18]。是否辦理《房屋產權證》對交易場所選擇的影響方向和對交易契約期限的一致,均表現為顯著負向影響。即使村集體辦理《房屋產權證》,企業也愿意選擇村集體為交易場所,這是因為南海區實施股份合作制改革后,村集體相當于一個經濟實體,即使沒有辦理《房屋產權證》,村集體對于企業來說也更有保障;然而在選擇與個體進行交易時,企業更看重其辦理《房屋產權證》,調研過程中通過訪談發現企業這樣的選擇原因在于和個人討價還價的費用相對村集體要更低。承租方廠房租金稅的繳納顯著正向影響交易對象的選擇,即需要繳納廠房租金稅的交易對象為村集體進行,不需要繳納廠房租金稅的交易對象為個體房東。調研發現,與村集體的交易會嚴格按照交易程序進行,村集體不會承擔稅費的繳納,這也有利于市場的規范運行;另外,一些談判能力較強的企業在與個體房東進行交易時,會將繳納廠房租金稅的部分轉移給房東。
6 結論與政策含義
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早在20世紀80、90年代就出現了,經歷了從“隱形”、無序市場到“可見”、規范市場。本文根據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理論構建了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效率及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框架。土地市場效率取決于市場運行過程中的投入回報、供給側成本、需求側成本以及政府對市場干預、中介介入等多方面成本的集合。本文重點基于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特征,構建需求側市場交易影響因素模型,希望給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建設、規范提供一個思路。供給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個體)對于市場及交易費用的影響,市場中介、政府干預等主體對市場效率的影響尚待研究。此外,市場交易從三個維度分析:資產專用性、交易的不確定性、交易頻率,但不同交易方式選擇對交易費用的三個層面具有重要影響,具體的影響機理將在后續做深入研究。

表2 南海區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及其影響因素Tab.2 Th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factors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in Nanhai District
根據南海區區、鎮(街)、村三級交易平臺2010—2015年的市場交易數據總結出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發展特征: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供給方)的高度自組織性,降低了集體建設用地市場需求方和個人產權細碎化的締約和履約成本;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主體交易預期的長期性、締約的短期性,帶來市場較高的交易頻率;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客體是存量建設用地,而非增量,這使得價格有較大的上升空間;集體建設用地市場公開交易的歷史較短,相應市場監管、調控的制度滯后,市場交易波動性大。在總結出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特征的基礎上,采用398份對企業面對面的問卷調研數據,根據威廉姆森的市場交易費用理論,對南海區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果表明:資產專用性越強,企業越傾向于選擇長期契約、在交易平臺與村集體交易,驗證了威廉姆斯交易成本理論認為長期契約有利于給予投資者進行投資的信心[25];資產專用性越強,企業越傾向于選擇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交易以均衡投資和收益之間的風險,這一研究結果同時也表明集體經濟組織化水平是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很關鍵的因素。交易行為的不確定性越強,企業越傾向于選擇較短的契約期限,以降低企業對預期的不確定性;市場交易這樣一種“買進”戰略是存在風險的[25],因而企業傾向于選擇與村集體進行交易以減少市場的機會主義行為并達到降低市場交易風險的目的,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越強,企業將面臨越高的履約風險,重新締約可使其在全部過程中獲得正常的收益[14-17,25],因而集體建設用地市場能更有效地發展;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越強,企業越傾向于選擇與農村集體進行交易。集體經濟組織作為一個經濟實體能夠較好地保障市場的透明度,并規范化市場交易程度,制度的不確定性較弱,因而企業會面臨相對較低的交易成本,有助于提高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的有效性。這與威廉姆森闡述的“交易環境的變化無法預測使得擬定和實施的契約收益變得復雜;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交易費用的增加”交易費用理論一致[14-17]。
為了提高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發展的有效性,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明晰土地產權和房屋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和保障,在進行市場交易前,應對交易地塊和房屋進行確權登記頒證,并明確以出讓、出租方式取得的權利所對應的產權登記類別,以減少交易過程中的討價還價和交易費用。(2)為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規范化和合法化,可以將村集體設為集體建設用地的交易場所,即使是轉租也應該在村集體相關工作人員的監督和見證下進行交易,為集體建設用地的發展提供保障,降低市場交易的不確定性,從而達到市場發展的有效性。(3)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作為集體建設用地市場交易的第三方規制,為交易信息的發布、流通提供渠道,以減少承租方信息搜尋、手續規范等過程的交易費用,提高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的效率。
(References):
[1] 周小平,王情,谷曉坤,等. 基于 Logistic 回歸模型的農戶宅基地置換效果影響因素研究——以上海市嘉定區外岡鎮宅基地置換為例[J] . 資源科學,2015,37(2):258 - 264.
[2] 曹祺文,吳健生,全德,等. 基于空間自相關的區域農地變化驅動力研究——以珠三角地區為例[J] . 資源科學,2016,38(4):714 - 727.
[3] 葉玉瑤,張虹鷗,許學強,等. 珠江三角洲建設用地擴展與經濟增長模式的關系[J] . 地理研究,2011,30(12):2259 - 2271.
[4] 劉志佳,黃河清. 珠三角地區建設用地擴張與經濟、人口變化之間相互作用的時空演變特征分析[J] . 資源科學,2015,37(7):1394 - 1402.
[5] 鄧世文,閻小培. 珠江三角洲城鎮建設用地增長分析[J] . 經濟地理,1999,19(4):80 - 84.
[6] 許學強,李郵. 珠江三角洲城鎮化研究三十年[J] . 人文地理,2009,24(1):1 - 6.
[7] 葉玉瑤,張虹鷗,劉凱,等. 1988—2006 年珠三角建設用地擴展的空間差異分析[J] . 熱帶地理,2012,32(5): 493 - 500.
[8] 陳綺嫻,劉毅華. 土地產權視角下佛山市南海區建設用地擴張特征分析[J] . 廣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15(2):81 -88.
[9] 劉憲法. “南海模式”的形成、演變與結局[J] . 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土地卷)第八集,2011:77 - 141.
[10] Kung K S.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J]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30(2):395 - 414.
[11] Yao 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d Lease Market in Rural China[J] . Land Economics,2000,76(2):252 - 266.
[12] 金松青中國農村土地租賃市場的發展及其在土地使用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含義[J] . 經濟學(季刊),2004,3(4):1003 -1028.
[13] 田傳浩,方麗. 土地調整與農地租賃市場:基于數量和質量的雙重視角[J] . 經濟研究,2013,(2):110 - 121.
[14]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M] . New York and London: Free Press,1985.
[15] Williamson O E.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J]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1,36(2):269 - 296.
[16] 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2):233 - 261.
[17] Williamson O E.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8] 羅必良,李尚蒲. 農地流轉的交易費用:威廉姆森分析范式及廣東的證據[J] . 農業經濟問題,2010,(12):30 - 40.
[19] 陳強. 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第二版)[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20] 羅必良,何一鳴. 博弈均衡、要素品質與契約選擇——關于佃農理論的進一步思考[J] . 經濟研究,2015,(8):162 - 174.
[21] 何欣,蔣濤,郭良燕,等. 中國農地流轉市場的發展與農戶流轉農地行為研究——基于2013—2015年29省的農戶調查數據[J] . 管理世界,2016,(6):13 - 23.
[22] 葉劍平,豐雷,蔣妍,等. 2008年中國農村土地使用權調查研究——17省份調查結果及政策建議[J] . 管理世界,2010,(1):64 -73.
[23] 馬賢磊,仇童偉,錢忠好. 農地產權安全性與農地流轉市場的農戶參與——基于江蘇、湖北、廣西、黑龍江四省(區)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 . 中國農村經濟,2015,(2):22 - 37.
[24]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 Economican. s,1937,(4):386 - 405.
(本文責編:戴晴)
Econometric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and Its Impact Fac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872 Market Transaction Data and 398 Questionnaire Data in Nanhai District, Guangdong Province
ZHANG Ting1, ZHANG An-lu1, DENG Song-lin2, HU Yue3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Jiangxi Province Water Conservancy Planning and Designing Institute, Nanchang 330029, China; 3.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208,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in Nanhai District by using the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ransfer data from 2010—2015, to explorethe impact factors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by utilizing 398 questionnaire data, and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The methods of Tobit model and the binary Probit model were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market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were as follows: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howed the high degree of self-organization; the frequency of market transaction was high; the market object was the existing construction land; the market fluctuations were severe. 2)Assets specificity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market contract period and trade object, as Williamson’s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considered that long-term contract is conducive to give confidence to investors; the self-organized level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was the key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3)As the uncertainty of transactions became stronger, firms tended to choose a short-term con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xpected risk; market transactions had “buy-in” strategic risk, therefore, firms tended to transact with the village collective with the aim of reducing the market transactions risk, thereb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ket transactions. In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firstly, well delineating property rights of land and house is the premise and the guarantee; secondly,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third party of regulating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land economy;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market characteristics; impact factors; market efficiency; econometric research
F301.1
A
1001-8158(2016)11-0022-10
10.11994/zgtdkx.20161207.152648
2016-09-07;
2016-11-08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4JZD00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373095);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71573101);中央高校科研基本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2662016PY078)。
張婷(1988-),女,江西吉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經濟學。E-mail: zhangting19880909@163.com
張安錄(1964-),男,湖北麻城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經濟學、土地可持續利用。E-mail: zhanganlu@mail.hza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