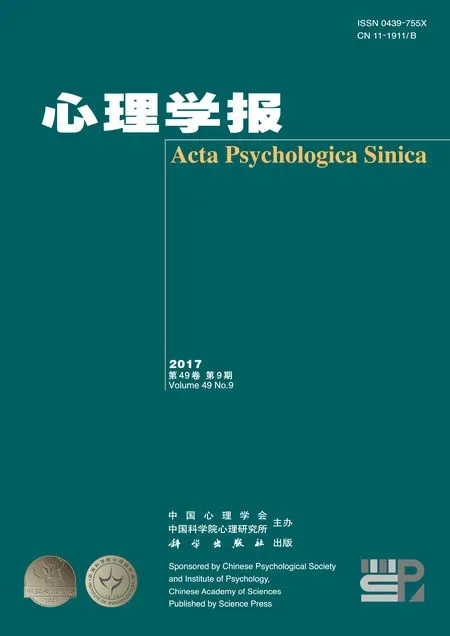謙遜領導的影響機制和效應:一個人際關系視角*
毛江華 廖建橋 韓 翼 劉文興
(1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武漢 430073)(2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武漢 430074)
1 引言
謙遜(humility)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從謙字的構成上來說“謙”由“言”和“兼”構成,寓意為說話要兼顧自己和他人的利益,由此產生謙遜的概念。自上古母系社會開始,中國就有尊重女性謙下、好靜等特質的習慣和傳統。而隨著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等流派對謙遜內涵地認可,謙遜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道德規范。從古到今,人們對于謙遜的鼓勵和推崇遍布于社會的每個角落,“孔融讓梨”、“虛懷若谷”等典故也被世人不斷地傳頌。然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文化沖突以及全球競爭的加劇使得個體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多,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程度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突出地自我展示并開始質疑謙遜的有效性(Gu,1990;Chen,1993)。
在組織領域中,這種對謙遜的質疑表現得尤為強烈,其中爭議的焦點則在謙遜領導的有效性方面。一方面,部分學者基于傳統領導的視角認為有效的領導應該是強勢的(例如威權領導,Farh &Cheng,2000)、意志堅定的以及無所不知的(Meindl,Ehrlich,&Dukerich,1985),其應該能獨立果斷地處理企業的重大決策,并展現出高度的魅力以帶領企業走向卓越(例如變革型領導)。他們認為,領導表現謙遜不僅不能帶來積極的效應,反而讓下屬產生領導軟弱的認知,進而導致其對領導的決策和命令產生質疑和抵抗(Tangney,2000)。另一方面,學者認為隨著知識經濟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知識爆炸和能力多元化使得領導個人知識和能力的局限成為了阻礙企業快速發展的柵欄(Weick,2001)。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管理者需要通過表現謙遜來發揮員工的優勢,促進團隊的融合,從而保證企業能很好地應對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Vera &Rodriguez-Lopez,2004)。2014年央視《東方時空》對 15000名員工的調查發現,38.2%的員工喜歡溫和謙遜的領導1《生命時報》2014年07月15日第十版,http://paper.people.com.cn/smsb/html/2014-07/15/content_1452125.htm。由此可見,目前謙遜領導的有效性在理論和實務界均存在爭議,而解決這一爭論一方面可以回答新時代背景下領導如何才能產生積極效應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能解決中國傳統謙遜文化在現代環境下的適應性和有效性問題。
從現有對于謙遜領導的研究來看,謙遜領導在組織中的有效性得到了初步地驗證。研究發現,在個體層面,謙遜領導能提高下屬的績效(Owens &Hekman,2012;Owens,Walker,&Waldman,2015)、滿意度(Owens,Johnson,&Mitchell,2013),并促進下屬組織認同(曲慶,何志嬋,梅哲群,2013)、工作投入(Owens et al.,2013;唐漢瑛,龍立榮,周如意,2015)以及創造力(雷星暉,單志汶,蘇濤永,楊元飛,2015)等。在團隊層面,謙遜領導通過構建群體的謙遜氛圍可以促進團隊績效的提升(Owens &Hekman,2016)。此外,在組織層面,謙遜CEO也能通過對高管團隊的授權和整合提升企業績效(Ou et al.,2014)。盡管現有研究部分驗證了謙遜領導的有效性,但細致梳理可以發現,這些研究僅關注了謙遜領導對下屬角色內行為和績效的影響效應,而對謙遜領導與下屬角色外行為(例如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尚未給予關注。組織公民行為屬于員工的周邊績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其與員工任務績效存在顯著的差異和不同的觸發條件和機制。例如,員工角色外行為的產生可能更多地需要員工有較強的內在動機(Borman &Motowidlo,2014)。以往謙遜領導對員工角色內行為影響效應和機制的結論可能并不適用于解釋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考慮到員工組織公民行為對于員工自身責任履行、團隊合作以及組織績效的重要性(Farmer,Van Dyne,&Kamdar,2015),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效應對于進一步揭示謙遜領導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以往在探究領導對下屬態度和行為的影響過程中,關系視角是一個比較普遍的視角(Erdogan,Bauer,&Walter,2015)。然而,現有從關系視角探究領導對下屬的影響研究中,大部分關注于領導與下屬的交換關系,例如領導成員交換關系,而對領導與下屬之間其他形式的關系關注較少。Clark和Mills (1993)指出,人際交往過程中存在兩種關系模式,交換關系(exchange relationship)和共享關系(communal relationship)。交換關系注重公平,關系雙方希望在付出之后有所回報。共享關系注重對方的需求,關系雙方在付出之后不期望回報。現有的研究大多數關注領導與下屬之間交換關系,而對領導是否能促進下屬共享關系的形成仍沒有得到理論上的解答。相比于其他通過利益(例如交易型領導)、能量和理想(例如變革型領導)來激勵下屬的領導方式,謙遜領導更多地采用一種“安靜”的方式通過喚起下屬的發展過程等來從內心吸引下屬建立共享關系(Owens &Hekman,2012)。因此,從共享關系模式而不是交換關系模式來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態度和行為的影響能更好地揭示謙遜領導的影響效應。在本研究中,本文將結合人際吸引的特質吸引視角探究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對下屬組織公民行為影響過程中的作用。
在人際關系視角下的人際吸引過程中,關系雙方是否被吸引不僅取決于一方的特質和行為(特質論,Barrick,Mount,&Li,2013),還取決于另一方對這種特質和行為的解讀(情境論,Huston,2013)。由于謙遜是一種美德,謙遜的領導能從特質上吸引下屬,但在中國情境下,由于謙遜是一種社會規范,下屬難以通過領導的謙遜行為來判斷其真實的謙遜水平(Bond,Leung,&Wan,1982),因此謙遜領導對下屬的人際吸引受到下屬對領導謙遜解讀的影響。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inferred motives for leader humility)指的是從下屬角度去歸因領導表現謙遜的動機,當員工歸因領導謙遜為不同動機時,謙遜領導對下屬的人際吸引力將產生變化(Lam,Huang,&Snape,2007;Owens &Hekman,2016)。以往研究在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影響時,僅從領導中心論(leader-centric)的范式將下屬作為領導影響力的接受者,較少考慮下屬對領導行為的解讀。本文在揭示謙遜領導的影響效應時,將進一步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影響過程中的調節機制,進一步豐富謙遜領導的有效性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和貢獻有以下三點:首先,本研究是第一個對比交換關系和共享關系兩種關系模式在領導和下屬關系中的差異和效應,打破了以往研究在探討領導下屬關系時僅關注交換關系的研究局限,進一步豐富領導理論以及領導成員交換理論。其次,本研究從特質吸引視角揭示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影響機制和效應,為解釋謙遜領導的有效性提供新的視角。最后,本研究整合人際關系中的特質吸引論和情境行為論,第一個以下屬為中心(follower-centric)從下屬對領導動機歸因的視角揭示謙遜領導有效性的邊界條件,從而為謙遜領導的有效性做出貢獻。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圖見圖1。

圖1 本文的研究模型
2 研究理論與假設
2.1 謙遜領導的內涵
在組織領域中,謙遜領導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其原因在于傳統領導被認為是強權、強勢的,而領導表現謙遜反而被看作是一種軟弱(Ensari &Murphy,2003)。隨著越來越多學者對謙遜內涵的研究和探索,謙遜領導在現代日益動蕩的市場環境下逐漸得到認可和推崇,Tangney (2000)等學者先后指出謙遜領導是知識經濟時代中企業成功的關鍵。2012年,Owens和Hekman (2012)在前人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上通過質化研究方式揭示了謙遜領導的三個關鍵行為:承認個人的不足,放大下屬的優勢和貢獻以及可教性。之后,Owens,Johnson和Mitchell (2013)進一步對謙遜領導的概念進行了定量地研究,并提出了謙遜領導的三個維度:清晰的自我認識(willingness to view oneself accurately),欣 賞 他 人 (appreciation of others’ strengths and contributions)以及可教性(teachability)。清晰的自我認識指的是有能力和意愿來客觀地評價自己,形成一個精確的、非防衛性(non-defensive)的自我認識(Tangney,2000;Exline,Baumeister,Bushman,Campbell,&Finkel,2004)。欣賞他人指的是贊賞他人的價值和貢獻(Tangney,2000),承認他人的優勢而不覺得有威脅(Exline et al.,2004)。可教性指的是對新想法、新觀點、建議等保持開放性,并虛心向他人請教(Tangney,2000)。此外,在謙遜領導的內涵方面,其他學者也提出了補充性的觀點,例如,Nielsen,Marrone和Ferraro (2013)指出謙遜領導具有一種關系認同導向(relational identity orientation),其更關注他人的福利和需求。
謙遜領導與其他幾種以下屬為中心的領導風格具有一定的區分性(Owens &Hekman,2012),例如仆人型領導、參與型領導以及分享型領導。首先,謙遜領導與仆人型領導的主要差異在于:(1)謙遜領導讓下屬知道能成為什么,而仆人型領導教導下屬怎么服務他人;(2)謙遜領導能通過提高員工的心理安全、允許領導與下屬之間的角色互換等措施幫助員工消除不確定性(Owens &Hekman,2012)。其次,謙遜領導與參與型領導的差異在于謙遜領導通過關注領導與下屬之間的關系或互動來促進下屬績效的提升,而參與型領導強調的是讓員工參與到決策制定過程(Owens &Hekman,2012)。最后,謙遜領導與分享型領導的區別在于,謙遜領導是一種垂直的領導方式而分享型領導是一種水平的領導方式(Owens &Hekman,2012)。此外,謙遜領導也與發展型領導具有區分性,例如前者關注對員工心理因素的促進和激發,而后者更多地關注員工的職業發展(Rafferty &Griffin,2006)。
隨著研究的開展,謙遜領導的有效性逐漸在各個研究層面得到支持。例如,在組織層面,謙遜領導被認為能提升組織內部運營的流暢性,激發持續性的變革(Owens &Hekman,2012)。同時,實證研究也發現謙遜 CEO有助于提高高管團隊的一體化程度和授權氛圍,進而提高中層管理人員的績效(Ou et al.,2014)。此外,近期的研究也發現謙遜領導能在團隊中營造一種集體謙遜(collective humility),從而促使團隊形成一種集體促進性焦點,進而提升團隊績效(Owens &Hekman,2016)。謙遜領導有效性的主要發現集中在個體層面,研究發現謙遜領導能對員工產生較多方面的積極效應,包括提升員工滿意度、工作投入(Owens et al.,2013;唐漢瑛等,2015)、組織認同(曲慶等,2013),激發員工的創造力(雷星暉等,2015)以及強化員工的工作績效等(Owens et al.,2015)。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謙遜領導對下屬影響效應的研究主要關注于下屬的角色內行為,如工作投入、績效(Owens et al.,2015)等,謙遜領導對員工角色外行為的影響效應還不明確。同時,雖然我國具有悠久的謙遜文化歷史,但目前國內對于謙遜領導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另外,我國學者在對謙遜領導進行翻譯時,大部分采用將“humility”翻譯為“謙卑”。在詞典中,“謙遜”、“謙卑”與“謙虛”存在互相定義的情況,三者都表示“不浮夸、低調、不自高自大”之意。然而,“遜”在詞典中有“不如、比不上”和“辭讓、退讓”的意思,消極含義較少。而“卑”則有“低下、低劣”的意思,具有更多的負面含義。結合Owens和Hekman (2012)最初對謙遜領導的定義和內涵分析,本研究將以“謙遜領導”作為“leader humility”的中文翻譯。
2.2 謙遜領導,交換關系和共享關系
人際關系是人與人在相互交往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心理關系,是人社會屬性的表現方式和實現途徑(Arnold &Boggs,2015)。人際吸引指的是個體之間在主觀上感受到的時間或空間、直接或間接、現實或希望的相互依存關系,是人際關系中的具體因素,指的是個體感情上的相互喜歡和親和(Huston,2013)。在人際吸引的研究領域中,學者主要遵循兩種研究視角,一種是基于性格特質觀點的特質論(Barrick et al.,2013),另一種是基于社會互動觀點的情境論(Wrzus,H?nel,Wagner,&Neyer,2013)。特質論的人際吸引學者認為,他人的特質是影響個體是否與之建立友好人際關系的重要影響因素(Barrick et al.,2013)。例如,Malouff,Schutte和Thorsteinsson (2014)的元分析發現,特質情緒智力與戀愛關系滿意度正相關(r=0.32)。情境論的學者認為,人在不同情境下存在行為的不一致性,人際吸引的產生是個體對他人、自己以及周圍環境的社會信息進行復雜加工而成(Wrzus et al.,2013)。
Clark和Mills (1993)指出,人際吸引之后個體會形成兩種模式的關系,交換關系和共享關系。交換關系注重關系雙方的公平,關系一方幫助對方之后,希望對方立即有所回報。一旦對方沒有給予及時的回報,個體就會產生被剝削的感覺。在交換關系中,雙方都比較關注對方所做的貢獻,一般不會因為能夠幫助對方而感到心情愉快。相對于交換關系,共享關系更注重對方的需求,個體在幫助對方之后,并不期望對方立即有所回報。在共享關系中,個體會因為能夠幫助對方而感到心情愉快,例如戀人關系(強共享)和幫助陌生人(弱共享)等。對于共享關系,Mills和 Clark (1982)進一步指出,所有人都可能處于共享關系中的一方,如果被吸引,即使是陌生人也愿意無償的去幫助他人。
謙遜領導與下屬關系的建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一方面,基于人際吸引視角下的互惠吸引律(mutually beneficial and attractive rule)(Luo &Snider,2009),當他人滿足了個體在心理上的榮譽感、價值感時,個體更容易通過互惠機制與他人保持友好親密關系。謙遜領導欣賞下屬的優勢和貢獻,下屬會感受到榮譽感和受重視感從而與謙遜領導建立較高的交換關系。另一方面,人際吸引的特質論視角認為,特質是個體相對穩定的基本特性,具有較高的情境一致性,是個體吸引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Barrick et al.,2013)。在謙遜領導的定義中,Owens等(2013)認為領導的謙遜行為是內在謙遜水平的一種反映,其采用的是特質論的領導定義方式。謙遜一直以來在中西方都被認為是一種美德(胡金生,黃希庭,2006;Ou et al.,2014)。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認為,美德代表了兩個極端表現的中間區域,而謙遜正好代表了兩個負面極端自大和自卑的中間區域(Vera &Rodriguez-Lopez,2004)。結合人際吸引的特質論和謙遜的美德屬性,當領導表現謙遜時,下屬容易被吸引而產生較高共享關系。
關系親近性(relational closeness)是一個描述個體對某種人際關系感興趣程度的概念,其指的是個體對他人情感親和性(emotional affinity)、親密性(intimacy)以及心理粘性(psychological bonding)的主觀體驗(Vangelisti &Caughlin,1997)。關系親近性更多地是描述關系一方被另一方所吸引而代表著一種共享關系的建立,其與領導成員交換(LMX)的差異在于前者更強調單方面的喜歡和親近,而后者強調關系雙方在付出和收益方面的平等性(Clark &Mills,1993)。本研究認為謙遜領導不僅能與下屬建立交換關系,也能通過謙遜特質的吸引提高下屬的關系親近性并與下屬建立共享關系。謙遜領導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促進下屬的關系親近性:首先,謙遜領導清晰的自我認識能讓下屬感覺到領導的真誠,Anderson (1968)基于555個描述特質的詞語研究發現,真誠是影響人際吸引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領導通過謙遜所表現出來的真誠能更好地提高下屬的關系親近性從而建立親密的關系;其次,謙遜領導能欣賞和肯定下屬的優勢和貢獻,不將下屬的優勢作為對自己的威脅,并虛心向他人請教學習(Owens et al.,2013)。Nielsen 等(2013)指出,謙遜領導具有關系認同導向(relational identity orientation),這樣的領導更關心下屬的福利和需求。人際吸引視角下的互補吸引律(mutually complementary and attract rule)指出,關系雙方的個性、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途徑成為互補關系時,會產生強烈的吸引力(Maxwell et al.,2012)。因此,謙遜領導通過對下屬需求的滿足和福利的關注會使下屬感覺到自己所缺少的內容得到了領導的補充,從而被謙遜領導所吸引,產生更高的關系親近性。以往的研究表明,謙遜領導會提升下屬的工作滿意度(Owens et al.,2013)和感知領導的社會化魅力(Nielsen,Marrone,&Slay,2010),這些都可能促使員工與領導保持較好的人際關系。基于上述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當控制了領導成員交換關系后,謙遜領導與下屬關系親近性正相關。
2.3 謙遜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指的是在組織的正式報酬體系中沒有規定但對組織有益的員工自主行為(Bolino,Hsiung,Harvey,&LePine,2015)。根據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是員工的角色外行為,其并不在組織的賞罰標準范圍內,并對組織整體的績效具有積極作用。Williams和Anderson (1991)按受益對象將組織公民行為分為指向個體的組織公民行為(OCB-I)和指向組織的組織公民行為(OCB-O)。其中,幫助行為是比較典型的指向個體的組織公民行為,其指的是個體體諒他人并且提供幫助的人際互動行為,有利于與他人建立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Smith,Organ,&Near,1983)。建言是比較典型的指向組織的組織公民行為,其指的是組織內員工為了改善現狀而主動表達建設性意見或指出組織中存在問題或措施的人際溝通行為(Van Dyne &LePine,1998)。由于組織公民行為在組織中的重要性,以往的學者不斷從各個方面探究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因素(Zhang,Huai,&Xie,2015)。
從以往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來看,動機(想不想做,例如內在動機,Piccolo &Colquitt,2006)和資源(有沒有能力做,例如認知和社會資源,Kim,Van Dyne,Kamdar,&Johnson,2013)是影響員工實施組織公民行為的兩個重要因素。謙遜領導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領導方式(bottom-up leadership approach),其更關注于員工的福利和需求(Oc,Bashshur,Daniels,Greguras,&Diefendorff,2015)。結合謙遜領導的內涵,本研究認為謙遜領導將正向促進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謙遜領導能提高員工實施組織公民行為的動機。謙遜領導通過清晰的自我認識與對他人的欣賞,能和下屬建立良好的共享關系(Clark &Mills,1993),即下屬愿意不考慮關系得失地做一些有利于領導的事情,這些事情既包括努力提供建議(即建言),也包括幫助同事更好地適應工作(即幫助),因為同事的績效也是領導績效的考量之一。同時,Ainsworth和Bowlby (1991)的研究發現,在依戀的關系中,雙方會出現類似的行為模式。當下屬對謙遜領導具有高的親近感后,下屬會更多地為領導著想,采用領導的行為模式來更多的提供建議和幫助他人,從而幫助領導更好地進行管理。其次,謙遜領導能增加下屬的心理資源。謙遜領導對下屬的欣賞能使下屬認識到自己的優勢,謙遜領導虛心向他人求教也能促進下屬內在效能和自尊的增加(唐漢瑛等,2015),使得下屬相信自己有能力處理好各種事情,從而增加了下屬實施組織公民行為的心理資源;最后,謙遜領導能增加員工的外部資源。具有關系認同導向的謙遜領導更多地關心員工的福利和需求(Nielsen et al.,2013),愿意并主動給下屬提供必要的資源支持,從而使下屬有更多的外部資源來履行自身角色內的工作和角色外的公民行為。綜上所述,謙遜領導將通過增加員工動機和資源兩個方面促進下屬的組織公民行為。
具體來講,對于建言而言,由于謙遜領導虛心向他人求教,對新想法和意見保持足夠的開放性,因此下屬有更多的動機和更高的心理安全來進行建言行為。而對于幫助行為來說,謙遜領導通過與下屬保持較好關系并肯定和贊賞下屬的優勢能促使下屬具有動機和資源去幫助其他員工。在謙遜領導以往的研究中,學者發現謙遜領導能正向促進員工的工作滿意度(Owens et al.,2013)和組織認同(曲慶等,2013),而這兩種員工態度均被發現是組織公民行為的有效預測因素(Zhang &Chen,2013)。基于以上推理和實證研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謙遜領導正向促進下屬的組織公民行為,包括建言(2a)和幫助行為(2b)。
在人際關系領域中,人際吸引所產生的喜歡、依戀等關系的建立會改變關系雙方以往的態度和行為(Eastwick,Luchies,Finkel,&Hunt,2014)。在上述謙遜領導對下屬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過程推導中,本研究從動機和資源兩個關鍵因素進行分析。同樣的,從人際關系視角來看,本研究認為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和下屬組織公民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而這種中介作用的形成也可以從動機和資源兩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在動機方面,當謙遜領導通過自身獨特的品質和關系認同導向吸引下屬產生了親密關系時(假設 1),根據自我驗證理論(self-verification theory),個體會從不斷尋找線索或采取行動來證實自我觀念的正確性(Xu,Huang,&Robinson,2015),其就會通過增加建言和幫助行為使領導以及領導所管理的團隊呈現出更好的績效狀態,從而通過證明自己喜歡或依戀(關系親密)的對象是一個在社會比較中具有優勢的個體以滿足對自我選擇的驗證。同時,當謙遜領導吸引下屬建立良好的共享關系后,下屬會愿意不考慮得失地做一些有利于領導的事情。因此,當謙遜領導增加了下屬的關系親近性后,下屬組織公民行為的動機會增加。其次,在資源方面,根據自我擴張理論(self-expansion theory,Aron &Aron,1997),個體會將親密他人的資源、觀念以及認同納入到自我從而實現對自我概念地成長(Graham &Harf,2015)。Aron和 Aron (1997)還指出,關系親近性是關系雙方將對方納入自我(inclusion of other in self)的最主要因素。因此,當謙遜領導與下屬建立了較好的關系親近性之后,下屬會逐漸將領導的資源、觀念以及認同當做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從而有更高的自我效能和資源來實施組織公民行為。綜上所述,從動機和資源兩個角度的分析,謙遜領導會通過提高與下屬的關系親近性從而增加下屬的組織公民行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當控制了領導成員交換關系之后,關系親近性仍中介謙遜領導與下屬組織公民行為建言(3a)與幫助行為(3b)之間的關系。
2.4 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的調節作用
盡管Owens,Johnson和Mitchell (2013)采用領導特質方式定義謙遜領導行為,但 Owens,Walker和Waldman (2015)的研究也指出,領導謙遜的特質是“可塑造的”,領導可以選擇表達謙遜的情境。同時,Owens和Hekman (2012)也指出,謙遜在組織中也可能被當作自利的工具(instrumentally and with self-interest)。由此可見,領導可以對不同的下屬表現不同程度的謙遜。結合中國的謙遜文化情境,在組織中,領導表現謙遜有時候并不是因為其具有謙遜的特質。Bond等(1982)認為,在中國,個體表現謙遜有時候被視為一種印象管理策略,因為當謙遜這種道德成為社會規范后,就難以通過外在表現來推測內在真實道德水平。具體而言,在研究中國人的自謙時,胡金生(2007)將自謙分為“實性”和“虛性”兩種,“實性”自謙與西方定義的謙遜相一致,體現的是個體內在的謙遜水平,“虛性”自謙則強調個體對他人的印象管理。之后,基于對中國大學生自謙的研究,胡金生和黃希庭(2009)發現中國人在表現謙遜時存在防御性、自我發展和提升形象三種動機。因此,在中國情境下,領導表現謙遜存在多種動機,對不同的下屬可能表現出不同程度以及基于不同動機的謙遜。
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是從下屬角度去歸因領導表現謙遜的動機,其可以分為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和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兩種(Lam et al.,2007)。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指的是下屬認為領導表現謙遜是成就、績效導向的(achievement-focused),是為了實現更高的工作任務目標(Owens &Hekman,2012;Owens et al.,2013),下屬會更多的將這種動機的領導謙遜認為是有幫助的。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指的是下屬認為領導通過表現謙遜來營造較好的社會形象和領導聲望(胡金生,黃希庭,2009),下屬會更多的將這種動機的領導謙遜視為是不真誠的、虛假的。根據特質論的人際吸引研究結果來看,Anderson (1968)發現,人際吸引中最受喜愛的品質為真誠和誠實,最不受喜愛的品質為說謊和假裝。因此,本研究認為當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為績效改進時,領導的謙遜行為會被感知是匹配的,從而增加了對下屬的人際吸引力,下屬的關系親近性會隨著增加。同時,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自我驗證動機會促使下屬去尋求領導關注績效、追求卓越的其他相關線索(Xu et al.,2015),從而進一步增加對領導的親近性。而當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為印象管理時,領導的謙遜行為被認為是虛假的、偽裝的,對下屬的人際吸引力會下降,下屬的關系親近性也會隨著下降。同樣的,在這種情況下,下屬的自我驗證動機會去尋找領導虛偽、偽裝等其他線索(Xu et al.,2015),從而進一步降低對領導的關系親近性。以往類似的研究也暗示出相同的結果,例如Lam等(2007)在研究領導對下屬反饋尋求行為的歸因時發現,當領導認為下屬是為了績效改進時,反饋尋求行為對領導成員交換關系的正向影響會得到增強,當領導認為下屬是為了印象管理時,反饋尋求行為對領導成員交換關系的正向影響會得到削弱。基于以上推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4a:當下屬更多的歸因領導謙遜動機為績效改進時,謙遜領導與關系親近性之間的正向關系會得到增強。
假設4b:當下屬更多的歸因領導謙遜動機為印象管理時,謙遜領導與關系親近性之間的正向關系會得到減弱。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和調查過程
為保證研究設計的嚴謹性,本研究采用多時段、多數據來源的數據調研方式。本研究選取湖北省武漢市和襄陽市的 13家發展成熟、規范的企業作為樣本來源,其中,10家為上市公司。在這13家企業中,6家為制造企業,3家為房地產企業,4家為高科技軟件企業。本研究調研了這 13家企業中的72個團隊,其中科研團隊21個(29%),生產團隊30個(42%),銷售團隊13個(18%),職能部門團隊8個(11%)。每個團隊由一名團隊領導和若干團隊成員組成,72個團隊的平均成員為4.91個。為避免同源誤差(common method bias),本研究采用領導?下屬匹配的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實證研究。同時,調研過程分為兩個時段進行。
在第一階段,下屬報告與領導的接觸頻率、共事時間,并評價領導的謙遜程度,同時評價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7周之后,在第二階段,下屬評價對領導的關系親近性和領導成員交換關系,領導評價下屬的建言和幫助行為。為保證兩階段和上下級匹配的準確性,我們采用填寫姓名的方式進行匹配,并運用一些補償措施消除被調研人員的其他顧慮。首先,我們在調研過程中隔離了上級和下級,在發放問卷的過程中,本文作者之一直接到工作現場將問卷發給相應的領導和員工,兩者在不同位置填寫問卷,40分鐘后,研究者從問卷填寫者手中直接回收問卷。其次,我們給每位參與人員編制了一個編號,在數據錄入時僅用編號代替人員姓名。最后,我們強調了調研活動的保密性和科研用途。我們為每個問卷填寫者提供一個簡單描述調研目的的介紹信和一份價值5元的小禮品。介紹信中同時還指出了本次調研活動的匿名性和保密性。
在第一階段中,本研究共發放 72個團隊領導和350名團隊員工。在第二階段,本研究總共回收具有有效匹配效果的團隊領導64份,團隊員工295份,團隊領導的兩階段回收率為 89%,團隊成員的兩階段回收率為84%,平均一個領導匹配4.61個下屬。在領導方面,女性占 48%,男性占 52%,平均年齡為39歲(SD=8.74),平均在企業中工作9.9年(SD=9.4)。在員工方面,女性占56%,男性占44%,平均年齡為31.6歲(SD=8.38),平均在企業中工作5.4年(SD=6.9)。本研究采用單因素ANOVA對領導謙遜和關系親近性在行業和部門間的差異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領導謙遜在不同行業(F=1.24,p>0.05),和不同部門(F=0.68,p>0.05)中沒有顯著差異。同樣的,關系親近性在行業(F=2.00,p>0.05)和部門(F=1.03,p>0.05)間也不存在顯著差異。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來自于國外較為成熟的測量方式,為保證其在中國情境下的效度,本研究采用標準的翻譯?回譯程序對英文量表進行處理,以保證量表題項在語義上的完整性。
謙遜領導:我們采用Owens等(2013)所編制的3個維度9個題項量表。此量表已經被學者在中國情境下使用(曲慶等,2013;唐漢瑛等,2015;雷星暉等,2015),顯示出良好的信度。其中,清晰的自我認識維度3個題項,欣賞他人維度3個題項,可教性維度3個題項。量表的總體信度為0.95。題項包括“我的領導承認他人有超過自己的知識和能力”、“我的領導經常對他人的長處表示贊賞”以及“我的領導愿意傾聽他人的想法和建議”等。采用李克特7點制量表進行評價,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關系親近性:我們采用 Vangelisti和 Caughlin(1997)開發的7個題項量表。該量表的信度為0.87。量表題項包括“我與領導非常親近”、“我經常與領導交流私人事情”以及“我喜歡和領導一起工作”等。采用李克特7點制量表進行評價,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領導成員交換:我們采用 Scandura和 Graen(1984)開發的LMX-7量表。Bauer和Green (1996)對 LMX-7量表中的一個題項進行了改編,我們研究中僅采用了Scandura和Graen (1984)量表中余下的6個題項,這個量表已經在中國情境下得到了檢驗(Schaubroeck &Lam,2002)。該量表的信度為0.82。舉例題項包括“我的領導經常運用他/她的權力來幫助我解決工作上的問題”以及“我的領導認可我在工作上的潛力”。采用李克特 7點制量表進行評價,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建言行為:我們采用Van Dyne和LePine (1998)開發的6個題項量表。該量表的信度為0.97。采用配對的方式由領導評價下屬的建言行為出現的頻率,采用李克特7點制量表進行評價,1表示從不做,7表示總是做。量表題項包括“該員工經常為了能更有效的開展工作而提供建議”、“該員工經常提供建議來解決工作相關的問題”以及“該員工經常對工作項目提供改進意見以使項目更好”等。
幫助行為:我們采用 Smith等(1983)開發的 6個題項量表。該量表的信度為0.92。采用配對的方式由領導評價下屬的幫助行為出現的頻率,采用李克特7點制量表進行評價,1表示從不,7表示經常。量表題項包括“該員工幫助缺勤同事完成工作”、“該員工主動向新員工介紹組織和工作情況”以及“該員工幫助工作任務重的同事完成工作”等。
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和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采用Lam等(2007)的績效改進動機歸因和印象管理動機歸因量表,兩個量表分別由 7個題項進行測量。這兩個量表最早被用于測量領導對下屬行為的歸因,本研究在保留原意的情況下轉變為下屬對領導動機的歸因。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測量在問卷調查時緊跟著謙遜領導的測量,下屬被要求回答“你認為之前問題中領導表現出來的行為動機是什么?”其中,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題項包括“希望能更好的履行他/她的職責”、“希望增加我們對他/她的信任”以及“希望幫助我們提高績效”等。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題項包括“希望得到我的關注”、“渴望提升他/她的個人形象(使我相信他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以及“因為形勢所需”等。采用李克特7點制量表進行評價,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本研究對這兩個量表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數據較好的提取出對應的兩個成分,共解釋了總方差的 69%,表明這個量表在中西方情境下并沒有顯著性的差異,因此可以用來測量我國員工對領導謙遜的動機歸因。在信度檢驗中,兩個量表的信度值分別為0.89和0.83,顯示出較好的信度。
控制變量:以往學者在研究人際吸引時發現時空接近性(proximity/propinquity effect)會影響交往雙方的關系(McAllister,1995)。本文從人際關系視角出發時,將對領導與下屬人際接觸頻率以及接觸時間進行控制。因此,為更好的驗證謙遜領導在人際關系中的作用,本文將控制領導成員接觸頻率以及領導?下屬共事時間兩個變量。領導成員接觸頻率采用McAllister (1995)的3點制題項量表,下屬被要求回答“您與上級(領導)的交流互動頻率”,其中1代表每天,2代表每周,3代表每月。領導?下屬共事時間由下屬報告與領導共事的客觀時間(單位為年)。
3.3 研究方法
在以往對謙遜領導的研究中,學者均采用將謙遜領導作為團隊層變量,其原因主要為 Owens等(2013)在定義謙遜領導時,將謙遜作為領導特質的一種行為表現,認為“謙遜是一種在社會情境下表現出的個人特質,可以采用行為視角進行特質研究”。本文將遵循以往研究的范式,將謙遜領導作為團隊層變量進行研究。在計算謙遜領導組間組內一致性相應指標后(rwg和 ICC),本研究將謙遜領導聚合到團隊層。通過計算,謙遜領導的 rwg值為 0.88,ICC1值為0.44,ICC2值為0.79,均大于Jame (1982)等人提出的臨界值,因此,謙遜領導符合聚合條件,可以聚合成團隊層變量。本研究將探究團隊層面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影響,在處理跨層數據時,本研究采用HLM 7.0軟件進行處理,采用多層線性回歸對數據進行處理。同時,在驗證中介效應時,本研究將使用 Preacher和 Hayes (2004)的 SPSS syntax進行間接效應的Bootstrap檢驗。
4 研究結果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和信效度檢驗
團隊層和個體層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以及各個量表信度見表1。從表1中可以看出,謙遜領導與關系親近性正相關(r=0.49,p<0.001),與建言正相關(r=0.24,p<0.001),與幫助行為正相關(r=0.37,p<0.001)。關系親近性與建言正相關(r=0.35,p<0.001),與幫助行為正相關(r=0.38,p<0.001)。
在正式進行假設檢驗之前,本研究首先運用驗證性因子分析對變量進行區分效度檢驗。根據Zhang和Bartol (2010)的方法,本研究將謙遜領導、關系親近性、領導成員交換、建言、幫助行為、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以及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的測量題項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從表2中可以看出,7因子模型相比于其他模型來說具有更好的模型擬合程度(χ2=2041.42,df=1059,TLI=0.91,CFI=0.92,RMSEA=0.06),顯示出本研究中的變量間具有較好的區分效度。

表1 變量描述性分析、相關性分析及量表信度分析
4.2 主效應及中介效應檢驗
由于本研究從團隊層面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影響效應,因此在假設檢驗時從多層線性模型方面進行。從表3中的模型1a和1b中可以看出,當控制了接觸頻率和共事時間之后,謙遜領導對關系親近性的跨層影響效應為 0.46,且在統計上顯著(p<0.001),驗證了假設1。同樣的,從模型2a和2b,3a和 3b中也可以看出,當控制了接觸頻率,共事時間和領導成員交換之后,謙遜領導對員工建言(α=0.22,p<0.05)和幫助行為(α=0.40,p<0.001)具有正向影響,驗證假設2a和2b。在驗證假設3a和3b時,從模型2a、2b和2c來看,當關系親近性加入到模型 2b后,謙遜領導對建言的影響效應由0.22變為0.16,并且不顯著(p>0.05),而此時關系親近性對建言的影響效果顯著(α=0.16,p<0.05),可見關系親近性完全中介了謙遜領導對建言的影響,初步驗證假設3a。同樣的,從模型3a、3b和3c來看,當關系親近性加入到模型3b后,謙遜領導對幫助行為的影響效應由0.40減少為0.34,兩者均顯著,同時關系親近性對幫助行為的影響效應也顯著(α=0.15,p<0.01),可見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與幫助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初步驗證假設3b。
為進一步從跨層模型中驗證關系親近性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Sobel方法進一步對中介進行驗證(Preacher &Hayes,2004)。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與員工建言之間的中介效應 Sobel檢驗值為3.64 (p<0.001),表明關系親近性的中介效應顯著,進一步支持假設3a。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與幫助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 Sobel檢驗值為 3.92 (p<0.001),表明關系親近性的中介效應顯著,進一步支持假設3b。同樣的,為進一步驗證關系親近性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Preacher和Hayes (2004)提出的Bootstrapping方法對間接效應進行檢驗。通過3000次的Bootstrapping,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與建言之間的間接作用為 0.26,95%的置信區間為[0.1622,0.3730],不包含0,因此間接效應顯著,支持假設3a。同樣的,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與幫助行為之間的間接作用為 0.19,95%的置信區間為[0.1208,0.2774],不包含0,因此間接效應顯著,支持假設3a。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N=295)

表3 多層線性模型分析結果
4.3 調節效應檢驗
由于理論與統計檢驗在層次上的一致性,本研究對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在團隊層謙遜領導與關系親近性之間的調節作用進行檢驗。通過跨層回歸分析,從表4中可以看出,模型4b顯示出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對謙遜領導與關系親近性之間的調節作用不顯著(α=?0.08,p>0.05),假設4a未得到支持。從模型4c可以看出,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對謙遜領導與關系親近性之間的調節作用顯著(α=?0.16,p<0.01),假設4b得到驗證。

表4 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的調節作用回歸分析
為進一步清晰的說明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的調節效應,本研究遵循以往的做法,在簡單回歸的基礎上采用正負一個標準差代表高低的方式繪制了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對謙遜領導和關系親近性關系的調節作用圖。Simple Slope檢驗顯示,當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低時,t=3.06 (p<0.01)。而當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高時,t=1.91 (p>0.5),表明調節效應顯著。如圖2所示,本研究的假設4b得到了支持。

圖2 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的調節效應示意圖
4.4 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驗證關系親近性在領導成員關系之外中介效應的穩健性,本研究采用 Preacher和Hayes (2004)提出的雙中介檢驗方法對關系親近性和領導成員交換的中介作用進行同時檢驗。5000次樣本Bootstrapping結果顯示,對于領導謙遜和建言行為的關系,關系親近性的間接效應顯著(效應值為0.25,95%置信區間從0.15到0.37),而領導成員交換的間接效應不顯著(效應值為0.02,95%置信區間從?0.02到0.09),進一步驗證假設3a。對于領導謙遜和幫助行為的關系,關系親近性的間接效應顯著(效應值為0.17,95%置信區間從0.10到0.26),而領導成員交換的間接效應不顯著(效應值為 0.03,95%置信區間從?0.00到0.08),進一步驗證假設3b。
為進一步驗證下屬歸因的謙遜印象管理動機調節作用的穩健性,本研究對謙遜領導、歸因的謙遜績效改進動機和歸因的謙遜印象管理動機三者的三項交互對關系親近性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三項交互作用不顯著(α=?0.13,p>0.05)。此外,本研究還進一步驗證了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對謙遜領導與領導成員交換之間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謙遜領導與歸因的謙遜績效改進動機的交互項對領導成員交換的影響不顯著(α=?0.06,p>0.05),謙遜領導與歸因的謙遜印象管理動機的交互項對領導成員交換的影響也不顯著(α=?0.09,p>0.05)。
5 分析與討論
5.1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從人際關系角度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效應,以及關系親近性和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研究發現:(1)當控制了領導成員交換后,謙遜領導對下屬關系親近性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 1);(2)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建言(假設2a)和幫助(假設2b)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關系親近性在謙遜領導與下屬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關系中起中介作用(假設3a和3b);(4)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調節謙遜領導對下屬關系親近性的正向影響(假設4b),具體的,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的印象管理動機越多時,謙遜領導對下屬關系親近性的正向影響將會被削弱。研究結果顯示,本文的大部分假設得到了很好地支持。
在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對謙遜領導與關系親近性的調節作用假設方面(假設 4a),本研究的數據并未給出有利地支持,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的調節作用不顯著。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基于特質吸引理論,謙遜領導對下屬關系親近性的積極影響是因為下屬對領導謙遜特質的喜歡。當下屬歸因領導謙遜為印象管理動機,領導謙遜特質的吸引力會大大下降,因為這種謙遜是不真誠的。但是,當下屬歸因領導謙遜為績效改進動機,其對領導謙遜特質的實質性影響并不明顯,因為下屬可能會認為謙遜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因此,當下屬歸因領導謙遜動機為績效改進時,其對領導的關系親近性改變并不明顯;其次,“負面偏好” (negativity bias)效應指出,個體會更多的關注負面的信息和事件(Rozin &Royzman,2001),而對某些正面的事件認為是理所當然。由此可見,當領導表現謙遜時,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對下屬關系親近性的影響會更大,影響效應會更顯著。而若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為績效改進動機時,下屬可能認為這是應該的,從而獲得不顯著的影響。此外,對于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績效改進動機的測量方式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來的研究可以在這個方向上進行深入的挖掘。
5.2 理論意義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有以下三點:
首先,本文首次對比了交換關系和共享關系在領導和下屬關系中的差異和效應,突破了以往在探討領導下屬關系時僅關注交換關系的研究局限,進一步豐富了領導理論以及領導成員交換理論。以往研究在探究領導成員關系時,絕大多數的研究都關注的是領導成員交換關系,例如 LMX (Rockstuh,Dulebohn,Ang,&Shore,2012),較少有研究涉及交換關系之外的其他關系。Clark和Mills (1993)在提出人際關系模式時,不僅闡述了交換關系的普遍性,也提出了共享關系的重要性。在領導與下屬關系中,不僅存在學術界普遍認識到的交換關系,還存在共享關系,即下屬單方面的喜愛領導,并愿意做有利于領導的事情。本研究從理論和實證上比較了交換關系和共享關系在影響領導有效性方面的差異性,發現當控制領導成員交換關系后,關系親近性依然能解釋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影響效應,從而為領導理論和領導成員關系理論等方面的文獻做出貢獻。
其次,本文從特質吸引視角揭示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影響機制和效應,為解釋謙遜領導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視角。在特質與領導的關系中,以往的研究更多的關注于特質對領導涌現的影響(Goktepe &Schneier,1989),即什么樣特質的個體更有機會成為領導(即領導特質理論),而對特質是否能幫助領導更好的管理下屬缺乏足夠地關注。本研究從特質吸引的角度出發,認為并發現謙遜領導對下屬有較高的吸引力,能吸引下屬與領導保持親近的關系,并促使下屬去做組織公民行為。本研究一方面通過從特質角度解釋領導有效性為領導特質理論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謙遜領導對下屬的影響機制。
具體的,本研究通過驗證謙遜領導對員工角色外行為的正向影響揭示了謙遜領導的有效性。在探究謙遜領導對員工影響效應的過程中,盡管以往學者從績效(Owens &Hekman,2012;Owens et al.,2015)、滿意度(Owens et al.,2013)、工作投入(Owens et al.,2013;唐漢瑛等,2015)等方面揭示了謙遜領導對員工角色內行為的正向影響,但基于 Borman和Motowidlo (2014)對任務績效和周邊績效的分類,謙遜領導員工周邊績效的影響效應仍不明確。本研究以組織公民行為中建言和幫助行為作為員工周邊績效的代表,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建言和幫助行為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顯示,謙遜領導正向促進下屬的建言和幫助行為,這與之前謙遜領導影響效應的研究具有一致性(Owens et al.,2013;唐漢瑛等,2015)。由此可見,謙遜領導會正向促進下屬的組織公民行為,謙遜領導的有效性從周邊績效角度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
最后,本研究整合人際關系中的特質吸引論和情境行為論,率先以下屬為中心從下屬對領導動機歸因的視角探究謙遜領導有效性的邊界條件,從而為謙遜領導的有效性做出貢獻。在人際關系的研究中,除了特質吸引理論,學者更多的從情境行為角度出發認為人際吸引的產生是個體對他人、自己以及周圍環境的社會信息進行復雜加工而成(Wrzus et al.,2013)。因此,本文在特質吸引論的基礎上,從下屬對領導謙遜行為的動機歸因視角進一步探究謙遜領導對下屬關系親近性的影響。盡管以往的研究開始關注謙遜領導的邊界條件,但大多是以領導為中心的研究,即在謙遜領導的影響下,不同特質的下屬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權力距離、調節焦點),缺乏從下屬視角對謙遜領導影響進行評價的研究。本研究從下屬對領導動機歸因的視角探究謙遜領導影響的邊界條件既整合了人際關系領域特質論和情境論視角,也率先以下屬為中心探究了下屬對謙遜領導的理解,進一步豐富了謙遜領導的研究。
5.3 實踐啟示
本研究的結論對現有的企業管理具有一定的啟示和指導意義。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環境以及“互聯網+”行業變革的出現,企業外部市場環境的動態性和變革性越來越強。在這種情境下,企業管理者需要改變原來指派式、命令式等領導風格,更多地發揮下屬的優勢并向下屬學習。本文的研究結論指出,謙遜領導能正向促進員工關系親近性和組織公民行為。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培養更多的謙遜領導來促進企業的內部和諧和績效。在此方面,Nielsen等(2013)提出了培養謙遜領導的六個指標:(1)具有超越自我的愿景;(2)在愿景下保持謙遜的姿態支持和幫助他人;(3)對反饋進行分析;(4)保持學習筆記;(5)嘗試自我犧牲;(6)積極傾聽。同時,本研究還發現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會削弱謙遜領導與下屬關系親近性之間的正向關系,因此,企業管理者在表現謙遜時,應該增加真誠的謙遜行為,減少基于印象管理動機的謙遜行為。在企業管理制度方面,企業也可以增加領導與下屬溝通的便利性,從而減少下屬對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的歸因。
5.4 研究局限與未來研究展望
盡管本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價值的結論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所調研的企業樣本雖然來自于多個地區,但均處于同一省份,結論的外部有效性可能存在局限。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跨地域、跨國家的調研方式,進一步增強本文結論的外部有效性。其次,盡管Owens等(2013)開發的謙遜領導量表在我國具有一定的適用性(曲慶等,2013;雷星暉等,2015),但其是否完全反應了我國領導的謙遜仍存在質疑。毛江華,廖建橋和劉文興(2016)指出,中西方謙遜存在多個方面的差異。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借鑒Oc等人(2015)的做法,進一步深入研究本土的謙遜概念。最后,本研究在探究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時,盡管采用了以往成熟的量表從利己(印象管理)和利他(績效改進)兩個方面進行歸因(Lam et al.,2007),但仍存在從其他角度進行歸因的可能性,例如下屬歸因領導謙遜是穩定的(特質),還是不穩定的(情境行為)。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對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進行深入地探討。此外,除了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存在多種類別之外,領導自身的謙遜動機也可能不同。胡金生和黃希庭(2009)以大學生和社會大眾為分析對象發現個體自謙存在防御性、自我發展和提升形象三種動機。然而,由于領導角色的特殊性,領導謙遜動機是否也是這三種形式,這一問題也有待未來的研究進行進一步的探索。
6 研究結論
基于人際關系視角,本研究采用兩個時段上下級匹配的調研方式以295份上下級配對數據作為分析對象,探究謙遜領導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同時探究在這個過程中下屬歸因的領導謙遜動機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謙遜領導通過提高下屬的關系親近性促進下屬實施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包括建言和幫助行為。在這個過程中,當下屬歸因領導謙遜印象管理動機高時,謙遜領導的積極效應將會得到削弱。可見,領導謙遜地表達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未來的研究可以在此方面進行進一步地探究。
Ainsworth,M.S.,&Bowlby,J.(1991).An ethological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American Psychologist,46(4),333–341.
Anderson,N.H.(1968).Likableness ratings of 555 personality-trait word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9(3),272–279.
Arnold,E.C.,&Boggs,K.U.(2015).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nurses(7th ed.).London:Elsevier Health Sciences.
Aron,A.,&Aron,E.N.(1997).Self-expansion motivation and including other in the self.In S.Duck (Ed.),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or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s(2nd ed.,pp.251–270).London:Wiley.
Barrick,M.R.,Mount,M.K.,&Li,N.(2013).The theory of purposeful work behavior:The role of personality,higher-order goals,and job characteristic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38(1),132–153.
Bauer,T.N.,&Green,S.G.(1996).Development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A longitudinal test.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9(6),1538–1567.
Bolino,M.C.,Hsiung,H.H.,Harvey,J.,&LePine,J.A.(2015). “Well,I’m tired of tryi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citizenship fatigu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00(1),56–74.
Bond,M.H.,Leung,K.,&Wan,K.C.(1982).The social impact of self-effacing attributions:The Chinese case.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18(2),157–166.
Borman,W.C.,&Motowidlo,S.J.(2014).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A special Issue of human performance.Oxford:Psychology Press.
Chen,R.(1993).Responding to compliment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ers.Journal of Pragmatics,20(1):49–75.
Clark,M.S.,&Mills,J.(1993).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unal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s:What it is and is no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6),684–691.
Ensari,N.,&Murphy,S.E.(2003).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attribution of charisma to the leade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92(1?2),52–66.
Eastwick,P.W.,Luchies,L.B.,Finkel,E.J.,&Hunt,L.L.(2014).The predictive validity of ideal partner preferences: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Psychological Bulletin,140(3),623–665.
Erdogan,B.,Bauer,T.N.,&Walter,J.(2015).Deeds that help and words that hurt:Helping and gossip as moder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advice network centrality.Personnel Psychology,68(1),185–214.
Exline,J.J.,Baumeister,R.F.,Bushman,B.J.,Campbell,W.K.,&Finkel,E.J.(2004).Too proud to let go:narcissistic entitlement as a barrier to forgivenes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7(6),894–912.
Farh,J.L.,&Cheng,B.S.(2000).A cultural analysi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In J.T.Li,A.S.Tsui,&E.Weldon (Eds.),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pp.84?127).London,UK:Palgrave Macmillan.
Farmer,S.M.,Van Dyne,L.,&Kamdar,D.(2015).The contextualized self:How team–member exchange leads to coworker identification and helping OCB.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00(2),583–595.
Goktepe,J.R.,&Schneier,C.E.(1989).Role of sex,gender roles,and attraction in predicting emergent leader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74(1),165–167.
Graham,J.M.,&Harf,M.R.(2015).Self-expansion and flow:The roles of challenge,skill,affect,and activation.Personal Relationships,22(1),45–64.
Gu,Y.G.(1990).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Journal of Pragmatics,14(2),237–257.
Hofmann,D.A.(1997).An overview of the logic and rationale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Journal of Management,23(6),723–744.
Hu,J.S.(2007).Self-modesty in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vision.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27(3),19–21,43.
[胡金生.(2007).傳統和現代視野中的自謙.心理學探新,27(3),19–21,43.]
Hu,J.S.,&Huang,X.T.(2006).A research on self-modesty in Chinese society.Psychological Science,29(6),1392–1395.
[胡金生,黃希庭.(2006).華人社會中的自謙初探.心理科學,29(6),1392–1395.]
Hu,J.S.,&Huang,X.T.(2009).Preliminary study on self-modesty:One significant behavioral style of Chinese.Acta Psychologica Sinica,41(9),842–852.
[胡金生,黃希庭.(2009).自謙:中國人一種重要的行事風格初探.心理學報,41(9),842–852.]
Huston,T.L.(2013).Foundations of interpersonal attraction.New York:Elsevier.
James,L.R.(1982).Aggregation bias in estimates of perceptual agreement.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67(2),219–229.
Kim,Y.J.,Van Dyne,L.,Kamdar,D.,&Johnson,R.E.(2013).Why and when do motives matter?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motives,role cognitions,and social support as predictors of OCB.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21(2),231–245.
Lam,W.,Huang,X.,&Snape,E.(2007).Feedback-seeking behavior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Do supervisorattributed motives matter?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0(2),348–363.
Lei,X.H.,Shan,Z.W.,Su,T.Y.,&Yang,Y.F.(2015).Impacts of humble leadership behavior on employee creativity.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8(2),115–125.
[雷星暉,單志汶,蘇濤永,楊元飛.(2015).謙卑型領導行為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研究.管理科學,28(2),115–125.]
Luo,S.H.,&Snider,A.G.(2009).Accuracy and biases in newlyweds' perceptions of each other:Not mutually exclusive but mutually beneficial.Psychological Science,20(11),1332–1339.
Malouff,J.M.,Schutte,N.S.,&Thorsteinsson,E.B.(2014).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A meta-analysi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42(1),53–66.
Mao,J.H.,Liao,J.Q.,&Liu W.X.(2016).A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humility studies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Management Review,28(3),154–163.
[毛江華,廖建橋,劉文興.(2016).中西方謙遜的研究回顧和比較分析.管理評論,28(3),154–163.]
Maxwell,H.,Tasca,G.A.,Gick,M.,Ritchie,K.,Balfour,L.,&Bissada,H.(2012).The impact of attachment anxiety on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in early group therapy interactions among women with binge eating disorder.Group Dynamics:Theory,Research,and Practice,16(4),255–271.
McAllister,D.J.(1995).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38(1),24–59.
Meindl,J.R.,Ehrlich,S.B.,&Dukerich,J.M.(1985).The romance of leadership.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0(1),78–102.
Mills,J.,&Clark,M.S.(1982).Exchange and communal relationships.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121–144.
Nielsen,R.,Marrone,J.A.,&Ferraro,H.S.(2013).Leading with humility.London:Routledge.
Nielsen,R.,Marrone,J.A.,&Slay,H.S.(2010).A new look at humility:Exploring the humility concept and its role in socialized charismatic leadership.Journal of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Studies,17(1),33–43.
Oc,B.,Bashshur,M.R.,Daniels,M.A.,Greguras,G.J.,&Diefendorff,J.M.(2015).Leader humility in Singapore.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6(1),68–80.
Ou,A.Y.,Tsui,A.S.,Kinicki,A.J.,Waldman,D.A.,Xiao,Z.X.,&Song,L.J.(2014).Humbl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s’connections to top management team integration and middle managers’ response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59(1),34–72.
Owens,B.P.,&Hekman,D.R.(2012).Modeling how to grow:An inductive examination of humble leader behaviors,contingencies,and outcom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5(4),787–818.
Owens,B.P.,&Hekman,D.R.(2016).How does leader humility influence team performance?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contagion and collective promotion focu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9(3),1088–1111.
Owens,B.P.,Johnson,M.D.,&Mitchell,T.R.(2013).Expressed humility in organizations:Implications for performance,teams,and leadership.Organization Science,24(5),1517–1538.
Owens,B.P.,Walker,A.S.,&Waldman,D.A.(2015).Leader narcissism and follower outcomes:The counterbalancing effect of leader humility.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00(4),1203–1213.
Piccolo,R.F.,&Colquitt,J.A.(2006).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job behaviors: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e job characteristic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9(2),327–340.
Preacher,K.J.,&Hayes,A.F.(2004).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Instruments,&Computers,36(4),717–731.
Qu,Q.,He Z.C.,&Mei,Z.Q.(2013).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leader humility o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and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China Soft Science,(7),101–109.
[曲慶,何志嬋,梅哲群.(2013).謙卑領導行為對領導有效性和員工組織認同影響的實證研究.中國軟科學,(7),101–109.]
Rafferty,A.E.,&Griffin,M.A.(2006).Refining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Distinguishing developmental leadership and supportive leadership.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79(1),37–61.
Rockstuhl,T.,Dulebohn,J.H.,Ang,S.,&Shore,L.M.(2012).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and culture:A meta-analysis of correlates of LMX across 23 countrie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97(6),1097–1130.
Rozin,P.,&Royzman,E.B.(2001).Negativity bias,negativity dominance,and contagi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5(4),296–320.
Scandura,T.A.,&Graen,G.B.(1984).Moderating effects of initial leader–member exchange status on the effects of a leadership intervention.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69(3),428–436.
Schaubroeck,J.,&Lam,S.S.K.(2002).How similarity to peers and supervisor influences organizational advancement in different cultur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5(6),1120–1136.
Smith,C.A.,Organ,D.W.,&Near,J.P.(1983).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Its nature and antecedent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68(4),653–663.
Tang,H.Y.,Long,L.R.,&Zhou,R.Y.(2015).Humble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subordinates' work engagement: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8(3),77–89.
[唐漢瑛,龍立榮,周如意.(2015).謙卑領導行為與下屬工作投入:有中介的調節模型.管理科學,28(3),77–89.]
Tangney,J.P.(2000).Humility:Theoretical perspectives,empirical finding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1),70–82.
Van Dyne,L.,&LePine,J.A.(1998).Helping and voice extra-role behaviors:Evidence of construc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41(1),108–119.
Vangelisti,A.L.,&Caughlin,J.P.(1997).Revealing family secrets:The influence of topic,function,and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14(5),679–705.
Vera,D.,&Rodriguez-Lopez,A.(2004).Strategic virtues:Humility as a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Organizational Dynamics,33(4),393–408.
Weick,K.E.(2001).Leadership as the legitimation of doubt.In W.Bennis,G.M.Spreitzer,&T.G.Cummings (Eds.),The future of leadership:Today’s top leadership thinkers speak to tomorrow’s leaders.San Francisco:Jossey-Bass.
Williams,L.J.,&Anderson,S.E.(1991).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and in-role behaviors.Journal of Management,17(3),601–617.
Wrzus,C.,H?nel,M.,Wagner,J.,&Neyer,F.J.(2013).Social network changes and life events across the life span:A meta-analysis.Psychological Bulletin,139(1),53–80.
Xu,E.,Huang,X.,&Robinson,S.L.(2015).When self-view is at stake:Responses to ostracism through the lens of self-verification theory.Journal of Management,doi:10.1177/0149206314567779.(in Press)
Zhang,X.M.,&Bartol,K.M.(2010).Linking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intrinsic motivation,and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3(1),107–128.
Zhang,Y.,&Chen,C.C.(2013).Development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determination,supervisor identification,and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4(4),534–543.
Zhang,Y.,Huai,M.Y.,&Xie,Y.H.(2015).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voice in China:A dual process model.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6(1),2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