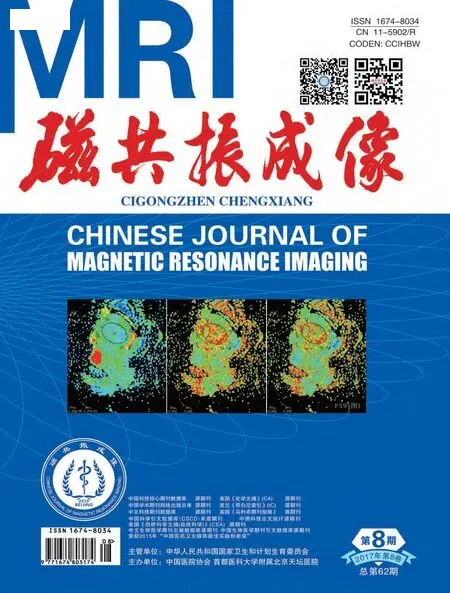經濟狀況對不公平感相關決策的影響:基于靜息態的fMRI研究
鄭軼潔,徐佳琳,鄭麗,李林,楊光*,郭秀艷
公平是社會決策過程中的一項基本準則,通常指在社會活動中任何一個個體或團體在付出和收獲等各個方面都應受到不偏不倚的對待。已有研究通過靜息態磁共振成像技術(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探究了人們受到不公平對待后進行經濟決策的個體差異[1]。然而,不公平感相關的經濟決策是一個復雜的加工過程,會受到多種情境因素的影響[2-3]。前人研究發現,經濟狀況作為一種影響因素在經濟決策的過程中起到調節作用[4-5],但其對不公平感相關決策中產生影響的個體差異及內在神經機制尚待進一步探究。
功能連接作為一種常用的探測腦區間線性相關的手段,被廣泛應用于靜息態fMRI的研究中[6-7]。在復雜的認知加工過程中需要整合來自不同腦區的各種信息,自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者們提出對于腦的研究應從功能整合的角度出發,并提出了功能連接的分析方法,著重研究間隔空間腦區的神經水平在時間上的相關性。基于前人研究,背外側前額葉皮層(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參與到不公平感相關的決策加工過程中[3,8],而丘腦則參與了社會經濟地位的加工過程[9-10]。本研究借助于靜息態fMRI的功能連接分析方法,使用在不公平感相關決策中常用的最后通牒博弈任務(ultimatum game,UG),從個體差異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靜息狀態下以上腦區與其他腦區內在連接的強度差異,是否能夠預測在面對來自不同經濟狀況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時的行為反應及公平感感知。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共有30名健康的右利手被試(平均年齡為23.2歲,標準差為1.4,范圍為20~26歲)參與本研究,其中包含21名女性和9名男性。所有被試的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且無任何精神病史。所有被試都自愿參與本研究,并在研究開始前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已獲得華東師范大學人體實驗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任務設計
本研究共分為磁共振掃描和行為任務兩部分,為避免任務內容對被試的靜息態掃描結果產生影響,所有被試首先進行靜息態fMRI的掃描,然后進行行為任務。
研究采用的任務改編自最后通牒博弈任務[11]。經典的UG任務通常由兩名玩家組成,一名是提議者的角色(proposer),另一名則是被試擔任的回應者角色(responder)。在任務中,兩名玩家共同獲得一定數目的錢(m元),并由提議者決定如何在自己與回應者之間進行分配,即分配給回應者x元(0<x≤m),留下m-x元給自己。回應者需要選擇接受或者拒絕提議者提出的分配方案。若回應者選擇接受該方案,則玩家雙方按照提議者的分配方案各得到相應的金額;若回應者拒絕接受該方案,則雙方都得不到這筆錢,即雙方收益都為0元。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加入了提議者的經濟狀況這一變量。在進行UG任務前,被試會了解到提議者的經濟狀況,然后他們作為回應者參與到任務中。
任務開始前將告知被試以下信息:(1)他們會參與一項經濟決策任務,任務中他們會遇到72名不同的搭檔,這些搭檔都是來自于與他們同一所大學的學生。(2)任務中他們的搭檔會作為提議者決定如何分配50元,而被試將作為回應者來決定是否要接受提議者的分配方案,若選擇接受,則兩方按照分配方案得到相應金額;若選擇拒絕,則兩方受益為0。每一項分配方案來自于不同的分配對象,且在研究開始前進行采集。(3)考慮到學生尚且沒有收入,試驗中提議者的經濟狀況將由他們的家庭月收入水平來決定。經濟水平將通過一個十級的“經濟階梯”(economic ladder)來表示[12],其中最低的第一級階梯表示最差的經濟狀況;反之,最高的第十級階梯表示的則是最好的經濟狀況。本研究中的提議者來自于第一級階梯(經濟狀況較差)或第十級階梯(經濟狀況較好)。最低及最高的家庭月收入水平的設置參考了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4)每一個提議者的分配方案以及被試(回應者)是否接受該分配將決定被試和提議者的最終所得。被試最終的酬勞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被試參與本研究的保底收入50元,另一部分則是根據所有任務結果中隨機抽取6%的決策結果相加所得。
本研究的任務采用的是混合設計,不同經濟狀況的任務區組交替出現。在一個區組中,被試會先看到6 s關于提議者經濟狀況的提示,經濟狀況通過一個漸變色的柱狀圖來表示,當標志指向柱狀圖頂端時表示提議者經濟狀況較好,指向柱狀圖底端時表示提議者經濟狀況較差。提示之后,被試會依次得到來自相同經濟狀況的6名不同提議者的分配。每一次分配中,被試會先看到持續3 s的分配界面,界面會顯示提議者分給自己及分給被試的金額。然后,被試需要在接下來的決策階段決定是否接受這一分配方案,決策階段有3 s的限制時間,被試通過在鍵盤上進行相應的按鍵做出反應(右手食指按“3”代表“接受”,右手中指按“4”代表“拒絕”)。當被試做出反應后,程序會通過在他們所選擇的選項外顯示一個藍色框來進行反饋(圖1)。兩次分配之間有2~4 s的空白間隔,在分配界面和決策界面之間插入了500~1500 ms的空白間隔。每一個區組包含2個公平分配(¥25:¥25)和4個不同的不公平分配(¥20:¥30,¥15:¥35,¥10:¥40和¥5:¥45),順序上隨機排列。每一個區組耗時70~75.8 s,每兩個區組之間有5 s的間隙時間。正式任務共有12個區組合計72次分配,其中6個區組中所有的提議者都來自于經濟狀況較好組,另外6個區組中所有的提議者都來自于經濟狀況較差組。不同經濟情況區組出現的順序在被試間進行了平衡。
為避免被試聯想到自己熟悉的人而影響其決策,任務中72位提議者都以姓名的縮寫為標記出現在屏幕上(如“Zhang Liang”縮寫為“Zhang L.”)。在正式任務之前,被試首先會練習4個區組(每種經濟狀況的提議者各占兩個區組)共24次分配,做到能夠對任務材料反應自如。
任務完成后,主試給被試呈現與任務中相同的提議者經濟狀況及分配方案。這時需要被試對于每一個分配方案進行利克特9點量表的公平感評分,其中1分表示極度不公平,9分表示極度公平。同時,主試也詢問了被試自身的經濟狀況,其中1分表示最差的經濟狀況,10分表示最好的經濟狀況。
1.3 磁共振掃描參數
本研究磁共振成像的掃描分為高清結構像掃描和靜息態fMRI掃描兩部分。研究中所有被試的腦數據采集于西門子3.0 T磁共振成像系統(Magnetom Trio TIM,Siemens,Erlangen,Germany)。首先通過T1加權的多平面重建序列得到結構像的數據,序列參數如下:TR 2530 ms,TE 2.34 ms,掃描層數為192層,層厚為1 mm,FOV 256 mm×256 mm,采集矩陣大小為256×256。然后進行靜息態的fMRI數據掃描,一共掃描240幅圖像,總時長8 min 6 s。掃描過程中被試需要閉上眼睛且保持不作思考的清醒狀態。靜息態fMRI掃描采用的是梯度回波平面成像序列(echo planar imaging,EPI),序列參數如下:TR 2000 ms,TE 30 ms,FOV 192 mm×192 mm,采集矩陣大小為64×64,掃描層數為33層,層厚為4 mm,層間距為4 mm。
1.4 靜息態fMRI數據分析
本研究中靜息態腦數據的預處理和統計分析使用了基于MATLAB環境下的DPARSFA工具包(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for Resting-State fMRI;http://www.restfmri.net/forum/DPARSFA)。
首先進行腦數據預處理,過程分為以下幾步:(1)刪除前10幅全腦圖,以排除因開始掃描時儀器的不穩定所造成的影響;(2)時間層校正:減少在一次全腦掃描中因為層與層之間掃描時間差造成的差異;(3)頭動校正:將掃描中的每一幅圖與第一幅圖進行對齊,當被試平動超過1.5 mm,或轉動超過1.5°時,則認為該被試頭動過大,數據需要被排除;(4)將頭動校正后形成的平均EPI圖像和T1加權成像所得的結構像進行配準;(5)將配準后的高清結構像分割成白質、灰質和腦脊液,并標準化到MNI空間;(6)根據先前處理得到的標準化參數,將功能像進行空間標準化(以3 mm×3 mm×3 mm的體素進行重采樣);(7)去除線性漂移造成的影響;(8)使用帶通濾波去除0.01~0.08 Hz頻率之外的頻率成分;(9)去除頭動、白質和腦脊液等協變量因素對于數據的影響;(10)使用6 mm半高寬的高斯核進行空間平滑。
功能連接的分析過程如下:首先根據以往研究[9,13],以右側被外側前額葉皮層(MNI 26,48,22)、右側丘腦(MNI 6,-18,6)的MNI坐標為圓心,構建6 mm為半徑的球形種子點,計算種子點與大腦各體素之間的功能連接并獲得通過費舍爾Z轉換(FisherZ)的大腦功能連接圖。然后通過回歸分析進行功能連接與行為數據間的相關性分析。當腦區激活水平通過體素水平(voxel level)P<0.001(未校正)及簇水平(cluster level)P<0.05(family-wise error,FWE校正)的閾限,則認為腦區激活顯著。
進一步通過SPSS統計分析工具對功能連接結果通過費舍爾Z轉換所得的系數與行為結果進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得到相關系數并畫出散點圖。當P<0.05時,認為功能連接系數與行為結果有顯著相關。本研究中主要關注的行為結果為回應者對于來自不同經濟狀況的提議者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以及公平感評分。
2 結果
2.1 行為結果
當提議者給出公平分配時,回應者會接受所有的分配并給出較高的公平感評分。本研究主要探究回應者對不公平分配的反應,因此關注的行為變量為被試對于不同經濟狀況提議者提出不公平分配時的拒絕率及公平感評分。配對t檢驗分析發現,得到不公平分配時,被試對于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拒絕率(范圍是0.54~0.92)顯著高于對經濟狀況較差的提議者的拒絕率(范圍是0.21~0.75) (t(29)>12.54,P<0.01)。同時,對于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公平感評分(范圍是1.79~4.00)顯著低于對經濟狀況較差的提議者的評分(范圍是2.33~4.63) (t(29)>8.23,P<0.01) (圖2)。
此外,實驗中還記錄了被試自身的經濟狀況。單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被試經濟狀況的平均水平為4.63±0.93,與代表經濟狀況較差的1和代表經濟狀況較好的10差異顯著(ts>21.44,Ps<0.01)。這表明任務中設置的經濟狀況較好的條件顯著好于被試本身所處的經濟狀況,同時任務中設置的經濟狀況較差的條件也顯著低于被試本身所處的經濟狀況。
2.2 腦數據結果
研究結果表明,腦區間功能連接與對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之間的相關,主要體現為當提議者經濟狀況較好時,右側DLPFC和右側內側前額葉皮層(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MNI 12,57,21)的功能連接與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之間的負相關(r=-0.80,P<0.01,圖3A)。腦區間的功能連接與對經濟狀況較差的提議者提出不公平分配時的拒絕率之間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相關。
腦區間功能連接與對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感評分之間的相關,主要體現為當提議者經濟狀況較好時,右側丘腦與左側MPFC (MNI -6,63,9)的功能連接與被試對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感評分之間的負相關(r=-0.59,P<0.01,圖3B)。腦區間的功能連接與對經濟狀況較差的提議者提出不公平分配時的公平感評分之間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相關。
3 討論
本研究借助于靜息態fMRI的功能連接分析方法,從個體差異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了大腦區域之間的內在連接對于不同經濟狀況影響不公平感相關決策的預測作用。行為結果表明,相較于經濟狀況較差的提議者,被試更可能會拒絕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并且對他們的分配感到更不公平。提議者不同的經濟狀況對于回應者的公平感感知及決策反應起到調節作用。靜息態fMRI結果表明,腦區間的功能連接與行為結果之間相關顯著。當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給出不公平分配時,右側DLPFC和右側MPFC的功能連接與拒絕率之間呈現出負相關,而右側丘腦與左側MPFC的功能連接與公平感評分之間呈現出負相關。

圖1 任務流程。A:當標志指向柱狀圖頂端時表示提議者經濟狀況較好;B:指向柱狀圖底端時表示提議者經濟狀況較差;C:在每一個實驗串中,分配界面顯示3 s,決策界面顯示3 s,被試需要在決策界面選擇接受或拒絕。當被試做出反應時,在其所選選項上會出現一個框,顯示時間為1 sFig.1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A: An arrow pointing to the top of the histogram indicating the High economic status; B: An arrow point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histogram indicating the Low economic status; C: In each trial, the proposal screen was presented for 3 s. Then the decision cue appeared and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decide whether to accept or reject the offer within 3 s by pressing corresponding buttons. Once they responded, a frame outside the selected choice would be presented for 1 s to provide feedback of their decision.

圖2 得到不公平分配時的拒絕率(A)和公平感評分(B)(*表示P<0.01)Fig.2 A: Rejection rates to unfair offers, B: Fairness ratings to unfair offers. * indicates P<0.01.
在腦區間功能連接與對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之間的相關分析中發現,右側DLPFC和右側MPFC的功能連接與對經濟狀況較好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之間呈負相關,即DLPFC與MPFC的功能連接越強的個體,更可能會接受對于來自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以往對于不公平感相關決策的研究中發現,DLPFC和整合與雙方責任、自身行為及其后果等有關信息,并做出最適合當前情境下的行為有關[3,8],而MPFC的功能與識別他人的意圖和目的有關[9,14]。因此,DLPFC與MPFC的功能連接越強的個體可能更善于整合與他人意圖相關的信息,在決定是否接受不公平分配時會更加理解他人,從而導致對于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降低。
腦區間功能連接與對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感評分之間的相關分析發現,右側丘腦與左側MPFC的功能連接與被試對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感評分之間呈負相關,即丘腦和MPFC的功能連接越強的個體,對于來自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分配感到更不公平。前人研究發現,丘腦的激活受到社會情緒刺激的調節作用,人們對于社會經濟地位更高的對象有更強的情緒喚起[9,15]。因此,當得到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時,人們會感到更強的負性情緒。又如先前所說,MPFC與識別他人的意圖和目的有關[9,14]。因此,丘腦與MPFC的功能連接越強的個體在理解他人意圖的同時會受到較強的負性情緒的影響,從而對來自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分配感到更加不公平。
本研究目前的研究結果尚無法分析特定腦區功能是與普遍的任務控制或注意控制有關,還是與特定的決策過程有關。這一點在未來研究中,筆者可以進一步設計實驗進行觀察。

圖3 A:以右側背外側前額葉皮層為種子點和右側內側前額葉皮層的功能連接與對經濟狀況較好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的拒絕率之間呈負相關;B:以右側丘腦為種子點和左側內側前額葉皮層的功能連接與對經濟狀況較好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的公平感評分之間呈負相關Fig.3 A: Rejection rat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C between right DLPFC and right MPFC; B: Fairness rating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C between right thalamus and left MPFC.
4 結論
本研究借助于靜息態fMRI的功能連接分析方法,探討了個體在靜息狀態下大腦區域之間的內在連接強度差異,能否預測其在面對來自不同經濟狀況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時的行為反應及公平感感知。結果發現,相較于經濟狀況較差的提議者,人們在更多地拒絕來自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的不公平分配的同時,也會感到更加地不公平。此外,當不公平分配來自于經濟狀況較好的提議者時,右側DLPFC和右側MPFC的功能連接與拒絕率之間呈負相關,右側丘腦與左側MPFC的功能連接與公平感評分之間呈負相關。以上結果表明,DLPFC、丘腦及MPFC在靜息狀態下的功能連接能夠預測人們在整合搭檔的經濟狀況并進行不公平感相關決策過程中的個體差異。
[References]
[1] Wu Y, Zang Y, Yuan B,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decision making after unfair treatment. Front Hum Neurosci, 2015, 9(5): 123.
[2] Guroglu B, Van Den Bos W, Rombouts SA, et al. Unfair? It depends:Neural correlates of fairness in social context.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2010, 5(4): 414-423.
[3] Guo X, Zheng L, Cheng X, et al. Neural responses to unfairness and fairness depend on self-contribution to the income.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2014, 9(10): 1498-1505.
[4] Holm H, Engseld P. Choosing bargaining partner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bout income, status and gender.Exper Econo, 2005, 8(3): 183-216.
[5] Haile D, Sadrieh A, Verbon HA. Cross-racial envy and underinvestment in South African partnerships. Cambridge J Econ,2008, 32(5): 703-724.
[6] Biswal B, Yetkin FZ, Haughton VM,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the motor cortex of resting human brain using echo-planar MRI.Magn Reson Med, 1995, 34(4): 537-541.
[7] Horwitz B, Friston KJ, Taylor JG. Neural modeling and functional brain imaging: an overview. Neural Netw, 2000, 13(8-9):829-846.
[8] Sanfey AG, Rilling JK, Aronson JA, 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Science, 2003,300(5626): 1755-1758.
[9] Zink CF, Tong Y, Chen Q, et al. Know your place: Neural processing of social hierarchy in humans. Neuron, 2008, 58(2): 273-283.
[10] Hu J, Blue PR, Yu H, et al. Social status modulates the neural response to unfairness.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2016, 11(1): 1-10.
[11] Guth W, Schmittberger R, Schwarze B. An experimental-analysis of ultimatum bargaining. J Econo Behav & Organiz, 1982, 3(4):367-388.
[12] Adler NE, Epel ES, Castellazzo G, et al.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 2000, 19(6): 586-592.
[13] Feng C, Luo YJ, Krueger F. Neural signatures of fairness-related 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 a coordinatebased meta-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2015, 36(2): 591.
[14] Frith CD, Frith U. The neural basis of mentalizing. Neuron, 2006,50(4): 531-534.
[15] Britton JC, Phan KL, Taylor SF, et al. Neural correlates of social and nonsocial emotions: An fMRI study. Neuroimage, 2006, 31(1):397-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