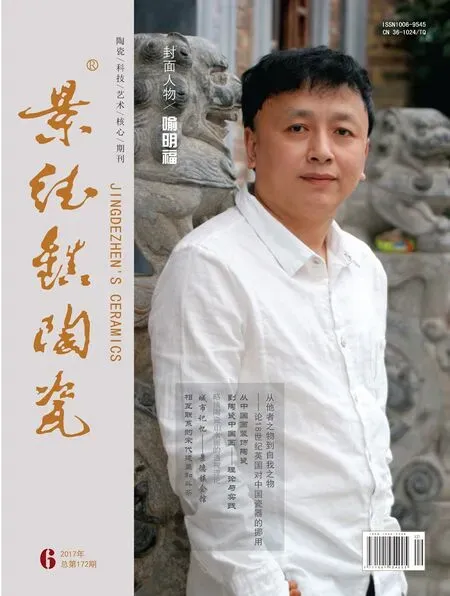從他者之物到自我之物
—— 論18世紀英國對中國瓷器的挪用
/徐胤娜 侯鐵軍(景德鎮陶瓷大學科技藝術學院)
文化學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論及文化和器物時指出:“思想、信息、藝術品和實踐,并不是簡單地被采納。恰恰相反的是,它們會被調適去適應新的文化環境。首先,它們會被去情境化,然后被再情境化、歸化和本土化。”
18世紀英國社會對中國瓷器的接受和反應正體現了伯克所謂的“文化轉譯”現象。盡管當時的英國社會,從上到下,都被卷入中國瓷器的熱潮之中,但他們并不消極被動,而是通過各種方法和途徑,把瓷器這個他者中國之物轉變成自我之物,為世界陶瓷貢獻了英國人的偉大智慧。
一、“拱形圓柄鑲金飾”:18世紀英國的鑲嵌瓷
“為進口器物加裝和鑲嵌金屬(金、銀或鍍銀)裝飾的做法,在14世紀晚期的歐洲文獻中就有記錄。當時很多具有異域情調的器物,如貝殼、巖石、水晶、鴕鳥蛋和象牙等,都加裝了黃金和白銀,以突顯它們的稀有和美麗”。
與上述價值不菲的裝飾品不同的是,瓷器不但是可供觀賞的藝術品,也是用途廣泛的日用品。在日常使用的過程中,人們不免要移動、接拿瓷器,用瓷器盛裝食物,乃至難免使其與其他器物發生碰撞(如勺子與盤子),這便加大了瓷器破損的危險。因而保護脆弱易碎的瓷器(如給沿口、手柄、蓋子、底座加裝金屬器),是為瓷器加裝鑲嵌的另一個初衷。
正是基于上述象征、審美和實用等目的,中國瓷器自16世紀進入歐洲社會后,為它加裝鑲嵌金屬的做法就開始了。“在17世紀的荷蘭,許多瓷器就用這種方式來裝飾”,到18世紀中期,“巴黎的瓷器加裝是瓷器加裝史上的黃金時代”。
在英國,早在16世紀末,就有給瓷器加裝鑲嵌的記錄。一位名叫塞繆爾·雷納(Samuel Lennard) 的商人就曾為一只灰藍釉中國瓷器加裝鍍銀。及至18世紀,隨著大量中國瓷器的進口,瓷器不再像16、17世紀那樣稀有和昂貴,然而還是有一些人為心愛的瓷器或家族遺傳的老瓷器加裝鑲嵌。在18世紀英國女詩人喬安娜·貝利(Joanna Baillie)的詠陶詩《致茶壺》(Lines to a Teacup)(1790)中,就有這樣的描述:
茶壺嘴直巧玲瓏,壺身美麗煥雅姿。
拱形圓柄鑲金飾,穹圓蓓蕾飾蓋子。
完好無缺站此地,韻文謳歌好主題。
從古時起流至今,此物美麗又得體。
據吳文婷的研究,“中世紀至18世紀以前,鑲嵌較常以由外箝住或包覆瓷體裝成,而在18世紀前后開始……,瓷體大幅度的經由被切割、鉆孔、栓上鑲嵌來改造”。“有些可以看得出來原來是花瓶,但是瓶口硬生生的被削去,瓶肩及瓶身處被橫向切開,切開處的邊緣鑲上鍍金的銅質金屬邊框,組裝后便是有蓋的藏物罐”。
經過加裝鑲嵌后的中國瓷器,不僅在物理層面大受改造,有的還變得面目全非,其原本的功用和意義都被篡改,或者如彼得·伯克所言的,從功能和美學等方面,被“去情境化” 和“再情境化”了。約翰·蓋伊(John Gay)的《致一位酷愛古瓷器的女士》(To a Lady on Her Passion for Old China)(1725)中的古瓷罐正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看著這些古瓷罐,或白或藍或金鑲。
器物純潔又精致,看起來如女人般。
它們因美而價高,卻太精致不實用。
插花飾金天青色,裝點家居添榮光。
蓋伊詩中的瓷器,原本是素雅的青花瓷,現在則被鑲上了金飾(再情境化)。不但如此,原本被制造出來用以盛裝物品,有著較高實用價值的瓷罐,在經過英國人的加裝后,其原本的功用特性也遭到遮蔽,變成了一個“精致”而“不實用”的裝飾品。
二、“式多奇巧,歲無定樣”:18世紀英國的定制瓷
英國人將中國瓷器本土化的另一個重要手段是定制瓷器。據陶瓷史專家大衛·霍華德的統計,整個歐洲的定制瓷有“5000多種”,但其中“有3000多種是銷往英國市場的”,它們主要是由英國皇室、貴族和公司所定制的以家族徽章或公司商號圖案為主的紋章瓷。
物質文化研究認為,“器物有做‘社會工作’的能力。器物可以指代亞文化關聯、職業、財富、有限活動的參與,或者社會地位的某個方面——社會身份的所有方面”。上述王公貴族等,正是利用了瓷器這一物質文化的能動性表征和建構身份,區隔和厘清階級或等級界限。一方面,這些飾有家族徽章、標志、個人畫像的紋章瓷,以可見、可觸的物質形式,外化了瓷器所有者的財富和地位,讓他們在旁觀者的羨慕、驚嘆和嫉妒中,“調和自我身份和尊嚴的形成”。另一方面,它們將這一家族的成員乃至擁有紋章瓷的其他家族或階層聯系在一起,“為正式和私人的場合創造了醒目的陳列品”,“為傳播諸如社會地位和家庭紐帶等思想提供了一種理想的、新的途徑”,將自己與其他社會群體、階級或部落區隔開來,為無形的階級和等級區別劃出了一條有形的物質界限。
除紋章瓷外,英國人還定制了不少符合他們生活和飲食習慣的瓷器,如馬克杯、雙頸油醋瓶、托比杯、天鵝湯碗、甜品臺、潘趣酒碗、調味汁瓶等。此外,也有不少定制瓷的裝飾圖案取材于宗教、神話和寓言場景,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對此,《景德鎮陶錄》記載道:“洋器專售外洋者,商多粵東人,販去與洋鬼子載市。式多奇巧,歲無定樣。”以至于“器型之繁,紋飾之豐,數量之多,為前所未有”。
由于中西繪畫理念、技法、主題和文字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中國畫工在收到“式樣奇巧、歲無定樣”的訂單或樣品后,往往無法完全理解樣品的內容與文化背景知識,因而所繪就的瓷器圖案也就難免出現錯誤(例如,經常寫錯紋章瓷上的字母,繪畫題材內容也得不到忠實的表現)。為此,“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于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窯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西商”。在廣州為瓷器裝飾繪彩,便于接受歐洲商人的直接監督和指導,可以避免和減少差錯。對此,1793年跟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約翰·巴羅(John Barrow)有著較為詳細的記錄:“陶瓷廠把大量全素的瓷器運往廣東,購買者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樣式上色……輸往廣東的歐洲彩色版畫在那里被如實地復制。但這樣做時,他們沒有對自己的畫進行思考。原有的或意外的缺點和瑕疵,他們必定照錄。所以他們僅僅是忠實的臨摹者,絲毫沒有感受到擺在他們面前的藝術品的魅力或美麗。”
巴羅雖然贊揚了中國畫工的臨摹水平,但僅僅把他們定性為“忠實的模仿者”,小覷他們無法欣賞歐洲藝術的美麗,并以歐洲繪畫的標準為圭臬,批評中國繪畫不懂明暗對照法,謬誤百出。巴羅本人不懂中國語言,對中國藝術精神也是一無所知。他對中國瓷器繪畫的批評,不僅是無知者無畏的表現,更是體現了蒸蒸日上的大英帝國社會精英的帝國心態。
然而,從中外陶瓷藝術交流的角度來看,“充滿謬誤”的定制瓷開創了一種新的雜交物質文化,豐富了陶瓷藝術的器型與裝飾,促進了不同藝術理念的互通。而從文化轉譯的層面上來看,用中國白瓷裝飾歐洲紋樣的定制瓷,實際上是把中國瓷器以歐洲文化對其進行填充,并有意識地將自己的意愿加諸在中國瓷器之上,否定中國瓷器的紋樣乃至繪畫理念,將技藝精湛的中國畫工貶低為純粹的模仿者,改變中國瓷器原有的器型,用自己所青睞的文飾和器型來取代中國瓷器原本的形式和內容,有著明顯地將瓷器本土化,把他者之物收編為自我之物的傾向。
三、“媲美中國最好的瓷器”:18世紀英國的仿制瓷
“幾乎從18世紀中葉英國開始大規模生產瓷器開始,英國陶工就模仿中國青花瓷的器型和裝飾”。他們仿造的中國青花瓷和德化白瓷足以亂真,受到國人的普遍歡迎。當時最著名的仿制瓷廠有“弓”(Bow)、“新廣州”(New Canton)“沃切斯特”(Worcester)和“利物浦”(Liverpool)等。
1750年,“弓”瓷廠在廣告中宣稱,其所生產的瓷器已近乎精湛,不比日本瓷器差。1763年的《牛津雜志》中的一篇文章則聲稱,沃切斯特瓷廠所生產的瓷器,可以與中國最好的瓷器相媲美:“沃切斯特瓷器的胎體要比它們都更為精細和潔白,甚至幾乎都可以與中國最好的瓷器相媲美。……它是如此地與東方最好的瓷器(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相像,以至于常常被用來模仿中國或日本瓷器,用以替代整套瓷器中的破損器物。它們之間的差別,就算鑒賞家本人也無法察覺,有些時候沃切斯特還會被錯當成外國產品。”
當然,所謂的仿造,并不是機械地復制。在模仿的過程中,英國人往往發揮自己對遙遠中國的想象,挪用中國器物的某些文飾(如山水、樓臺、花鳥等),對它們進行置換、變形和拼貼,最終生產出一個中西合體、古今并置,“符合某種歐洲美學設計傳統而被打上了‘中國’標簽的”雜交瓷器。
更有甚者,不僅在器型和裝飾上假冒中國的名義,還通過文學敘事,為中國瓷器上的裝飾圖案杜撰出浪漫而凄美的“中國”愛情故事,在賺得大量利潤的同時,也迎合了英國人對神秘而古老的中國的好奇。這類瓷器中,最著名、最流行且影響最深遠的便是在18世紀八九十年代由英國陶人托馬斯·明頓(T h o m a s Minton)所設計出的“柳樹紋樣”(Willow Pattern)青花瓷器。此類瓷器上的紋樣以柳樹為中心,在其右側是蒼松環繞的樓閣亭臺和曲欄小徑。柳樹下方有一座三孔石橋,橋上三人正在行走。遠處水面上有一葉扁舟,其上方的空白處則繪有一對飛鳥。
圍繞柳樹紋樣瓷器,英國人還杜撰出了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雖然這個故事有多個版本,但它們所描繪的故事大致相同:一個年輕漂亮的大戶人家女子孔思(Koong Se),不滿父親的姻緣安排,準備與自己中意的青年才俊張生(Chang)私奔。在家中私拿細軟期間,被父撞破,進而被追(橋上三人)。成功逃離后,兩人隱姓埋名過上男耕女織的愜意生活。不想好景不長,行跡敗露,父親隨即帶人棒打鴛鴦。孔思寧死不從,準備點火燒房。危急關頭,天神出面,將一對有情人化為飛鳥,最終兩人得以超脫,從此翱翔天際,比翼人間。
柳條紋樣瓷器及其故事,挪用了中國瓷器裝飾中的一些紋樣,并編造了一個近似于《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故事,然而這些看似非常中國的器物和故事,完全是英國人假借中國元素而杜撰出來的地地道道的英國器物和英國故事。它將遙遠的、神秘的中國視為一個唯美的烏托邦,并借助它上演了一出交織著親情與愛情、背叛與忠貞的浪漫而感傷的故事。故事最終的結局,也是老套的西方敘事手段——在緊要關頭,通過安排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的介入,讓這出悲劇以相對圓滿的喜劇而收場。
讓情況變得更加復雜的是,英國人還將柳樹紋樣瓷器當作樣品,運至中國,讓中國人仿造生產,然后運回英國。如此的出口返內銷的生產模式,不僅進一步加深了此款瓷器源自中國的假象,也讓器物的身份變得更為撲朔迷離,最終使得它變為一款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雜交器物,完成了將瓷器這個他者之物收編成自我之物的使命。
四、結語
18世紀英國植物學家、詩人伊拉斯謨·達爾文(E r a s m u s D a r w i n),在他的詩集“植物園”(Botanic Garden)中,曾謳歌了威治伍德在陶瓷領域所作出的成就,認為后者制造出的瓷器“為英國島嶼打扮了新裝”。18世紀下半葉,英國人在本土找到了高嶺土,并通過設立陶瓷促進機構,發明制瓷工具,革新瓷器產品,改善生產組織程序等方式,使得瓷器獲得長足的發展,乃至創造出了骨質瓷這一新的瓷器品種。之所以能有如此的成就,這與他們在早期通過鑲飾、定制和仿造的方式挪用中國瓷器分不開。研究這一段歷史,不僅有助于了解18世紀英國瓷器發展的歷程,也為我們進一步探索18世紀中英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視角。
[1]North,Michael.Artist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 e t w e e n E u r o p e a n d A s i a,1400-1900,R e t h i n k i n g Markets,Workshops and Collections[M].New York:Ashgate Publishing,2010:1-2
[2]Kerr,Rose,and Luisa Mengoni,Chinese Export Ceramics [M].London:Victoria & Albert Museum,2011:81
[3]Wilson,Gillian,and Francis Watson.Mounted Oriental Porcelain in the J.Paul Getty Museum[M](Revised Edition).Los Angeles:The J.Paul Getty Museum,1999:1,7
[4]吳文婷.18世紀以中國瓷器完成的歐洲金屬鑲嵌工藝[J]。2013(1):110-111頁
[5]Gay,John.To aLady on Her Passion for Old China[C].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2-3
[6]Kerr,Rose,and Luisa Mengoni.Chinese Export Ceramics[M].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2011:39
[7]Woodward,Ian.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M].Sage Publishing Ltd.,2007:p.135
[8]Woodward,Ian.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M].Sage Publishing Ltd.,2007:135
[9]藍浦.鄭廷桂.景德鎮陶錄圖說[M].連冕編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80
[10]萬鈞.東印度公司與明清瓷器外銷[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4):119
[12] 萬鈞.東印度公司與明清瓷器外銷[J].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4):120
[13]喬治·馬戛爾尼,約翰·巴羅.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著[M].何高濟,何毓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313-314
[14]Joseph J.Portanova.“Porcelain,The Willow Pattern,and Chinoiserie”[W].New York:New York Time,2014
[15]Stacey Loughrey Sloboda: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unia,2004:66-67
[16]Valentine Green,A Survey of the City of Worcester[M].London:J.Butler for S.Gamidge,1764:233-234
[17]Eugenia Zuroski,Chinese Things,British Identity,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in the Long Eighteengh Century[D].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2006:9.6
[18]侯鐵軍.茶杯中的風波——瓷器與18世紀大英國帝國話語政治[J].外國文學評論.2016(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