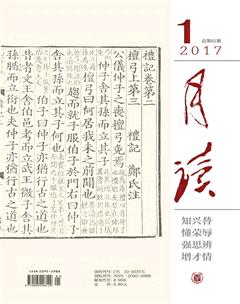唐宋八大家:酷愛讀書的官員
唐曉敏
“唐宋八大家”是家喻戶曉的文學大家,他們還有另一重身份:都是官員——韓愈做過吏部侍郎,柳宗元當過刺史,王安石做過宰相,歐陽修、蘇轍做過副宰相,曾鞏在多地任過知州,蘇軾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蘇洵也當過秘書省試校書郎。這些文豪兼官員,一個共同特點是酷愛讀書。
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一生,即是酷愛讀書學習的一生。在《進學解》一文中,韓愈借學生之口,說自己“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在《上兵部李侍郎書》中又說自己“性本好文學”,“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
柳宗元也是這樣。他遍讀先秦兩漢典籍,在《讀書》詩中說自己“幽沉謝世事,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柳宗元指導韋中立作文,說自己作文的經驗是“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顯然,這些書籍都是柳宗元精讀過的。柳宗元在永州時寫過《辯〈列子〉》《辯〈文子〉》《辯〈晏子春秋〉》《辯〈亢倉子〉》《辯〈鹖冠子〉》等文章,對《列子》等著作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些書籍,自然也是柳宗元仔細讀過的。
歐陽修也酷愛讀書。《歐陽公事跡》說歐陽修自幼喜歡讀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讀書,是歐陽修一生的愛好。直到晚年,他作《讀書》詩,還這樣寫道:“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篇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初如兩軍交,乘勝方酣戰。當其旗鼓催,不覺人馬汗。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幾案。”他把讀書看作天下最快樂的事情。
蘇軾嗜書如命,向來為人所知。他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講:“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于人之耳目,而不適于用。金石、草木、絲麻、五谷、六材,有適于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于人之耳目而適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他認為,唯有書籍是又有用,又能給人帶來愉悅,且用之無窮的。蘇軾一生都在不間斷地閱讀書籍。他被貶黃州時,更是以讀書為樂:“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還留下這樣的趣事:一日他讀杜牧《阿房宮賦》,讀了好幾遍;每讀徹一遍,就再三嗟嘆,到很晚還不睡。有兩個老兵,都是陜人,服侍左右。坐得久了,很以為苦。一人操著口音長嘆:“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另一曰:“也有兩句好!”頭一人大怒,說:“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從中可見蘇軾癡迷讀書之一斑。“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萬卷始通神”,這都是蘇軾讀書的心得體會。
王安石也是無所不讀。既讀儒家經典,也讀其他各類書籍。他在《答曾子固書》中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邵氏聞見錄》還有一個關于王安石讀書的故事,說韓琦任揚州知州時,王安石剛進士及第,在揚州任僉判。王安石每晚讀書至天亮,清晨來不及洗漱就匆忙上班。韓琦疑其不檢點,夜飲放蕩,對王說:“你年紀輕輕,應該認真讀書,不要自棄。”你看,整夜讀書,竟造成了誤會。
在唐宋八大家中,蘇洵認真讀書的時間較晚,他曾說自己“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但蘇洵為讀書,下了非常大的決心。他“每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圣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
曾鞏和蘇轍也都愛好閱讀。曾鞏在《南軒記》中,講自己在這間書屋中的讀書情形:“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托遠、山镵冢刻、浮夸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于此。”蘇轍在《張恕寺丞益齋》中寫道:“人生不讀書,空洞一無有。”“我家亦多書,早歲嘗竊叩。晨耕掛牛角,夜燭借鄰牖。經年謝賓客,饑坐失昏畫。堆胸稍蟠屈,落筆逢左右。樂如聽鈞天,醉劇飲醇酎。”在讀書中體會到純真的樂趣。
唐宋八大家對讀書的酷愛,讓他們有理想,有境界,有才華,有豐富的精神生活。通過讀書,他們開闊了視野,提升了人生境界。讀書讓他們超越身邊環境的局限,能夠了解歷史上志士仁人的精神世界,并受到深刻影響。歐陽修就說:“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瑰杰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后,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唐宋八大家以歷史上的杰出人物為自己的榜樣,因此,他們無論是在哪兒為官,都能為民眾做好事。韓愈在潮州只做了八個月的刺史,卻贏得當地長久的尊敬和崇拜,以至于讓那里的山與江姓了“韓”。
酷愛讀書,讓唐宋八大家有了豐富的精神生活,讓他們因此能夠正確看待和處理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對生活中物質方面的不足,能夠淡然處之。如蘇軾在密州做官時,物質條件很差。他在《后杞菊賦并序》中寫道:“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蘇軾作為一個州官,竟然要去采野菜度日。但他并沒有抱怨,“求杞菊食之”,尚能“捫腹而笑”。顯然,蘇軾對物質生活的匱乏是不甚在意的,這樣的官員,自然也難生貪腐之心。
由于讀書,唐宋八大家特別重視精神生活而看淡物質享受,這是值得敬佩的。可以說,多讀書,讀好書,也有廉政教育的價值。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