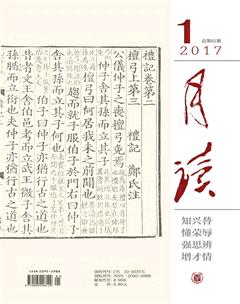答司馬諫議書
某啟a: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b,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c,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d,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e,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f,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g,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h,胥怨者民也i,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j,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k。
(《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
注釋:
a 某啟:古時書信開頭格式,表示寫信人向對方啟告。
b 君實:司馬光,字君實。
c 強聒(guō):嘮叨不休。
d 名實:古時兩個相對的哲學范疇,名指形式,實指內容。《論語·子路》說:“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e 侵官、生事、征利、拒諫:指侵奪官吏職權,制造事端,爭奪百姓財利,拒絕接受諫議。王安石變法,設“制置三司(鹽鐵、戶部、度支)條例司”,“侵官”說的便是此項舉措。
f 人主:這里指宋神宗趙頊。
g 壬(rèn):佞,指巧言諂媚、不行正道。
h 盤庚之遷:指盤庚遷都。商朝原來建都奄(今山東曲阜),因常有水患,盤庚即位后,決定遷都于殷(今河南安陽西北)。這一決定受到百姓、官吏、貴族的一致反對,盤庚先后作有三篇誥文,即《尚書·盤庚》(上中下),說服官民同意遷都,然后“百姓由寧,殷道復興”。
i 胥(xū)怨:相怨,多指百姓對上的怨恨。
j 膏澤:本指滋潤土壤的雨水,用以比喻施加恩惠。
k 不任區區向往之至:古時寫信的客套語,向對方表達仰慕之情。不任,不勝。區區,形容誠懇真摯。
大意:
安石啟:昨日承蒙您來信指教,我認為與您交游往來,彼此親厚,已經很長時間了,但是議論政事時,見解卻常常不一致,應當是我們學術見解和政治方略多有差異的緣故。雖然想強作解說,但最終一定不會得到您的理解,因此只好簡略地復上一信,不再一一為自己辯白。再三思量,承蒙您向來對我看重厚待,書信往來不可粗率冒失,因此我現在詳細說明如此作為(施行新法)的原因,希望或許能得到您的諒解。
讀書人所看重和爭論的,尤其在于“名”“實”之辨。“名”和“實”一旦明辨,天下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清晰了。現在您來指教的,是認為我侵犯官員職權,憑空制造事端,斂財與民爭利,拒絕勸諫批評,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誹謗。而我則認為,接受皇上的旨意和命令,研究法令制度,在朝堂上討論并加以修訂,而后授命相關部門執行,這不是侵犯官員職權;推行先王實行過的政策,興辦于國家和百姓有利的事業,革除弊端,這不是惹是生非;為國家管理財政,這不是為了搜刮錢財;摒棄荒謬錯誤的言論,拒斥奸佞之徒,這不是拒絕勸諫和批評。至于怨恨和誹謗眾多,那是我早已預料到的。
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已不是一天兩天,士大夫們多數認為不需關心國家大事,隨波逐流,取媚眾人就可以了。皇上想要改變這種狀況,而我不考量反對者的多少,只想竭盡全力協助皇上來對抗他們,眾多的反對者怎么會不氣勢洶洶地批評責難呢?商王盤庚遷都殷地時,老百姓全都埋怨,不僅是朝廷上的士大夫而已。但盤庚沒有因為這些埋怨和反對改變遷都計劃,是由于經過深思熟慮而后采取行動,正確的決策無所謂后悔的緣故。如果您責備我占據高位很久,卻沒有能協助皇上大有作為,為百姓帶來恩澤,那我知曉并承認錯誤;但如果說現在應當無所事事,墨守成規,那就不是我能領教的了。
沒有機會和您見面,想念仰慕之至。
【解析】
北宋嘉祐年間,王安石、司馬光同列朝班,特相友善,時與呂公著(字晦叔)、韓維(字持國)并稱“嘉祐四友”。然而,二人卻因治國理念不同而逐漸疏遠。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推行新法,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推行青苗、均輸二法,統籌財政,不意受到士大夫堅決反對。熙寧三年,司馬光連作三書以勸。第一書《與王介甫書》長達三千余字,責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要求廢除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便是對此書的回復。
《答司馬諫議書》針對司馬光的責難,從高處入手,論證變法的名正言順,令指責不攻自破,并且批判了士大夫因循守舊的不良習氣,表現了改革的決心與勇氣。王安石稱,變法乃“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之舉:其制定法令的程序合理合法,先是“受命于人主”,而后“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再“授之于有司”。其目的則是“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為天下理財”。也正是因為變法為“度義而后動”的舉措,所以致怨天下“而不見可悔”。除了正面的辯駁,王安石又宕開一筆,批判士大夫茍且終日,一味“守前所為”,對于這些人的指責,明確表示“非某之所敢知”,態度十分堅決。
王安石所表現出的果敢與擔當,與《宋史·王安石傳》中所說的“三不足”精神相輔相成,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正是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傳承與發揚,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將激勵當代人樹立遠大理想、勇于擔當并堅定前行。
(選自《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百篇》,中華書局2016年10月出版。譯者: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