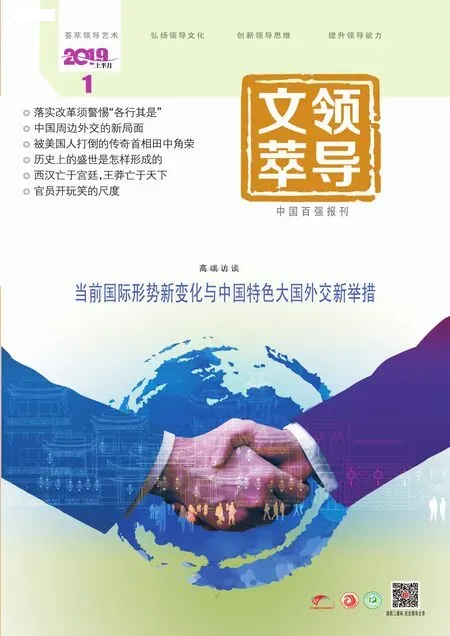事必躬親
任大剛
在中國,“事必躬親”是個蝙蝠型詞匯,它一會兒被當成褒義詞使用,一會兒被當成貶義詞使用,到底是“飛禽”還是“走獸”,要看你的著眼點在哪里。
比如近期的新聞報道中,作為褒義詞,“事必躬親”被用于贊揚某地一名號稱第一“和事佬”的人民調解員;檢查黃河防洪工作;扶貧。被用于貶義詞,則包括某地總工會打破“事必躬親”傳統思維定式,巧借社會專業力量提升服務職工水平;某公司CEO事必躬親,獨斷專行;還有勸告領導何必“事必躬親”的,等等。
在表面上,“事必躬親”是一種工作方式,但如果從韓非子的角度深究開來,恐怕就不是工作方式那么簡單。
齊桓公喜歡穿紫色衣服,全國老百姓紛紛仿效,都穿紫衣服。那時候,五匹素布還抵不上一匹紫布。齊桓公為此憂心忡忡,對管仲說:“如此日甚一日,不能停止,我該怎么辦?”
管仲說:“想要制止這種狀況,為何不自己不穿紫衣服呢?您就對近侍們說:‘我特別厭惡紫衣服的氣味。如果有近侍恰巧穿紫衣服進見,您一定要說:‘稍微退后一點,我厭惡紫衣服的氣味。”桓公照辦了。結果第一天,沒有一個侍從官穿紫衣服;第二天,都城中沒有一個穿紫衣服;第三天,齊國境內沒有一個穿紫衣服。
這是齊桓公身體力行、制止一種陋習的案例。
還有一個故事是有關子產的: 話說子產擔任鄭國的相國。鄭簡公對子產說:“我現在喝酒不能盡興,祭祀器皿不大,各種樂器聲音不響亮。我不能專心于國事,使國家不太平,百姓不安寧,種地的和打仗的人互相扯皮,這些過失也有你的份。你有你的職責,我有我的職責,咱們各自管好自己的職責吧。”于是子產經過五年經營,盜賊絕跡,路不拾遺,桃樹棗樹的果實遮蔽街道也沒有人伸手去摘,錐子刀子丟在路上,三天內就有人送回。這種情形三年不曾改變,民眾沒有再挨餓了。
從工作成效看,可以看出子產主抓的事務實際是很具體的,其中包括以清除盜賊為主的社會治安,厘清物權,搞好農業生產,而不再像之前一樣,跟鄭簡公一起喝大酒,可謂事必躬親。
但據此認為韓非子贊同事必躬親,卻也失之簡單。
宋襄公與楚軍作戰,因為楚軍沒有過河,沒有擺好陣勢,宋襄公拒絕發布作戰命令,等到楚軍做好準備才開戰,結果大敗,自己大腿受傷,三天后就死了。
對這個著名故事,韓非子評價說,這就是追求親自實行仁義帶來的禍害。一定要依靠君王親自去干,然后民眾才聽從,這就是要君王自己種田吃飯,自己排在隊伍里打仗,然后民眾才肯從事耕戰。這樣一來,君王不是太危險了嗎?而臣子不是太安全了嗎?另一個故事是這樣的,魏昭王想親自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孟嘗君說:“大王想參與管理國家的事務,那么為什么不試著學習法令呢?”昭王才讀十幾條法令就躺下打瞌睡了。韓非子問,君主不親自掌握權勢,卻想做臣子應當做的事情,那么打瞌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嗎?
從以上故事,可以看出,“事必躬親”這種工作方法,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厘定其性質。韓非子認為,君王的權勢須臾不可脫離其手,在這個前提之下,你干什么都可以,包括“事必躬親”,如果權勢不在手上,“事必躬親”恐怕是加速滅亡的昏招。
而在今天,如果民意和信息是暢通的,那么是否事必躬親,就不應該那么截然對立了。
(摘自《雜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