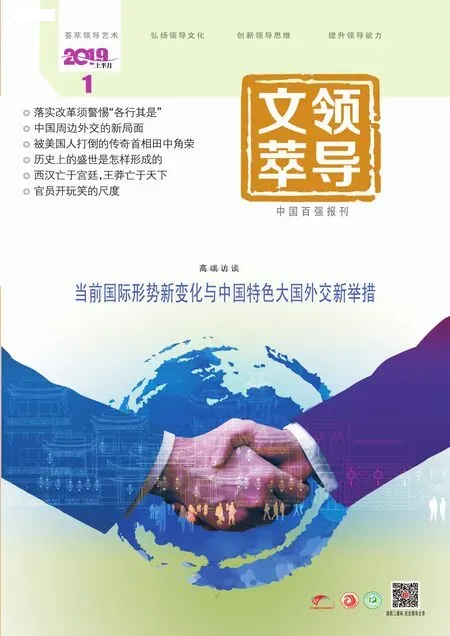周恩來:“退休之后想去演話劇”
梁秉堃
周總理是北京人藝的奠基人、創業者,他提議建立第一個“全國專業話劇院”,并推薦曹禺當院長,還批準建設首都劇場……
正如冰心所言:“我所見過的和周恩來總理有過接觸的人,無不感受到總理特別的關心和愛護。這并不奇怪,因為總理付出的‘愛最多,接受的‘愛也最多。”那些與周總理在一起的日子,人藝人無法忘懷。
導演間的“特殊座位”
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周總理喜歡看北京人藝的戲。但他日理萬機,工作很忙碌,經常要等到下午工作結束后,才問秘書晚上有沒有安排,如果沒有就去看戲。
那時,首都劇場的楊經理在演出前,都會留幾張票以備不時之需,一般會等到演出半小時后才會把這幾張票處理掉。一天,楊經理剛把預留的幾張票售出,突然接到通知,總理要來看戲。無奈之下,楊經理只好把第7排中間幾個座位的觀眾換到其他地方。不久后,周總理來到劇場開始看戲。
中途,周總理到小休息室休息,他問道:“我坐的座位上原來是不是有人?”楊經理只好說出實情。周總理有些激動地說:“胡鬧!人家先來,我后來反而要把人家趕走,不能這樣。楊經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請回原來的座位,還要道歉!”周總理停頓了一下,又說,“劇場里不是有個導演間嗎?我就在里面看戲好了。”
從此以后,似乎有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周總理只要遲到了,就要到看不太清又聽不太見的導演間里去看戲,不能有特殊安排。
于是之被批“臺詞不清”
1961年夏天,劇院正在演出《雷雨》。一直支持曹禺這個代表作的周總理再一次來看戲。
新中國建立以后,《雷雨》由北京人藝首演,演員也是全新的陣容,其中,于是之扮演周萍。在一次演出中場休息時,導演夏淳跑到后臺,告訴于是之:“總理對你的臺詞不滿意,聲音太小。”演出結束后,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夏衍來到后臺,對于是之說:“你要做好準備,總理會批評你。”
隨后,周總理來到小休息室,大家落座后,于是之很緊張。但周總理并沒一開口就批評于是之,而是首先談到“大躍進”中一些過火失當的行為,勞逸結合注意不夠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
直到最后,周總理才把話題轉到于是之身上。他說:“你的聲音太輕,觀眾聽不清,不好。”接著又說,“一個演員在臺上要做到‘目中無人,心中有人。眼睛老看著觀眾就忘了戲里的環境和人物關系,但只顧自己的‘真實,心里忘了觀眾,聲音小得叫人聽不見,也就沒有了群眾觀點。”
親自過問兩出劇
1961年4月,周總理來到首都劇場,觀看歐陽予倩的作品《潘金蓮》。演出結束后,他還專門召開了座談會,邀請劇作者、導演、演員、劇院領導人等參加,并讓他們各抒己見。不少人提出了這出戲里的不足之處。
隨后,歐陽予倩說:“1924年寫戲時,我看到許多婦女受壓迫,心中很悲憤,就寫了這出戲。”周總理說:“歐陽老說到當時的思想活動,我完全理解。可這個戲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慮對青年人的影響。張大戶壓迫潘金蓮,她反抗值得同情。可后來她殺了一個老實的農民,還和西門慶私通,這就沒法讓我們同情了。如果她為了求解放,選擇出走或自殺,會使人同情。”大家紛紛點頭贊同。周總理看了看歐陽老繼續說:“我見到劇中的問題,覺得應該向你提出來。你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太好,一定多保重。”就這樣,一個帶有原則性的戲劇創作座談會,在推心置腹的氣氛中結束了。座談會后,劇院決定停演《潘金蓮》。
1958年,老舍的新作《茶館》在首都劇場演出,很快出現“一票難求”的場面。但中央文化部的一位領導嚴厲批評北京人藝領導的“右傾”思想,在組織創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掛帥而是專家掛帥”。實際上,是在指責《茶館》為民族資產階級“大唱挽歌”。于是,連續上演59場的《茶館》被打入“冷宮”。
周總理聽聞此消息后,跟于是之說:“請你轉告黨委書記,《茶館》這個戲改一改還是可以演的嘛!”
1963年7月7日下午,周總理看了《茶館》后,向焦菊隱和黨委書記趙起揚說:“《茶館》這個戲沒問題,是一出好戲。第一幕發生的時間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過這個意見不要向下傳達,以后我親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如果不是周總理及時“出手”挽救,恐怕觀眾就無法欣賞到《茶館》了。
總理的話劇情結
周總理先后在人藝看了41次演出,而且每次看戲以后,都堅持要到舞臺上來,向全體演職人員表示感謝,還要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周總理來看現代劇目《年青的一代》。演出結束以后,他照例來到舞臺中間,談了二三十分鐘。他不僅提肯定意見,也會提出批評,比如指出某個女演員的褲子過短不大好看,等等。當時周總理的話音剛落,導演立即表態:“那好,我們一定按照總理的指示修改。請總理放心!”
正當大家鼓掌時,周總理的神情突然嚴肅起來。他說:“我談的并不一定對。我看,藝術作品的好壞要由群眾說了算,而不是由一兩個領導決定。今天談的話如果是經過集體討論的中央決定,那一定要執行。至于我個人的意見,僅供參考。”說到這里,他微笑了一下,“盡管我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觀眾,但畢竟也是一個人嘛。”掌聲再一次響起。
周總理的藝術情結大約要從他18歲在南開學校發表的一篇文章算起。他在《吾校新劇觀》中主張:“新劇的內容,是不要脫離現實;新劇的形式,應該是語言通暢,意含深遠,悲歡離合,情節昭然。”同時,周總理還在“南開新劇團”里,改編劇本、評論演出、扮演角色……他扮演過《一元錢》里的孫慧娟,當時不允許女生登上舞臺,他就主動承擔了“男扮女裝”的角色。
20世紀70年代初,周總理一再對人們表示:“我退休之后想去演話劇,就扮演曹禺寫的《家》里那個大少爺。現在看到的演出都不太滿意,我是有這種封建家庭生活經歷的,完全可以演好。”
有人說:“如果今生周恩來總理沒有做政治家的話,那么他肯定會是一個優秀的藝術家。”
(摘自《中國文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