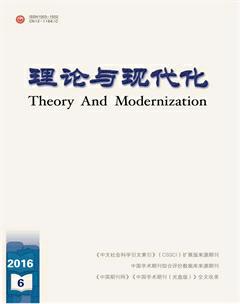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與中國城鎮化反思
陳然
摘 要:自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術界發生空間研究轉向以來,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已經經歷了理論開拓、全面發展和多元發展的階段,尤其是在城市社會來臨的背景下,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具有了新的理論意義。城市作為一種空間組織形式,是新馬克主義空間理論產生和發展的“場域”,其空間重組與再造是資本積累和空間權力共同作用的結果。事實上,空間生產作為中國城鎮化的重要內容,同樣也充斥著資本的邏輯和權力的力量,這種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鄉空間分異、鄉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構和“城—鄉”社區空間與身份認同的迷失。因此,如何重構漸漸趨式微的“熟人社會”,以及如何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變應是中國城鎮化發展關照的核心問題。
關鍵詞: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空間生產;資本循環;城市變遷;鄉村城鎮化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6)06-0118-08
“20世紀的社會理論歷史是時間和空間觀念都缺失的歷史” [1]。但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空間理論研究似乎正在成為當今學術界的新熱點,亦成為分析社會問題的全新視角。正如福柯所認為的,“20世紀預示著一個空間時代的來臨,我們正處在一個同時性和并置性的時代,我們所感知和經歷的世界正在成為一種時空節點的相互聯接”[2]。“空間研究漸漸成為一門顯學,人們對于空間的實踐意義更加關注,關注人作為空間主體性行為和空間的生產,空間正在變為一種社會生活的經驗事實”[3]。因此,空間作為一種新的敘事和理論轉向開始逐漸進入地理學、社會學和城市學的研究視野,形成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其中以列斐伏爾、哈維、卡斯泰爾斯、索佳等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城市學派,正式開啟了社會理論的空間研究轉向,成為理論體系相對成熟的空間研究理論體系。作為一種研究視角,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所強調的資本積累、空間生產和集體消費等核心議題給當下中國的城市社會變遷帶來雙重啟發意義。一是“社會—空間”理論為認識、解讀和反思城鄉空間變遷提供新的路徑;二是轉型期的中國城市也為“社會空間”理論的發展提供了“現場”和“診斷所” [4]。
一、歷史與脈絡: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緣起與發展
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出現了“資本主義城市危機”(城市郊區化、失業率增加、工人運動和勞資沖突等)。在這一背景下列斐伏爾、哈維和卡斯泰爾斯等一批學者敏銳地洞察到城市空間正在成為資本主義緩解危機的“商品”。因此,“城市作為資本主義場域下促進生產、交換和消費的空間,開始被真正研究。城市化是資本主義所有方面的對立統一體” [5]466-479。而一批社會學、地理學、城市學和政治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紛紛將研究的視角和主題轉向城市(空間),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空間的研究來獲得新的理論創建。在此基礎上,根據歷史線索和研究主題,本文將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發展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理論開拓階段: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這一時期的理論特征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和結構主義理論,研究城市(空間)的政治性和階級性,“這使得城市社會學的每一個理論闡釋都隱含了馬克思的‘幽靈” [6]。卡斯泰爾斯也認為自己是“采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采用法國學者路易斯·阿爾杜塞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并以此來認識城市現象的”[5]86。因此,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主題主要涵蓋了資本積累、空間資本化和城市運動等方面的內容,研究者力圖分析城市空間資本化和集體消費作用下的資本主義延續和擴張。代表人物包括哈維、列斐伏爾、卡斯泰爾斯、瓊·洛基肯、克里斯坦·托波羅夫和戈達德等一批法國學者。列斐伏爾在這一時期的理論成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他首先認為城市是系統性的存在,是人的社會性的空間化表現,體現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一定意義上,空間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占有空間并生產出一種空間成為資本主義減緩危機和實現資本積累的主要手段之一。為了實現其空間理論的系統化,他還通過類型學視角將空間劃分為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s)、空間的表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與表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個要素,即分別對應空間的實在(lived)、想象(conceived)和認知(perceived)等三個層面。實際上,他的空間理論已經從研究的客體視角轉向了主體視角,大大拓寬了空間理論的外延。曼紐爾·卡斯泰爾斯(Manuel Castells)①對于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研究也是從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解釋城市問題開始的。他的代表作之一《城市問題:馬克思主義方法》(1972),被看成是開展馬克思主義空間研究的“最重要的城市社會學著作之一” [7]。哈維在這一時期的突出貢獻則是提出了資本的“三次循環”理論,以此來分析資本主義與城市空間的關系,具體可見其《資本的城市化》一書。在哈維看來,城市(空間)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表現,因此“城市化是資本的積累過程。城市作為特殊空間,使得勞動力、商品和資本要素自由流動,見證了組織關系和空間關系的變革,同時又產生了矛盾和沖突。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資本的控制下產生的,直接體現了某種政治權力”[8]。
(二)全面發展階段:現代性視角下的空間思考
這一階段是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研究的全面發展時期,不僅涉及領域多(社會學、城市經濟學、地理學和城市規劃等),而且研究的主題也更為多元化。尤其在全球化和現代性的背景下,研究者更加關注空間形成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機制,以及考察當代社會城市空間安排的結構化演進過程。雖然,這一時期有關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成果的作者并非都是新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城市、資本和階級沖突的理論。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是大衛·哈維、馬克·戈特迪納、華勒斯坦、梅西、哈維·莫洛奇、喬·R.費金和沙倫·朱肯等。列斐伏爾指出,“空間是社會的生產。空間已經不僅僅是指事物處于一定的場景之中的那種經驗性的設置,也是指一種態度與習慣實踐,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社會秩序的空間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Social Order)”。他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進一步指出:空間已經在當前的生產模式中成為一種現實,與商品、金錢和資本一樣承擔著全球化進程的使命。卡斯泰爾斯則認為,現代性背景下現代資本主義越來越依賴國家提供的城市物品和服務,即“集體消費”,以此來充分保證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集體消費在空間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容易導致勞資斗爭,進而演化為國家和城市社會運動間的矛盾。而這一矛盾恰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的結構性矛盾,“表明馬克思所關注的發端于勞動過程的矛盾已經讓位于因‘集體消費不足而導致的城市社會運動”[9]。馬克·戈特迪特(M. Gottdiener)在批判傳統城市空間研究的過度技術化傾向的基礎上,強調城市研究的“社會—空間”視角,并認為空間關系涉及資本、勞動和技術變遷。他還著重分析了政府和房地產在改變城市空間結構中作用及其資本運作機制。吉登斯對于空間的研究則是放置于社會結構性視角下來分析的,其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借鑒時間地理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諸如區域化、時空抽離、場所、在場和不在場的空間概念;二是利用這些概念來分析社會互動在空間結構中是如何影響和改變社會的資源分配和運行機制。因此,吉登斯是將社會結構與空間結構聯系在一起分析的。
(三)多元化發展階段:后現代視野下的空間轉向
進入20世紀80年末和90年代初,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轉向和趨勢,突出表現為:一些學者開始將“后現代主義、后福特制和后資本主義”等后代性的理論視角運用到城市空間的研究中。正如哈維所認為的:“空間重組成為后現代時期的核心議題。時空壓縮導致的文化實踐與政治實踐出現劇烈的變化,這構成了后現代時期的重要特征”。蘇賈則是通過批判性視角進入空間理論研究,并發展出了一套“空間—歷史”辯證法。他用“三重辯證法”(社會性、空間性和時間性)來透視空間與社會的關系。福柯則致力于權力與知識空間化趨勢的考察[10],他的空間理論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認為空間是構成社會權力運作的場所和媒介,我們的生活是在空間中被安排的,如學校、醫院、監獄、超市、公司等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場所和區域。為此,福柯還大量使用空間的隱喻來表達空間的無處不在,如位移、區域、領土、景觀、地平線、群島等[2]。二是福柯關于空間與知識的關系,在他看來,在后現代語境下知識能夠改變空間和實施權力。“知識一旦按照區域、領地、移植、置換和過度來加以分析,人們就會捕捉到知識作為權力形式和傳播權力效應的過程”。可見,后現代語境下新馬克思空間理論更多地是沿著“空間—權力—知識”的邏輯展開的,它們不僅承認空間的實現性和普遍性,而且都對關系、知識和權力對空間的塑造進行了重點的理論關照。蘇賈更是致力于整合各種空間理論論述來形成一般意義上的后現代空間理論。哈維則提出了后現代主義視角下的空間體驗與“時空壓縮”。他認識到,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空間是被淹沒下“時間—歷史”的維度中,而后現代主義則重新發現了空間,并將其作為獨立存在來研究。哈維將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的時空體驗稱之為“時空壓縮”,旨在說明“后現代主義條件下,時間在加速和空間范圍則在縮減” [11],而原因依舊是資本主義的本性在于“用時間來消滅空間” [12]。20世紀80年代中期,卡斯泰爾斯開始轉向信息化網絡研究,相繼出版了《信息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1996)、《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1997)和《千禧年之終結》(End of Millennium)(1998)等三部曲。他在書中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信息技術正在改變城市的形態和整個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對地方之間互動性的強調,使得空間之間形成流動的交換網絡,促使了新型城市空間即流動空間的興起”。
二、資本積累與空間權力:城市空間生產的邏輯
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是在資本主義城市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也是最先被運用到城市(空間)問題的解釋中。因此,從一開始城市及問題研究就成為了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主要研究議題。可以說,城市不僅構成了新馬克主義空間理論產生的社會條件,更是成為理論運用與發展的實踐“場域”。總體上來看,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關于城市研究是以空間的社會性為理論原點,進而以資本和空間為核心變量。
(一)資本循環積累:城市空間塑造的重要動力機制
“資本流通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前提條件。為了解決過度投資和過度生產(資本第一循環)所帶來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價值,過剩的資本就需要尋求新的流通方式,即資本轉向對建成環境(特別是城市環境)的投資,進而推動城市的擴張和發展(資本第二循環)。由于資本轉化的暫時性和循環性,使得資本積累創造的城市空間帶有很大的不穩定性,隱藏了一定的城市危機(城市無序擴張和大拆大建),進而為進一步的資本循環和積累創造條件” [13]。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資本循環和積累構成了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機制。雖然列斐伏爾和哈維對資本主義的過度積累持批判態度,但是資本作為城市發展的要素是不容忽視的。同時,也在馬克思主義與城市研究之間嫁接了一座橋梁。
哈維延續了列斐伏爾的資本循環理論,認為面對過剩的資本和勞動生產力,資本主義往往通過城市建設等生產項目將資本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以空間換時間。哈維將資本積累與城市化的關系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是資本第一循環的結果,生產部門的危機是城市發展的最主要動力。防止危機的有效方式就是用長期計劃來吸收過剩的資本。二是城市物質環境的建設有助于加快資本積累,在一定時間內維護資本主義的穩定。這樣越來越多的資本被嵌入到空間中被當作土地資本或固定在土地上的資本,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第二自然”(經由人類改造的自然,城市構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三是資本主義城市化與資本積累之間依然存在著矛盾和沖突。為此哈維用“空間修復”(spatial fix)來說明這一空間邏輯。理論上,這種“修復”包含著兩層基本含義:第一,資本危機在空間上的修復,是指“整個資本的其中一部分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內以某種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國土之中和國土之上” [14],二戰后美國郊區化的發展,為資本開拓了新的市場,也刺激了新的消費需求;第二,資本危機在時間上的修復,即“資本主義通過時間延遲和地理擴張來解決資本危機的特殊辦法”,如資本主義的“分期付款”金融政策將大量住宅擁有者成為負債人,在某種意義上建立了資本與負債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在時間上達到緩解資本主義危機的目的。事實上,我們看到了資本積累與“空間修復”對于影響城市化發展的意義。
(二)權力與沖突:城市空間占有與分配的社會性與政治性
空間充滿著社會關系,它不僅靠社會關系來維持,也在生產著社會關系。正是空間的這一社會性決定了空間具有政治性,空間離開意識形態就不再是一種科學的對象,它總是包含著政治性和策略性。在列斐伏爾看來,城市居住空間分異、空間等級和人際距離都是空間社會性和政治性的表現。為了從空間主體實踐視角進一步說明空間的社會屬性,列斐伏爾劃分出了三種不同空間活動類型:“物質空間活動、空間性標識和標識性空間,強調不同空間給人帶來的感知、實踐和想象”。在此基礎上,哈維從人與空間互動出發,概括了空間的三種特性:“可接近性與距離、空間的分配與使用、空間的控制” [15]。進一步,哈維將空間的社會性引入到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的階級性分析中,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空間關系浸透著階級含義,空間受到性別、種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影響” [15]。顯然,資本主義城市空間已經變成了包含社會關系的“抽象空間”,甚至空間本身已成為商品。因此,“我們現在得出一個實質性的觀點:資本主義通過對空間的征服和整合而得以延續。空間不再是被動的地理環境和幾何體。它甚至已經是國家機構的一種工具”。
根據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理論,城市既是社會結構,也是權力結構,具有政治性。無論是空間的社會分異,還是資本積累和“集體消費”作用下產生的階級矛盾和權力斗爭,都決定了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中存在著矛盾和緊張,“資本主義社會的關系不可避免地大量產生激烈的相互沖突” [16]。卡斯泰爾斯在《城市與民眾》(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1983)一書中著重分析了歐美社會的城市社會運動。在他看來,城市是政治經濟關系的產物,城市社會運動的本質是城市居民對政府權力的反抗,是城市民眾為了獲取高水平的“集體消費”、社會文化的改造與認同和政治上的自治管理等目標而進行的維權斗爭。
阿德爾納·約翰·雷克斯是從城市住宅的角度來分析不同住宅階級之間的沖突的。他在《種族、社區和沖突》(1967)中指出,城市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和階級沖突中“被構建的環境”(Greated Environment),其中住宅對階級形成和階級沖突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城市中存在不同的高低不等住宅階級,國家提供的國民住宅為低收入者提供了優惠。但是背后交織著多種權力關系,哪些人能夠擁有國民住宅顯然是官僚、市場和權力等多種因素平衡的結果。這為不同住宅階級之間、政府和民眾之間埋下了沖突的根源。英國另一位學者帕爾在雷克斯的基礎上,提出了“城市管理者”理論,指出資源分配不平等是造成城市社會沖突的根源。他認為城市資源的分配是由處在優勢經濟結構地位和擁有權力的科層官僚所決定,因此,城市是典型的“社會—空間”體系。此外,哈維的《后現代性的條件》(1989)、沙倫·朱肯的《后現代城市景觀:文化與權力研究》(1992)、喬·R.費金的《新城市理論》(1998)和馬克·戈特迪納的《新城市社會學》(The New Urban Sociology)(1994)等。這些著作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通常用“權力—沖突”和“權力—階級”的理論概念來分析城市問題。
(三)空間重組與再造:“流動空間”與全球城市化網絡
20世紀后半期以來信息技術與社會變遷的互動,對城市與空間產生了實質性的沖擊。一時間“全球化空間”、“全球城市網絡”、“世界城市”等概念成為潮流。全球化與地方之間的互動,打碎了行為的空間模式,城市空間成為流動的交換網絡,并促使新的空間即流動空間的興起。為此,卡斯泰爾斯認為,全球化使時空不斷被壓縮,全球化中的城市社會正在變成“網絡社會”。在網絡社會中,地點空間的邊界正在變得模糊,空間在新技術的作用下正在被不斷壓縮,地點的作用也在被弱化。
與流動空間和網絡社會相伴而生的另一個主題是城市空間的異化。薩森在其《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1995)一書中提到:所謂的全球化城市已經成為世界經濟、政治和權力交叉重合的空間。全球化作用下的“權力空間幾何學”,正在以幾何級的速度和廣度在全球城市網絡中實現著權力的蔓延與擴張,從而加劇了資源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平等。因此,我們看到的各種空間極化現象,“富人堡壘型社區、紳士化社區、城市群、居民空間分異、邊緣城市、城中村、貧民窟等都是城市空間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典型表現” [17]。Smith在《全球視野中的第三世界城市》(Third World Cities in Global Perspective)(1996)一書中以一種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方式,分析了世界體系擴張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城市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形成原因。蘇賈(Soja)在《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2005)一書中主要采用了“社會—空間辯證法”分析了全球化浪潮下城市面臨的諸如后殖民主義、階級和女權主義等問題。美國社會學家沙朗·佐京(Sharon Zuki)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2006)也認為在全球城市化背景下,文化已經不再是人類生活的附屬地位,儼然已經成為同經濟一樣控制和影響城市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決定城市競爭力和發展模式的關鍵性要素。
三、理論與實踐:空間理論視角下的中國鄉村城鎮化反思
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鄉村的城鎮化,而鄉村的城鎮化也構成了現代意義上“城市化”過程的主要內容。這一過程中,工業文明取代農耕文明,現代生活方式取代傳統生活方式,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現代意義上的城市逐漸代替自然增長的城市,也最終使城市戰勝了鄉村” [18]。因此,在現代與傳統的相互作用下,中國的鄉村城鎮化是一個交織著各種政治、經濟、權力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城鄉社會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如大規模的征地運動、城鄉結合部的“過渡性社區”、失地農民問題、城中村和農民工進城等社會現象和問題的出現。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源于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城市危機的批判性反思,是否可以被運用到中國的城鎮化發展的解釋與研究,國內學者自2003年②以后已經做了積極的嘗試。在閱讀大量文獻的基礎上,本文嘗試著運用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分析邏輯和主要議題,來分析當前中國鄉村城鎮化進程中的現象與問題,一方面通過文獻閱讀梳理出國內相關研究的主要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現有的理論研究的梳理,尋找到將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運用到鄉村城鎮化分析的新視角。
(一)資本邏輯下的城鎮空間生產
根據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城市化空間即是資本的空間化,體現的是資本對利益追求在城市空間的塑造過程。“城市空間在本質上是一種資本建構的環境,是資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結果” [16]。因此,城市空間具有資本性和文化性,具有一定的“城市文化資本”③的價值與意義。這一空間生產的資本邏輯,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的城市分析,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鄉村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劇烈變遷。表面上來看,鄉村城鎮化過程體現的是鄉村空間與社會的變遷,而真正推動鄉村城鎮化的卻依然是資本的作用機制。本質上看,鄉村城鎮化是城市資本積累在鄉村的延續。如土地增減掛鉤的政策,使得鄉村土地被占用變得合法化,大量的農民被“制度性”地安排到城鎮社區集中居住,形成所謂的“準城鎮化群體”。而城市的資本力量不僅獲得了資本投資的新項目,而且通過房地產的開發和“房貸”與農民之間建立了某種“利益機制”。因此,中國各地出現的各種撤村并點、過渡性安置社區和新型農民社區等,事實上依舊是城市資本力量和政府權力控制和作用下的結果。如臺灣學者夏鑄九④在分析臺灣彰化縣的空間變遷中論述了在經濟發展和利益的驅動下,空間結構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過程,并開創性的提出了一個如列斐伏爾和蘇賈“三元空間觀”相對應的“經濟—政府(政策)—文化分野” [19]新的空間觀。費孝通先生在《江村經濟》一書中對于開弦弓村社會變遷的記述,同樣是向我們展現了一個鄉村在資本和市場的作用下,如何實現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在觀察中國村莊轉型中,毛丹也認為“鄉村被越來越卷入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建構過程中,城市與農村,市場與農村之間的關系正在被重新整理和安排”[20]。
(二)城鄉空間的權力性與不平等性
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具有政治性。空間不僅是發生沖突的場所,也是斗爭的目標本身。因此,空間是一種政治和權力的生產” [21]。空間的生產、占有與分隔正是政治和權力的體現,因此,城鎮空間也往往成為社會力量博弈和對抗的場所。這一理論同樣也適用于中國的鄉村城鎮化分析。根據卡斯泰爾斯的觀點,城市是作為“集體消費”的空間“場域”而存在的,由于集體消費品主要是政府來供給,地方政府利用公共資源的壟斷權力,如企業一般地追求短期政治利益。因此,政府利益與城市增長的雙向“尋租” [22]現象就會發生。在這一權力機制的作用下,鄉村城鎮化中的強制拆遷和補償不均等現象時有發生,成為政府與群眾沖突的主要原因。而沖突中所謂的農民集體行動,已經不再是環境中的個人困擾,甚至演化為“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話題”[23]。如張鵬⑤在《都市里的陌生人》書中,指出了空間本質的政治性,并分析了表現于其中的權力關系。楊念群則直接運用空間與權力的理論對城市醫療空間轉向進行了分析,描述了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如何被侵入、打破和重組[24]。因此,國家和政府權力對傳統區域的侵入,不僅容易破壞原有的穩定的生活秩序,而且這種空間權力又在塑造著空間中主體的行為。如潘澤泉主要通過運用“社會空間”理論,來研究農民工的“主體性”存在,即國家權力對農民工主體的塑造力量,以及農民工作為主體與這種塑造力量相抗衡的過程 [4]。朱健剛認為,社區存在“權力的三重組織網絡”;李友梅則從社區的日常生活框架,提出了簡單社區、復雜社區和流動社區的分野。一個可見的事實是,研究者們已經明確認識到城市空間并非一個被動的容器,而是一個“由資本、法律、秩序構造的空間,展示的是合乎資本與權力運行邏輯的自然結果:不同收入階層所占據的被分割的生活、生產及消費的空間和場域”。
(三)鄉村日常生活秩序的沖擊與解構
列斐伏爾不僅開創了“空間生產”的理論維度,還有力地將空間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引入空間的生產過程中,實現了向日常生活實踐的社會空間轉向,將空間的普遍性分析“嵌入”到了“在場”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因此,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分析的“三位一體”⑥架構,就成為分析空間生產對于日常生活秩序解構與重構的依據。在資本和國家權力的入侵下,城鄉社會結構會出現“侵入與接替”⑦的變遷過程,這一過程主要包含“三種形式:一是城鄉間物質和文化的對流;二是資本和市場的傳導;三是城市現代化生產生活方式對鄉村的輻射” [25]。哈維在《后現代現狀》一書中也指出,“時間和空間的客觀概念必然通過物質實踐與過程創造出來,這些空間實踐過程再生產了社會生活”。而中國鄉村城鎮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在市場和國家權力的作用下,原有的鄉村日常生活秩序逐漸解體。李培林在《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一書中運用村落邊界和生活空間半徑分析了城鎮化過程中居民日常生活秩序的變化。一個基本結論就是:“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村民,其三大村落邊界實現了分化,村民的生活半徑得到了大大的延長” [26]。臺灣人類學家黃應貴也認為空間變遷重塑了主體行動者的生活習俗、聚落形態、家庭結構和儀式空間等。張京祥在對南京江東村的空間與社會變遷的實證研究中,論述了江東村居民是如何從傳統農業生產者轉變為工業生產者的過程,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在資本和市場的沖擊下發生的變化。因此,在鄉村城鎮化的過程中實現的空間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和瓦解了傳統鄉村的日常生活秩序,居民的自然、社會和文化邊界逐漸走向分離,傳統走向消失,現代性成為新的文化特征。
(四)“城—鄉”社區空間的體驗與身份認同
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空間性”概念即人們在創造和生產空間的同時,也受到空間的形塑與影響,以尋求主體性身份認同和本體性安全空間。因此,列斐伏爾將(社會)空間看作是一種社會化產品,每一個社會和每一種生產模式都會生產出自己的空間。因此,將空間生產的理論分析延伸到“日常生活”領域,實際上是強調了社會行動者主體意義上的實踐模式,更加注重對行動者主觀感知的分析。在以往關于中國鄉村城鎮化的研究中,人們把主要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鄉村空間的整體敘事分析上,而較少關注作為行動者農民自身主觀意義上的空間體驗和身份認同。而農民對于空間的體驗和感知,恰恰反映是空間社會性最真實的表現。“從空間視角來看,鄉村城鎮化的過程是傳統空間被打破,逐漸走向城鄉空間一體化的過程”[27]。傳統的“熟人社會”結構被解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全新的社會關系網絡。從“鄉土”中被“解放”出來的農民不得不面對全新的空間,體驗著另一種生活方式,也需要重塑主體意義上行動模式。由于現階段鄉村城鎮化大多是政府權力和資本驅動下產物,并不是農民自發的行為。因此,“失地農民在被動城鎮化的過程中,會出現自我認同失調的問題。主要原因是失地農民是被動城鎮化的,時間性效應致使自我認同的轉換滯后于物質搬遷,空間性效應帶來的相對剝奪感也阻礙了自我認同系統的轉換” [28]。為此,有學者⑧提出從“社會身份完整、角色期待、賦權和環境互動等方面,實現新舊角色之間轉換的道路通暢” [29]。因此,在鄉村城鎮化的過程中,作為空間實踐主體的農民面臨著新舊空間的體驗變遷。尤其是對于已經喪失傳統“熟人社會”關系網絡的失地農民來說,如何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變就成為了一個必須要關照和解決的問題。
注釋:
① 卡斯泰爾斯曾是列斐伏爾的學生,直接受到前者的影響,但同時又有自己的批判。卡斯泰爾斯將列斐伏爾的空間研究和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理論結合到自己的城市研究中,建立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框架。
②整體上講,大陸學界對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的研究起步較晚,大量的有關研究基本上都出現在2003年之后。因此,大陸學者運用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經驗性研究也在2003年以后。(根據CNKI知網的文獻主題搜索,搜索“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共有文獻214篇,其中發表于2003年之后的文獻是179篇,占總數的83.6%,而2003年之前的僅有35篇,只占總數的16.4%)
③“城市文化資本”這一概念是由南京大學張鴻雁教授在布迪厄文化資本意義上首次提出來。詳見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由張鴻雁所著的《城市文化資本論》。
④臺灣夏鑄九是國內最早將新馬克思主義社會空間理論引入并運用到實證研究的學者。他早在1988年就將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引入實際的研究分析,在對臺灣彰化縣的空間變遷研究中,論述了國家是如何通過政策的中介來對待經濟發展,以及空間結構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在這項研究中,夏鑄九將空間理論運用到實際研究為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在中國的實證研究開創了出色的范例。
⑤張鵬的《都市里的陌生人》首先明確將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應用于中國大陸社區的人類學研究,他認為“社會空間”在后社會主義時期的權力、空間、政治和國家—社會關系的重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她在研究中特別強調空間的可生產性,并指出空間本質的政治性,分析了表現于其中的權力關系。
⑥列斐伏爾提出的空間生產的“三位一體”,對應的分別是空間實踐(涉及主體行動)、空間表征(屬于想象層面的行為,包括各種符號)和表征空間(代表著生活經歷)。
⑦根據張鴻雁的觀點,區域空間結構演變一般分為四個四階段:第一,低水平均衡發展階段,表現出城鎮規模小和封閉性結構特征;第二,核心集聚式發展階段,出現區域性“發展極”;第三,城市擴散功能階段,城市的邊界得到大大擴展,形成區域城鎮群結構;第四,高層次均衡發展階段,變現為網狀化和多中心化。
⑧毛丹在結合實證的分析中,還進一步指出:城郊農民市民化是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大命題,并且承認政府運用撤村并居的辦法在推進城郊農民市民化至少有一個方向性的積極意義,即通過政府的行政干預和政策引導,讓農民能夠順利實現群體角色的轉換。
參考文獻:
[1] 約翰·厄里. 關于時間和空間的社會學[M]//布萊恩·特納,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M]. 李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5.
[2] 米歇爾·福柯. 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M]//包亞明. 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8-28.
[3] 潘澤泉.空間化——一種新的敘事和理論轉向[J]. 國外社會科學,2007(4).
[4] 潘澤泉.社會、主體性與秩序:農民工研究的空間轉向[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3.
[5]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77.
[6] William G. Flanagn, Contemporary Urban Sociolog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86.
[7] Kieran Mckeow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rxist Urban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s[M].1987:95.
[8] 大衛·哈維.希望的空間[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8-9.
[9] 孫江. 空間生產——從馬克思到當代[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9.
[10] 何雪松. 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J]. 社會,2006(2).
[11] 包亞明. 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89.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
[1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46-53.
[14] 大衛·哈維. 新帝國主義[M]. 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72.
[15] 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M].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1989:262.264.
[16] D. Harvey.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M].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1985:15-16.
[17] S.Sassen.Rebuilding the Global City: Economy Ethnicity and Space,Anthony D.King ed,Re-presenting the City: Ethnicity,Capital and Cul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etropolis[M].London: Macmillan,1996:23-42.
[18]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8.
[19] 夏鑄九. 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臺灣彰化平原的個案[J]. 燕山大學學報哲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
[20] 毛丹.村莊大轉型[J].浙江社會科學,2008(10).
[21] 列斐伏爾. 空間政治學的反思[M]//轉引自包亞明. 現代性與空間生產.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9-62.
[22] 張應祥.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述評[J]. 學術研究,2006(1).
[23] 米爾斯. 社會學的想象力[M]. 北京:三聯書店,2001:6.
[24] 楊念群. “蘭安生模式”與民國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間的轉換[J]. 社會學研究,1999(4).
[25] 張鴻雁. 侵入與接替:城市社會結構變遷新論[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1:432-433.
[26] 李培林. 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9-42.
[27] 陳占江. 空間、認同與社會秩序——轉型期城中村問題研究[J].學習與實踐,2010(3).
[28] 張海波,童星. 被動城市化群體城市適應性與現代性獲得中的自我認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農民的實證研究[J]. 社會學研究,2006(2).
[29] 毛丹. 賦權、互動與認同:角色視角中的城郊農民市民化問題[J]. 社會學研究,2009(4).
Abstract:Since the "space-turn"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1960s, the neo-Marxist theory of space has experienced the stages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multiple development. It has new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society. As a typ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the city is the "field" of the neo-Marxist theory of space. Its spatial re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pace power. In fact,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also accompanied with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power.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is force include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disorder of rural daily life and the econstruction of "city - village" community space and identity loss. Therefore, the means to reconstruct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o realize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from peasants to citizens should be the core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Keywords:neo-Marxist theory of space;the production of space;capital cycle;rural urbanization
責任編輯: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