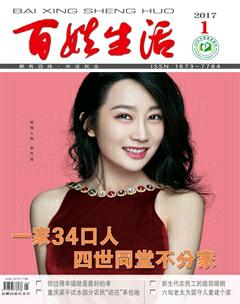重慶梁平試水部分農民“退還”承包地
編者按:201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要求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不斷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意見》要求,不得違法調整農戶承包地,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意見》還要求,加快放活土地經營權,具體包括引導土地經營權流向種田能手和新型經營主體、依法依規開展土地經營權抵押融資等措施。鼓勵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管、代耕代種等多種經營方式,探索更多放活土地經營權的有效途徑。
近年來,作為全國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重慶市梁平縣正在小范圍地探索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試點。在實施“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試點”的村組,該舉措受到那些有非農職業、非農收入的農戶的歡迎,這為放活土地經營權,深化農村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年來,在重慶市梁平縣的少量鄉村,部分農民嘗試向村社集體退還自己的承包地,獲得補償后,正式“洗腳離田”。“退地”意味著,當事農民不再把土地看成生計和保障的“命根子”,而是與土地進行切割,邁向全新的生活;退給集體的土地,則使得農業有了長期集約化經營的基礎。
習近平曾強調:“中國深化農村改革的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問題。”梁平縣部分農民的“退地”實踐,為處理這一關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選擇。據記者在梁平縣的觀察,至少在當下及可預見的短時期內,“退地”將受到一些農戶的歡迎,其效應是積極的。在這一問題上,基層群眾展現了驚人的創造力,不同村組基于各自的情況,摸索出不同的路徑和模式。
花園村1社:整社退出,統一用地
合興鎮護城村1組,是梁平縣嘗試退地的先行者。該組由原來的花園村1、2、3社合并而成。原花園村1社盡管緊鄰縣城,但耕作的自然條件并不優越。這里地勢起伏,很難使用農耕機械,只能靠人工耕種。僅靠從土地里“刨食”,很難“挖出金娃娃”,社里現在還有40多歲的單身漢。
近二三十年,打工浪潮席卷西部山鄉,1社的年輕人幾乎全部遠赴他鄉。同時,很多農民外出做生意,好幾戶人家舉家搬到縣城,賣建材、燈飾或副食。此外,社里還有一批木匠靠手藝為生,已經與種植業脫離關系。
和多數西部農村一樣,這片土地上只剩下“386199(婦女、兒童和老人)部隊”留守。留守者無力耕種自己的田地,承包給村民的120多畝田地中,只種了大約二三十畝,其他的近百畝田地都不同程度地荒蕪了。撂荒最嚴重的地方,瘋長的雜草遮蔽了柚子樹,人都鉆不進去。
“梁平柚”是中國三大名柚之一。2010年,梁平縣提出在合興鎮打造1萬畝的“中國名柚園”,其核心示范區有3500畝、12萬株柚子樹。同時,在園內建設“兩縱兩橫一環”觀光道路,開建柚子專業市場、大型停車場、名柚廣場和星級農家樂,試圖把“中國名柚園”建成該縣特色的旅游觀光和農戶增收的亮點工程。建成后,預計年產優質柚果兩萬噸,年接待游客5萬人次,預計年總收入可達1~2億元。
這項政府主推的“中國名柚園”工程,改變了花園村1社的頹勢。1社有23畝田地被征用修建通往“中國名柚園”的道路,這導致三四戶人家失去土地,組里需要重新調配土地。要調配,就得丈量。可是,雜草比人都高,無法進入田里丈量。而且,曾經的地界已被掩沒,很難區分某片田地究竟是誰家的。
怎么辦?“干脆集體收回”成了幾乎唯一可行的路子,經過五六次會議的商討,村民基本就此達成一致。現年70歲的組長王中杰在群眾中很有威信。他已經做了48年的組長,在他的協調下,收回土地所面臨的問題逐一找到解決方案。
老百姓之所以都贊同“退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幾家農業公司相中了這片被大量撂荒的土地,他們出的價能讓村民獲得更高的收益。
社里的36戶人家中,其中兩戶種了梨樹,經營得非常好,而且梨樹正處于豐產期,前景可期,這兩戶人家的土地也位于一個角落、不影響其他土地的整體使用。于是,這兩戶在認真考量后決定不參加。其余34戶都自愿“退地”。這34戶人家的土地進行了“打包”丈量,堡坎、坡地等全被圈入,最后量出179畝土地。社里將土地分別租給3家公司,其中“田”和“地”的租金略有區別,田為600斤黃谷/年、地為400斤黃谷/年,一直出租到2027年。
去年,當地的黃谷價格為1.3元/斤,折算下來,社里去年的租地收入超過10萬元。扣除基本開支后,這些收入由1社的110名農民平均分配,人均約990元,無論此前承包地的遠近、好壞,都“一視同仁”。
這筆收入比辛苦種地還高。“以前土地荒著,基本沒有收入,現在一個人一年差不多有1000元,肯定劃得來。”60歲的王中凡告訴記者,“以前種地,也就糊個口;而今,1000元能買多少米?”
“退地”會不會成為讓老百姓失去“命根子”的“致命賭博”?護城村1組的農戶認為自己有“定心丸”:從眼前看,租金收入比種田高;從長遠看,只要承租的公司經營得好,就會一直有收益,如果經營得不好,農戶重新接手,經幾家承租公司整治后的耕種條件,也比當初好多了。
對于接手這片土地的3家承租公司而言,直接與集體而不是每家每戶簽合同,權屬問題比過去的“土地流轉”更加明確,不再擔心“萬一有一戶反悔就很難辦”,也更敢于長期投入。另外,規模化種植也讓他們得到了政府補助。
規模經營、大筆資金投入、強化科技,提高了這片土地的產出率,村莊的面貌也改變了。以前,沿著土路挑糞去澆樹,一個來回要一個多小時;現在,鋪設了管道,兩三分鐘就能搞定。換言之,同樣的土地,務農的人少了,收成卻更多了。人們種地需要路過一個名叫“獅子河溝”的河谷,過去,雜草叢生的河谷溝被傳“鬧鬼”,晚上沒人敢走;而今,經過整治后,“大半夜都敢走了”。
這種“先定下家、整社‘退地、統一轉租”的“退地”模式,得到了異口同聲的稱贊,讓相關各方都從中受益。
義和村1組:整片退出,定制用地
在海拔較高的蟠龍鎮義和村1組,農戶們也已自發“退地”。
義和村1組有一眼出水量較大的山泉,適合發展冷水魚養殖。過去,土地被切割成小塊分戶承包,沒法大規模養魚,因此這眼山泉一直未能充分利用。2014年,在云南經商多年的金帶鎮仁和村農民首小江看上了這眼山泉,計劃投資1000余萬元在此建設冷水魚養殖基地。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開發計劃,項目總占地40畝,其中基礎設施建設用地15畝。然而,土地問題成為項目落地的最大瓶頸。
一方面,對首小江來說,項目總體投資規模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多,如果以“一年一付”的方式租用土地,一旦農民中途毀約、要求收回土地,或在某個節點“坐地起價”,就可能讓自己的巨額投入“打水漂”,影響持續穩定經營。另一方面,農民雖然希望流轉土地,但也擔心大戶因經營不善拖欠租金、甚至“跑路”,而基礎設施建設用地難以復耕,會留下“后遺癥”,影響自己的利益。換言之,業主和農民雙方都傾向于選擇“買”,而不是“租”。能“買”的前提,是農戶退出承包地。這片15畝基礎設施用地包括耕地11畝、宅基地3畝、林地1畝,共涉及21戶承包農戶,而他們幾乎全都搬到了鎮上或縣城,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已經多年沒有從事農業生產,有徹底“退地”的意愿。彼此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談判就有了基礎。經過多次公開協商,首小江與農戶順利地達成了有償退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意向。
因為牽涉眾多法律規定,此次“退地”分成“六步走”:
第一步,2014年12月,義和村1組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形成決議,明確了“退地”的方式,達成“不分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統算3.45萬元/畝”的補償標準,為“退地”奠定基礎。
第二步,21戶農民向村社集體提出申請,自愿永久放棄15畝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使用權),并獲得同意。
第三步,經村民代表大會表決同意,首小江以“農遷農”的方式,交納3000元“入戶費”,將戶口從梁平縣金帶鎮仁和村遷到義和村——成為該村的村民,才有資格獲得宅基地使用權、優先取得土地其他方式承包權。
第四步,獲得土地承包權資格的首小江,將補償價款交付給村社集體,村社集體再交給“退地”農民。農民交回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獲得3萬元/畝的一次性補償。
第五步,村社集體將15畝土地采用“其他方式”承包給經營大戶首小江,用于冷水魚養殖基地基礎設施建設。每畝溢價0.45萬元,歸村民小組集體所有。
第六步,雙方持相關材料,到縣級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機關進行登記,報縣級農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門備案。
這意味著,農戶的“退地”獲得了法律意義上的確認,經營大戶獲得了相關土地的承包經營權。
“退地”的結果,讓當事各方皆大歡喜。對于21戶農民來說,他們的土地如果自己種,一年純收入很難超過3000元,而“退地”獲得的一次性補償,是種地收入的好幾倍。況且,他們中大多數人并未務農,這筆上萬元的補償堪稱“天上掉餡餅”。而且,這21戶農民并不認為吃“餡餅”會透支未來:他們都在城鎮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根本就沒想再從這片土地中找飯吃”,“退地”不會影響他們的生存。
村民游世玲一家3口人,共有0.8畝承包地,這次退出了0.45畝。游世玲全家都住在蟠龍鎮上,做燈具生意,他們也不愿意務農了,家里的土地已經撂荒近10年。游世玲說:“與其讓土地荒蕪,還不如退出來,能有一筆補償收入。”村民藍家梅退出0.53畝土地,得到1.8萬元補償。“家里土地地塊偏遠,還是河灘地,莊稼都長不出來,政府也不可能征用。現在退出來了,補償還算不錯。”藍家梅說。
轉包這些土地的農業大戶首小江認為,這種方式對自己更有利。他說:“漁業投資規模大,還要配套倉儲和管理用房,一期投資就要300多萬元。以前我也打算租地,但擔心農民中途變卦,現在農民完全退出土地,由我承接過來,就可以放心投入,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
由此,“退地”擺脫了此前“流轉”時“農民怕老板‘跑路,老板怕農民反悔”的困境。而義和村1組因為擁有山泉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其補償標準遠高于同期國家征地補償標準。
梁平縣義和村1組“整片退出”的“退地”模式,被各方認為有利于有效利用退出地,并能促進產業發展,因而被梁平縣確定的兩個試點地區之一的屏錦鎮萬年村作為借鑒。
川西村9組:整戶退出,集中用地
禮讓鎮川西村,是梁平縣另一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退出試點村。
在川西村9組,部分農民的“退地”需求顯得較為強烈。近年來,川西村9組村民的收入來源已經非常多元:外出打工者有務工收入;當地的豆筋(一種用黃豆制成的形如竹棒的食品)產業發達,留守者為豆筋工廠打工,每天能掙100多元;如果選擇自己做豆筋,收入還能更高一些。也就是說,當地農戶無論是外出打工,還是自己創業經營,收入都比種地高得多,“退地”風險預計相對較小。
目前,川西村9組土地暫未確定“下家”,當地鎮政府墊資,替將來的“下家”向村民支付了“補償金”。這也是它與前兩個案例的最大區別。
政府墊資退出的土地,并非“燙手山芋”。因為當地的田地非常平整,找到優質“接盤者”的概率很大。目前,已經有多家公司和務農大戶表達了意向。
川西村9組“退地”時非常慎重,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很多希望“退地”的農戶都暫不具備條件。自認為能跨過“門檻”的21戶農民報名申請“退地”,仍有6戶被“篩”掉。
2016年5月初,7戶農民獲得了“退地”的資格,總面積超過28畝,“退地”農民每畝地將獲得1.4萬元補償,他們已經辦完了相關手續。9月初,記者來到這個村子時,第二批8戶農民也已經通過“審核”、簽訂了協議。
川西村9組選擇了整戶退出全部承包地的方式,退出的82.12畝地用“小并大、零拼整”和“確權確股不確地”的辦法,集中于一處,今后就能集中利用。
縱觀梁平縣試點探索的“退地”工作,堅持了“農民自愿、民主決策,退用結合、市場運作,守住底線、嚴控風險”3條原則,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讓老百姓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他們探索出的整戶退出、整片退出和整社退出這3種方式各具特色,可以滿足不同地方及農戶的差異化“退地”需求。
整戶退出模式,以農戶“退地”需求為導向,有利于加快進城農民市民化的進程,促進城鎮化、工業化,其推廣價值或許更大,但“退地”補償金籌集的壓力相對較大。
整片退出模式,以業主用地需求為導向,最大好處是土地“退出”即可利用。可解決部分甚至全部“退地”補償金,有利于發展高效設施農業。但由于不是整戶退出,促進城鎮化、工業化的力度相對較弱。
整社退出模式,以現實問題和產業發展為導向,有利于解決土地撂荒地界不清、征占地后土地調整困難等問題,還有利于促進特色產業發展。但農戶意見難統一,需有德高望重的干部或“鄉賢”來組織。
追蹤:部分農民為何愿意有償“退地”
1978年冬,安徽省小崗村18位農民“貼上身家性命”,在“大包干”的契約上摁下鮮紅的指印,從此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在小崗村“大包干”等農業生產責任制基礎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38年過去了,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民及其子女外出打工。以家庭為單位而分割出的一片片農村土地,有的被精心耕種,有的被撂荒,有的被“流轉”。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部分農民愿意有償“退地”,主要是因為在小片的土地上務農,獲得的效益無法令他們滿意。
梁平縣禮讓鎮川西村9組現年61歲的村民蒲昌友,是該組第二批“退地”的8戶人家之一。蒲家共有8.1畝田地,“辛辛苦苦種一年,賺不到5000元,卻累得要死”。
盡管蒲昌友曾是當地的農業技術員,精于農耕,但他卻堅持認為,用傳統農業的方式種地“實在太劃不來,沒有意思”。以耕種1畝田水稻為例,他詳細算了以下一筆賬。種1畝田的開支如下:1.犁田,年紀大了不可能自己去犁田,除餐飲、香煙外,人工費得100多元;2.插秧,人工費得100多元,如果稻田滿足機插條件,約60元;3.肥料,100多元;4.種子,70元~80元;5.農藥,根據當年的雨水、病蟲害的嚴重程度而有所浮動。為了控制稻瘟病,至少打藥3次。自己打藥大約30元~40元,雇人打藥得花60元~70元;6.收割,以2015年的行情計算,大田、整田每畝大約60元,小田、異形田得70元~80元。
種1畝田的收入又如何呢?水稻每畝產量也就1000斤左右,這兩年稻谷售價都沒超過1.3元/斤。“折算下來,扣除成本,即使不扣除自己的人工費用,每畝田的實際收益也只有600元左右。”蒲昌友說。
除了種植業,是否可以開展養殖?川西村農民曾有養豬的傳統,但如今,整個川西村9組,只有貧困戶鄭因菊一戶在養豬,其他農戶都是買肉吃。
“養豬專業戶養得多才能賺錢,一般家庭養三五頭豬,能不虧本就謝天謝地了。”蒲昌友說,“總之,按照傳統的方式,小規模的種植、養殖不賺錢,只能保證自己有飯吃,解決溫飽。”
蒲昌友家的情況,是讓他決意退出承包地的另一個因素。“如今,我年紀大了,身體差了,做不了繁重的農活了。”他有一兒一女,兒子在重慶主城開車,女兒在梁平縣城開婚慶公司,兩人從來不曾務農,“不愿種地,也不會種地,將來也不可能回來種地”。
蒲昌友并不擔心退出承包土地之后的風險。首先,他自己當過兵,政府有補助;加之購買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老伴兒也有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這些補助加上‘退出承包地的8萬元的一次性補助,老兩口的生活保障基本就夠了”。他說:“‘退地之后,我就離開這片田地了,去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
同組60歲的馮輝祿,比蒲昌友更加迫切地希望能盡早“退地”,“辛辛苦苦種一年的田,不如出去打一個月的工”。“我已經20年沒有種田了。”馮輝祿曾經在湖北從事釀酒業約20年,因為年齡大了,患上了腰疼病,沒法繼續釀酒,轉而去深圳做保安,每月能有兩三千元收入。“打工比種田輕松,收入還高。”他的妻子也在工廠里打工,每月2500元,“晚上在家加班,每月還能有1500元的收入”。
在馮輝祿看來,自家的承包地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價值。“我出門去打工,如果請人在老家替我種田,不僅沒多大的收益,打工回來后,還得請他吃飯道謝。算經濟賬,并不劃算。”馮輝祿告訴記者,“以前需要交農業稅的年代,我寧愿用打工的收入來交農業稅,也不愿意種田。現在不繳農業稅,更不愿種了。”
“早些年我就在想,如果有人來買這些田地的經營權就好了。”馮輝祿同樣表示“退地”后自己并沒有太多后顧之憂。他的大兒子在廈門,最初為別人打工,后來自己開公司,經營辦公用具;小兒子在廣東中山打工,進修大學文憑后,目前在做別墅裝修設計。“他們已經不可能回來種地了。”馮輝祿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