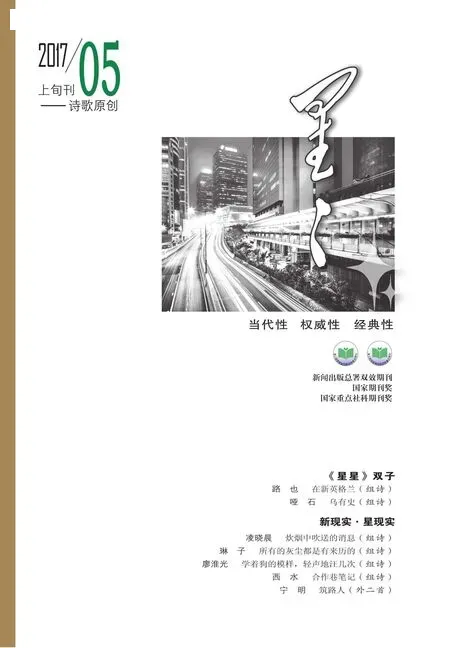片刻的歡愉
倮 倮
片刻的歡愉
倮 倮
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詩歌的閱讀給我?guī)頍o窮的樂趣,但如果這種閱讀與詩歌寫作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樂趣便會隨著寫作的深入而逐漸消失殆盡。
偶爾靈感乍現(xiàn)寫出的“得意之作”,與名作一比較便顯得蹩腳。當自己深思熟慮以為又寫出“代表作”時,然后卻發(fā)現(xiàn)這已經(jīng)是前人寫爛的東西,而且語言、意象等也顯得笨拙。
我感到絕望——寫作帶給我的歡愉是短暫的,痛苦和絕望才是長期的。
有近十年的時間,我基本上沒寫。制造文字垃圾污染人們的眼睛,還浪費紙張,無論怎么看都是一件極不環(huán)保的事情,甚至可恥。知恥而后勇才是好的人生態(tài)度,但古往今來星河燦爛的絕妙華章已經(jīng)讓我失去了勇氣。
一段時間我只是閱讀,但是閱讀又讓我蠢蠢欲動。可是——我真的有點不知所措——這是我沒有過的經(jīng)驗。
如果寫作給我?guī)淼氖峭纯啵瑸槭裁催€要寫?如果痛苦能讓我的精神升華,我是不是需要寫下去?
“詩是翻騰的內(nèi)心之嘆息,詩是被心譜成音樂的宇宙”(蘇利-普呂多姆)。這樣的形容難免不讓人心潮澎湃。
怎么辦?怎么辦?
寫吧,有時候覺得真的沒有什么意義。
然而,身邊朋友的影響卻是無處不在的,馬拉、阿魯、徐林、余叢、唐不遇、容浩、夢亦非、龐白、黃土路……他們的薦讀和寫作,難免不讓我又心癢手癢,偶爾涂鴉,被他們真誠點贊,這種朋友之間的認可又讓寫作有了些動力。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沒野心也不勤奮,更多的時候,我是一個充滿生命活力和趣味的人,熱愛美酒、美食,我對喧囂、繁華的生活充滿懷疑,卻又一頭扎進這樣的生活。
我知道。我是不可救藥的。
可是,在某一個早晨醒來后,我突然幡然醒悟似的,勤奮起來……偶爾的閑暇時間及時間的邊角余料都被閱讀填充。
這當然不能成為寫作的理由。
我?guī)缀跏菬o話可說了。
如果一定要進行解釋,要么它是一種藥,可以緩解我的生命之痛;要么我是吃錯了藥,寧可用無限的痛苦來換取片刻歡愉;要么它是一種毒藥,我已經(jīng)中毒太深。
當然,還有一個解釋,我愿意在尋找“真”的過程中忍受痛苦,而我本身是真實的。蘇利-普呂多姆說:“在文字中,如果能做到真實,那就夠獨特了。優(yōu)秀的獨特性不是別的,而是記錄心靈語言的完美的真實。如果真實只有一種,那么,唯有心靈是獨特的。文學的獨特性可以用幾個字來概括:人心變化所引起的永恒的真實。”
我的詩歌有我的呼吸、淚水和汗水在里面,甚至是我“生活”的再現(xiàn)。我觸摸,我感知,我感動,我說出!
評論家謝有順說:“而有感而發(fā)正是詩歌寫作最重要的精神命脈。”“詩人是受消費文化影響最小的一群人,風起云涌的文化熱點,出版的喧囂,均和真正的詩人關(guān)系不大,他們是社會這個巨大的胃囊中無法消化的部分,如同一根精神的刺,又如一把能防止腐敗的鹽,一直在時代的內(nèi)部堅定地存在著。”
我愿意用長久的痛苦換取片刻的歡愉或許只是為了“真正的”三個字,或許是為了另外三個字:“真”“善”“美”,甚至可能是只為一個字“真”。這才是我人生認識論的大問題。
我用詩歌中的“真我”對付世俗生活中的“假我”,用一種痛來緩解另一種痛。沒有撫慰,只是讓蒼涼和感傷變成了文字,文字又變成了針線,把虛妄刺破,把破碎的日子連綴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