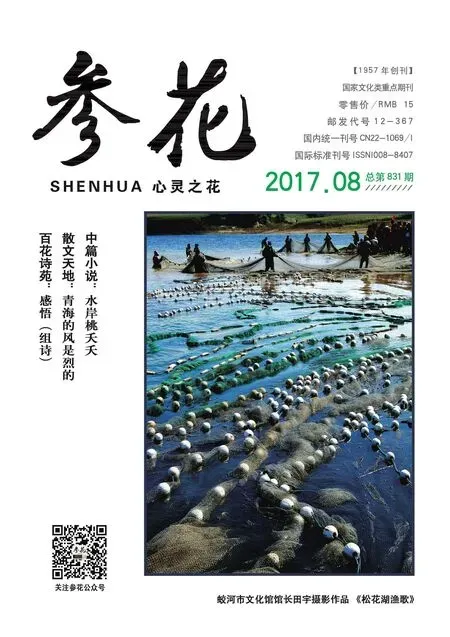東湖柳色(外一篇)
◎張燕
東湖柳色(外一篇)
◎張燕
黃土高原上,鳳翔新城,一派江南風光。
一城柳色半城湖,接天蓮葉荷花紅。
東湖清澈明凈,碧波粼粼;岸柳依依,倒影綽綽;魚兒在柳枝間穿梭,小鳥在湖波中飛翔。
公元一〇六一年寒冬,關中西北冰天雪地。
蘇軾趕赴鳳翔府,出任判官。上任始伊,他大膽革除吏治弊病,取締多種橫征暴斂的條款,減輕了百姓負擔,城鄉日漸春回地暖。
來年,鳳翔地區又遭受春旱,三月無雨,麥苗、油菜幾近枯黃,百姓面臨夏田絕收和饑荒。為此,蘇軾心急如焚,他親自帶領民眾,登上太白山絕頂求神乞雨。果真,鳳翔地區連降三天及時喜雨,田禾逢雨轉黃變青。全城百姓歡慶天降甘霖,蘇軾與民同歡同歌。他將自己住宅中的一間小亭命名為“喜雨亭”,隨后,他又揮筆寫出喜雨般洋洋灑灑飄落的千古奇文《喜雨亭記》:
一滴雨珠,是一顆寶玉;
一滴雨珠,是一粒糧粟。
一滴雨珠,關乎百姓饑飽;
一滴雨珠,牽動太守憂思。
由此,這篇以雨為題的《喜雨亭記》,也就與眾多的遠離百姓疾苦的所謂文章迥然有別——它沒有士大夫的閑情逸致、無病呻吟;它沒有文人墨客的空洞浮泛、小愁小怨。《喜雨亭記》可謂一曲人間絕唱。
蘇軾的思考從求神乞雨開始,又進了一步;他認為靠天信神賜雨,是靠不住的,唯有靠人靠民才是解除西北旱災的根本抉擇。從此,一個修筑水庫的藍圖在蘇軾的倡導下變成奇跡般的現實。
他親自率領全城數萬民眾,開據鳳城城東區的深溝和洼地,形成一個大水庫。他又把城北的鳳凰池水引入這個水壩。水庫竣工了,既能防洪蓄水,又能灌溉萬畝農田,一舉解除了大西北的大旱之災。這座水庫,如今改名“東湖”。
豐盈充沛的東湖水,蓄滿的是蘇軾水樣的愛民情結。東湖水,又是《喜雨亭記》不朽的現實版。
繼往開來保護東湖的后來者,還有清代愛國名將左宗棠。
今日東湖岸邊茂盛如林的“左公柳”,就是左宗棠在一八七六年初春率領六萬軍隊,開赴新疆收復失地,途經鳳翔地區栽植的。
棵棵柳樹,蒼勁挺拔,高聳入云,一如堅毅不屈的左公其人,守護著東湖的春夏秋冬。
那年,他夜宿東湖喜雨亭。東湖水波泛起他與蘇軾息息相通的“心憂天下”的愛民情懷。他成長在湘江之濱的柳莊,他的故居,至今還屹立著他親手栽植的兩棵“左公柳”。蘇軾自號“農人”,以農為榮;左公自號“湘上農人”。蘇軾寫詞,以示愛柳如癡:“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滿庭芳·歸去來兮》)左公愛柳,情有獨鐘。他率領大軍西征途中,沿途栽柳。軍隊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綠洲。
數年之后,與左宗棠的同代人、湘江巡撫楊昌浚出使西北時,目睹所到之地,綠柳成林,鳥鳴枝頭,百業興旺,即賦詩《恭誦左公西行甘棠》:
大將籌邊尚未還,
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
引得春風度玉關。
東湖周圍,以至大西北,柳樹成蔭,無疑是保護東湖水源的天然綠色屏障,大環境變綠了,也與東湖的興廢息息相關。又如蘇軾與左公的風骨——柳樹是最平凡的樹木,最易栽植,最易成活;它最耐旱,最耐寒;它不僅能防止水土流失,還能抗擊暴風雨雪;它不折不倒,耐腐耐久;它在哪里成蔭,哪里就是一片春光,哪里就會五谷豐收,百姓安康。
東湖水,因蘇軾而名世;東湖柳,因左公而不朽。
東湖與左公柳,相依相生,相映相輝,融為一體,自然而瑰麗的湖光柳色。
馬尾橋畔迎春花
馬尾橋,長約三十米,寬約五米,高達數十米,是一座古老的鄉村土橋,“飛架”深溝南北,直達岐山周公廟名勝風景區。
這座古建土橋最大的亮點,就是土橋兩側陡峭的土坡上,長滿密密層層、四季常春的迎春花。
走近迎春花,我一如觸摸到它的血脈和靈魂。在它繁密的深綠色的枝條下,伸展著碗口一般粗壯的黃灰色的主干。它鱗狀的枯皮,一片一片,如騰飛的龍爪,撲躍的虎足。它生長的年代有多么久遠?它常青的生命多么永恒?據說一九八五年全國迎春花盆景大賽上,一盆迎春讓世人驚嘆:它的古老的樹齡已達五百余年。由此,迎春花也改寫了人們對它輕視的短淺目光。它并不是毫不起眼的小草小花;它也毫不低矮,毫不卑微;它堪與松、柏比肩,堪與竹、梅媲美。
馬尾橋畔的迎春花,生命力極其強盛。長長的枝條節骨處,都能萌生出氣根,如同南方生長著氣根的大榕樹。它與大榕樹氣根浮在天空的不同之處,還在于迎春花的氣根,隨著枝條的節節伸展,氣根卻深深扎入泥土;它步步為營,穩扎穩打,任你使足勁力,也難拔出;即使你拔出一節,采折一枝,它仍能自生自長,更繁更茂。由此,我也明白了馬尾橋遭遇洪水襲擊的驚險一幕——每年夏秋之際,山洪順溝洶涌而來,洪水卷動著碾盤大的山石,在深溝內咆哮怒吼,沖撞猛擊,發出雷鳴般的轟響,可謂亂石崩云,溝土坍塌。可是,一溝山洪,卻在馬尾橋下的大孔洞里,收斂了桀驁不馴的野性,慢慢平衡了,平穩地流向橋西的周公水庫。由此,我又明白了,這座古建土橋,千百年來不塌不崩的根本原因——原來,它是土橋兩側千萬枝迎春花護衛的功績。面對山洪,迎春花擺開會戰大陣,它一層緊扣一層,一隊緊靠一隊。它那密集的枝條,如同伸展的手臂,臂臂緊挽,手手緊拉,組成一道防衛土橋,抗擊山洪的綠色堤壩。為此,我說,誰道迎春花“無處使用”,誰道迎春花“難挑大梁”?
我愛迎春花,不只愛在山洪暴發時,還愛它在數九寒冬之時。
數九的寒風,一如凜冽的刀片,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尖利的哨聲。它咔咔嚓嚓,斷折了馬尾溝邊大樹的枝椏,打上蒼涼而光禿的印記,但它卻折不斷馬尾橋畔迎春花的枝條,掃不脫迎春花的碧翠色澤。它的枝條,雖然細如柳枝,弱如草葉,但它柔韌得富有彈性和筋力。寒風能把它揚起,但它又能輕盈、自如地落下,一如翩翩起伏的芭蕾舞,又如一曲“二十四橋明月夜”優雅的洞蕭聲。
北風愈嚴寒,枝條愈翠綠。此刻,我細細一看,在這數九寒天里,迎春花的枝條上,節節吐露出點點如豆的赤紅色的花苞,恰似瑪瑙珍珠,又如嬰兒睜開的眼睛。
品嘗馬尾橋畔的迎春花,更能讓我如癡如醉。醉眼看花,亦幻亦真,別有情趣。
此刻,馬尾橋畔的迎春花,在漫漫一坡綠枝翠葉的映襯下,如同一河碧波。金色的花朵,一如碧波上濺起的浪花,它處于橋畔的峭壁上,又是立體的、從天而瀉的花的瀑布。
瀑布不息地流瀉著,流瀉著泥土純樸的氣息,流瀉著天空湛藍晶瑩的亮色,流瀉著春風清明濕潤的暖意,流瀉著萬物萌芽深情的呼吸:“迎得春來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
馬尾橋,是古橋,也是新橋;是古道,也是嶄新大道。橋面上,托載著飛轉的車輪,行人的腳步;也托載著夜空星斗,晨霞朝日,陰晴冷暖。大橋畔上的迎春花,護衛著大橋,也托舉著大橋。大橋的負重,時時刻刻牽動著它的脈博,它的胸膛一起一伏,它的血脈嘩嘩跳動。
由此我更明白,迎春花心連著大橋,心連著海角天涯。
如同一座里程碑,給這座大橋改寫了一個嶄新的名稱:迎春花橋。
(作者單位:陜西省寶雞市群眾藝術館)
(責任編輯 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