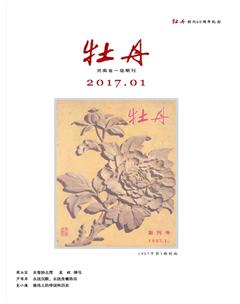孤寂的“囚禁”歲月
吳曦,福建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文學(xué)》特邀編審,霞浦縣作協(xié)常務(wù)副主席。現(xiàn)為《霞浦》鄉(xiāng)訊報主編。主要從事小說、散文、報告文學(xué)創(chuàng)作,已在《福建文學(xué)》《廈門文學(xué)》《紅豆》《青春》《青年作家》《鴨綠江》《散文天地》《散文百家》《散文選刊》《散文世界》《中國文學(xué)》《延安文學(xué)》《延河》《芳草》《當(dāng)代小說》《四川文學(xué)》《南方文學(xué)》《北方作家》《湖南文學(xué)》《滿族文學(xué)》等各類報刊發(fā)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xué)100多萬字。
CT的造型像圈套,機(jī)床把人裝進(jìn)套里,按預(yù)設(shè)的程序讓你現(xiàn)出原形,你無法隱瞞真相。接下來你要在一個更大的套中,乖乖配合程序,糾正真相的亂碼。
在我看來,CT更像墓穴,機(jī)床緩緩把人送進(jìn)去,讓我想起當(dāng)年祖母被推進(jìn)墓穴的情景。一口巨大的棺槨在陽光下閃著紅光。棺槨底下墊著的兩根木棍,在四個大漢的用力下,隨法師的呼喚滾動起來。棺槨被送進(jìn)墓穴,連同七十三歲的祖母。
現(xiàn)在,時隔四十六年的兩個鏡頭在瞬間重疊。躺在機(jī)床上的我,被預(yù)設(shè)的程序控制著,按醫(yī)生的指令,做著舉手、交臂、吸氣、呼氣的動作。四周十分安靜,唯有機(jī)器在輕輕喘息。感覺自己被深埋在土里,聽得到大地的脈動。
這一刻,人無法預(yù)測生命的真相,只能靜靜等待一雙無形眼睛的秘密窺視。當(dāng)真相現(xiàn)出可怕原形的時候,與當(dāng)年的祖母就只有時間上的差別了。
好在我的差距隔著未知的時空。當(dāng)年的祖母,在墓門關(guān)上的一瞬間,就已經(jīng)陰陽兩隔。而我,即使“墓門”關(guān)上了,仍然在“墓”的外頭。
我被告知是急性肺炎和慢性支氣管炎,需立即住院。
被四周雪白的顏色與福爾馬琳氣味包裹著的我,瞬間被拋離慣性的軌道。日常的節(jié)點(diǎn)出現(xiàn)一個短暫的休止符。頭上點(diǎn)滴的吊瓶和手腕白色的長蟲,意味著我又一次被某種程序所控制,必須暫時告別正常的秩序。等到第二次進(jìn)入“墓穴”,證實(shí)體內(nèi)亂碼糾正的結(jié)果后,才有權(quán)利擺脫控制,回歸正常。
我曾經(jīng)有過兩次“偏離”。第一次“偏離”,為四十多年后的這一次埋下長長的禍根。因?yàn)橹夤車?yán)重炎癥,長時間咳嗽不止。
我從小不適應(yīng)家鄉(xiāng)的海風(fēng),它讓我頭暈?zāi)X昏,常常傷風(fēng)感冒。久而久之,落下了氣管炎。第一次被按在病床上,十五歲的我,既不知所措,又覺慶幸。在短暫的慌亂之后,很快就安定了下來。因?yàn)槲业玫搅似匠5貌坏降拇龊透改傅膽z愛。且暫時擺脫繁瑣的學(xué)業(yè)。醫(yī)生和護(hù)士每天進(jìn)進(jìn)出出。在我的眼里,她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既漂亮又溫柔,是上帝派來拯救人類的天使。她們每天在我小屁股上扎針,雖然疼,但那綿柔的手指,觸著小屁股時,有種異樣的感覺,便覺痛并愉快著。我甚至天真地想,要是能一直呆在這里,有多好呀!
時間對于同一件事情,往往讓人感覺錯位。經(jīng)歷的事多了,心理空間就變得擁堵且混雜。四十多年后的這一次,感覺就有點(diǎn)怪怪。每當(dāng)護(hù)士端著盤子走進(jìn)病房,心里都會咯噔一跳,以為又來扎針了。倒不是因?yàn)榕绿郏祭掀だ先饬恕E碌氖亲o(hù)士手舉針筒時的那一瞬間,也不知道針什么時候落下來的恐懼,這個過程感覺十分漫長。你連一口氣都不敢吐出來,憋著等待針與臀的碰撞,恭候疼痛的降臨。懸著的心開始野馬撒蹄。我常常對那些未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的事胡思亂想,深陷恐懼泥潭。明知這是一種“未知恐懼癥”,但就是抑制不了。
倒是第二次住院沒有恐針的陰影。確切地說,是被另一種恐懼沖淡了。那次患的是痢疾,肚子痛了一天一夜,也拉了一天一夜,整個人幾近脫水,變了原形。任憑如何吊瓶扎針,沒有任何感覺。一種痛苦嚇跑了另一種痛苦。
假如不是身體的亂碼太離譜,不是疼痛頻繁,頻繁扎針,偶爾可以“生”一兩次病,堂而皇之地借此機(jī)會住住院,清閑一下,算是對忙碌、繁雜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一種回避與逃離。權(quán)當(dāng)一次身心的走穴。即使下一刻,或者下下一刻,死神找上門來,你可以對它說,我已經(jīng)認(rèn)識你了,不過那是在一個很遠(yuǎn)的地方與你遙遙對視。
誰都明白,生命的弓一張一弛,張弛有度。而往往很多人,沒到“張”不開時,是不會想到“弛”。只有到紅燈亮起的時候,才意識到弓需要維修保養(yǎng)了。
除了有條件或有機(jī)會去療養(yǎng)院療養(yǎng)外,我以為住院是最佳的選擇。這時候,你可以將自己徹底清空一下,讓身心整個兒懸置起來,成為被邊緣了的局外人,在某種預(yù)設(shè)程序的掌控下,做你想做的事。比如毫無掛礙、靜靜地看手腕上緩緩蠕動的水;數(shù)頭頂上吊瓶懸懸的水滴,一滴一滴……
和進(jìn)進(jìn)出出的小護(hù)士調(diào)侃,咸的淡的,或者不咸不淡,眼睛色迷迷地盯著人家好看的臉,還有隆起的乳房、豐腴的臀部。
還可以和同室病友聊聊天,說些有用沒用的,或者毫無顧忌說那些葷、素、黃的段子,沒事逗著樂。
住院一周來,其實(shí)我是沒有同室病友,一個人占據(jù)整個病房,成了孤家寡人。憑著我與院長是老鄉(xiāng)和老朋友的關(guān)系,我享受了獨(dú)居一室的待遇。這是院長對我的關(guān)照,也表達(dá)了他的一份心意。其實(shí)這種關(guān)照事與愿違。院長的本意是讓我清靜和安心,而他“送”給我的是寂寞與孤獨(dú),讓我更加心煩和鬧心。除了偶爾和醫(yī)生、護(hù)士,還有送餐的妻子說一兩句話外,平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
人真是一種怪物,有時自相矛盾得不可理喻。忙碌的日子里,總想清閑一下。真正清閑了,又覺寂寞無聊不自在。自己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不容易挨過一周,來了一位說不清多大年齡,也不知得什么病的病友。他和我一樣,也是“走院生”,白天來晚上回,沒有家人看護(hù),只是到點(diǎn)有人送餐。有了傾訴的對象,我逮著機(jī)會和他聊。他話不多,只是時不時回應(yīng)一兩句,或者提一兩個疑惑的問題。更多的時候是當(dāng)聽眾。可我也不是饒舌聒噪之徒,喜歡賣弄嚼舌頭。只是閑得無聊悶得慌呀!
這位當(dāng)了我一周同室病友,也當(dāng)了七天聽眾的“好人”出院后,又來了一位我連臉都沒看清楚的病人。他是在我出院的前一天來的。很搞怪的一個人!總共不到一天時間,上床下床、進(jìn)進(jìn)出出數(shù)不清次數(shù),不是上衛(wèi)生間,就是找醫(yī)生找護(hù)士,心頭像是有團(tuán)什么沒解開的結(jié)。神情很憂戚很慌亂。我估摸是腸胃上出了什么毛病。
說實(shí)話,我有不少時候與醫(yī)院親密接觸。但多半是“看病人”,不是“做病人”。“看”與“做”,實(shí)在是兩種不一樣的境遇。
父親住院時,我把自己弓成一只蝦,靜靜地蜷曲在父親的腳邊,一動不動,簡直就是蝦的雕塑,生怕一不小心,弄醒了好不容易入睡的父親。
父親無休止的呻吟,讓我痛苦。無法為父親分擔(dān)一點(diǎn)點(diǎn)痛苦的我,盼望著睡神的降臨,讓他暫時忘卻疼痛,哪怕是一兩分鐘也好。
寒夜深深,對于困到極限的我,只能以這種極端的姿勢,在父親的床尾“委曲求全”了。此種“造型”的痛苦,事后留下了烙鐵一般的痕跡和陰影。只是當(dāng)時被父親的痛苦呻吟消解了。
許多年后,我常常夢到四肢蜷曲地被鎖在很小的箱子里,或者塞進(jìn)狹窄的石縫中,可怕的是意識清醒卻無法動彈。時間漫漫,如同凌遲的刀在身上一片片地剮。或者火在底下慢慢地烤。
那時候的病房擁擠得無法插足,病床緊挨著病床,更談不上為看護(hù)人放一張簡易的折疊床了。所有的護(hù)理都只能與病人擠一張床。
不困的時候,拿一張小凳子坐在病床邊,看頭上的吊瓶。無聊時,拿張報紙或者一本書,有一搭沒一搭地翻翻,不能太投入,否則會出事。
有一年,兒子闌尾手術(shù),點(diǎn)滴打到半夜。忙碌了一天的我,實(shí)在太困,不知不覺昏睡過去了。醒來時嚇了一大跳,點(diǎn)滴打完管子回血了。醫(yī)生說,要是再遲一點(diǎn),麻煩就大了。其時,兒子麻藥尚未完全退去,還在迷糊中。
父親沒吊瓶時,我就在病房進(jìn)進(jìn)出出,如同無頭蒼蠅,心里很慌亂,一直無所適從,不知道進(jìn)進(jìn)出出要干什么。父親的病,讓一家人悲傷致極。我們誰也不敢將真相告訴父親。也許有些事情,瞞著當(dāng)事人更好,這就是生活。雖然殘酷,也不乏善意。
我可以在病房里外隨意走動,但卻不能走得太遠(yuǎn)。父親隨時有事叫我,要吃藥喝水,要吐痰撒尿……
最遠(yuǎn)的地方,就在這一樓層的門口,即聲音所及之處。最常做的,就是在病房走廊麻木地來回走動,腦子一片空白,腳步機(jī)械得像木偶。
說實(shí)話,夜晚比較難熬。那些日子,我感覺每一個晚上都無比漫長,長到無邊無際。到最后,只好數(shù)數(shù)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挨到天亮。
我非好事之徒。可那段時間,總盼望夜夜有事發(fā)生。
父親住的是外科病房。按理,父親該住內(nèi)科,只因我嫂子是外科護(hù)士長,“以職謀私”,內(nèi)轉(zhuǎn)外,照顧起來方便。
外科是多事之科,隔三差五總有人半夜送進(jìn)來,不是車禍,就是其他事故,缺胳膊斷腿。包扎,搶救,動手術(shù)。鬼哭狼吼,上上下下,忙成一片,折騰了一整夜。
我也不得閑。在父親病房轉(zhuǎn)一轉(zhuǎn)后,就到搶救室外走一走,再溜到護(hù)士值班室聽一聽。然后把看到和聽來的,跟其他病友的看護(hù)人進(jìn)行分享,悄聲地議論、交流,把一個平常、簡單的事故,添油加醋成了幾近傳奇的故事。這個夜晚,就在突如其來的一場事故和好奇心的驅(qū)使下,不知不覺地打發(fā)了。
還有夜半歸西的。凄涼的哭聲,深夜里倍加瘆人。最忌諱死人之事的我,那陣子則一反常態(tài),跑到病房看死人。
生活沒有永遠(yuǎn)的常態(tài),背叛是常有的事。凡事一旦到了極限,反彈就免不了。只因漫漫長夜,把我折磨得幾近崩潰了。
父親一生只住過兩次院,一次是痔瘡手術(shù),一次是二十年后的這一次。前者是生命的中轉(zhuǎn),后者是生命的終結(jié)。
細(xì)數(shù)下來,在醫(yī)院看護(hù)病人不下十?dāng)?shù)次了。除了父親這一次外,還有后來岳父的前列腺毛病住院,妻子的子宮肌瘤,兒子的闌尾手術(shù),岳母的腿骨折……再沒有比父親那次更辛苦,更勞心勞血、歷盡折騰了。
就說岳父那回吧,我和兩個內(nèi)弟輪流看護(hù)。白天我們照常上班,只負(fù)責(zé)早上到取藥窗,把藥拿給當(dāng)班的護(hù)士。晚上,一個上半夜一個下半夜。岳父是早期病癥,沒有當(dāng)年父親的病情嚴(yán)重,我們很少聽到他痛苦的呻吟。至于更多的事,已經(jīng)記不起來了,因?yàn)闆]有父親那次的辛苦,印象也就模糊了。
說起來,這前前后后十?dāng)?shù)次,抵不上父親那一次辛苦勞累,至今想來都有點(diǎn)后怕。也許,這是老天的安排。是在考驗(yàn)一位兒子對父親有著怎樣的孝心?這孝心是真是假,是軟還是硬?能否經(jīng)得起生生折騰呢?
責(zé)任編輯 楊麗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