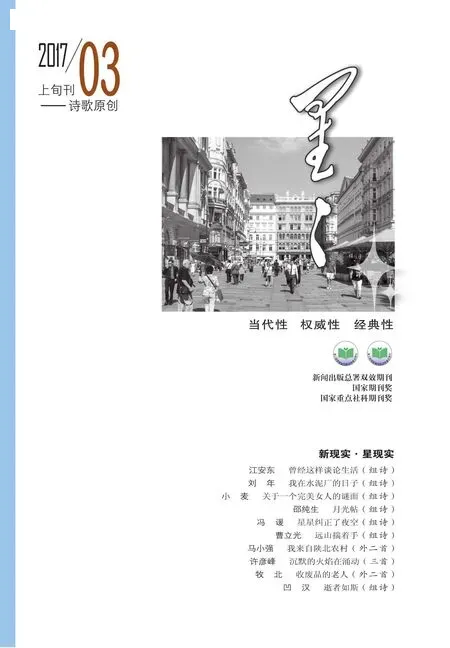唱給故鄉的反調
趙劍鋒
唱給故鄉的反調
趙劍鋒
瑞士醫生讓·雅各·哈德最早提出了鄉愁一詞,從此,這個詞語就像鄉愁一樣開始泛濫起來。
鄉愁就是思鄉病,有病就得治,“一個生病的人因為他并非身處故鄉而感覺到的痛苦”,這些痛苦,既有生理上的征候,也有心理上的裂痕。楚漢戰爭中,項羽及其軍隊被困于垓下,漢軍士兵唱楚地歌曲以引起楚軍思家之情,瓦解戰斗力,項羽聽聞四面楚歌起,慌率八百殘部自刎烏江。病入膏肓的楚軍和霸王,與其說是被劉邦擊敗了,弗如說是被鄉愁擊敗了。
每個人都有一個精神的故鄉,哪怕這些故鄉都在淪陷。
故鄉最能牽扯人心的便是有溫度的熟稔的人、事、物,一個正面或側面,一個低飛或高翔,一個轉身或離去,一個永別或永生,一雨露,一花草,一點頭,一回眸......都是病因!
所以,近年來,我處于半荒廢狀態的個人寫作對故鄉因子的偏向性植入顯得格外刺眼和投入。
隨著中年時光的步步倒逼,對于生命題材的探索自然多了些思考,許多故鄉的創作印記也像白發一樣漸次多了起來。當然,也可以這樣理解,好多的遺憾還沒來得及落地生根,那些始料未及的驚喜便從天而降,從而讓人無法對接生命過渡期的惶惑給予好好改善也未可知。
古人曰: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可能我還沒有達到有天下、據天下、 以天下為天下的氣魄,但我有罐子、捧罐子、破罐子破摔的氣勢。
古人還曰: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可能我也不能達到這種境界,畢竟桃李不言,先于春風已破敗,江湖不才,夜雨掌燈早飄搖。
古人不曰了,我還想曰。其實我不想背離城市,更不想逃離城市。今天的城市文明取代昨天的城市文明,早晨的霧霾取代黃昏的霧霾。我們每個人的故鄉也不干凈。有歷史的原因,風俗的原因,地理的原因,信息的原因,暴力美學強制性改變生態環境帶來的惡劣現狀也令人堪憂!
霧霾是一座城市的墓碑,城里住著的都是亡靈。
村莊是故鄉的墓志銘,故鄉住著祖宗十八代的前世與今生。
我們之所以熱愛故鄉,是因為故鄉有匠人和匠人精神滋養和浸潤著我們的衣食住行,他是我們活著的證據。
我們之所以熱愛故鄉,是因為快樂時光里總有殷實的陪伴,不管是某些人物還是某些動物,他們是生命的忠實伙伴。
城市化作為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加速了人與土地與莊稼與農具與家畜的生分感和違和感,而更加重視在市場條件下的等價交換原則帶了的商業意識和金錢意識。作為視作經典理想主義的“田園牧歌”“桃花源”式的生活汲取通通被打碎,直到把這種“理想”奉為更高級的名副其實的理想。
沒故鄉的找故鄉,有故鄉的想故鄉。故鄉的失落與代償、升華與感慕,給寫作者帶來了雙重選擇。故鄉,走不完的風雨兼程,走不出的地老天荒。
或許有一天,故鄉也開始破敗,霧霾籠罩著莊稼的鼻息,反而城市一派明朗,我們對城市的厭惡變成了喜愛,城市成為新一輪的故鄉。是時,我們便是故鄉的證人!
天下沒有遠方,人間都是故鄉。